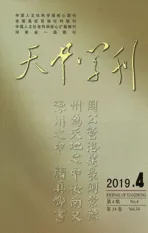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2019-01-19洪树华
洪 树 华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264209)
近十几年来,中国叙事文化学引起学界的注意及重视。国内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是由宁稼雨提出的,如中国人民大学张国风说:“近年来,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吸收国内主题学研究成果,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首创中国叙事文化学,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框架……”[1]扬州大学董国炎认为:“宁稼雨还撰写主题学和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个名称。”[2]南京大学苗怀明说:“从理论资源来看,宁稼雨首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3]宁稼雨及其他学者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拟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做一番梳理与审视。
一
如前所述,中国叙事文化学是由宁稼雨提倡的。宁稼雨不是偶然随意而发,而是经过精心思索、不断实践摸索之后提出的。早在2009年宁稼雨就指出:“近些年来,学界人们已经厌倦并唾弃那些要么新学科、动辄新体系大而空的空疏学风,期待并倡导扎实而实事求是的学风。鉴于此,有关中国叙事文化学学科建设的设想,尽管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在尽力实践和摸索,但一直希望能以一个具体而实在的成果作为具有说服力的奠基和准备。”[4]8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稼雨就一直从事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研究,经过多年的潜心治学,先后出版了《魏晋风度》(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魏晋名士风流》(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多年前宁稼雨针对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提出了初步设想,他认为,作为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有必要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框架体系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这就是他数年来思考并努力为之经营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中国叙事文化学构成之一是索引编制,构成之二是个案研究[4]5―8。数年之后,宁稼雨针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工作做出了明晰的归纳,他说:“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的工作,其一为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其二为故事主题类型个案研究,其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索引编制是基础,个案研究是主体,理论研究是指南。”[5]19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工作做到何种程度呢?可以肯定的是有关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卓有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理探讨
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倡导者,宁稼雨一方面笔耕不辍,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具体问题研究,另一方面始终不忘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理探讨。
首先,明晰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之间的关系。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方法之一,自传入中国之后,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如王立就在主题学研究上卓有成就,著有《中国文学主题学》等。那么,何谓“主题学”?陈鹏翔在《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如果要给它下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6]5此外,陈鹏翔还对母题与主题做了说明,他说:“除了上提母题与意象、象征一些微妙的关系外,母题与主题的关系也得略为釐清。主题学中的主题通常由个别的或特定的人物来代表,例如攸里息斯即为追寻的具体化,耶稣或艾多尼斯(Adonis)为生死再生此一原型的缩影等。母题我认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断出现的意象所构成,因为往复出现,故常能当作象征来看待。”[6]24然而,主题学毕竟是外来的学术研究方法,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民间故事,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大不相同。宁稼雨认为:“主题学和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之间是师生关系,但不是替代关系,后者是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故事主题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其意义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有在转换研究方法基础上创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作用。”[7]19宁稼雨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之间的关系。他把中国叙事文化学视为中国化的主题学,认为:“作为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有必要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框架体系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法,构建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这就是笔者数年来思考并努力为之经营的中国叙事文化学。”[4]5宁稼雨还专门撰写《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一文,分析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之间的异同关系。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母本来自西方主题学,这个从属关系决定了二者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二者必然具有相似相通点。但相似、相通不等于完全等同,没有翻新变异也就失去了中国叙事文化学存在的意义。进而他对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的异同关系做了细致的探讨。他指出:主题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民间故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为主要体裁的书面叙事文学作品;在流传方式和过程上,小说戏曲与民间故事非常相似——同一故事类型在不同时间空间传播中有不同表现样式。最后,他总结说:“由于民间故事与中国古代书面叙事文学之间有多种相似性,所以使中国叙事学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成为可能;同时,由于民间故事与书面文学之间存在差异,主题学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读中国民间故事和书面叙事文学,所以需要在借鉴主题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关系所在。”[8]可以肯定地说,宁稼雨长期以来在吸收、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吸纳国内主题学的研究成果,联系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形,将主题学研究予以中国化,进而提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
其次,确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关于故事的分类,引起学者关注更多的是“AT 分类法”,即20世纪初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奈和美国学者汤普森对民间故事所做的分类工作。宁稼雨在认识到汤普森和阿尔奈的“AT 分类法”(对世界民间故事的类型做了全面总结和归纳)的局限的基础上,又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等著作的启发下,确立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编制方案,他说:“吸收前人成就,从中国叙事文学的实际出发,创立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9]20他还认为,故事类型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所以科学合理地确定故事类型的分类原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首要工作和任务[9]18。早在2007年,或者更早的时间,宁稼雨就有编制以中国书面叙事文学为主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想法,他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一文中指出,在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体系框架上不能机械照搬“AT 分类法”,要另起炉灶。他在金荣华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的基础上做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在编制《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时,把故事主题分为6 类: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其中,天地类,包括起源、变异、灵异、纠纷、灾害、征兆、时令共7 个小类,34 个故事。怪异类,包括起源、矛盾、统治、生活、异国等22 个小类,597 个故事;人物类,包括农耕、家庭、君臣、政务等41个小类,1278 个故事;器物类,包括天物、造物、异物、怪物等21 个小类,169 个故事;动物类,包括生变、帮助、奇异、征兆等13 个小类,共118 个故事;事件类,包括人神关系、天人关系、人鬼关系、战争、习俗等12 个小类,719 个故事[10]。后来,宁稼雨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一文中把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分为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其具体设想和进展情况是:首先编制《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作为整个中国叙事文化学工程建设的起步工作,并且重申了上述故事主题类型分类的构想[11]101―102。宁稼雨把以中国书面叙事文学为主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编制视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成部分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索引的编制处于探索初期,上述分类是否完全合理,归类是否恰当,也都值得商榷和探讨。不过,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文体由古代小说、戏曲、叙事诗文及相关的史传等构成。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倡导者,宁稼雨在文献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完成了先唐叙事文学的故事整理工作,出版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对唐前叙事文学中的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归纳。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宁稼雨能够多年潜心细读,挖掘出2900 多个故事,并予以归类和总结,实属不易。
再次,探讨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联系,宁稼雨已注意到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叙事文学乃至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声称要明确界定中国叙事文化学中的“叙事”理念。他在《叙事· 叙事文学· 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一文中指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是文体意义,兼及方法的意义。二者之间产生关联的纽带则是“叙事”与“文化”之间偏正语法关系的解读,即所谓“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的文化学研究。这样的研究视角本身的方法意义正是叙事文学走向中国本土化的尝试探索之一。进而,宁稼雨对中国叙事文化学学科所涉及的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三个层面分别从狭义、广义的角度予以详细阐释[12]。如此一来,中国叙事文化学所涉及的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就不再含混不清,读者也从宁稼雨的阐释中大致明确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不可避免的联系。又如文本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联系,宁稼雨在《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一文中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核心视角是故事类型,而就书面叙事文学而言,故事类型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同一类型中不同故事的文本;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故事文本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对文本的关注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起点;因此,以文本研究为纽带,应该能够找到一些古今中外叙事文学研究之间的有机关联。他根据文本研究时间状态的不同,把文本研究大致分为文本前研究、文本自身研究、文本后研究三种类型,并对这三种类型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宁稼雨非常重视文本文献研究,认为文本自身的真实性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强调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任务重心是对同一故事类型不同文本形态做出梳理和解读分析。没有对于每一文本真实年代和原貌的准确厘定,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一切后续工作都是劳而无功的。于是,如何正确判断每个文本的真实年代和真实原貌,就成为一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他还深刻认识到文本鉴赏角度的重要性,重视从文本鉴赏角度对文本进行赏析,评价、品味、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和艺术韵味。这是中国古代具有悠久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国文本批评、文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它肇始于汉魏六朝的人物品藻活动。人的审美、自然的审美和文学艺术的审美三位一体,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鉴赏传统。这个传统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本解读程式,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文本解读有了坚实厚重的参照依据[13]。再如目录学与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方面,宁稼雨认为,叙事文化学研究与传统小说戏曲同源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超越了小说戏曲这两种主要的叙事文学文体,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与每个故事类型相关的任何文献材料。这就需要对相关的各种文体、文献材料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而通过目录学来查找各种文献的线索又是必需的渠道。他还认为,目录学对故事类型研究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这方面,作用比较大的仍然是传统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私家藏书目录。同时,近现代以来几代学者共同鼎力协作,在古代叙事文学目录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也给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文献搜集提供了很大便利[14]。宁稼雨所说的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相关的文献包括历代正史目录学著作、带有目录学性质的笔记、明清时期小说戏曲书目、现代人所著通俗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目录、现代人所著文言小说书目、现代人编综合性小说书目等。宁稼雨对各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所做的介绍,实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起步工作,给相关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另外,宁稼雨还对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做了分析,主要包括:文本流传的时间跨度、文本流传的体裁覆盖面、个案故事类型的文化意蕴构成等。同时他认为,从个案故事类型的入选标准角度来看,还需要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能否入选为个案故事类型的研究行列;二是在可以入选研究的个案故事类型中,在研究规模的预估上会有怎样的差别[5]21。
(二)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
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倡导者,宁稼雨除了不断发表文章探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话题,还十分重视对故事主题类型的研究。他说:“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和白手起家,而是在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以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研究对象,其意义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有其在转换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创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作用。”[11]99宁稼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论文,如《女娲造人(造物)神话的文学移位》(《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文史知识》2008年第6期)、《女娲神话的夭折》(《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文学移位:精卫神话英雄主题的形成与消歇》(《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等,以女娲神话、精卫神话、孟姜女传说作为研究的对象,具体分析其中的故事演变及其文化意蕴。这样的分析和考察,与主题学研究有契合之处。几年前,宁稼雨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台湾学者陈鹏翔主编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并由此线索了解了海外主题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我深受触动,并感觉把主题学研究引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应该大有文章可做。最基本的理由是主题学的研究对象——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故事形态的多变性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7]19陈鹏翔主编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收入了21 篇论文(内有两篇同名),其中《王昭君故事的演变》《杨妃故事的发展及与之有关之文学》《梁祝故事的渊源与发展》《祝英台故事叙论》《从西施说到梁祝——略论民间故事的基型触发和孳乳展延》《韩凭夫妇故事的来源与流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西王母故事的衍变》《历代王昭君诗歌在主题上的转变》等文章涉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故事的演变。这些研究成果对宁稼雨触动很深,唤起了他把主题学研究引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想法。
除了宁稼雨致力于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外,近十几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也投入中国叙事文学的个案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梁晓萍的《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西施故事的叙事模式与女娲论之隐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艳遇西施故事与其文化心理》(《文学与文化》2006年第12期),孙国江的《古代“桑女”文化原型的演变及其影响下的“秋胡戏妻”故事研究》(《辽宁师专学报》2009年第3期)、《负锁主题故事的原型及其演变》(《求索》2010年第8期)、《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地域化演变》(《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刘杰的《先秦两汉介子推故事的演变》(《晋中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宋前目连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阐释》(《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汉武帝求仙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分析》(《天中学刊》2015年第6期),夏习英的《绿珠故事的演变与美女祸水论》(《九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与宁稼雨合作,《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张雪的《清代木兰故事婚恋主题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木兰易装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天中学刊》2013年第3期)、《木兰故事的孝文化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天中学刊》2014年第6期),杜文平的《西王母会君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天中学刊》2013年第1期),郭茜的《论东坡转世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姜乃菡的《钟馗嫁妹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步非烟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李万营的《由鼓盆到劈棺——论庄子鼓盆故事在戏曲小说中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明武宗游幸猎艳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意蕴》(《天中学刊》2016年第1期),许中荣的《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天中学刊》2016年第3期),詹凌菲的《李师师故事的演变与古代青楼文化》(《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李春燕的《“人面桃花”故事的演变与文化内涵》(《九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恩报观念影响下的燕子楼故事之演变》(《语文学刊》2010年第23期)、《梅妃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语文学刊》2015年第20期)、《燕子楼故事的演变与思慕美人情结》(《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唐明皇游月宫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天中学刊》2013年第6期)等。上述所列的成果都是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个案研究,它们大多数出自宁稼雨带领的青年学者,如此众多的成果确实令人惊叹。他们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以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中的故事为选题,如吕堃的《济公故事演变及其文化阐释》(2009年)、郭茜的《东坡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2009年)、刘杰的《汉武帝故事及其文化阐释》(2010年)、韩林的《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2012年)、张雪的《木兰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2013年)、刘莉的《隋炀帝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2013年)、姜乃菡的《钟馗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2014年)、李悠罗的《张良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2014年)、杜文平的《西王母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2014年)等。他们在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对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做了文本故事演变的细致梳理,进而深入探讨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可以这样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个案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二
宁稼雨大力提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如张国风说:“宁稼雨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主题学中继承了一个基本的思路,那就是不再以作品为研究的单元,而是以情节、人物、意象作为研究的单元,着重探讨其独立的演变轨迹。其新意在于力图对故事、人物、意象的演变作出文化的解释,并且试图借这种研究将小说、戏曲和诗文打通,将叙事文学的各种形式打通,将其统摄到文化的背景之中。”[1]郭英德说:“从宁稼雨及其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将西方的主题学研究‘中国化’,从而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的学理依据可以浓缩为三个关键词,即‘中国’、‘叙事’、‘文化’。”[15]陈文新说:“近年来,宁稼雨教授大力提倡叙事文化学,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指导他的诸多博士——一群青年才俊,一起探索,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他们的贡献,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古典小说领域的这种叙事文化学研究,有助于拓展中西会通之路。”[16]从上述专家、学者的评论看,宁稼雨所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在当今学术界的意义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诚然,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在主题学的启迪之下形成的,它强调的是中西结合,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借鉴叙事学理论,重点关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主题类型。然而,中国叙事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一,撰写《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著作。一门学科的产生,离不开学者大力倡导,离不开理论著作的弘扬,尤其是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专著。以中国叙事学为例,迄今为止笔者所见的理论著作就有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美)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书华的《中国叙事之学:结构、历史与比较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又如叙事学,就有胡亚敏的《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杰拉德· 普林斯的《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中国叙事学或叙事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与以上理论著作的支撑密切相关。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存在,需要有一部奠基之作。那么,宁稼雨提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要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目前最急迫的是要有一部理论著作。其实,早在2009年宁稼雨就注意到这点,他说:“在类型索引和个案分析实践摸索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撰写《中国叙事文化学》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概念定义、方法使用、对象范围,以及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故事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整体观照。这一工作目前尚在准备阶段,但中国叙事文化学能否建设成功并且成熟定型,最终却要取决于它。”[4]8笔者相信宁稼雨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在读者眼前。
其二,成立相关的学会或研究会。为了便于学术交流,促进学科的发展,成立相关的学会或研究会也是不可忽视的。从目前国内的学术组织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叙事学学会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学会机构的成员少则一百人左右,多则三四百人,这些成员对学会机构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鉴于目前的态势,笔者建议:先成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会或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心,挂靠南开大学文学院。待时机成熟,研究队伍壮大,再成立中国叙事文化学学会,或者成为中国叙事学学会之下的分属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会,并且每两年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会议,吸纳新成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综上所述,宁稼雨提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至今已走过十几年的历程,无论是学理探讨,还是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都有不少的成果。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在学术界赢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