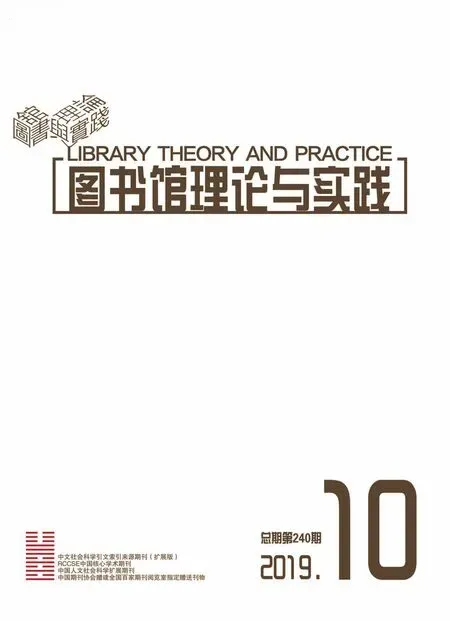北魏官修目录《魏阙书目录》与《甲乙新录》考证
2019-01-19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刘 节(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1 《魏阙书目录》的编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隋唐以后成为古典图书目录主流分类方法的“四分法”即产生于此时。当时官方颇为注重编撰图书目录,尤以南朝为盛,北朝官修目录目前则仅知两部:《魏阙书目录》 与《甲乙新录》。其中《魏阙书目录》 见于《隋书·经籍志》,[1]991仅言其为一卷,未题撰者,亦不知其具体编于何时。《隋书·经籍志》总序云: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1]907
由此可知,在孝文帝迁洛之前,北魏秘府藏书匮乏,其后有“借书于齐”之事。以常理论之,借书自然是借未藏之书,即所缺之书,因而借书需要整理记录图书缺乏的具体情况。如此似可推知,在“借书于齐”前,《魏阙书目录》 就已然编成。或许因为有如此的推论,一些学者就直接认为《魏阙书目录》是为“借书于齐”而编撰。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准确,古之治目录学者亦未闻有持此论者。南宋学者郑樵著有《通志》,其中《校雠略》 言及《魏阙书目录》,郑氏基于对古代目录学的认识,认为“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阙目录》 一卷”。[2]依郑樵所见,固然《魏阙书目录》可做求书之用,但其编撰应是古人编书的惯例,并非完全出于求书,更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借书于齐”而编成。清人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参合齐魏史事与郑樵之说,认为《魏阙书目录》“因借书而流传江左,时当齐明帝建武中”。[3]姚氏虽然将该目录的流传与“借书于齐”相联系,但是他认可《通志·校雠略》古人亡书有记的基本观点,并且他在考证中提及孝文帝诏求天下遗书,实际亦未将《魏阙书目录》的编撰完全与“借书于齐”关联。
根据记载,北魏自建国至孝文迁洛之前,朝廷至少进行过两次正式的图书搜集工作。第一次是在道武帝天兴三年(400),时任博士、定州大中正李先向道武帝建言:“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随后“班制天下,经籍稍集”。[4]789第二次则在文成帝在位时,太安年间高谧专典秘阁,其“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4]752有关这两次图书搜集是否编撰目录的问题,史籍并无明文记载。考虑到《魏阙书目录》本身就于北魏正史无载,如果根据《隋书·经籍志》推论其编成于北魏“借书于齐”前,那么上文所述两次搜集图书之际皆有可能编成阙书目录以供求书参考。当然,“借书于齐”时所依据的阙书目录显然要反映最新的北魏藏书情况,故而当时的阙书目录应编于文成帝集书至孝文帝迁洛期间,是否具体成书于孝文帝时,则不得而知。
北魏孝文帝之后,南北朝都曾经历书厄,北有尔朱荣之乱及周齐混战,南有萧绎焚书及朝代更易之兵祸,官修目录毁失于期间实属正常,即《隋书·经籍志》 所谓“先代目录,亦多散亡”。观《隋书》 所收目录书,其中属南朝官修目录者凡八部,而目前所知南朝官修目录总共不过十一部。[5]《隋书》明言“簿录类”为“总其见存”。可知隋唐时南朝官修目录其实大多流传于世,而北朝唯一见于正史的官修目录《甲乙新录》则不见于《隋书》,说明该目录当时已经失传,北朝图书搜集保存工作之落后可见一斑。北魏官修藏书目录不传于世,而阙书目录却能为隋唐政府收藏,此不能不使人疑惑。或许正如姚振宗所言,《魏阙书目录》 因其曾送于南朝而得以流传,南朝藏书事业要比北朝发达,而且秘阁书录播于异域,正为其传世增加了可能性。
如上所述,《魏阙书目录》 的成书年代及流传情况似乎已有大致脉络,然而,若据郑樵“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的观点,隋唐时所见《魏阙书目录》亦未必是孝文帝时之阙书目录。“徙都洛邑”以来,魏廷藏书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北朝藏书长期不及南朝,阙书目录或亦有新编。对于此种可能性,学者亦不可轻易否定。
2 《魏阙书目录》与《南齐书》所载借书
前文已叙《魏阙书目录》 编撰与流传的大致情况,其中北魏“借书于齐”是十分重要的相关历史事件。此事为《隋书·经籍志》 明文记载,历来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佳话,然而,考之史籍,借书一事存在许多疑点。
根据《隋书》 的说法,借书发生在“孝文徙都洛邑”之际或其后,具体也就是接近太和十七年(493) 的时间点。北魏“借书于齐”其实是明确记载于南北朝正史的,但是具体情况却与《隋书》 的说法有所歧异。据《南齐书·王融传》,齐武帝永明年间,北魏就曾遣使借书,当时王融上疏劝说武帝同意,武帝也认可了王融的看法,但最终结果却是“事竟不行”。[6]818-820《南齐书》所录王融奏疏中提及当时北魏“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所谓丘颓,姚薇元考证认为是指北魏司空苟颓,其鲜卑姓名为若干丘颓,[7]而苟颓殁于太和十三年(489),即齐永明七年,则此次借书应当发生在永明元年至七年之间(483-489),即北魏太和七年至十三年。按《魏书·高祖纪》,北魏在此期间曾两次遣使至南齐。第一次在太和八年的五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4]153第二次是在太和十三年的八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侯灵绍使于萧赜”。[4]165《魏书》的遣使记录正与《南齐书·魏虏传》相合:“明年冬(永明二年),虏使李道固(李彪)报聘”[6]989、“至七年,遣使邢产、侯灵绍复通好”。[6]990北魏借书应当就发生在这两次聘使活动中,至于是发生在永明二年,还是七年,可以做进一步考证。
《南齐书·王融传》叙及王融建议借书前有“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融赠诗及书,俭甚奇惮之,笑谓人曰:‘穰侯印讵便可解?’寻迁丹阳丞,中书郎。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云云。[6]818由此可知,王融上疏建言在其从叔王俭任开府仪同三司之后,当时其本人官职为中书郎。又据《南齐书·王俭传》,王俭于永明五年首次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但他并未接受,至六年,朝廷重申任命。[6]436如此,王融上疏自然是在永明五年或六年之后,因而可以确定,北魏遣使求书应当是发生在南齐永明七年(489),即北魏太和十三年。
以上所述乃是《南齐书》所记北魏“借书于齐”的时间考证,显然其结论与《隋书》 的说法歧异很大,因而有可能两书所说的借书并非一回事。姚振宗在考证《魏阙书目录》 时注意到了这两条相关史料,他在该条考证下先是引用了《隋书·经籍志》 总序中有关借书的文字,其后注案语云:“《王融传》有虏使遣求书事”。这里似乎是将二者等同,文末又有案语曰:“(《魏阙书目录》)因借书而流传江左,时当齐明帝建武中(494-498)”。[3]如此姚氏明确“借书于齐”发生于北魏迁洛之后。如果不是姚振宗在考证中刻意保留异说的话,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将《南齐书》与《隋书》 的借书记录混为一谈,而没有发现其中的歧异。要想解决两条记录之间的歧异问题,首先必须确定《隋书》 所言发生在迁洛之际或其后的“借书于齐”是否真正存在,这可以从分析南北朝正史所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及其后与南齐进行的聘使活动入手。
3 北魏迁洛借书考辨
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在太和十七年(493),此年北魏出使南齐凡两次。第一次是在正月乙丑,“诏兼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4]171《魏书》记北魏使齐凡十二次,除本次皆有正副使二人,且惯例以散骑常侍(有员外与通直之别)为正,以散骑侍郎或尚书郎为副。《北史·魏孝文帝纪》记此年正月乙丑出使为“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8]109《魏书·邢峦传》亦言其出使经历。[4]1437《南齐书·魏虏传》载本年八月北魏官员鹿树生(鹿生)对南齐的移文称:“前使人邢峦等至”。[6]993综上可知,此次出使是以邢峦与刘承叔为正副使,《魏书》 应有缺漏,邢峦与刘承叔的使命于《魏书》 中未见记载,《南齐书》中却可见端倪。
《南齐书·魏虏传》 言“十一年,(魏)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6]992十一年为永明十一年,即太和十七年,此年稍后齐武帝去世,同传紧跟其后记载了前所述北魏鹿树生之移文,其中有“前使人邢峦等至,审知彼有大艾”云云。综合《魏书》 与《北史》之记载,邢峦与刘承叔二位使者是在正月乙丑日出发,而《南史·齐武帝纪》 记载本年“夏四月癸未,魏人来聘”。[9]则二人抵达建康的时间恰在齐武帝去世前夕。综合来看,邢峦使团应当就是“遣露布并上书”者,也就是说邢峦与刘承叔承担的是近于宣战的使命,在此期间显然是不可能发生借书的。
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 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4]172九月壬子,北魏再次派出使者前往南齐,“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兼员外散骑侍郎贾祯使于萧昭业”。[4]172此事在《高聪传》中有进一步的讲述:
高祖定都洛阳,追诏聪等曰:“比于河阳敕卿,仍届瀍洛,周视旧业,依然有怀,固欲先之营之,后乃薄伐。且以赜丧甫尔,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玺书,以代往诏,比所敕授,随宜变之,善勖皇华,无替指意。[4]1520
根据《魏书·高祖纪》 记载,孝文帝于此年九月丁丑正式放弃南征,确定迁都之计。正在此后,孝文帝派人追及使团,通知高聪等人放弃南征,并且“更造玺书,以代往诏”。可以推知,前所发给使者的国书应当仍与宣战事宜相关。如此,孝文帝亦有可能在更换的新诏中加入借书事项,但是《南齐书·魏虏传》中的记载似乎并不支持此种可能。该传将此次出使与上叙鹿树生移文关联,兹将有关文字全录如下:
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节、安南大将军、都督徐青齐三州诸军事、南中郎将、徐州刺史、广陵侯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鹿树生移齐兖州府长史府:“奉被行所尚书符腾诏:皇师电举,摇旆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霭。以去月下旬,济次河洛。会前使人邢峦等至,审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义,闻丧寝伐。爰敕有司,辍銮止轫,休马华阳,戢戈嵩北。便肇经周制,光宅中区,永皇基于无穷,恢盛业乎万祀。宸居重正,鸿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铭庆。故以往示如律令。”并遣使吊国讳。[6]993
四个少年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身体中的内息由各自的丹田里焕发出来,流动在他们的身体之间,如溪丘与河山,回应着回旋的声浪,或如沃冰雪,或如入洪炉,也许接下来的大音,就会让血冲出经脉,冲出百会穴,血箭一般,溅射到他们头顶的花朵上,但少年们心意已决,并不害怕。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引文所记载的时间并不准确。鹿树生的移文其实就是北魏行所尚书传达的孝文帝诏书,其中“爰敕有司,辍銮止轫,休马华阳,戢戈嵩北。便肇经周制,光宅中区,永皇基于无穷,恢盛业乎万祀。宸居重正,鸿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铭庆”云云,正与孝文帝指示高聪等人所说的“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相合。如此,鹿树生移文南齐的时间最早应在孝文帝九月丁丑(晦日) 放弃南征之后。并且,若依《魏虏传》的时间,则文中所说“以去月下旬,济次河洛。会前使人邢峦等至,审知彼有大艾”则可解释为“七月下旬,魏军济次于河洛之滨,恰逢前所派使者邢峦等人返回,确知对方有大丧”。据《魏书·高祖纪》,本年七月份北魏军队尚未从平城开拔,而齐武帝死于七月晦日(戊寅),[6]61-62若邢峦等人向魏廷传达了齐主的确切死讯,岂能在七月就返回?实际上,《魏书》 记载北魏军队渡过黄河的时间是在九月下旬(戊辰,廿日)。综上所述,鹿树生的移文时间极有可能是太和十七年十月,而绝不可能是八月。
这样,《南齐书·魏虏传》 所载“并遣使吊国讳”指的就是九月出发的高聪使团,高聪使团所携孝文帝诏书内容应当与鹿树生移文相似,并增加了吊国讳的文字。南北史书皆未记载此次出使涉及借书,并且此时南北关系紧张,谨慎地认为高聪使团并未借书是比较合理的。
在高聪、贾祯使齐之后,孝文帝又于太和十八年(494)六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使于萧昭业”。[4]174北魏使团抵达建康时正值萧鸾篡位,孝文帝随即讨伐萧鸾,魏使为齐人所虐待。[4]1055南北关系在战后并未恢复,卢昶即使身肩借书使命,亦不可能完成。自此以后,齐魏断绝外交,南北之间直到梁普通元年(520)才恢复通使。[10]
分析孝文帝迁洛之际及其后的北魏使齐情况,可以发现北魏在此期间向南齐借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其实南齐不向异国借书是有制度可循的。《南齐书·宕昌传》的记载,永明六年,宕昌王梁弥承也曾遣使向南齐借书,而齐廷未允借,并解释说:“秘阁图书,例不外出”。[6]1033由此可基本确定北魏是不太可能从南齐处借得官方藏书的。所谓“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的说法恐怕是《隋书》之误。借书一事有之,不在迁都洛阳之后,而在齐武帝永明七年(489),且并未成功。至于“秘府充实”也自然与借书无关,就在南北关系破裂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4]1055很有可能在此次向民间诏求图书以后,北魏藏书才有所充实。既然北魏借书发生在南齐永明七年,那魏廷的阙书目录最迟在此年就应该已经编成,由于北魏并没有成功从南齐借到图书,则该目录编成以后更多是应用到了向民间集书上。无论北魏是否成功从南齐借到图书,《魏阙书目录》的存在都体现了魏廷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也反映了孝文帝时北魏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推行汉化改革的时代背景,而对于《甲乙新录》的考证也必须建立在如此的史实基础之上。
4 《甲乙新录》的编撰与体例
北魏另一部官修目录《甲乙新录》 未被《隋书·经籍志》收录,而在《魏书·儒林传》中可见其记载:
(孙) 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4]178
北魏秘府藏书充实以后,自然需要编撰目录以便查阅,《甲乙新录》 遂应运而生。由于该目录并未能流传于世,相关记载也寥寥无几,其体例自是无法确切得知,但是通过一些侧面记载仍然可以推测其实。该目录既然名为“甲乙新录”,则应当是继承荀勖《中经新簿》之基本体例,采用甲乙丙丁四分之法来对图书进行分类,有所疑问的是,甲乙所指与《中经新簿》是否一致?
《中经新簿》撰于西晋,当时所设甲乙丙丁四部粗略对应后世四分法之“经子史集”四部,而至东晋李充编撰《晋元帝书目》时,将《中经新簿》之乙丙两部互换,遂使甲乙丙丁对应后世常用之“经史子集”。[11]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认为北魏与东晋隔绝,未必会使用李充的编写体例,因此怀疑《甲乙新录》 所录为经子两部。[12]来新夏所著《古典目录学浅说》 中的观点与余氏基本相同。[13]两位先生认为北魏与东晋隔绝,这并无问题,然而,自李充编《晋元帝书目》[14]至《甲乙新录》之成书,已历百年有余,其间南北关系经历了漫长发展,早已不是隔绝状态。
北魏皇始元年(396),晋安帝遣使于魏,[4]28由此至北魏与南齐断交,南北聘使活动有九十三次之多,其中东晋使魏有六次,北魏使晋有三次,刘宋使魏有三十次,北魏使宋有二十九次,南齐使魏有十三次,北魏使齐有十二次。[15]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其中涉及文化交流自然是不可避免之事。兹举两例,即可见南北文化交流之通达。
根据《南齐书·王融传》 的记载,王融在永明九年(491)作《曲水诗序》,十一年,北魏使臣房景高与其应对时说:“在北闻主客此制(《曲水诗序》),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6]821房景高的话透露出当时南朝文坛的消息是能够传达到北朝的,固然房景高未能在北方及时看到王融的著作,但是他提及“胜于颜延年”,则说明稍早一些的南朝著作应该是能在北方见到的。这在另一个例子中可得到明证。南朝宋齐之时的文学家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以为作诗的规范,而同时代的北魏甄琛认为沈约的文学理论不依古典,系穿凿之说,因此找来沈约年轻时所做的诗文,指出其中不合“四声八病”规范的地方,用以诘难沈约。沈氏听闻此事,则专门写了一篇《答甄公论》来回应甄琛。[16]虽然无法确定沈甄二人的争论是否为及时的回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南北朝对立之时,双方著名文人的诗文作品和相关理论是可以互相流传的。自李充以来,南朝官修目录皆以甲乙丙丁四部为“经史子集”,如此重要的目录体例变化,北方学者不可能不知,而且北魏朝廷既有意借书于南朝,也必然留心于南朝图书事业,了解四分法之演变乃是自然之事。
北魏既然能够知道四分法次序之变化,那《甲乙新录》所录就未必是经子。考虑到《甲乙新录》之编成正值孝文帝在位,而孝文帝醉心于汉化改革,于典章文物多摹仿南朝,[17]6则秘阁藏书分类不应例外,亦当采李充之法为常例。当时北魏朝廷为施行改革,任命了一批北来的南朝士人,这些南士很有可能推动了北魏秘阁藏书制度的改革,其中当以王肃为最。
王肃出身著名的琅琊王氏,其生于南朝,长于南朝,在南齐曾官至秘书丞,永明十一年(493),其父兄并为齐武帝所杀,于是北奔魏廷,得到孝文帝重用。《北史·王肃传》称:
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8]1540
对于王肃与北魏礼制改革的密切关系,史书明文记载,而陈寅恪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亦有论述,自不必赘言。王肃仕齐时为秘书丞,正是执掌秘阁图书之职,并且王肃是南齐目录学家王俭的从侄,王俭在刘宋时曾经参与编撰官修目录《元徽四部书目》。陈寅恪考证认为王俭以熟知朝章典故知名,而王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17]16所谓“流风遗著”主要指南朝礼制之学,但以常理论之,曾任秘书丞的王肃所受薰习的知识必然也包括目录学。如此,王肃北奔以后,北魏秘府藏书之分类实不可能仍以荀勖旧体为法,卢昶编《甲乙新录》 于其后,“甲乙”所指应是经史。
此外,自李先建议北魏道武帝向全国收集“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以来,魏廷十分重视收藏史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魏太武帝之时,“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1]964由此可知,北魏所藏史部书籍颇为丰富,而《魏书·卢昶传》又称卢昶“学涉经史”,卢氏编撰秘阁藏书目录不可能舍史部而录子部。因此,所谓《甲乙新录》就是当时北朝使用南朝目录学体例编撰的官方藏书目录。
《甲乙新录》 除其体例问题外,还有一问题值得学者关注。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既然名为“新录”,则在此之前应有一“旧录”。史书并未记载北魏孝文帝以前编撰藏书目录之事,而当朝所撰目录除《甲乙新录》 以外,仅知有《魏阙书目录》。以常理推知,编撰所缺书籍目录必然要清楚现有藏书几何,既已清楚藏书情况,则不可能不做记录。据前所考证,至少北魏孝文帝时的阙书目录早在齐永明七年(489) 就已经成书,这样,卢昶编撰《甲乙新录》远在阙书目录成书以后。如果《隋书》所载《魏阙书目录》确为北魏借书于齐所依据的阙书目录,那么,《魏阙书目录》与《甲乙新录》所对应的“旧录”或许有着极大关系。或者《魏阙书目录》 虽名为“阙书目录”,但同样记录了藏书情况,则《魏阙书目录》即“旧录”;又或者《魏阙书目录》之外尚有一不为史书记载的藏书目录,则此即“旧录”。由于史料匮乏与个人能力有限,笔者对这一问题仅能做出如此的推测,具体结论只能寄希望于后来之有识者。
5 余论
通过探究《魏阙书目录》与《甲乙新录》的相关疑问,可以看到当时南北之间在文化上的交流与渗透,也能够发现两录编撰之时,北魏政权正以摹仿南朝的方式在文化上进行自我改造,以期取代南朝成为华夏正统的文化象征。因此,北魏编成阙书目录,并以此向南齐借书,而《甲乙新录》 的编撰则从体例上与南朝最新的目录学发展相合。从这个角度来说,《魏阙书目录》与《甲乙新录》的编撰可以视为北魏汉化改革的两个成果。然而,这两部目录的编撰信息也体现了当时北魏所藏图书远少于南朝,后来北方又经战乱,官方藏书有所散失,更加不及南朝秘阁所藏。如此看来,这应当是北朝近三百年间仅有两部官修图书目录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