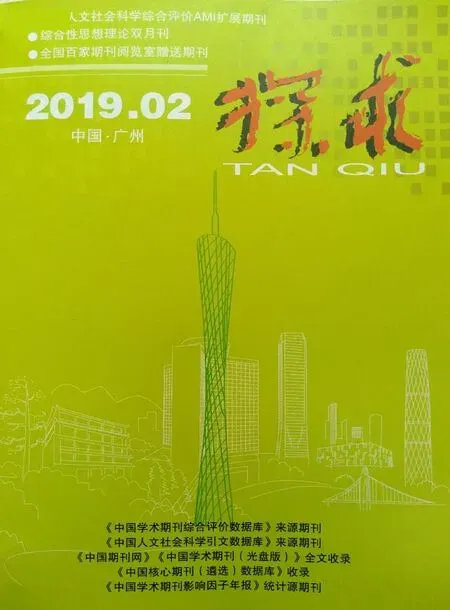宋代广州扶胥浴日文学景观书写初探
2019-01-18赵晓涛
□赵晓涛 罗 欢
广州旧有著名景点“扶胥浴日”(又称“波罗浴日”),系指登临今属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古属番禺县境)南海神庙西侧小岗上的浴日亭观看海上日出,为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一。[1](P303-316)
南海神庙古属扶胥镇。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三四○记载“扶胥镇在番禺县东南三江口”,并引北宋王存主编的《元丰九域志》云“(番禺)县有瑞石、平石、猎德、大水、石田、白石、扶胥七镇。”
唐宋时期珠江两大支流西江与北江在三水一带汇合后,其中一部分自西向东流经广州城南,再向东八十里。这八十里水道“是由受地质构造和海潮共同影响所形成的广州溺谷湾逐渐发展而来”。[2](P82)之后在扶胥镇附近与自东向西流动的珠江另一大支流东江汇合,水面变得格外开阔,形成西东流向的珠江漏斗湾并至此转弯,转向北南流向的狮子洋大漏斗湾,处于内河与外海的交汇地段,既受西东流向的江水影响,又受时常溯江而上的海潮影响,“自此出海,溟渺无际”(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可谓江海形胜之地。因此扶胥镇近旁的珠江黄木湾建港条件优越,很早就是广州外港,而扶胥镇则由此发展成为一大集市,中外商人坐商船或者当地渔民驾渔船出海时通常先到南海神庙向南海神祭拜,祈求护佑旅程一路平安,是当时及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记载“浴日亭,在扶胥镇南海王庙之右”,“小丘屹立,亭冠其颠”,唐宋时这里三面环水,“前鉴(一作“瞰”)大海(即狮子洋),茫然无际”。每当夜幕渐退,一轮红日从洋面上冉冉升起,万顷碧波金光披染,霞光万道,瑰丽多姿,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浴日亭始建于何时,已难考证,一般认为始建于唐代。北宋绍圣初年(1094),大文豪苏东坡被贬至岭南惠州,途中曾慕名到坐落于扶胥镇的南海神庙游览,并登亭看日出,被“扶胥浴日”的壮丽景观所吸引,诗兴大发,写下了《南海浴日亭》一诗,感叹“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诗因亭作,亭仗诗威声名远播,因此也就被人称为“浴日亭”。①另据南宋方信孺《浴日亭》诗前小序引《番禺杂志》可知该亭曾名“看海亭”。
一、扶胥浴日文学景观之滥觞
广州在盛唐时期已拥有中国海上贸易特别是远洋对外贸易的大港,并进入文学世界成为书写对象。如唐代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着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描述的便是当时广州港口货物贸易的盛况,虽未直接点明是在扶胥镇、黄木湾所见,但不妨视作如此。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大文豪韩愈因《谏迎佛骨表》一事被贬潮州,途经广州,应其好友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戣之请,欣然写下了一千多字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以纪念孔戣修葺南海神庙事。韩愈这篇碑文记载了孔戣治理岭南的经验,以及唐代祭海习俗。碑文结构安排巧妙,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精粹隽美,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如韩愈描述南海神庙的位置“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还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这是南海神庙首次进入文学作品,并由此成为一个文学景观。与《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写作时间大约同时,韩愈还有六首《赠别元十八协律》诗,其六“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两岩虽云牢,水石互飞发。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诗句,以他的切身体验,对珠江入海口自扶胥直至屯门一带浪潮汹涌、水石激发的自然地理景观,作了富于动态且夸张的文学性书写。
进入宋代,随着岭南特别是广州海洋贸易的进一步开发,广州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显着提升,在官方的倡导下,南海神崇拜日隆,浴日亭旁的南海神庙随之声名益盛,远播中外。南海神庙、黄木湾一带开始更多地进入文人士大夫的笔下,成为他们对于广州这方风土的主要记忆之一。
如北宋大文豪苏轼被贬谪岭南,后在离开广州之际,作《发广州》一诗写道“蒲涧归钟外,黄湾落木初”,将南海神庙旁的黄木湾视为他在广州停留期间值得忆念的两大去处之一。后来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在《贺新郎·题蒲涧寺》一词中亦是以“且游戏、扶胥黄木”勾连起蒲涧和黄木湾广州这两处景观。徐宝之《寄李南金》诗句“梦忽堕千里,扶胥黄木湾”,南宋洪适《秋阅致语口号(为广帅作)》诗句“使星两两下人间,南伯来临黄木湾”,李昂英《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词句“万项黄湾口”“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②宋末元初牟巘《次韵无党留别》诗句“黄木扶胥最奇处,想留句子待浮洲”等皆可为证。至于洪适为送别提举市舶司的韩姓友人所作《韩提舶饯行致语口号》诗句“黄木湾头波湛碧,阳关声里柳吹青”,更是点明南海神庙、黄木湾为饯行之处。
以上唐宋作家们的文学性书写,为宋代扶胥浴日文学景观书写做了必要的铺垫。下面结合宋人有关文学作品,试就扶胥浴日地理景观在宋代经由文学性书写而成为文学景观,[3](P236-237)作出一些具体分析。
二、宋代扶胥浴日文学景观书写
山海交会、江海相接、通江达海、视野开阔的地段特点,加上夏季从南海刮来的东南季风以及台风盛行所带来云气蒸腾、降雨丰沛、波涛汹涌的气候特征,构成包含扶胥浴日在内的南海神庙文学景观区文学性书写的自然地理条件基础。
如程公许《县斋秋怀》(其六)“云涛扶胥口,烟雨汇泽涯”,表现扶胥一带江海汪洋无际的壮阔景象。曾丰《辞东庙途中作》:“海近微茫白,山穷次第平。固然天远大,加以眼高明”,刘克庄《题江贯道山水十绝》(其五):“茆山千万迭,不得见天全。帆出扶胥口,无山只有天。”都写出了船只在顺流驶过重重山岭,出扶胥口时山到尽头,只见天连水尾水连天、海天一色的开阔景象。此外还有如刘克庄《扶胥三首》(其一)“一阵东风扫曀霾,天容海色豁然开”等,这些诗句都是对这种自然地理形态的形象描摹。
在这种自然地理形态的基础上,海面日出成为这一带自然地理景观的点睛之笔,而建于南海神庙右旁拔地而起的小岗丘上的浴日亭则成为最佳视点,尽收其间灵气,可谓自然风景和历史建筑的综合体。“扶胥之口,又以地低而先见日。扶胥为广东诸水之汇,南海之神庙焉。其南百步,有一峰,巍然出于林秒,是曰章丘。俯瞰大洋,惊涛怒飘,倏忽阴晴,万里无际。一亭在章丘上,以浴日名。”[4](P2)宋人往往径直以“浴日亭”为题,来抒写在浴日亭上远眺所见、所思。
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自定州被贬岭南惠州,九月路经广州时与子苏过等人游南海神庙,并特地早起登上浴日亭观看日出景象,在眼前壮观景象的激发下,心情一时大好,写下《浴日亭(自注:在南海庙前)》一诗。全诗如下: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沧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5](P9499)
关于苏轼此诗,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八评“剑气”二句“日欲出时,当空先有红气一道,浮而不动者良久,其色不见,则东方渐白。此由日未出时,其光漏出海上,又自海激射于天也。此句正形容其状。”评“坐看”以上三句,“乃日出时一定次叙”,直到“忽惊”“此句日始出”。[6](P1615)王文诰此评可谓尽得苏轼此诗描摹扶胥浴日景象之精微。东坡此诗一出,小小的浴日亭名声大噪、播在人口,引得后世来此游历的诗人竞折腰。③如南宋方信孺《浴日亭》诗称许“坡仙想得江山助,八语端为天下豪”,刘克庄同题诗句“暮年笔力全衰退,甘与韩苏作后尘”。至于追和之作,更是代不乏人。如清人宋湘《每过扶胥口,不维舟亦无所作。今日读崔君〈波罗外纪〉,遂用坡公浴日亭韵以发之,兼谢崔君》诗句“文字不来摹日月,韩苏已早占江山”,在追和中对韩愈碑文和苏轼诗作可谓退避三舍。苏轼这一诗作名篇,通过后世诗人的传诵和追和,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后世诗人对于“扶胥浴日”这一景观的审美认知和地理想象。
苏轼之后,刘弇写有《题广州浴日亭》,全诗如下:
谁识咸池万顷中,源流穷处与天通。气蒸古木千岩晓,浪拍扶桑四远红。
焰焰骊珠初出海,腾腾乌翼渐摩空。不须更问乘槎客,只此波间是月宫。[5](P12033)
刘弇此诗,境界阔大,想象丰富,气势夺人。诗人将此处海面比作神话中的“咸池”,极力夸扬海面的壮阔无际,将波底比作神话中的“月宫”,似乎日月皆出入于其中;又将初日比作神龙口里的“骊珠”,“焰焰”一联对仗特别工稳,且富于动感。“气蒸”一联,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时空结合,远近结合。
而谢举廉的《浴日亭》诗“煌煌太阳精,浴以沧溟水。光润无纤滓,畏爱从此始。”[5](P12982)寥寥四句,集中描摹海面初升起的太阳,精炼至极。稍感遗憾的是,此诗对浴日亭本身则不见落笔。
在苏轼诗作的影响下,吕定有追和苏轼之作《浴日亭和苏学士韵》,全诗如下:
危亭突兀倚青山,坐对扶桑碧海湾。紫雾欲生龙伯庙,洪涛先涌虎门关。
光摇宇宙花生眼,影动阑干酒上颜。遥望蓬莱宫阙晓,一轮飞挂碧云间。[5](P31078)
此诗描叙了浴日亭的方位、朝向:背倚青山、坐对海湾,也写到了近旁的南海神庙,以“紫雾欲生”其间来渲染南海神的神奇、威严,“洪涛”句写出海潮汹涌而来、闯关夺门而入景象,特别是颔联中字面上以“龙”对“虎”,更显此地襟带山海、龙争虎斗的形胜之处。诗人以“扶桑”、“蓬莱宫阙”来比拟浴日亭上所见到的奇丽景观。
洪适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至二十五年(1155)皆居广南东路,期间在广州知州方滋为友人黄公度接风所设的歌舞宴会上,应方滋之令代为创作了一组(或曰一套)共12首《番禺调笑》转踏词。④每首转踏词前皆有七言八句诗一首,诗词连缀,相互递转、相互发挥,以反映广州十二处名胜古迹、风土人物。其中第六首题为“浴日亭”,移录如下:
扶胥之口控南溟。谁凿山尖筑此亭。俯窥贝阙蛟龙跃,远见扶桑朝日升。蜃楼缥缈擎天际。鹏翼缤翻借风势。蓬莱可望不可亲,安得轻舟凌弱水。
弱水。天无际。相去扶胥知几里。高亭东望阳乌起。杲杲晨光初洗。蓬莱欲往宁无计。一展弥天鹏翅。[7](P1370)
洪适诗的首句描叙了浴日亭的独特地理位置:扶胥口、控南溟。“贝阙”、“扶桑”、“蜃楼”、“蓬莱”、“蛟龙”、“弱水”等来源于神话的名物,特别是将此处海面比作神话中的“弱水”,极力突显其险恶难渡,必须借托神话中的大鹏翅翼才能去往可望难即的蓬莱仙岛,让此地充满奇幻的神话色彩。后来的方信孺《南海百咏·浴日亭》诗句“亭倚蓬莱几许高,下临无地有惊涛”,则是在心理感知上将下临惊涛的浴日亭和蓬莱仙境直接拉到一处,更加凸显浴日亭的瑰奇色彩。
淳熙八年辛丑(1181),杨万里在广东常平使者(治所广州番禺)任上,二月十三日拜谒南海神庙,并写下《南海东庙浴日亭》《题南海东庙》《谒昌黎伯庙》《二月十三日谒两庙早起》等纪行诗。其中《南海东庙浴日亭》一首移录如下:
南海端为四海魁,扶桑绝境信奇哉!日从若木梢头转,潮到占城国里回。
最爱五更红浪沸,忽吹万里紫霞开。天公管领诗人眼,银汉星槎借一来。[8](P918)
诗人在诗的开头将此处比作神话中的“扶桑绝境”,在末尾更是幻想此处直通天上的“银汉星槎”。“日从”一联中对太阳的经行联想到神话虚构的“若木”,而对海潮的奔涌簸荡则联想到真实存在、远在海外不可望及的“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最爱”一联生动勾画眼前的浴日壮丽美景。而在《题南海东庙》一诗中,杨万里发挥了更为大胆奔放的想象力,叹为天下奇绝。全诗移录如下:
罗浮山如万石锺,一服南走如渴龙。雷奔电万遮不住,直抵海滨无去处。
低头饮海吐绛霞,举头戴着祝融家。珠宫玉室水精殿,万水一日朝再衙。
青山四围作城郭,海涛半浸青山脚。客来莫上浴日亭,亭上见海君始惊。
青山缺处如玉玦,潮头飞来打双阙。晴天无云溅碎雪,天下都无此奇绝。
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
海神喜我着绮语,为我改容收雾雨。乾坤轩豁未能许,小试日光穿漏句。[8](P919)
诗人驰骋想象、驱遣造化,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诗人将罗浮山与南海神庙近旁的青山勾连起来,认为南海神庙近旁的青山是罗浮山的“一服南走”,并以“渴龙”作比,从而赋予南海神庙一带自然景观以雄阔的地理座标。诗人接连以“珠宫”“玉室”“水精殿”来比喻此处水府,尽见其瑰奇。以百官朝衙来比喻此处万水奔会,尽见其威仪。“青山四围”二句精确描画此处的山海形胜。“青山缺处”以下四句则是极力描画此处海潮盛大之势,夸许为“天下都无此奇绝”。“海神”以下四句则是以拟人之笔写出海色天容之变化。“南来”二句,诗人以有“千门万户”之称的西汉长安城建章宫作比,极力称扬拜访南海神庙所见不虚此行,在他的岭南经行中着实不可或缺、值得大书特书。
刘克庄于嘉熙四年(1240)以广东转运判官摄帅时,追随苏轼行迹也曾拜谒南海神庙,并再三致意,写有多首诗作,成为继苏轼、杨万里两位宋代文学巨擘之后,又一位着力书写扶胥浴日文学景观的宋代文学大家。叶适《题刘潜夫诗什并以将行》一诗写道:“寄来《南岳第三稿》,穿尽遗珠簇尽花。几度惊教祝融泣,一齐传与尉佗夸。”他嘉许刘克庄诗稿,将刘克庄书写岭南的纪行诗特地拈出予以表彰,而刘克庄书写南海神庙及扶胥浴日文学景观的几首诗作自是其中精彩之处。其中《浴日亭》移录如下:
归客飘然一叶身,尚能飞屐陟嶙峋。危亭下瞰嵎夷宅,积水上通河汉津。
叱驭为臣前有志,乘桴从我更无人。暮年笔力全衰退,甘与韩苏作后尘。[9](P742)
和吕定一样,刘克庄亦以“危亭”来称浴日亭。据《尚书·尧典》记载“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孔安国注:“东夷之地称嵎夷。”⑤诗人下视此处水府,将之想象为神话传说中的嵎夷之宅,并进一步想象此处水流上通银河。诗作最后点明自己追慕韩、苏两位文章巨公足迹而来并写下此诗。
刘克庄另一首《又追和坡韵一首》移录如下:
亭傍乔木拂云天,亭下高桅泊晚湾。白是张骞曾泛水,青疑徐福所求山。
羊城隔雾愁回首,鲸浸收风喜见颜。却笑金乌并玉兔,辛勤出没雪涛间。[9](P743)
“亭傍”一句描摹浴日亭之高,“亭下”一句描摹帆船向晚靠泊景象,“白是”一句将此处水府比作传说中张骞到过的银河,“青疑”一句将远处山岛比作徐福入海求仙的神山。诗人眼见“羊城隔雾”“鲸浸收风”,并逗露日月皆出没于此处水府。
刘克庄《扶胥三首》移录前二首如下:
一阵东风扫曀霾,天容海色豁然开。何须更网珊瑚树,祇读韩碑也合来。
旸谷扶桑指顾间,冯夷得得报平安。为言博望乘槎至,莫作师襄击磬看。[9](P711)
第一首“一阵”二句写出了诗人对扶胥一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真切感知。“何须”二句则见出诗人对前贤文化遗珍的钦慕胜过对南海出产的奇珍异宝的喜好。第二首跟上述一些诗作一样,诗人也是以“旸谷”“扶桑”“冯夷”和张骞“乘槎”等神话传说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知。
三、结语
综合以上文学作品对南海神庙、浴日亭一带地理环境的书写,可以见出在宋代诗人的地理感知与文化体验中,“扶桑”“蓬莱”“银汉星槎”等是南海神庙、浴日亭一带最能勾起他们联想的虚拟性文学地理意象,从而让作为自然景观而言尚非独绝的南海神庙、浴日亭一带,能以亦真亦幻、真幻难辨而充满浓厚神话传奇色彩的独特面相在文学景观世界中呈现,后世诗人的书写基本上逃不出这些文学地理意象的组合。[3](P324-330)扶胥浴日(南海神庙)由此得以生成为兼具自然和人文双重特征的一处著名文学景观。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扶胥浴日(南海神庙)文学景观完全满足评判一个景观是否属于实体性文学景观的六个标准[3](P236-237):第一,有过韩愈、苏轼、杨万里、刘克庄等著名文学家的品题赋咏,至今留下包括唐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宋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在内计唐碑1通、宋碑11通;第二,留下不止一件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并至少一个流传久远的文学掌故;第三,具有见证和体现广州通海放洋之外向性的海洋文化内涵;第四,具有一定的观赏性(或者说一定的审美价值);第五,在古今游人(或读者)中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⑥第六,在遭到自然或者人为的毁损之后,仍具有重建的必要,故历史上南海神庙(包括浴日亭)多次重建(包括扩建)。
[注 释]
①(明)张诩《浴日亭》诗的题注:“在南海庙右,小山屹立,前瞰大海,构亭其上,宋苏子瞻有诗”,现今亭中立有一方《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作为纪念。
②周笃文《宋百家词选》认为李昂英《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可与柳永西湖之词、东坡赤壁之咏,鼎足而三”。
③在今南海神庙门外章丘岗上的浴日亭内,有苏轼南海浴日亭诗碑(高1.54 米、宽0.84 米)。原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碎,寻回重拼。据清人翁方纲《粤东金石略》记载其时此碑下半部已略损,故碑之大小只约略而言。碑正书5行,第一行是“南海浴日亭”诗题。其余4行各14字,诗曰:(略)诗后题小字4行,行书:“右绍圣初元东坡先生谪惠州,过浴日所作也。壁间今存小刻,乃后人所书。□微有舛异。筠旧得此真迹于湘中,嘉定辛巳(1221)立夏,祇奉皇帝祝册来谒祠下,因出以寿诸石,□(以)补斯亭之阙,盖斯亭观览之伟,固自足以雄视海天,而此诗词翰之神,尤足以弹压千古,是可私其□□□无传也哉!清源留筠端父书。”同治《番禺县志·金石二》辑录有此诗碑碑文。
④转踏又称传踏,用于队舞表演、演唱故事,有关论述可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
⑤嵎夷何指,诸说不一,参见刘玉明《嵎夷考略》(《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王洪金《嵎夷考》(《东南文化》2008 年第1 期)、刘凤鸣《嵎夷、旸谷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6卷第2辑,2011年)。
⑥仅以唐宋碑刻为言,其影响可从元人王按弹(溥化)《奉命修理南海王祠偶成一律以纪岁月》“数行石篆忆昌黎”,明人薛纲《浴日亭诗》“珍重坡翁诗刻在,日争光彩水争雄”,清人孟邵《登浴日亭诗》“大苏当日留题处,老眼摩挲幸一看”,裘行简《承祭南海庙礼成述事》“韩碑苏碑字斑驳”“名文名笔罗文章”,黄河澂《南海神祠》“地灵不共桑田变,剩有唐碑历数朝”,伊秉绶《登浴日亭次东坡韵》“摹罢唐碑挝汉鼓,几多余韵在人间”,晚清丘逢甲《波罗谒南海神庙五十二韵》“上为浴日亭,破晓奇景臻。苏诗俨在石,驳落未尽泯”等诗句见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