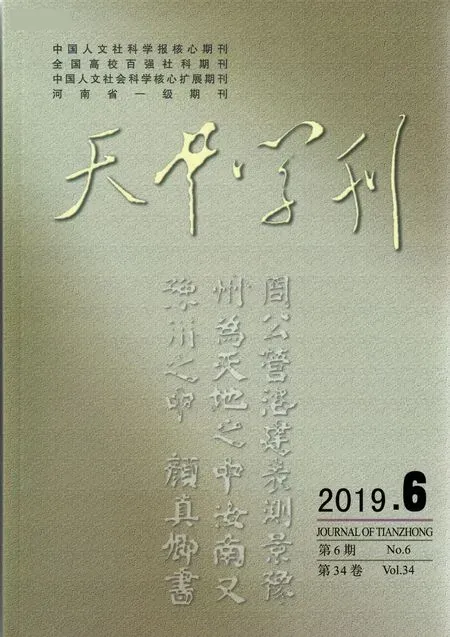《论语》“言教”思想的核心语义及其启示
2019-01-18朱荣英
朱荣英,谭 琳
(1.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2.许昌市魏都区实验学校,河南 许昌461000)
《论语》的言行观教育即“言教”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强调君子应力戒空谈浮言、非礼妄言,反对巧言令色、言过其实,主张慎言敏行、言信行果;认为当言则言、时而后言,懂得辟言、厉言,可从知言、慎言、辟言过渡到知仁、知命、安身,可从静修之“言道”过渡到不言之身教,做到言行合一、践言力行,如此等等[1]。本文诠释《论语》“言教”思想的微言大义,对破解当代语言学中言与仁、言与信、言与行、言与默等一系列难题,以精美的艺术语言把握存在之真谛,颇具理论意义。
一、《论语》“言教”思想的核心语义
(一)君子应“知言”“慎言”“厉言”“放言”
孔子认为,“与师言之道”,也就是“相师之道”(《论语》季氏第四十二),君子出言吐词要合乎言道,有序有礼,特别注重对弟子及大众进行言传身教、仁德感化。孔子主张君子立身处世要懂得“言教”礼数,具体要做到:“知命”“知礼”“知言”。如果不懂得对“命”和“礼”的默而知之、自我把握,当然就不能安身立命、建功立业;而如果不能“知言”,不善缄言,即不善于分辨和把握人们言谈的技巧与时机,就“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三)。为何凭“知言”就可“知人”呢?这是因为,“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从一句话中就可以弄明白这个人的智慧与否,因而“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第二十五)。君子之言,既要“言中伦,行中虑”,即言谈话语要遵循社会伦理,符合世道人心,也要懂得有时应该沉默寡言,“隐居放言”(《论语》微子第八),即过隐居生活,收敛自己,莫谈时事。真正的君子之言,不仅要谨言慎行而且要“厉言”“厉己”,话语严正而精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第九)君子讲话时,要庄重威严、和蔼可亲,言语深沉而富有魄力。当然,除遵循“言教”外,君子也要善行不言之教、述而不作。譬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第十九),上天以其风生水起、日夜循环的各种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降神圣之谕。对此,君子虽然言不能及,但应畏天畏命,“畏圣人之言”,而小人肆无忌惮,做不到这一点,常常“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八),失口猖言,遭人诟病。
(二)君子应“以言践仁”“行修言道”
因天人合一、言行不二,故而尽心、知性可知天,知言、践言而知人,行修言道、践仁知天。易言之,人在说话,话也在说人。所以《礼记》上说:“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2]君子要淡泊功名利禄,不语怪力乱神,不言稼穑捕猎等鄙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第一),少谈论财货与利禄,多赞颂天命与仁德。儒家认为“立言”即是“言仁”,“学仁”才可近道,而循序至精谓之学、受之于师谓之传、三省吾身谓之悟,此三者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言教”之本[3]。如何“言仁”“学仁”呢?言在利仁、其言若拙,言行一致、质朴无华。相反,若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则“鲜矣仁”(《论语》学而第三);若心口不一、空谈浮言,则违于仁。孔子一向耻巧言、倡讷言,认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第二十五)。对此朱熹注曰,君子传习仁道、讲究“言教”,应力戒以言代行、妄滕口说,应“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4]。若“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第十四),不假思索、直言不讳,就会远离仁德;君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第十三),不学习诗词礼法,就不要空发言论,而要言必有理,言必有据,出言有章,放言得体。
(三)君子应“言而有信”,以诚立身
孔子主张,君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第七),言语要恪守信用、一言九鼎,人而无信,岂能立身行事?君子之言,要“言善信”,信不足则言不行,贵言事随、希言取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主忠信”(《论语》学而第八),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第二十),谨遵“言教”、安仁利仁,这是孔门“言教”之要旨,也是修身立德之根本。对于察人、知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第十),言顾行、行顾言,言行不二,言扬行举。人“无信不立”,但“信”不是盲目的愚信,不是远离仁心的偏信,而是传习仁义的笃信,“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行恭敬诚信,即使是到了蛮貊荒野之地,仁道也行得通;“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第六),若言行相悖、自食其言,即使是在本乡本土也不能“践言”行世。而那种“言思忠,事思敬”(《论语》季氏第十),言语诚恳、嘉言善行,因“信近于义”,其“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十三)。朱熹批注说,“言可复”就是说其言不虚,言近于礼,能够以行“践言”,言亦可宗,远离耻辱,安身立命。从谨遵礼制之“言教”过渡到言之可复的身教,以身作则,言行相称,君子有所不言,言必切当,有所不为,为必志成。若是那些语言上的君子、行动上的矮子,势必一事无成。故而,君子要言出必行,以行践言,谈言微中,言芳行洁[6]。
(四)君子还要讷言敏行、言信行直
君子“言前定则不跲”,三思后行,敏学讷言则行事无不顺。衣食住行,无非是随遇而安、素位而行,要重视闻道乐行、闳言崇议,“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十四)。“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第二十四),不能口不择言、行不副言,要善于以礼义来匡正自己的言行,力行其言,说到做到,不能徒托空言、吞言咽理。君子还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第十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要言出必行,以行践言,勿轻易允诺、轻言寡信。孔子告诫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第二十二),以不能践言为耻,不能兑现其言,悖言乱辞、言与心违、言不顾行、言不及行,就会言多伤行,成为无稽之谈。所以,“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第二十七)。若“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第二十),大言不惭、言之过甚,必失信于人,处处为难。若身居高位,更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样就能够“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第十八)。要多闻多见、隐而不言、言信行果,就会减少过错。
(五)君子要“以言见礼”、德言容功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强调“以言见礼”,善于察言观行、恬淡少语,认为君子要善于“辟言”(《论语》宪问第三十七),躲避难听的话,因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乡党第二)。言谈举止,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要符合“言教”的规定,在不同的场合,方言矩行、情见乎言、合乎礼制。善言者,因人而言。如:在同乡人面前,言语要温和谦恭,表现出不善言谈的模样,“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在宗庙祭祀或者面见君臣时,要表现出既善于辞令,又健谈而慎言的样子,“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第一)。每当上朝,与同僚或下属讲话时,要温和持重、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理直气壮。“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地位较高的上级官员谈话,要和颜悦色、中正诚恳,“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在君主面前言语,要恭恭敬敬、谨慎小心,“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第二)。在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要脸色庄重,脚步加快,出言慎重,显得中气不足的样子,“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论语》乡党第四)。在进食或休息的时候不要言谈,“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第十)。而到了太庙,每时每刻都询问礼义以显诚敬之心,“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第二十一);在车中,也要按礼行事,不要高谈阔论,“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第二十六)。对旧的礼法,虽然非常熟悉,也要有一种求实态度,因资料有限、不足为凭,“吾能言之”而“不足征之”;若文献足够,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第九),等等。
(六)君子注重“时而后言”,言行相顾
孔子讲究言而有道、言而有礼,不能口无遮拦、胡言乱语,特别强调“时而后言”“义而后取”,认为若“时而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第十三),轮到自己发言,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们不会厌烦。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即使是天长日久,也要信守诺言、仁义当先。朋友之间的好言相劝,即使是肺腑之言,也要讲究言谈技巧,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论语》颜渊第二十三),若多口多舌、诡言浮说,就会自取其辱、徒增烦恼。要善于观察人言谈时的特殊表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论语》颜渊第二十),就会闻达天下、言行相符。孔子认为“君子之言”与“小人之言”有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论语》子路第二十八),良言近仁,言必有中,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第十七),闲言闲语,不着边际。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三),小人多言数穷,“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七),“词不达意”“过而不改”。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三)”,可与之言则言,不可与之言则不言,就“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八)。若“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六),不当言则言,就是浮躁;当言不言,就是隐言、失言;贸然而言,就是瞎了眼的失礼妄言。
(七)君子强调“名正言顺”,言默自如
对于言什么、如何言的问题,君子还要谨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治长第二十一)。有道时则尽显才智,一般人可做到;木讷装愚,是常人学不到的。君子懂得审时度势,言默自如,“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7]。唯君子能善行言道、言而有度,言与不言、言什么、如何言,皆中规中矩,合于礼法,深谙人间睿智、“言教”之妙。君子学以致用、言行合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若纸上谈兵、溢于言表,不切事理、言之无文,虽言之凿凿,又有何用呢?“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五)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应该“名正言顺”,认为这是从政之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事无成必然就会“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三)。所以,君子必须重视正名与正言,不能妄言非议,不能和盘托出,“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第三),君子需要一个值得称道的正当名分,更要把握一种立得住、讲得通、用得上的“言教”之道。怎样才能避免以言卖祸、言多必失?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第三)。君子之所以讲究言道,主张规训言谈、出言有法,是由于“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第十五)。这样说虽然有些言过其实,“言不可以若是”,但历史上的确频发因一言不当而导致兴衰的事。君子要言不烦,寡而实;小人巧言如簧,多而虚。君子之言,言而有宗,确能一言兴邦,一言济世;小人之言,僭而无征,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二、《论语》“言教”思想的当代启示
显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寻声定墨,立意运斤,这是《论语》“言教”思想的根本旨趣。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十一)语言只要能够传情达意、表达流畅、通晓易懂就行了,不必刻意追究文思奇巧与字句艳丽。若一味滞留于字句的凝练与润色上,刻意追求“拍案叫绝”“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样的效果,就会成为字句的奴隶,死于古人的句下,甚至会陷入“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窘境。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十八)文采与质朴必须妙合无垠,不能流于粗俗,也不能虚伪浮夸。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认为,“立文之本源”在于,“以文附质”“以质待文”,丧言不文、正言不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君子常言,未尝质也”,“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8]330。但是,语言之“达”,又有上下之分、雅俗之别。“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第二十三),积极向上、日进高明为“上达”,沉沦平庸、日究污言为“下达”。君子“上达”要通于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第十八)。“雅言”也就是“正言”,读诗书礼义,注先王经典,必正言其音,谨言表达。真正切当的、无倾向性的艺术语言,犹如“一种神话”[9],巧妙而艺术地运用语言,在匠心独运、反复斟酌下,就会达到文思神远,视通万里,字字珠玑,吐纳珠玉,言为心声,神与物游。语言呈现是“一种生命的形式”[10],要反复锤炼,“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8]338,务求“以一字为工”,这种“炼”“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11]111,妙笔生花,尽显生命之美,情动言外,隐含文理神韵。古人诗句中虽不言高远静闲、洒扫应对,而在文中却能以少总多、万取一收;对于景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事雕琢确能活灵活现、自然贴切,可谓文之精华,有隐有秀;言不在多,尽得风流。
《论语》倡导的“言教”,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著书立说,以言行世,“出‘言’如‘笔’,‘笔’为‘言’使”[8]413,因字生句,联句成章,积章成篇,连篇为著,表面看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实质上表达的却是人的内在神韵、风骨情志,揭示的是一种有深度的思想,语言就是思想表达本身。易言之,语言本身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思想,是能够被人直接感受到的思想。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2],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僵死的外在符号而是生命的深度即“灵魂的深度”[13]35。以理论的方式把握世界,须借助娴熟巧妙的语言艺术。理性语言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用语,是一种惊艳妙心的学术语言,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质与方法,最能体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黑格尔讲它是“诉之于心灵”[13]44并“经过心灵化”[13]49的东西。列宁说,决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14]。艺术地运用语言去驾驭思想,必须推敲文字、凝练语义。古人早就说过,“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改一字,界判人天”。而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艺术,更要重视合理表达那些突然涌现在意识内的东西,“惟陈言之务去”,摒弃一切文法理障,“不涉理路,不落言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才能在吟咏性情的微妙处,显得“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用最明确的科学术语来表达最真切的思想,确能深入揭示人的心理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学术语言的这种修辞方法“就是心灵的辩证法”。当然,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特别是语言上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学术语言所表达的都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东西,语言艺术说到底是生活的艺术,学术话语所表达的都是人民的思想,要做到“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属意为文、心与笔谋,趣幽旨深、内明外润,“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还要做到以“言教”荡涤世人浑浊之心,提振民族精神,净化人的心灵,开阔人的视界,“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于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15]。
现代西方哲学中有所谓“语言学转向”之说,论述的是语言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或存在论功能,强调语言作为思想交流的手段不仅能够指涉事物、传达思想,更能开显世界之本体与存在之真谛,甚至能够构造物质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意义。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就是语言所及的世界,世界就寓于语言之中,而人的存在意义也是语言所构造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唯有借助那种诗意的言说才能揭示人的本真之在。中国古代哲学也重视语言的工具妙用,从言与物、言与意、言与道的关系上看,语言不仅具有指涉作用,可“言之有物”“直言其事”,而且能够传达思想、言说道理,可“言以表意”“辞以达意”。但中西哲学也都谈到了语言的局限性问题。的的确确,语言有时也会束缚思想,窒息灵性,会抵达那种言不尽意、词不达意,不可说、不能说的地步。对那些在语言之外的、不可说、说不出的“非言之在”“不验之词”“不思之说”,西方哲学强调“沉默是金,语言是银”,认为能说的就要说清楚,不能说的就要悬置语言。唯有在语言的破碎处,隐秘的存在才真正开敞,唯有在语言休息时,真正的哲学才开始了言说。所以,语言只能说那些可说的,不可说的就不要说,“说不可说”非语言所能及,只能依靠非理性的临界体验即“畏、烦、死”的内在启示,或者借助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超越想象、诗意传达,或者干脆依靠神的召唤,才能聆听到那些神秘之在所传达的灵异之音等。西方的这种语言观与中国儒学“反巧言”“倡讷言”的“言教”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哲学也认为语言不是万能的,人们常常需要借助“非言”的物指、神谕、棒喝、敲击,去体悟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因“言不尽意”之故,才“立象尽意”“得意忘言”;由“正言若反”“大辩若讷”,才主张“寄言出意”“得意忘荃”;因“言语道断”“思维路绝”,才强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直指心体、默然心会。笔者认为,古代先贤忧之也深、言之也切,“文思极则奇,极深而研几”,那么言与非言的界限如何把握,“言”与“默”的矛盾该如何处置,如何“以意新而得巧,凭理趣而显奇”[16]?细究《论语》关于“言教”思想的核心要义,对破解这一难题或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