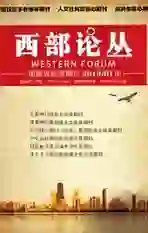对专利默示许可制度的略微思考
2019-01-17谢嘉利
摘 要:专利领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会推升交易成本,破坏利益平衡,导致司法工具化的倾向,法律必须对此加以回应。由此,与传统利益平衡机制相比更具灵活性的默示许可制度应运而生。在技术标准、产品销售、先前使用等多种情形中,机会主义行为广泛存在,而默示许可制度也都能提供良好的应对。借鉴合同法中的默示条款规则,将默示许可分为事实上的默示许可、习惯上的默示许可和法定的默示许可将对司法实践更具指导作用。我国已经具备了默示许可制度适用的法律前提,应在时机成熟时将其上升为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关键词:机会主义行为 专利默示许可 专利技术标准
一、专利领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与默示许可制度
目前,我国专利法中已经存在许多利益平衡机制。它们以侵权抗辩为代表,往往更多地侧重于实体权利义务的静态平衡,而缺乏对知识产权行使过程的动态关照。灵活的默示许可制度正是动态平衡机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知识产权制度面对很多实践中的尴尬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立法上还没有正式的默示许可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对默示许可的主张和承认。[1]
专利默示许可,也称隐含许可,是相对于以书面等形式确立的明示许可而言的,源生于合同法中的默示条款规则。有学者认为,专利默示许可是指专利权人以其非明确许可的默示行为,让被控侵权人(专利使用人)产生了允许使用其专利的合理信赖,从而成立的专利许可形态。[2]但笔者认为,这一表述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之处:第一,专利默示许可的主体不只是专利权人,还有可能是专利独占实施人、排他实施人等利害关系人;第二,“合理信赖”过于主观化且难以举证,更为重要的是,默示许可制度之所以成为必要,不仅是因为交易相对人产生了抽象的主观信赖,更在于其已经投入了一定的沉淀成本,形成了信赖利益。因此,本文认为,专利默示许可应该是指:基于事实、习惯或法律的规定,专利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外观上不作为的行为让专利实施人产生了专利许可的合理信赖,并产生了信赖利益,从而从法律上推定专利许可成立的专利许可形态。
上述使专利实施人产生合理信赖和信赖利益的不作为,可以称之为机会主义行为,是默示许可制度产生的经济动因。机会主义行为是新制度经济学上的概念,指当事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从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且不顾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行为是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实施的偷懒、欺骗、误导等行为。[3]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基础在于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总是以最低的花费和成本追求最高的收益与回报。[4]这就解釋了人们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与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不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完全洞悉而获得所有信息,这就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留下了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可能利用某种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优势,向对方隐瞒或者虚构事实,或者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这种情形在专利领域时常发生,比如,专利权人在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隐瞒专利权的存在从而诱使技术标准的潜在实施者为实施标准而投入大量沉淀成本,从而在后续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等情形。
相对于有形财产的交易而言,专利许可交易存在标的无形性、价值变动性、权利交叉性等特点,使得人的理性有限程度更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也大大增加。相比于《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的侵权抗辩和强制许可制度,默示许可制度具有灵活和有偿的特点,既能较好的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又可保证权利人的技术贡献所应得的对价,面对情形多变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独立的价值。
二、几种典型的专利机会主义行为与默示许可制度的应对
(一)围绕技术标准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默示许可
在进行专利许可时,专利权人的技术会面临其他智力成果的竞争,因此将自己的专利技术纳入作为公共产品的技术标准中去,会使专利权人更容易取得竞争优势,甚至获得市场独占地位。在这个过程前后,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专利权人有可能不披露或不充分披露其专利,以使该技术获得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从而被纳入标准之中,后又在他人实施该标准时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或在他人为实施该标准投入了一定的交易专用性资产后,[5]利用对方退出的巨大成本而获得优势谈判地位。这些行为会使专利权人获得远超出其技术贡献的经济利益,且扰乱市场的合理预期。若专利技术构成标准必要专利,这些行为往往还会变本加厉。
对此,基本所有的标准化组织都会有明示的规定或默示的习惯,规定其成员有义务披露知识产权。[6]这些行业惯例或交易习惯会成为默示许可认定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在美国,未披露而进入标准的专利会受默示许可的限制。美国法院也会在对默示许可的具体内容进行认定时,对由于技术和由于标准所带来的市场利益进行区分。[7]在Rambus案中,[8]法院认为,标准制定组织JEDEC在争议标准的说明中就指出,制定该标准的重要宗旨是兼容性。因此该标准带来的产品需求中,部分可能是因为Rambus专利所带来的内存速度上的提高,也必然存在部分需求是因为标准的兼容性而产生,对此,Rambus不应获取其所产生的利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第4号复函”称:“鉴于目前我国标准制定机关尚未建立有关标准中专利信息的公开披露及使用制度的实际情况,专利权人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或者经其同意,将专利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视为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在实施标准的同时实施该专利。”可见,对于围绕专利技术标准而产生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默示许可能够提供有效的应对,也是国际社会和我国均已采用的方法。
(二)围绕产品销售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默示许可
有时,专利权人并不销售其专利产品,而是销售该产品的零部件或半成品,这些零部件或半成品只能用于组装或制造其专利产品,并无其他任务用途,之后,专利权人又以购买者制造或组装其专利产品为由主张专利侵权。此种情形下,应当认定专利权人和购买者之间存在默示许可。
有时,将上述零部件或半成品组装或制造为专利产品的过程,还可能涉及到专利权人的专利方法,此时也应当认定存在专利方法的默示许可。在1942年Univis Lens Co.案中,[9] 专利权人Univis Lens公司就一种眼镜镜片及其制造方法享有多项专利,但其只制造该眼镜镜片的半成品(镜片毛片)并投入市场,购买的眼镜销售商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制作出最终的眼镜镜片(此制作过程会涉及Univis Lens公司的专利方法),Univis Lens公司据此主张专利侵权。审理该案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镜片毛片只能用于涉案专利的实施,而不具备独立的功能,因此,“销售镜片行为本身就同时构成镜片财产权的转移,以及许可买受人完成磨制镜片的最后步骤”,从而授予了专利方法的默示许可。
在DVD播放设备专利侵权事件中,我国许多生产企业指出,其制造的DVD装置的核心部件(如专用芯片)均从国外合法购买,并且是专为制造DVD装置而设计、制造的。笔者认为,此时专利权人销售该核心部件的行为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允许下游企业使用这些部件组装DVD整机,从而实施该专利的默示许可。这样的认定有利于维护专利交易的合理秩序,对于在国际专利许可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而言,更是尤为必要的。
(三)围绕先前使用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默示许可
如果专利权人先前存在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比如指导、推荐或默许他人实施其专利,其后又据此主张收取使用费或专利侵权的,专利实施者也有可能被认定已经获得了默示许可。在Wang Labs案中,[10]原告Wang Labs拥有一种内存模块SIMMs (Single In- line Memory Modules)的专利权。1983年12月,原告与被告三菱公司接触,并在隐瞒专利存在的前提下向其提供该技术产品的设计图纸、样品和其他细节,一再建议被告采用SIMMs技术。其后6年,原告又向法院起诉被告构成专利侵权。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被告已经获得了原告的无需支付使用费的默示许可。可以想见,若被告在谈判过程中即知晓该技术的专利状况,则有可能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不会采用该技术。若法院支持原告主张,势必会使类似情形中的交易相对人投入大量成本进行专利检索,而默示许可则解决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
三、专利默示许可规则的构建
上文对专利默示许可发生的情形进行了讨论,但构建系统的默示许可规则体系,可能会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司法实践更加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借鉴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规则,将专利默示许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事实上的专利默示许可
这也是合同法上默示条款规则的最早形态,要求法官在意思自治的范围内,对当事人本身的意思进行合理的推断,以弥补先前合同的漏洞。因此,这种默示许可以当事人已经具有明示而确定的交易关系为前提,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己经有专利产品销售合同、专利产品收购合同、专利许可合同、专利实施合作协议等情形,在此基础上根据合同目的和性质补充合同的内容。
此外,美国最早引入专利默示许可的案件——McClurg v. Kingsland案中确立的雇主“商业权”规则,也可放在这种类型中理解。[11]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对于专利权人作为雇员在受雇期间获得专利权的技术,作为雇主的企业应该可以通过默示许可来取得使用权。这其实是基于默示许可对雇佣合同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二)习惯上的专利默示许可
这是指根据交易习惯、行业惯例而推定的默示许可。专利许可的当事人对这些习惯具有较强的依赖和明确的预期,并且通常会依照这些规则行事。此类默示许可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尚未形成特别的交易关系,但由于属于共同的行业并且有达成交易的实质可能性的情形。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该类交易习惯的存在,并且证明这种习惯是众所周知的、固定的、合理的,且不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即具有公认性、固定性与合法性。[12]
在机会主义行为比较严重的技术标准制定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当数量的行业惯例,可用以认定默示许可的存在。包括ISO、IEC在内的国际性标准化组织以及众多的国内标准化组织都制定了自身的知识产权政策,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披露政策、知识产权谈判和评估政策、知识产权许可政策等。[13]如果标准化组织成员违反了该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在组织内部可能面临所参与的标准被搁置等后果,在法律上则可能由法院认定其专利已经颁发了默示许可。
(三)法定的专利默示许可
即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给予当事人实施知识产权的默示许可,而无需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行探究。此类默示许可适用于当事人之间既没有明示合同约束,也没有行业惯例或者交易习惯援用的情形,往往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而由法律直接确定。
法定默示许可与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是有区别的。其区别主要在于法定默示許可可为当事人的明示意思表示所推翻,从而更具有灵活性。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并非都是严格意义的法定许可,其中几种或称为法定默示许可更为合适,因为可以被著作权人的声明所推翻。[14]强调法定许可和法定默示许可的区别是有意义的。正是由于2012年3月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第一稿)将原来规定的对教科书和录音制品的法定默示许可修改为法定许可,压缩了法定默示许可的适用空间,有严重损害权利人利益的嫌疑,才会引起音乐产业界的强烈反弹。
事实上,一味扩展强制许可或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两种制度极有可能与权利人的意志完全相背,使其合理收益期望无法得到保证,从而引发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的适用应该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更加具有灵活优势的默示许可制度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注释:
[1]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朝阳兴诺公司按照建设部颁发的行业标准(复合载体夯扩桩设计规程)设计、施工而实施标准中专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专利权问题的函》([2008]民三他字第4号,本文简称为“第4号复函”。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默示许可的案例可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主编:《知识产权诉讼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2] 参见袁真富:《基于侵权抗辩之专利默示许可探究》,《法学》2010年第12期,第109页。
[3] See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Free Press, 1975:51.
[4] 参见张乃根:《法与经济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5] 交易专用性资产,即transaction-specific assets。资产“专用性”是指耐用性实物资本或者人力资本投入某一特定交易关系当中而被锁定的特性及其程度。一旦交易关系无法建立或者维系,投资于专用性资产的当事人所花费的转化成本或者推出成本是巨大的。同前注6。
[6] 参见赵启衫:《标准化组织专利政策反垄断审查要点剖析——IEEE新专利政策及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审查意见介评 》,《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0期,第53页。
[7] 参见刘强:《技术标准专利许可中的合理非歧视原则》,《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27页。
[8] Rambus Inc. v. F.T.C., 522F. 3d 456(D.C.Cir.2008).
[9]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316 U.S.241 (1942).
[10] Wang Labs v. Mitsubishi Electronics of America, Inc. and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103 F.3d 1571,41 U.S.P.Q.2d 1263(Fed Cir.1997).
[11] 参见[美]德拉特尔:《知识产权许可》,王春燕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2] 参见杨圣坤:《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制度研究》,《北方法学》2010年底2期,第132页。
[13] 参见刘强、金陈力:《机会主义行为与知识产权默示许可研究》,《知识产权》2014年第7期,第59頁。
[14] 本文认为,只有《著作权法》第43条第2款和第44条规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或者制品许可,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的使用特定作品制作课件许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定许可,而《著作权法》第23条、第33条第2款规定、第40条第3款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的教科书使用许可、报刊转载或者摘编许可、录音制作者使用许可和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许可实质上属于法定的默示许可。
作者简介:谢嘉利,1994年12月,女,汉,浙江省温州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