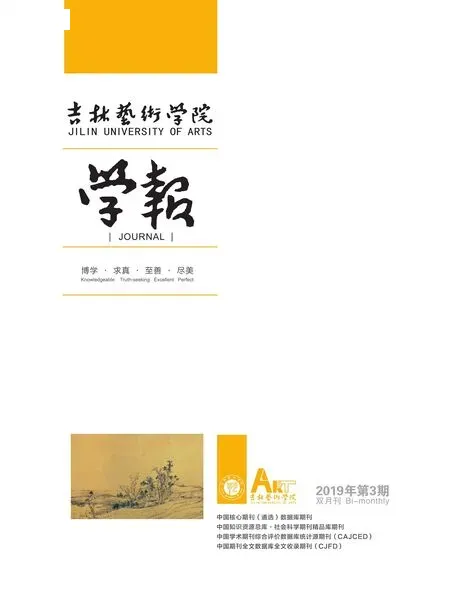书画篆刻与石雕艺术的表现技法
2019-01-15毛国典
毛国典
(江西省文联,江西 南昌,330046)
一、书法篆刻艺术的审美是石刻创作的基础
书法艺术的审美是书法字体石雕表现技法的基础和根本所在。何谓书法的审美?概括地讲即是汉字的结构、文字构成的法则、各种直线和曲线的穿插与组合、文字结构的对称与均衡、中轴线、里紧外松等。譬如在画廊、旅游景点等地方所见的即便是用毛笔进行书写,但其本质却与书法大相径庭。很多人都将书法艺术与毛笔字两个概念相混淆,这是一种缺乏书法审美和定位的表现。只有经过专业的书法训练或系统学习过书法专业才能真正地理解书法艺术。书法和书写毛笔字的共同之处在于其都是汉字,不同之处则在于书法强调的是对古人的传承。通俗地讲,毛笔字只是单纯地用毛笔写汉字,并不涉及传承和出处,更不存在艺术定位。专业领域的人懂得何谓行画行字,外行人则注重的是字体的花俏和速度。专业人士注重的是对字体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所谓“看门道”,并非仅仅停留在字体的表层之上。例如草书、行草书写的速度一般比正书、楷书、隶书和篆书快,如若没有传统和出处仅仅是执笔画圈,一味地追求速度,则很难达到行草书的艺术标准,故而书法的传统和审美尤为重要。
王羲之擅长多种字体,其中《圣教序》和《兰亭序》行书最为引人注目,堪称古代行书审美中的经典和标准,他的代表作品《圣教序》和《兰亭序》,虽均为本人所写,书法效果却有所不同。《圣教序》汇编了王羲之最秀美行书的精华,天质自然,温润典雅。《兰亭序》则是王羲之在兰亭雅集之际一气呵成的作品,通篇字体刚柔相济、俊逸遒劲,充满着激情,气韵生动,旁人难以匹及,故而王羲之的行书一直被引为经典,流传至今。
“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的行书如画工的笔画一般,匠心独运,将唯美主义达到一种极致的程度,点划、结字和用笔都极为精准,故被誉为行书的标准之作。因此若要研习行书,则可将“二王”的行书作为入门的基础,他们的行书从容娴和,又毫无造作的痕迹,起笔、运笔、收笔,直线和弧线均是里紧外松。领会了“二王”的书法,也就知晓了汉字的结构和运笔的法则。先将“二王”作为行书的源头进行临摹,再跨越到其他大家的行书,如米芾、黄庭坚、苏东坡等行书,也就比较容易了。
谈及楷书这种书法审美,很多人都以颜、柳、欧、赵为代表。即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赵孟頫,这实则为一种误解,楷书还包括南北朝时期的各种魏碑、墓志铭等。实际上,除行书、草书,一切字体均应称之为正书,其包含楷书、隶书、篆书三大类。例如颜真卿的楷书是极为华丽的,圆满而有劲骨,雄健的笔力,沉稳的气势,外柔内刚,圆而有力,开创了唐代的楷书典范,并创立了自己的书体,即“颜体”。颜真卿的楷书不像欧阳询、柳公权和赵孟頫的楷书,其笔法精准,同时对后人又留存发挥的余地,创作发挥后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风格,这也是颜真卿楷书的精华所在。
唐代是书法法度格外严谨的朝代,想把唐楷创作出自己的风格比较难,所以取法唐楷参加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国展相对魏碑入选比例较低,近十年以来,魏楷在中国书法论坛和展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审美与唐代有所不同,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分为拙和秀两大类,比如《龙门二十品》《爨宝子》《裴谭墓志》《张猛龙碑》等,这一时期无论拙和秀,笔划均以方笔为主,是一个人书丹,另一个人镌刻,刻工为了省时方便,把圆笔画刻为方笔,比如各种点和横竖的转折,所以形成了独特的南北朝楷书风格的符号。魏楷的书法审美也应合了当代人的书法审美取向,这也是当前楷书取法和创作的主流原因。同时,所有南北朝时期的魏碑都带有很强的“工匠味”,在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中应当引起注意,加以取舍。
简帛书中的每一个横划都以燕尾的形式出锋,早期的简牍帛书,所书者都是一些当地或部队官兵、文书所写,书写者的水平有高有低,其作用只是实用,把语言记录下来。这一时期的书法还不具备“审美功能”,只是当时的书写习惯。一手拿简,一手拿笔书写,抄手水平低,书写水平就低,抄手的文化素养高,书写就很熟练,相对书写水平就会高。并形成了自己的书写习惯,汉字的造型就会有一定的规律。比如早期的简帛字形偏长,如楚简,然后从长方形渐渐演变为扁方形,并且每一笔的横画均以“燕尾”的形式出锋,这种汉字的书写方法,正是从无审美、无规律、无装饰到有审美、有规律、有装饰的演变,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居延汉简中《相利善剑》,已具备了东汉时期隶书的所有特征和书写符号,西汉的武威仪礼简很有规律的扁方形字,如湖南马王堆帛书亦是如此。《皇帝经》《周易》里的字形均接近于正方,这便是当时书法的审美。另外,简帛书中的文字内容基本上都是于占卜、神灵、医药、叙事、军事战争的记载为主体,当今很多书法爱好者将规范的简帛当作范例进行临摹书写。当然,也有许多简帛不易作范本临摹,但却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简帛到汉隶,从多个燕尾蜕变至一个燕尾。字的书写方法改变了,尽管随着朝代的变迁,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也越来越进步,书法字体形式不断变化,直至清代及民国,书法审美的核心仍始终是传统和唯美。
如何将书法的审美与现实结合?首先,要开阔眼界,多看、多研究、多欣赏,有能力区分和领会作品背后传承的内涵,做到有传承、有出处,进而达到文字的唯美和典雅。提升对书法的审美,将书法的审美与石雕艺术融合,只有正确领会了书法字体的审美,才能雕刻出高水平的石雕作品,若仅仅应用工匠式的石刻,而对书法审美一无所知,必定会妨碍后期在石雕上的创作,使作品难以实现书法艺术与石雕艺术的高度统一,更不能走到一定的高度。
其次,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篆刻艺术有所研究,因为篆刻与石刻在技法和功能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篆刻,一般泛指汉印。汉印是指东汉之前的印,包括古玺印、秦印、汉玉印和将军印等,统称为汉印,它不单指汉代,也同时包含了汉代以前的印章。印章是被雕刻而成的,并非书写形成。与石雕和石刻的关系格外密切,可以一人书写,一人石刻,也可以一人书写,请人代刻。汉印又分官印和私印,从材质上分,有玉印、铜印、封泥印等,既可见于民间,也被王朝所用。王朝官方的印章是指政府部门或者部队行军兵戈中使用的印章。民间的汉印主要代表信物,用绳子穿挂起来束在腰间。汉玉印较硬,需借助工具才能够进行作业,而早期的古玺印和铜印均可直接雕刻或铸造出来。
还要提高石刻技艺水平,符合大众审美品位。古玺印的风格很明显,是直接应用单刀或双刀、 或单双刀并用进行雕刻的。古玺印以田字格、日字格或用边栏为固定模式,大小自然,笔划流畅。正因为古代的汉印、古玺印都天然质朴,现如今大多数石雕创作者都借鉴篆刻用刀的技法进行石雕创作。或工稳或写意,形成一种纯朴的石雕之美。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少字也可以多字进行创作。
古代时期的印章是具有实用性的,并非是以一种艺术品的形式出现。汉印基本是以双刀为主,汉印字法、章法便于安排,这也是当前很多印人用汉玉印或汉印做切入点进行篆刻艺术创作的缘由,朱文印印家取法古玺和封泥印为多。古玺印耗费精力较大,若用刀不流畅,弧线刀法不均匀,横线竖线刻不直,便难以再进行深度雕刻。从先秦古玺印到汉印,印章审美无论从书法的角度还是篆刻的角度,都在逐步定型,蜕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并兼具很强的装饰性和规律性。
石刻必须要注重中国的大众审美,大众审美就要以具象写实和唯美为主,这即是中国人的审美观,要在艺术创作中借鉴传统唯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因此,书法、美术界有成就的大家作品毋庸置疑地被列为佳品,而广为流传并被大众所接受,这其实还是书法一个审美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升自身的审美艺术水平,避免低俗和没有出处、没有传承的作品。要大量阅读传统经典之作,开阔眼界,方能辨别和提高自己的艺术品格和审美标准。
二、以书法的临摹实践来提升创作标准
书法实践可区分为两大类,第一是“临”,第二是“创”。“临”即指临摹,“创”则为创作。首先,对临摹要有定位,即一个人要先写一种书体,将一本法帖作为起点。首先做到:一家一帖,经典精临。绘画亦是如此,即从一家入手,学一家要似一家。
其次,把握临摹书体的规律。在临摹的过程中,无论是点划或是偏旁,都要像复印机一样,书法才能写到最好,对于以后临摹其他书体和碑帖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学习山水画。山是由许多小石块小山头为基础,堆集在一起后形成的高山,左右放置,可为低山、丘陵。临摹的核心在于找规律、找共性,学习并掌握古人的技法又能运用到书画创作和石刻艺术中去。
在临习的过程中要把点划拆开来学习,横、竖、撇、点、捺、竖弯钩、斜钩,即为单笔划,此时不要着急临帖,而是需要将单笔划精准的背记下来。接着则是把各种偏旁,即三点水、示字旁、火字旁、耳朵旁、木字旁等,从字体中脱离出来,专门背临单偏旁,当二者娴熟之后。第三步即合体字,将单笔划和偏旁组合在一起组成汉字,比如田加心,合为一字:“思”。“想”字便是“木”加“目”合成相,“相”加“心”,合为“想”,即组合字。组合需寻规律,里紧外松,字体中部要紧凑,撇、捺、长横、斜钩等部分则向左右扩张。临摹的步骤第一为点划,第二为偏旁,第三则为合体字。依据这样的顺序,效果会非常好,进步会非常的快。临帖最忌投机取巧,不专一,经常换帖。这样永远无法提升书法的实践水准。无论是临帖还是临画,目的均不在于因临摹而临摹,而是要传承古代大家的技法,立于巨人的肩膀之上,运用技法进行创作,从而获得学习书法和绘画的技法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是最终目的。
书法篆刻和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三者均源于传承。是一种具象写实的实践活动,故若将其与石刻融合到一起,临摹必将是书法篆刻和绘画实践的第一大要。
书法实践的第二大类是创作。创作是指在临摹的基础之上书写作品。比如节选一句古诗词,或临摹一则名言警句,书写文字性的内容便是创作了。创作是将古代的技法引用过来,领悟其精髓,不能改变字形与写法。而绘画与书法的差别则在于,当驾驭了古代的技法以后,绘画中山的形态、树的样式均可依据作者的创作意愿进行变化。无论山峰或大或小,绘画的技法均是大同小异的,形态更是可以随意修改。但书法的形状是无法更改的,技法更不能改变,所以书法很难任意发挥,而绘画却有着很大的创造空间。山、树形态均可变,唯技法不能变。,可以说,书法是在古人一家一帖的基础上借鉴与之相近的法帖互融,再把汉字重新组合,这便是传承。
学习汉碑《张迁碑》钝拙,《礼器碑》《曹全碑》便是较为清秀柔美的字体。无论秀美或钝拙,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字势拙有拙美、秀有秀美,风格不一,审美亦不同。要求研习者遵循各个朝代的书法字体风格,传承各种风格的审美。譬如敦煌写经来源于民间,而文征明、赵孟頫则并非出身于民间,再加之文征明、赵孟頫的主业是绘画,在绘画领域颇有建树。他们把绘画的技法和绘画的理念,具象写实的能力来进行书法的学习和创作,因此他们的书画作品皆以唯美为原则,千百年来唯美风格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当代人也同样取法文和赵是有原因的。而古代人的综合艺术修养,当代人是难以企及的,古代民间高手的作品没有机会存世,所见者甚少。而宫廷的职业画工和士大夫们的作品会有更多的渠道、更好的条件被广泛流传。
三、石雕艺术的雕刻技法和表现形式
石雕的技法可称之为刀法,即单刀、双刀。这种技法与篆刻和刻字的刀法联系较为紧密,但不同点在于材质和形态。单刀较为质朴,既自然又迅速。而双刀较为简便和工稳,上下左右各一刀,既能刻印章,又能刻顽石,故建议石雕初学者先应用普通的材质石头进行研习。对于书法来讲,横线、竖线以及各种直线和弧线,要确保单刀和双刀都熟练和精通,这是一种技法的训练,要多做实践和反复练习,需娴熟运用雕刻规律,直线能刻得笔直,撇画的弧线、捺画的弧线,要雕刻均匀、流畅,而不能显现出死结或用刀的失误,更不可出现跑刀,要如流水线一般细腻匀称。当技法娴熟后,再进行书写。当单刀、双刀均可刻字后再进行创作,若无十分把握,则不可在石料上雕刻,因为在石头镌刻,一旦损坏后很难进行修复和补救,只有具备娴熟的技法后,才可将双刀、单刀融会贯通,届时刻字自然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了。对于石刻,众人喜好各异,有人喜以书法为本体,有人喜以绘画为本体,有人欣赏浅刻,有人欣赏深刻。有人进行书法创作,能够将书法的技法运用娴熟,尤其是名家书法作品,能够将其惟妙惟肖地还原到石料上,让业内一看便知是某名家书法。实际上,做到这点并不难,归根结底终究是单刀和双刀技法能否娴熟应用的问题,其主要依靠作者技法的娴熟程度,因此,书法的石刻技法是简单易行的。
但以绘画为主体的石刻就较为繁杂了,譬如山水画,其可呈现出众多故事和题材。如树、山、云、水、草、田间山水中的人物及配景等,是灵动活泼、变化多样的。当雕刻的主体是人物时,可将山水作为配景,扩大人物比例,缩小山水比例。当雕刻的主体是山水时,则可将人物和房屋作为配景,从而体现错落有致的主次概念。雕刻风景或山水比较复杂。以树叶为例,传统树叶的画法为点叶、有夹叶画法,即将一片树叶用两笔勾勒,似工笔绘画一般。点叶的画法众多,熟记几种画法已足够。比如松叶的画法就应用了扇面一样的技法,弧线组合,再如绘制菊花叶,有“介字法”和“个子法”,无论向上亦或是向下均是一种方法,一笔绘制出一朵花瓣,但若应用夹叶画法则是两笔画出一个树叶。花瓣与树叶实则为同一方法,故而把各种树叶的画法造型能够很娴熟的掌握后就能运用自如。在石材上刻画图像,因石头上无法显现出水墨的层次感,故而要刻出黑白灰是十分困难的,不仅要将所雕刻形象的形态把握准确,更要将其大小掌握得精准,将平面的石刻体现出一种三维立体的空间感,由远及近的透视关系,利用视觉的错觉将平面转变为立体,即应用近大远小,近高远低的透视规律将平面的形态刻画出高、宽、深的立体画面。比如我们在观看电视时,能够感受到画面有前后的空间方位感,这是依靠透视关系由远及近来表现的。在进行石刻时,这种前后关系的表达可以将前面表现的内容或物体适当刻得肯定、具体、细致一些,后面表现的内容则要适当刻得概括、省略一些,用线要细一些。近大远小、视平线以下的物体越近越低,越远越高,视平线以上的物体越近越高,越远越低,这便是表现景物前后空间感的方法,通过透视元素表达物体的空间错落。
除此之外,也可采用版画技法或平面构成的技法,将线条与点密集地组合在一起,即通过大量的点,将点连成面连接后呈现出画面,再用曲线和直线分割。平面设计的技法也是应用点、线、面来呈现画面。点与线的长短、大小、曲直、交叉、疏密等技法,在石刻创作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一块石刻的效果、价值,除出自名家高手之外,点与线条组合成的画面质量也决定着一块石刻的价值,所以这些点线的基本要素在石刻创作中应用非常广泛,若点和线不存在,就无法构成基本的画面。石刻中的点是应用刀一点点雕刻出来的,很多密集的点汇集后就形成了“白”和“灰”两个层次,在靠近和紧贴前面的山头处不点,一点不刻则称之为“黑”。比如在进行山水画的雕刻时,山头上方可用刀尖点出很密集的点呈现为白,不用雕刻,只用外轮廓线把物体的外形表现出来即可,故应用点、线、面雕刻黑与白,即实与虚。点的密集程度是依靠点去呈现画面,尽量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点,用点组合“面”均匀一致、精秀美观,用线刻划外轮廓,才能雕刻出完整的画面。
要想表现物体的“高、宽、深”,即三度空间,就要理解绘画的基本透视规律,即近大远小,近高远低,还要注意画面的黑、白、灰,一幅完美的国画作品画面必须有最深的颜色,最浅的颜色(可以留白),介于黑白之间的色彩叫灰色,画面没有黑白灰三大色调空间感就会差,还要注意画面的黑白对比,即有的地方一定要用深色来衬托,凡是留黑的地方就一定要用白衬托;凡留白的地方就一定要用黑来衬托,而黑白中间即是灰,这样画面的层次感才能强烈,石刻艺术的黑、白、灰也是如此。
根据市场或者藏家需要,以古代、近现代的书法作品或国画作品(包括山水、任务、花鸟)为创作素材,可以直接把古代的书画作品复制在要刻的石材上,也可以取古代绘画中的一个局部,或用毛笔把前人的作品直接写在或者画在石材上,再仔细镌刻,还原前人作品的原貌,这类复制古人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如果作者能够独立创作,把字和画直接写在或者画在石头上,再镌刻,这类原创性作品更有收藏价值。
石雕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汇集了书法、绘画、设计、审美和技法,不仅仅是单方面地进行绘画和雕刻,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对一件作品的价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石刻创作作品除书法、山水画之外,也不乏以花鸟题材进行创作,包括梅兰竹菊等,但梅兰竹菊的题材太大众化,偏俗,而山水则较为高雅。以人物为主体的石刻虽高雅,但雕刻难度也随之提升了,在石头上面进行人物雕刻,必须要确保人物比例头像五官的比例,非专业人员很难把控人物的比例、五官以及表情,因为石头的面积相对较小,若仅仅是进行人物头像的雕刻便不难,若是在人物创作的基础之上附以动作和场景,将增加石刻创作的难度,故石刻以山水居多,而山水画的刀法、技法与篆刻十分相近,均是采用单刀和双刀。一般情况下以双刀居多,但在雕刻过程中,不一定全部应用双刀,也不必完全采用单刀,要根据画面和用刀的需要,双刀、单刀二者并用。篆刻技法有双刀也有单刀,如作者单刀使用较为娴熟,则无需加用双刀。在进行石刻的过程中,后方的远景及物体的形状都应以细线勾刻,绝不可过粗,一旦失误再补救是极为困难的。是石刻的线条如印章一样,开始刻时,白线(把轮廓线挖掉),先刻细一些,朱线(轮廓线留出来,把轮廓线之外的挖掉),先刻粗一点,这样便于修改。因此,线条还是应该先细刻,再慢慢向外扩、变宽,这样不论石头的品质如何,都能够灵活运用。切记,画面远景的线一定要极为精细,因为远景一般都是概括的,浮雕山水的技法在于绘画的功底,在领悟绘画的基础上,一切便不难了。再有,石头要用巧色和自然的纹理,有时树干和山的形状,也可借助石头本身的裂纹和纹样。再者,许多石头本身有花纹,若经验丰富者则可将石头的自然纹理作为画面。譬如画山水,可以先用淡墨铺垫,后依照自然的深浅变化进行线条的勾勒,这便是自然的纹理和形态,而山的形态本身并无标准之论,大小均可,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有高山、有丘陵。南方的丘陵比较多,北方直立的山比较多,均可应用形状来区分,而绘画技法大多一致,均是如此表现的。
雕刻完成后就是题款问题,可以落上作者的姓名,因印面小,宜用小刀为之。石刻上面的印是刻出来的,作者需要对篆刻的用字有一定的了解,作品无论是书画、陶瓷、紫砂或是石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钤盖印章作品才是完整的,若一个书法家的字不钤印,总会让人误认为作品是赝品,并不能说明书画家本人所作,且影响市场价值。因此,盖章是对作品完整性的一种呈现,而这种印章在古代和现代的表现也各有不同。例如唐代绘画有的无作者落款和钤印,是因为宫廷画家的任务是为皇帝或者皇族效劳,而为皇族效劳就是由皇帝和皇族们决定作品是进行人物创作还是风景创作。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创作中,作者仅仅充当工匠的角色,而不能够进行自我创作,作品不能表达作者的思想,故而部分作品是没有名字、没有提款,更没有年代,只能为佚名。特别是唐代时期和五代时期,很多作品只能通过后人的考证、历史的记录,才能推判作者是谁,如唐代王维的绘画,学术界直至如今仍未见一件真品,仅能通过历史和后人的记载推测王维的风格,再由专家经过文字的表述和记载,推测出与王维风格相似的作品,但这也仅限于推测,理论界颇有争议。特别针对于专门进行艺术品收藏的藏家和机构,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存在着名家作品与其他一般作者作品价值的不同,而古代作品即使没有落款,没有姓名,没有具体日期,也同样具有历史价值,根据朝代的先后,越久远历史价值越高,市场价格则更高。
书画、篆刻、石雕表现技法是一个宽泛的题目,需要以书画的审美和具体的实践为基础,在书写上进行“临”和“创”,再将石雕的表现技法熟练应用,融会贯通,作品格调高雅,熟练地掌握石刻的规律和技法,一件好的石刻作品才得以完美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