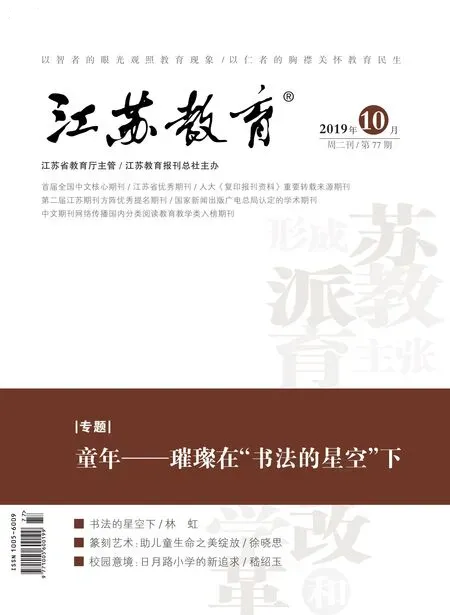“清人尚质”浅探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读后
2019-01-14俞建华
俞建华
康有为从1888 年腊月开始广购碑帖作资料的积累,到1889 年除夕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书论名著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也为“清人尚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乾隆年间的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一文中的观点尽管不很科学,但经他对尊碑进行有力鼓吹后,大大地启发了以后的一些书论家和书法家。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论书部分,就是在自己的实践上,尤其是在邓石如等人写碑成功的实践成果上,进一步开创了尊碑的风气。到了康有为,就在以往尊碑的基础上更充实和提高了对“碑学”的认识。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书法在美学上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书法新天地的勤奋探求。处于政治大变革前夜的晚清,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同样存在这个“变法”的课题。康有为就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书法的“变”是现实的需要,“变法”是不可逆转的书坛潮流以及求新的途径。
康有为认为,自有文字以来,甲骨、大小篆、八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无不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己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变,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文字为人们所用,就在于它有实际功用性,运用“便捷”。从“婉而通”的圆笔篆书变成“精而密”的方笔隶书是这样;从方严的楷书变成连绵的行草也是这样。实用,就是促使书体发展变化、促使书法艺术萌生的强大动力。
虽然汉字起源于绘画而成象形文字,但并没有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只是随着自身的演化规律,越来越减弱、消泯象形的痕迹,成为具有“意象”性的文字。这就为文字的美化奠定了先天的基础,也为中华民族拥有这独特的艺术开创了先决的条件。针对这个情况,康有为假设了论敌的观点:“或曰,书自结绳以前,民用虽篆草百变,立义皆同。由斯以谈,但取成形,令人可识。何事夸钟、卫,讲王、羊,经营点画之微,研悦笔札之丽。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中,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康有为回各道:“衣以掩体也,则短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观?食以果腹也,则糗藜足饫,何取珍馐之美?垣墙以蔽风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车以越山海,何以有几组之陆离?诗以言志,何事律则欲谐?文以载道,胡为辞则欲巧?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棊,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正是人们在求得温饱的物质基础上,才有求取精神享受的要求。求美,本来就是“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所以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儒家有一句者话:‘食、色,性也。’‘食’就是保持个体生命的经济基础,‘色’就是绵延种族生命的男女配合。艺术和美也最先见于食色。”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食”当然是物质基础,而“色”虽有绵延种族的功用,但在相当程度上更有满足人们感官需要的作用。这就孕育着对各种各样美的通求,也就是有思想意识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必然要灵化生活的“天理”。马克思说:“人还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朱光潜先生解释道:“人的生产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与美有联系,而美有美的规律。”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文字,就是按照它自身“美的规律”演化出书法艺术来的,而书法艺术又是按照自身“美的规律”发展得愈来愈兴旺。所以,康有为认识到:“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如:“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的钟鼎、籀字;“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的秦分(小篆);再使“碑体方扁,笔益茂密……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使当时的书体更加“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但还是要继续发展,“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综观书体的演化,用笔的进化,笔势的丰富,就形成了有几千年传统的书法艺术。
那么,清代书法的现状如何呢?康有为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他所处的正是北碑由“萌芽”而蓬勃发展的时代。面对以往的年代,康有为作了反思:由于康熙皇帝嗜爱董其昌书法、乾隆皇帝崇尚赵孟頫书法,使这两家成为当时朝野争唱的“帖学”时调,但书风日趋衰靡。继而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大盛,文人学者明哲保身,只在日益丰富的出土金石文物中证经引史而蔚成风气,借以免触文网。这样,由考古成果引到书法艺术上的探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自嘉庆、道光以后,帖学渐衰而碑学渐盛,但这时重视的还是唐碑。因为当时朝廷提倡写字要讲究规范,不能谬误。所以,点画妥帖、结体严密的欧阳询书体大受欢迎,继之,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亦被重视。然是馆阁体习气渐深,虽有家领导书坛,无复唐人雄深雅健之致。
只有当大量的北碑和南碑出土,在学术政制萌发维新之机的同时,书画界也积储了求新的力量。“咸、同之际”的书家被这些“隶楷错变,无体不备”的碑碣所倾倒。尤其是以“变法维新”为己任、深谙书道变化的康有为,在书坛上也走上“托古改制”“言古切今”的、以复古来创新的道路。“碑学”就这样进入了全盛时期。
康有为针对清代前期、中期“帖学”“唐碑”时期出现的流弊,指出“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中国的印刷术虽然最早彪炳于世,但在西洋近代印刷术未传入中国之前,古人的墨迹只能靠钩摹翻刻而流行。千余年来的屡翻屡刻,走样失神是必然之事。佳拓善本的追求成了书家一生的愿望。这样的物质基础自然成了书法发展的一大障碍。所以康有为又进一步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必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的确,与失神走样的阁帖、唐碑相比,未经摹拓、点画比较完好的南北碑,更便于临习者追摹精神的。
当然,康有为所以尊碑,主要还是时代审美观点的转变所致,“物极必反,天理固然”。自“晋人尚韵、唐人重法、宋人尚意”三个书法兴旺时期后,明人专尚气势形态,也不失为是对书法的贡献。而摆在清人面前的道路确已到山穷水尽。面对以僵化的观点学唐碑而成的馆阁体康有为不胜感叹:“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对唐碑的批评未免过分,但对当时的假唐碑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
康有为还以政治来作譬喻:“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在“时尚开新”的时代,书坛上的“人心趋变”“变”向何处呢?“隶楷谁能溯滥泉?”康有为认为必须从书法的源头本质处求取变法的力量和创新的营养。具体说来,就是取法唐碑以前的隋碑、南碑、魏碑与汉碑。
晋以后的南北朝碑版书风其实并不太受地域所限而大不相同。南碑如晋之《爨宝子》、梁之《瘗鹤铭》、陈之《赵和造像记》等,与北朝之碑一样都具有“隶楷错变”之美。所以康有为称之为:“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稀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但他对北碑中的魏碑更为推崇,认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峬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甚至提出“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可见偏爱之深。但他还是把南、北碑视作同一体系的,他归纳出:“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甜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的“十美”。其中“魄力雄强”“意态奇逸”“结构天成”确是南北碑胜过唐碑的地方,康有为这个见解是精辟的。
至于隋碑,康有为认为“风神疏朗,体格峻整”,有“大开唐风”之功。它本身能“得洞达之意”,是因为“隋世集六朝之余风也”的缘故。它与法度森严的唐碑相比较,尚多天真自然之趣。所以像《龙藏寺碑》这样的隋碑足可与魏碑中的《张猛龙碑》等同属“精品”之列。即使被康有为所肯定的少数唐碑,如《等慈寺碑》等,也是因为有“六朝遗意”“笔画丰厚古朴”“峻朴是魏法”“浑古有法”等原因。
从远古到明清,书法是遵循“古质而今妍”规律发展的。南朝虞龢就是这样认为,指出“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但“今妍”到明清出现的情况,促使康有为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尊碑的几条理由中就有“可以考隶楷之变”“可以考后世之源流”的目的。从魏上追,势必到汉,这“本汉”课题的提出也是必然的事了。
康有为从“真书之变中”敏感地注意到,汉魏之间书法“传变之速”在“上下百年间”进行得特别明显。从隶到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指出二王的成就,不光是“笔法之雄奇”“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学二王,都着眼于形态的妍丽,所以“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智过其师,始可传授”。对学《兰亭》不成而出现“平直如算子”的毛病,乃是“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当师其神理奇变,若学面貌,则如美伶候坐,虽面目充悦而语言无味”。这“意态奇变”“神理奇变”的关键在那里呢?康有为从王羲之的师承中发现,“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是研习李斯、曹喜、锺繇、梁鸽,蔡邕等泰汉名家的成果,所以能在初学卫夫人的基础上得“古朴”“奇变”之趣。再从学王的体系中观察,他认为“平原(颜真卿)得力处”在于汉隶《郙阁颂》的“体法茂密”。《裴将军诗》“其实乃以汉分之草,故多殊形异态”。另外如杨凝式学王羲之而得“奇宕”之致的原因,是杨能“变右军之面目”“以分作草”,所以能“神理自得”。康有为自负地说:“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绝世。”“本汉”,就是他们能“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
康有为把西汉时期意在篆隶之间的书体称为“分书”,把东汉时期波磔分明的书体称为“隶书”。自称“酷爱八分”,认为“朴茂雄逸,古气未漓”。而对于东汉桓、灵以后的“隶书”颇有微词:“巧而伤稚”“滋味殊薄”,连赫赫有名的《华山碑》也贬之为“实为下乗”。他把分、隶与楷书相比,则认为南北朝碑如“分书”,而唐碑就似“隶书”了。所以康有为“本汉”的实质就是崇尚“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以隶笔作缪篆,亦可附于西汉八分”以及“由篆变隶,隶多篆少之西汉分”。另外,还从十通留有书家姓名如寇谦之、王远等的南北碑中,认为不管用笔是方、是圆、或方圆互用,“皆源本分隶”。只有找到了这个“源头”,才能作出“抗旌晋宋,树垒魏齐”的成就来;所以才有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那样,通过“所师之古”后达到“神理奇变”的境界。
那么从北魏上溯两汉,最值得称道的书家是谁呢?康有为认为是三国曹魏的卫觊。他考证有名的《受禅表》不是钟繇或梁鹄所书,而是卫觊的手笔。赞扬此碑“鸱视虎顾,雄伟冠时”。卫觊的儿子卫璀,孙子卫恒、卫宣、卫庭以及玄孙女卫铄都是书坛名家。康有为还认为当时书坛上有一派书家师法钟繇“盛于南”,一派书家师法卫觊“盛于北”这样两大流派。而钟繇“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之故,尤其是“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故使张(怀瓘)、李(嗣真)续品,皆未及北宗。”康有为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南派”书圣王羲之也曾受卫家的启蒙,即王羲之第一个老师就是“北派”的卫夫人卫铄。所以他指出:“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结合南北亦可也。”
从这些分析推理中,康有为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南北碑才能救帖学、唐碑之弊,但还得上溯西汉以求“朴茂雄逸”的境界;就是南派帖学之祖的王羲之也曾得到过“北派”书法的好处。他认为在书法领域中知其源、清其本,才能使书法得到新生。
康有为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简要地提出“夫书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为冠冕”。就把“天然”提到首要的地位。清朝中期的书法,固然有“工夫”方画的问题,而更是“天然”方面的问题。“古质而今妍”的道路发到那时,愈“妍”而去“天然”愈远,因为造作过甚、法度化所形成的“妍”是没有生命力的,欲求“天然”之趣,还得返璞归真去力求“古质”。康 有 为“尊 碑”“本 汉”“传 卫”“宝 南”“备 魏”“取隋”“卑唐”无不都是圈绕这个课题展开论述的。
因此,康有为在大量出土碑版的优裕的客观条件支持下,他要把自己的理论变成可行的实践,设想“上通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则可使欧、虞抗行,褚、薛扶毂,鞭笞颜、柳,而畜苏、黄矣,尚何赵、董之足云?”大有睥睨千古、融合众体之气概。并且还想在笔法上做新的尝试:“及悟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字变之以圆。凡书画贵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章,笔笔皆留,以飞动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更以王羲之为榜样:“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处处体现他“托古改制”的精神。当然,目的还是求得“新理异态”的“自然佚出”,才“能移人情”。这就是康有为所追求的“书之至极”。
总的来说,《广艺舟双楫》可以说是清人“尊碑”的理论总结,是“清人尚质”的理论依据。
当然,康有为“卑唐”的偏见是不能使人苟同的,这既不符合书法发展的历史真实,也不利于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唐代楷书的高度成熟,就是在继承了“晋人尚韵”——天然之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有“造作”之迹,但生气勃勃的书家、名作很多。尤其是初唐几家,后人认为“唐初犹有晋宋遗风,学晋宜从唐人入”。宋黄山谷也说:“唐初字学劲健,故由初唐人书,并可推知右军真迹之妙。”就是中唐的颜、柳,对宋人的影响很大,清冯班说:“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开张了整整一代书风。东邻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无不学习中国的书法,从而使书法艺术在日本发扬光大。这走向世界之功亦在唐代。康有为出于自己的偏爱,割断这个历史,无疑是《广艺舟双楫》中的一个大疵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