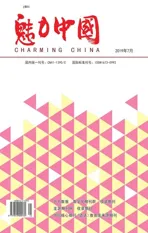中国书法作品在家庭装饰中的精神作用
2019-01-13傅桢晗
傅桢晗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秦代“书同文”以降,作为根植于文字本身的艺术,汉字的嬗变牵动书法的艺术性,在华夏先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在记录语言、交流思想、传播信息的实用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以汉字构造的日趋约易与书法贯气的日益加强为演变方式,造就了篆、隶、草、行、真五大汉字基本字体及书法基本书体,这是中华民族先民天才的审美感知能力与创造性智慧的高度结晶。”而字型的飘逸规整,笔墨的浓淡疏密,以人民生活为根基的书法艺术,闪耀着民族的光芒,以其独一无二的视觉审美内涵,屹立于世界艺术文化之林。也正是其所具备的人民生活贴近性,与艺术观赏的无限魅力,中国书法作品不仅能被置于高庙殿堂之上,亦可“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庭中装饰审美,陶冶情操,民族精神共同认知的重要存在。
鲁迅先生有言,“中国文字之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而书法以汉字书写为根发展,极尽形美、意美。时代变迁,书法演变,对书法的艺术研究同样蔚为大观,唐代著名书论家孙过庭《书谱》认为,书艺之一道,奥妙就在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否认书法是艺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法学》则认为书法在古代是写字,在现代是艺术。对于书法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论调争议不断。然而从属于自然科学的,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无法概述书法这一特殊的历史的、文化的产品。近年来在书法研究领域出现的话语研究则更能对书法的本质问题作出回单。汪碧刚(2019)提文化是书法的第一属性;赵婧等学者(赵婧 魏东方,2019)则从书法的美学原理提出书法的“象”“意”“法”三大本质;学者徐利明(2019)将其归结为书法四性,以绽书法完整的内涵。话语研究观照当下的书法发展,对书法的回答是含有社会语境的知识风尚。从当前总结的完整性来说,徐利明对于书法的四性描述更为全面。笔者对于书法作品在家庭装饰中的作用分析,将基于书法四性,以此为出发阐释其影响。
书法四性,从书法的根性谈起,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美学土壤之中,书法的书性得以传承。书性是书法本质,是不写字无以为“书”,是杂乱无章无以为“法”,“用笔、结字、章法、墨法”,方得形式与意蕴美实现,亦得审美的美性体现。然美亦不拘于阳春白雪,以文人情怀和学养加以融通和改造,合理适度地、恰到好处地注入个性的,书法便不被囿于横平竖直之间。而书法四美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R.阿思海姆在 《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解读视觉判断的问题时说:“对待图形的位置和 ‘力’的判断,并非由理智能力作出来的,它是靠观看所感应的知觉去判断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外显视觉的线条、结构与章法等刺激审美的主体,传递出主体需要的审美信号,回应审美主体的情感观照,传递作者凝结其中的内隐的丰富意蕴和心灵沟通,引发主体感受传统建筑显现的意趣和书法艺术表达的意境。(魏峰 唐孝祥,2018)如此审美价值,回归到实用价值取向大至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收藏价值,二是它营造的居室环境价值。(华伟,2005)介于书法作品的居室环境价值的普遍性,中国书法作品在家居中的应用得到了学者的广泛研究。对于书法作品在改变室内风水,提供和谐的宜居环境(陈协和,2008);悬挂字句以自勉,增添空间的文化氛围(苏倩薇,2018);书法留白对家居设计的启示(朱江,2011);再到对传统书法结构美的学习与设计应用(颜红影,2018),书法的家庭装饰意味浓厚。然而就当前的研究来看,对于书法作品产生文化辐射、陶冶情操的作用话语研究虽完备,然而大多诉诸于简单的陈述,仅有魏峰等学者通过书法作品审美态度影响审美心理四个阶段进行了具体分析。由此可知,关于书法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而对于书法作品在家居装饰中的精神作用研究虽有所开展,然而对其原理的探究仍有研究的余地。因此笔者将延续魏峰等学者对审美产生过程的研究,借鉴马彦蕾等学者以传播学原理解读书法作品作用,从认知原理出发,研究书法作品在家居装饰中的精神作用。
以书画为装饰的记载可以追溯至宋代。根据学者王冬松对《清明上河图》中书法元素的研究,宋代很多商家都有在店内悬挂书画的做法。“从功能上看,商家在店内悬挂书画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店铺的文化品位,以达到‘留连食客、茶客’的目的。”除了商业用途之外,宋代的一些政府办事机关中也可见到悬挂书法的情况。在闹市中间的一个简陋的办公“登记处”中,一幅大尺寸的草书作品营造出文化氛围。刘禹锡有语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显然的,早在宋朝期间,书画的装饰已作为文化的象征,彰显店铺之高雅脱俗,以吸引文人雅客,同时也成为官方的身份彰显标志。发展至今天,书法作品作为独特的民族艺术品亦不被置于高堂之上,而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
遵循传统生活的上下五千年传统被水泥森林所桎梏,自然的,是现代科技与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海德格尔倡导“诗意地栖居”,提倡在城市喧嚣中寻求文化的根基。人民对文化生活根基的寻求与文化自信的进步发展,使得传统艺术在家居装饰中的应用得到倡导。“广义上讲,所有的书法都有装饰性,这也是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艺术是我国传承了千年的文化艺术,其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形式、内容的意境创造对生活情操的陶冶。不仅如此,书法篆隶楷行草的丰富表现形式与扇面,条幅,对联等呈现方式,使得书法作品在与现代化的设计理念与表达思路中可以有效发挥。书法作品进入家庭,其带来的精神作用则更值得深入探讨。“书法……都蕴含着诸如‘中庸、阴阳’等的中国哲学美。这种美是需要大量接触书法、练习书法才能体会到的,现在的人们虽然不能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书法以深刻体会,但依然需要从欣赏书法中体会其中的道理。”个中道理需要如何体会,则需要引入认知态度理论以解释。
态度在心理学研究的传统上被看成是对某一大类的刺激的较长期的取向,例如人在居室中悬挂书法作品,从对之观赏而产生的具有感情色彩的态度。态度研究是心理学研究的常设议题,当前学者保持的基本认知,则是倾向于认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的三个部分来组成。认知包括个人对某个对象的认识与理解、赞成与反对的陈述内容;情感十个人对某个对象持有好恶,也是一种内心意向行为的准备状态,不是行动本身,而是行动之前的思想倾向;行为意向则表现为对行为的预设。11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审美态度的形成与态度的三部分之间的相关关系。根据魏峰等学者的研究,“审美主体(即人)从审美态度形成‘感知’,审美感受获得‘感兴’,展开审美体验‘妙悟’,实现审美超越‘物我两忘’的审美心理四个阶段。”很显然,在感知、感兴与妙悟是对态度的三个部分审美呼应。感知是初步的认知,感兴是从个人的角度对其产生好感,而妙悟则是主体对感知、感兴的反馈,可以视作一种行为意向。两者的对比也更突出了态度研究的根本性。只是在审美态度中,其存在超脱审美意向的态度存在——物我两忘,这将成为对书法作品鉴赏后产生的精神作用的深入补充。
因此,在书法作品成为中国家庭装饰的选择基础上,对家庭的精神作用首先从认知维度开始。对书法作品的理解与认识,首先是从其外显形态进行判断。外显形态的最直观接受便是视觉的感知。“在审美感知阶段,客体起着较主要的作用。书法艺术通过物象的形态、色彩、质感等刺激审美的主体,引发主体感受书法艺术表达的意境,”从书法的书性出发,便是对各种字体形态的感受,对字形组织的章法、以及留白与疏密、墨法浓淡等元素的简单感知并且在信息时代庞大的数据面前,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使得外显形态的范畴还可能扩展至对市场价值的了解以及对公众认可度的了解。包括作品的艺术价值,上述指标都可能成为人们感知书法作品外显形态的标准。在对外显形态的简单理解基础上,人们有区别地选择书法作品作为家庭装饰的存在。例如房间面积大的家庭可以选择大尺寸的,感官刺激强烈的书法作品,辅以裱框以彰显气派;上顶天、下立地的大型书法作品置于房间中,可以增加室内空间的通透感,甚至巧妙的设置能使作品成为独特的隔断,意趣盎然。小居室以尺幅小巧者为佳,例如利用空闲墙壁或居室门旁的墙上,根据宽窄不同,悬挂条幅式书法,在不同的空间中因地制宜,达到调节空间、环境气氛,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的作用。在认知阶段,人们基于实用性对书画进行悬挂,而在与环境的融洽结合之中,对空间的调整以及文化氛围的进入,使人收获或豁达宽阔或诗意人生的感受。在装饰与家居格局的和谐之中,对书法作品“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加深对其理解与肯定,度过认知的阶段性走向情感的态度。
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讲到:“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空虚,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了万象之美。”书法作品凝结意蕴,物像的存在外化审美主体的生命情感,以内心体验的方式获得“思接千古,神游八荒”审美超越,这个过程凸显出主体审美情感。以书法的根性来说,面对不断演进至今的书法作品,理解书法或质朴或精巧,或飘逸或凝重的风格,进而对于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鼎盛辉煌或是血流漂杵的朝代变换的感兴:对篆书的古意宏伟,引发对秦朝一统天下的豪情;见隶书的雄浑博大,则感程邈在狱中对篆书的去繁就简的伟大心境;钟情楷书的端庄正气,触及“颜柳欧赵”挥毫泼墨时不受拘束的风格演变;喜欢行书的清秀雅逸,则面《兰亭集序》中对生存与生活豁达与思考;热爱草书的飞扬流动,恣意狂狷的飘逸;甚至是瘦金体与宋朝偏安一隅的国家凋敝。正是书法的源远流长,在自己的居舍中触目生情,对书法作品的态度通过对书法意境美的欣赏后进入对其底蕴的逐渐认识,引发对书法作品的民族认同感。“中国书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在丰厚的文化滋养积淀中向前发展,文化与书法深度融合。”人们在思索民族变迁时,也正对中国的文化源流进行探索。一说书法中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书面留白与墨迹浓密的对比彰显阴阳协调的平衡,而在字体的变迁中,对字形的方正与端庄的一脉相承则是对儒家哲学君子之道的寄托。更有古人云:“书法乃人之衣冠,家之气象。”书法作品自古作为文化的象征,对家庭中成员的情操陶冶在感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世界本源论,正如书法对人心的感染,是在认同中,不断发衍出书法背后的独特含义而浸润万物。
当思想为书法作品所浸润时,行为的意向也就不断趋向其所引导的,贯通古今的智慧方向。在家庭中,这样的行为感召尤其表现于对家风的遵从。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训”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历代家训,无不体现在家匾、家联或中堂之中。所谓“家无书法无贤达”。书法在古代家庭不仅起装饰作用,而且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家训在对氏族子弟成人、成才、修身、齐家教育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现代的核心家庭语境下,家训鲜少成为一族传承,而是在城市的小家庭中,在家居装饰中的书法的内容为示意,且多为唐诗宋词,名言警句。繁复如《朱子家训》,五百多字涵盖了个人修养、家庭教育、处事哲学等诸多内容,阐明修身治家之道,彰显出了中华文化无比宽广的胸襟和卓尔特立。更有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 , 毋临渴而掘井”等更在小家庭中发挥作用。简约如“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甚至是“家和万事兴”的直接期望和愿景,都书写出了人生的至理名言。书法高度凝练文字的特点,配合字形组织的合适章法,便能完成从外显形态的体现,到内显形态的升华,最终抵达家庭中的成员们,从诗意的栖居,走向从心灵深处对行为规范的指导。对于规训的认识,给予人最深刻的人生动力,秉持信念,砥砺前行。勤俭持家、淡泊宁静、善恶分明的行为指导是态度必然走向行为的客观规律,亦是书法的精神作用最直观的体现。行为陶冶情操,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在致行合一之中物我两忘,神人以和。
笔者通过对书法作品的研究分析,将书法艺术的作用通过心理研究的范式分析,阐明其文化涵养的路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参考,以及仅对新近的研究趋势进行预测,缺乏对书法研究进行完整的脉络分析,因此在逻辑分析中有所疏漏。但书法作品的精神作用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方能摆脱单薄的文字阐述,真正走入人民生活。先贤林语堂所言:“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综观家庭书法装饰对家庭中人的态度改变以及行为指导,可以说,书法作品从外形上带来的视觉审美,至文化内涵的放射陶冶最终达成对人们行为的指导,书法作品对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现代人进行民族认同感的唤醒,加深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在尊敬与学习中引导人们迈向更好的生活。而如何将凝练了中华千年的民族精神与文明内涵的书法艺术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达到形式美与内在美的统一,亦是应当引发华夏儿女思考的共同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