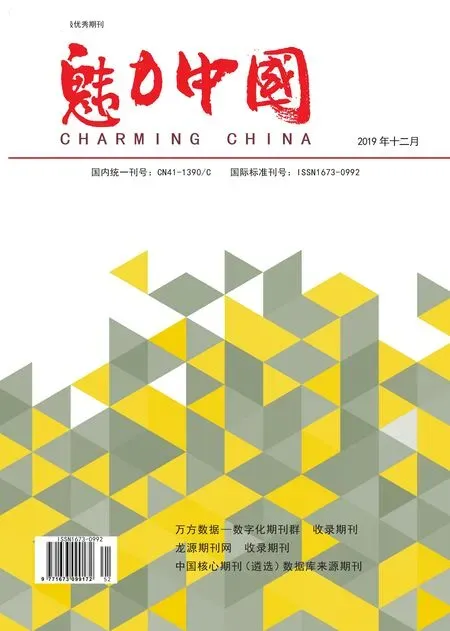论文学中的歧义现象及其审美价值
2019-01-13王建强
王建强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8)
歧义是指一个语言形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因而产生不同的理解,这属于自然语言的普遍现象。歧义在公文、论文,甚至散文、小说、戏剧中通常不允许存在,以致被剔出、被校正,而在诗歌中却意外地生存下来,而且还有意无意地被作者吸纳,给欣赏者留下鉴赏的矿苗,求新的满足,也给文坛时不时带进一点闹猛。
造成歧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的演变,地域的迁徙,环境的变化,习俗的嬗改,导致词义的拓展,都给歧义带来了存在的条件。但更多的还是语言自身的变化所造成的,诗句词序的错置变形,语法成分的飘忽不定,都会使歧义乘“虚”而人。也有因在特定社会历史范畴中所产生的语词随着历史的推移,巧合地拥有了新的意义,产生了歧义。正是这种种原因使歧义这一精怪在诗句中潜伏下来,使诗句所表达的内涵具有了不确定性,从而给人困惑感,激起鉴赏者探索的欲望,也就有了多一层面的鉴赏运作活动,使每一位鉴赏者的想象力骤然膨胀,骤然活跃,从而带来鉴赏的快感和满足,正如游三坛映月,每一位欣赏者都能在自己所看的坛里发现一轮皎洁的月亮一样,多么令人神往和惬意的事。
李白《菩萨蛮》中有这样一句诗:“寒山一带伤心碧"。看似普普通通,但由于历史人文的积淀,使这句话有了歧义,而鉴赏者又是站在后来的时空位置,以后来者的目光进行探视和审美,社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历史和艺术的叠影,就会有百倍的收获。李从军一这样诠释这句诗:“就连那远处碧绿的山色也使人着恼,叫人伤感。这似乎是静态的写生,是一种冷色的画面,但静态之中又夹杂着主观的感受,给人一种潜在的骚动感,撩人意绪。”(见《唐宋词鉴赏辞典》)这样的内心观照在钱钟书的《管锥编》中也能看到:“李白《菩萨蛮》亦云:‘寒山一带伤心碧’,观心体物,颇信而有微。心理学即谓人感受美物,辄觉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热泪滋等种种反应。”显然两位学者把“伤心”作为使动词看待,“伤心碧”就是“使人伤心的碧绿”。而何满子先生就不同意这种理解,他在《李白<菩萨蛮>赏析》一文中说:“‘伤心’在这里相当于日常惯语中的‘要死’或‘要命’。现在四川还盛行着这一语汇。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好得伤心’。或‘甜得伤心’之类的话,意即好得要命或甜得要死。这‘伤心’也如上海话中‘穷漂亮’、‘穷适意’的‘穷’字一样,作为副词,都与‘极’同义。‘伤心碧’也即‘穷碧’。”之所以有这样大相径庭的理解,且都能成立,都有道理,也正不必强求一律,就是因为诗句中的词语随着历史的推移、地域的变化,巧合地拥有了新的意义,产生了歧义,给鉴赏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新含义。我们既可与前一种理解欣赏不谋而合,也可和后一种观照心照不宣,更可以兼收并蓄,从两种方位交错着切入,多一份体会,多一份鉴赏,使审美的心灵多承受一次美的熏陶和洗礼,何乐而不为呢?
也有因词序的不同而产生了歧义,这更是多见的一种歧义现象,也是不同于前者的一种有意为之的现象。诗歌原不同于其他文体,情感的跳跃形成诗句的跌宕,格律和平仄又有意拆开原有的句子的语法结构,这种宽松无羁的语法结构偶一为之,就会使作品所描画的对象造成漫衍,再加上语词本身的含糊性特点,就极易产生歧义,而这歧义也就突然开拓了诗歌意象的领域,造成意象的渗透和铺展,以致模糊了本不会模糊的界限,使诗句有了—种内在的能力运动,撩拨起鉴赏者探索的热情,也就有了对这些诗句说不完的话题和开掘不完的领域。杜甫《春城》诗有这样两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可能理解成“感时”花也“溅泪”,“恨别”鸟也“惊心”,也可能理解成“感时”见到花(照理是应该愉悦的)也“溅泪”,“恨别”见到鸟(照理应该高兴的,因飞鸟给人生机勃勃之感)也“惊心”。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一句诗:“溧深林兮惊层颠”。是使“深林”“溧”,层颠“惊”呢,还是“深林”本身“溧”,“层颠”本身“惊”呢?这不必要去辨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康德曾经说过:“模糊观念要比清晰观念更富有表现方。”这种诗句的因歧义而造成的模糊不正是鉴赏者的驰骋之地吗?
现代诗歌少了平仄、押韵的羁押,少了因历史、习俗的变化而产生的词义、词序的不确定性,是否就没有或不会产生歧义呢?回答是否定的。今天的朦胧诗之所以朦胧自然是由于意象的不确定性,或含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造成的,也有是有意掐断或有意隐埋思维的链条造成的,但有些则是作者故意造成语词组合的错位,恍惚,使语词所揭示的含义飘忽不定,构成朴朔迷离的氛围,形成读者理解上的歧义困顿,结果构筑起朦胧的迷宫。像舒婷的《会唱歌的茑尾花》一诗中曾这样写道:“什么声响/唤醒我血管里猩红的节拍在我晕眩的时候/永远清醒的大海啊”。是“永远清醒的大海”发出的声响唤醒“我”,还是“什么声响”在我“晕眩的时候”唤醒了“我”,使“我”像“永远清醒的大海”,澎湃着情感的浪花,发出情感的呼喊。杨炼的《诺日朗》一诗中有这样一句诗“狼藉的森林漫延被蹂躏的美、灿烂而严峻的美”。这句诗同样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惑和捉摸不定,原因就在“被蹂躏的美、灿烂而严峻的美”这个短语该怎样理解,是把“被……美……美”理解成一个“被”和“……美”组成的介宾短语,还是将“被”和“蹂躏”“灿烂而严峻”组合在一起去修饰“美”。这种语词组合的隐性脱榫和随和嫁接,给人理解上带来了瞬间的迷惘和痛苦,但正是这种理解上的渴涩促使审美主体去作努力的纵深开掘,千方百计试图去破译蕴藏在语词背后的情感和意念密码,从而给审美主体以多层面的体验和愉悦。
可以看出不管现代诗人有意还是无意作语词的错位安排,客观上同样能造成歧义的产生。同样,不论是古诗还是现代诗,只要是诗歌,歧义的产生倒并不是坏事,适当的出现或适当的安排都将是一个探索不清或探索不尽的美好境地,都将使作品产生使审美主体欲罢不能欲“清”不行的焦灼感、鉴赏欲,是极吊胃口的一种特殊现象。可以这样说,诗歌中的岐义是一种美的“错误”和错误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