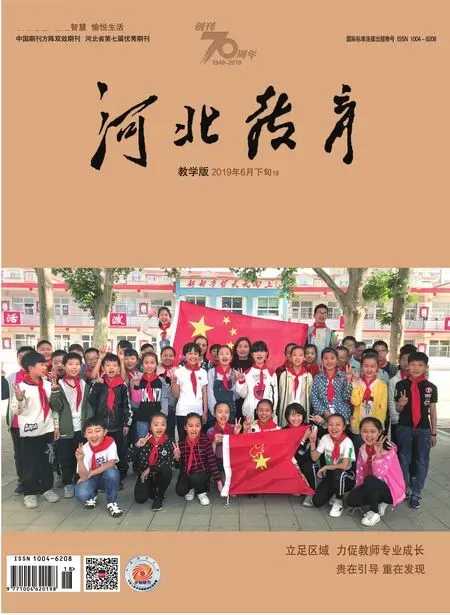“其坚不能自举”的爱情
2019-01-11韩田鹿
○韩田鹿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西厢记》的缘故。
“其坚不能自举”,是《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说的是惠子得到了一个大葫芦的种子,种下后收获了一个超大的葫芦。葫芦是用来盛水的,可这个葫芦根本承受不了整葫芦水的重量,一拿起来就会破碎。惠子的结论是:这玩意大是大,真的没用。
在如今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中,《西厢记》中的爱情就是这么个“其坚不能自举”的葫芦。
《西厢记》写的是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但他们仅仅是在谈恋爱吗?不,不,不,你想得太简单了。他们从事的,乃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从六十年代游国恩版《文学史》的“《西厢记》以同情封建叛逆者的态度,写崔张的爱情多次遭到老夫人的阻挠和破坏,从而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自由幸福的摧残,并通过他们的美满结合,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以及他们的斗争和胜利”;到二十一世纪袁行霈版《文学史》“按照礼教规定,‘父丧未满,未得成合’,偏偏在父亲棺材还在这里搁着的时候,莺莺却生出了一段风流韵事。王实甫把春意盎然的事件放置在灰暗肃穆的场景中,这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它既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也使得整个戏充满了浓厚的喜剧色彩”,虽然措辞有别,但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西厢记》中的崔张之爱,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反封建礼教”。在这种视角之下再看《西厢记》,这部作品忽然之间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崔张二人每一次对视的火花,都是一道撕裂封建礼教的闪电;每一句情意绵绵的话语,都是一声反抗封建礼教的呐喊;至于二人之间更为亲昵的行为,那就更是反抗封建礼教的英勇行动了。
何以如此呢?归根结底就是这样一个看法:虽然《西厢记》从头到尾都在写张生和莺莺的爱情,但爱情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它撑不起《西厢记》这样一部名著的意义。所以,崔张二人的爱情除了是爱情,它还一定是一些别的什么,而正是这个“别的什么”,才撑起了《西厢记》的意义。
“反封建礼教”就是文学史家在《西厢记》里“找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加上”的这个“别的什么”。但“反封建礼教”就一定有意义吗?以封建礼教的标准来看,难道潘金莲与西门庆不是反封建礼教吗?为什么同样的“反封建礼教”行为,在潘金莲与西门庆那里就被说成是荒淫无耻,而在张生莺莺那里就被热情歌颂呢?再说了,崔张二人真的反礼教吗?二人最后的结局,还不是纳入了封建婚姻的范围,而且还是得到了皇帝这个最大的封建头目的“赐婚”吗?二人反的又是什么呢?
所以,“反礼教”云云,实在是给《西厢记》戴上的一顶并不太合适的帽子。它既不符合我们直观、朴素的第一手阅读感受,也不符合作家时代的话语背景。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都不会专以摧毁儿女的幸福为己任;莺莺与老夫人的冲突,不过是两代人之间爱情婚姻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即使在现代也还普遍存在。
回到《庄子》里的那个大葫芦。惠子说那个大葫芦无用,但庄子就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不善于利用大的东西。你把这个大葫芦捆在腰上,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腰舟,利用它遨游五湖四海吗?大葫芦本身就有价值,而不必看它能装多少水。同样的,《西厢记》的意义就在于写了青春与爱情的美好,而不必在它一定承载了什么革命性的意义。莺莺和张生,一个学富五车,一个倾国倾城,他们由一瞥惊鸿而一见钟情,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里,演出了一幕真正的“春天的故事”。无论是人物的设定,还是情节的推进,都符合我们对于一场浪漫爱情的最完美的想象,而由于文学艺术引发我们情感的作用乃是所谓“内模仿”,所以,我们也就随着张生和莺莺,一起穿越回大唐,经历了一场完美的爱情。当我们听罢“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曲词时,想必有不少人的眼中心上都会漾起丝丝春意。它关乎青春,关乎爱情,关乎生命,难道这意义还不足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