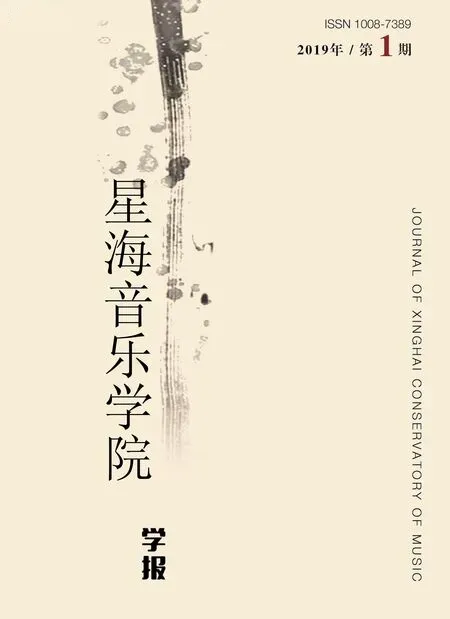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跨文化音乐学
2019-01-10刘经树
刘经树
跨文化概念从19世纪末就已在西欧开始,泰勒的《人类制度发展方法,关于婚姻和生育的规律》(1889)[注]① Edward Taylor,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Applied to Laws of Marriage and Descent”,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8: 245—269,1889.里已提出了这个概念。古巴民族英雄、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要人物马蒂在文章《新美洲》[注]② 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 “Nuestra America”, in: himself, Obras Completas, vol. 2.里,首次提出了跨文化性理论。
从20世纪上半叶起,古巴人类学家、音乐民族学家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1881—1969)的《古巴对位——烟草和蔗糖》(1940)一书,基于马蒂的理论,主张“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 是拉丁美洲身份的关键词,应用来取代当时惯用、有欧洲中心论倾向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又译“同化”)一词。如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所指出那样,跨文化虽与文化适应、传播(diffusion)、迁移(migration)或文化渗透(osmosis of culture)等惯用术语的含义近似,但“文化适应”的“前缀‘ac-’表示,‘未开化的人’应接受‘我们文化’的益处,正是他必须改变自己,皈依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注]Bronislaw Malinowski,Introduction,in:Fernando Oritz,Cuban Counterpoints,trnas. by Harriet de Onís, New York 1947, p.10.。也就是说,这些从欧洲迁徙到美洲的人虽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作出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但这些改变也给美洲文化的模式注入了变化,这明显有西方中心论痕迹。奥尔蒂斯却把“跨文化性”定义为“基于不同人的相遇与混合,重新创造一种新文化”[注]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culturalism, Sept. 29, 2018.。“跨文化性并不包含一种文化必须关心另一种文化的意思,而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它们都是积极、共享的,合作产生一种新的现实性。”[注]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culturalism, Sept. 29, 2018.
奥尔蒂斯还把“跨文化性”用于历史编纂学领域,构成一种有人类学特色的历史观念。他认为,不能用欧洲的进化论来观察古巴历史,“古巴的真正历史是它与跨文化性相互结合的历史”[注]Fernando Oritz, Cuban Counterpoints, trnas. by Harriet de Onís, New York 1947, p.129.。在古巴的历史上,首先来的是旧石器时代印地安人跨文化至新石器时代,然后,西班牙人才来到新大陆。那里,每一件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他们必须用文化的新同步信号来重新调整自己。同时,还有来自非洲黑人、其他移民的文化,他们的跨文化性经常反过来对古巴文化发挥影响或被影响。
在奥尔蒂斯的历史观念里,跨文化性在每一种历史现象上投下了阴影,甚至成为经济现象、社会存在乃至文化最基础的因素。例如,人种学名称在古巴,并非仅指种族出身,而且成为同时存在于古巴经济和文化的合成与历史的一种称呼。这种人类学视角也改变了古巴历史编纂学视角。奥尔蒂斯写道:
欧洲人在四千多年时间跨度里的文化全部色域,在古巴发生了还不到四百年。在欧洲,这种变化是逐渐地,在这里,它却突飞猛进。先有西伯尼人和古纳雅比伯人的文化、旧石器时代文化、我们的石器时代文化。……以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泰诺印地安人文化。……随着泰诺人,来了农业、与诺曼底生存相对的土生文化、富裕、部落首领、酋长。他们身为征服者进入,强加了首次跨文化。……然后,来了欧洲的文化飓风。……革命起义震撼了古巴人民,从根子上撕裂了他们的机制,摧毁了他们的生活。……如果美洲的印地安群岛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新大陆,那欧洲对美洲人来说就是一个更新的大陆。它们是两个世界,彼此发现并迎头冲撞。[注]Fernando Oritz, Cuban Counterpoints,trnas. by Harriet de Onís, New York 1947, p.130.
奥尔蒂斯的这本书论述了非洲-古巴的文化,古巴盛产的烟草和蔗糖在古巴和迁徙至欧洲的过程中,它们的制作和传播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的作用。但是,这本书长期以来没有在西方跨文化研究中得到充分重视,也未受到中国文化研究学界的注意。
在传统西方音乐史编纂学领域里,奥尔蒂斯的跨文化性冲击了以西欧国家为主体的音乐史编纂法则。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通史叙事原则,是按时间和国家的顺序,叙述各位重要作曲家各种体裁的作品[注]刘经树:《作品、结构史、人的历史——达尔豪斯的音乐史编纂学》,《音乐研究》2007年第2期,第64页。,它与跨文化观点的音乐史编纂不相符。跨文化性的出发点就是破除以地理、人种划分的国家和地区概念,以去除当下混血儿过去的文化性的新观念来纂写历史,不考虑本地人和新移民过去的人文、地理特性,着重描写他们在这个地域里重新创造的新文化现实性。正如奥尔蒂斯所说,欧洲和新大陆是两个世界,它们彼此发现并迎头冲撞。如果音乐史编纂的对象是如此的新地域的话,编纂者就不能按照原本以地理、人文划分的国家或地域来书写人们的历史。
传统西方音乐史按国家、地理、人文编纂的原则,也留下了“民族乐派”的问题,其根源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几百年来,西方中心论处于西方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表现在许多西方杰出学者的论著里。它的核心概念是西方人的“我”,完全不理会西方以外各个民族“他”的存在。比如,以西欧国家为中心来编纂音乐史,如何对待其他欧洲国家以致非欧洲国家的音乐?于是,产生了国别史。即使在传统音乐史编纂学里,通常把这些不属于西欧国家的音乐列为“民族乐派”,音乐史编纂者在此身处局外人的立场,暂时跳出了西方中心来看待各种音乐现象,把原本的“他”列为“我”。从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乐派”成了西方音乐史研究历史中的一块飞地[注]以20世纪末达尔豪斯的《19世纪音乐》为例,这部杰出的结构史中《民族歌剧观念》及《异国情调、民俗主义、仿古主义》两章,反映出与作者首创的结构史编纂学观念并不完全相符,靠西方中心论滋养的某些说法。参阅:Carl Dahlhaus, Die Musik des 19. Jahrhunderts, Laaber 1980, pp.180—187, pp.252—261。。奥尔蒂斯的跨文化性观念,颠覆了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编纂学里的统治地位,为音乐史编纂学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入口。
跨文化性也给音乐民族学原来仅从本民族立场看音乐现象的做法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角度。奥尔蒂斯历史观下的古巴文化,指多种民族文化在古巴的交融体。在本土文化里,有西班牙人与卡斯提人、安达卢西亚人、葡萄牙人、高卢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等,这是白种比利牛斯亚人与伊比利亚文化的交融。在首次移民潮中,来了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犹太人、黎凡特人、柏柏尔人,他们是地中海文化的代表。在古巴,不是某一个民族,而是多个民族和人种共同构成了古巴文化。我们在考察有移民或殖民地因素的地区文化时,应该站在跨文化的高度,来考虑各个民族在文化里的反映,比如,在考察俄罗斯作曲家在我国的创作,以及港澳地区的音乐生活时,中国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但它决不是原来各自地理区域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因此,不能从俄罗斯或中国音乐的角度来思考他们在中国的创作。
奥尔蒂斯认为,跨文化性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化的不同过程的更佳表达方式,因为,它不仅包含获得英语词“文化适应”真正意思的另一种文化,而这个过程也必然伴随失去或根除先前的文化,可以定义为“去文化”,以便后续地创造新文化现象的观念。最后,如马利诺夫斯基后继者学派所主张那样,文化联合的每一种结果类似于个人之间复制过程——子孙总是有双亲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总是与双亲的每一方都不同[注]Fernando Oritz,Cuban Counterpoints,trnas. by Harriet de Onís, New York 1947, p.133.。
跨文化性比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更具多元性,不认为仅仅是融合另一种文化(acculturation)或失去先前文化的根源(脱离传统文化,deculturation)。在后现代时代后殖民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跨文化经常可以是殖民征服的结果,也可以是本土人争取自己身份的战斗。这与一百多年前的殖民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跨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里全面展开。1971年,美国成立了“跨文化研究协会”,并创刊《跨文化研究一社会比较研究期刊》。1972年,“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在香港成立。国内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比较文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成立有“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学报》自2003年起,还连续几年设立“跨文化研究”栏目。近20年来,欧美音乐学界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跨文化音乐学研究,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拓宽了传统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加拿大跨文化期刊《反之亦然》(ViceVersa)主编塔西纳里(Lamberto Tassinari)认为,跨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新形式,基于消除点缀着宗教教义价值的帝国主义体验产物的传统身份和文化的观念,对立于从国家状态进化而来的传统单个文化。[注]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culturalism, Sept. 29, 2018.从1982年起,俄裔美国文学理论家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及他的团队发展了跨文化研究。他们发表的著作包括爱泼斯坦《未来之后——后现代和当代俄罗斯文化的悖论》[注]After Future. The Paradoxes of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 Press,1995.、贝里《跨文化实验——俄罗斯和美国的创造交往模式》[注]Ellen Berry,Transcultural Experiments. Russian and American Models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New York,1999. 全书23章有16章由爱泼斯坦撰写。、达格尼诺《全球迁徙时代的跨文化作家和小说》[注]Arrinna Dagnino,Transcultural Writers and Novels in the Age of Global Mobility,West Lafayette,2015.等。
后现代的全球化观念最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里。美国潮流研究者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元潮流》(Metatrends,1982)里,用汽车工业的发展作为全球化功能发生的例子。它产生的原因除了互联网发展等技术进步、世纪贸易自由、很多国家人口增长之外,还与二战后去除19世纪殖民主义有关。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和地理政治的变化,脱离了前殖民主义,明显影响了全球化进程。[注]转引自“维基百科”德语网页:http://de.wikioedia.org/wiki/Globalisierung, 2018年9月11日。伊丽莎白·凯特在论文《论跨文化——在外国重制和重作拉丁舞蹈和音乐》[注]Elizabeth Kate,On Transculturation: Re-enacting and Remaking Latin Dance and Music in Foreign Lands.里写道,“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不能再仅在面对面的关系里考虑跨文化性,但是,我们需要说明,抽象的相互交错关系通过面对面遭遇的一些层面。”[注]转引自“维基百科”英语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culturation, 2018年9月11日。她把这种现象描写为跨文化层面(layers of transculturat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跨文化交往的扩大, 出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ly)等概念。
“主体间性”是哲学概念,它指“如果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灵魂(纯客观的),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而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那么,它就是主观间性的。主观间性的东西与纯粹主体性东西形成对照,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与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或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观间性。”[注]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体间性摒弃了唯我论,证实了他者的心灵存在,建构了与跨文化性相近的共享世界,可以说是跨文化现象学哲学的基础。然而,跨文化性与过去常说的基于过去文化遗产的“多元文化”概念相对立。多元文化来自过去传统文化,其他文化与“永恒”的西方文化并存,而主体间性则强调当下不同心灵的共同性。
然而,“文化间性”一词并非哲学术语,体现出奥尔蒂斯的跨文化性的某些特点,在后现代学术研究中具有一定意义。
结 语
跨文化性扎根于跨越文化和国家定义的共享兴趣和文化价值,可以凭借“祖国以外的地区”思考方式来测定,“通过每一个问题的很多方面看问题”而不放弃信仰,允许自己的混血儿感觉而未失去人们的文化中心[注]Richard Slimbach, The transcultural Journey, at the Wayback Machine,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achived, 2010. 07.22.。文化变移确定了跨文化性的特点,不同的群体共享他们的故事、价值功能、意义和体验,这种共享、不断“搁浅”的过程释放出文化的强度和稳定性,创造出迁移和转换的条件。跨文化性寻求一种本体论,承认差异性和相同性不均匀的点缀,允许人类各个群体适应和吸取新的话语、价值、观念、知识体系,这种变迁状态总是寻求知识和存在的新领域。[注]Jeff Lewis,“Cultural Studies”,Sage, London, 2008.
西方音乐在中国,按传统文化研究来看,是西欧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的过程。然而,按跨文化性观念来看,西方音乐在中国被接受,中国人的各个群体以局外人身份与这种精英文化相交融,形成新的精英文化,在当今全球化潮流中闪烁着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