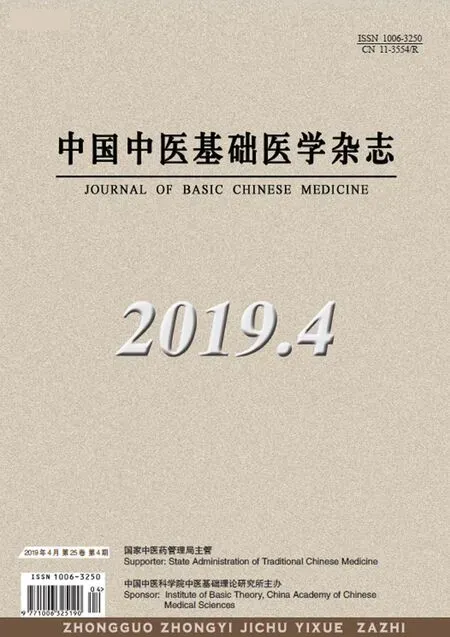从辨毒探讨痛风发病特点及解毒攻毒治疗
2019-01-09徐兆辉吴春飞梁桂洪梁祖建
徐兆辉,吴春飞,梁桂洪,梁祖建△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广州 510405; 2.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 广州 510240)
痛风是单钠尿酸盐沉积在组织、关节引起剧烈炎性反应的一种疾病,与尿酸的生成代谢紊乱直接相关,反复发作的关节疼痛、活动受限是其主要临床表现。痛风一般辨证认为是湿浊瘀阻、凝滞关节经络,导致气血不畅发病,分为湿热蕴结、瘀热阻滞、痰浊阻滞、肝肾阴虚等4型[1]。 但临床中痛风存在明显的急性期、间歇期、慢性期[2],而一般辨证的4种证型局限为急性发作期,且湿热瘀浊多相兼为病,很难截然分开;若按一般辨证思路,在间歇期、慢性期则存在辨证困难且与临床实际不符,也不利于痛风的整体、全程管控治疗。
历代医家多将痛风归属“痹症”“历节”等范畴,但痛风的发病特点和病因病机与痹症不同。笔者把“毒”的概念引入到痛风的诊疗中,化辨证为辨“毒”,从“毒”来论治痛风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特别是针对疼痛-痛风治疗的重点和难点,合理应用解毒、攻毒法及虫类药可快速缓解,现阐述如下。
1 中医学毒的内涵
《辞源》[3]中毒的释义:“恶也,害也,痛也,苦也,及物之能害人者皆曰毒。”在中医学中,广义的毒是指一切有害于机体的各种因素,这种因素无论来源于外界或体内统称为毒;狭义的毒是指邪气经过蕴藏积蓄,化合结聚不解,能够对机体产生明显损害的致病因素[4]。
毒分内外,外毒以外感六淫为主,邪盛为毒,邪积成毒。 前者,邪气偏盛猛烈则化为毒损害人体,这种毒具有明显的六淫特点。后者,微邪潜伏积聚、蕴育化毒,不仅具有原病邪的性质外,还因聚结化合,形成一种有别于原病邪的复合的致病因素。内生之毒源于体内,其产生是由内生五邪、代谢废物等积聚、蕴化,经过较长时间的郁酿交互为害,形成一种新的致病因素[5]。内毒来源可以是生理物质,又可以是病理产物,但必定经过蕴结的过程。就痛风来讲,内生湿、热、瘀、痰相结而化毒,是以内毒致病。
2 痛风之毒的成因
2.1 饮食不节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这是最早关于饮食与痛风发病的论述[6]。油腻厚味滋生痰涎,过食肥甘厚腻之人多湿生痰化热,是内毒生成之基础,湿、热、瘀、痰等各致病因素交叉、积聚、蕴育酿化成毒[7],西医称之为尿酸。
2.2 先天禀赋不足、脏腑功能失调
痛风之毒生成与先天禀赋不足相关,与脾胃、肾、肝脏腑功能失调关系密切。脾胃不足,运化失司,不仅不能运化水饮、聚而成痰湿化毒,而且亦不能分解运化已成之毒。“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肾脏分清别浊失常而导致排毒失常,毒留体内;另外肝主全身气机,肝失调达,气机不畅,毒滞不去。毒一旦产生,便又加剧脏腑功能失调,正衰邪积,形成复杂的病证。
2.3 脏腑蓄毒
流水不腐,脏腑藏毒不流,腐毒生矣!《中藏经》[8]:“夫痈疡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之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营卫壅塞而发者也。”
3 痛风之毒的致病机理
3.1 从热化火
痛风之毒是各致病因素蕴结而成,从热化火,蓄于脏腑,攻于手足,而为阳毒。《诸病源候论》[9]:“今毒气从脏腑而出,循于经络,攻于手足,故手足指皆肿赤焮痛也。”毒积蕴结,阻滞气血,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肿痛不休,由此脏腑蕴热、血脉经络郁热化火为痛风发病的先导。
3.2 伏于血脉,与血相结
脾与血关系密切:“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脾气健运则血生化有序;若脾失健运、痰湿内生易入血而与血结,阻遏经络气血。血气结聚,不可解散,其毒如蛊。气滞血涩或气滞血瘀,不通则痛;气滞和血瘀形成之后,为毒的不断积累创造了条件,最终形成毒积益甚、疼痛益加的局面。
3.3 毒浸溪谷
“至虚之处,便是容邪之所。”溪谷为经脉,向内灌注骨髓、肌肉的细小分支,为络脉交通之处,血行缓慢,营卫易于郁滞,痛风之毒更易从血脉中外渗此处。毒浸日久,反复发作,则“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引起骨质的破坏。《素问·气穴论篇》曰:“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腘,留于节凑,必将为败。”
3.4 难解难化,内攻有力
痛风之毒与血结与湿合,藏于溪谷、络脉,难清难泄,难解难化;长期积聚,内攻有力,蚀骨败血影响脏腑。
4 分期辨毒治疗痛风
近现代,西医认识到高尿酸是痛风的致病因素,降尿酸因此成为主要治疗手段,这对中医治疗痛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医家仿此立泄浊之法,或曰给邪以出路,多利用通泄淡渗利尿之品,希望尿酸得以排泄而痛解。孰不知毒热浸于溪谷、伏于血脉,岂可通泄、利尿而解?惟从痛风的根本病因病机入手,分期辨毒治疗实为正途。
4.1 痛风的病机
4.1.1 不通则痛 朱震亨[10]认为,痛风是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涉于冷水,或立湿地,或扇风取凉,或卧坐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当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全国名老中医朱良春认为[8]:“痛风,受寒受湿是诱因之一,但不是主因,湿浊瘀滞内阻才是主要病机,此湿浊之邪,不受之于外,而生生之于内也……凡此悉皆浊瘀内阻使然,实非风邪作祟。”因此不通则痛,痛风以气血经络痹阻不通为主要病机。
4.1.2 热毒壅滞 膏粱之人内多滞热,皮厚肉密,毒热从脏腑而出,循于经络,攻于手足,肿赤焮痛,内变为丁。痛风发作时患处红肿热痛,全身可寒可热,但局部为热毒壅滞为害无疑。毒热源自内出,无关外感,为痛风的独立致病因素;当然,随后也有因痹阻不通郁而化热的因素。
4.1.3 痛风与痹症不同 痛风和痹症同为痹阻不通致病,但痛风与痹症病因、表现存在明显不同。第一,“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前者多因外感诱发,后者为饮食不节,内生湿痰瘀热合而化毒,毒阻经络;第二,前者疼痛多伴有晨僵,后者无关节僵硬;第三,久病两者都会出现皮下结节,但前者皮色不变亦不会破溃,后者发作时红肿,缓解时皮色如常,日久可破溃,流出乳白色分泌物。由此,痛风和痹症病因病机不同,不能笼统套用痹症的辨证和治疗方法。
4.2 分期辨毒治疗痛风
毒热痹阻经络气血是痛风发病的根本,去毒热痹阻是治疗的关键。但痛风整个病程中存在急性期、间歇期、慢性期,分别对应毒盛、毒伏、毒结3种状态,化辨证为辨证辨病相结合即分期辨毒,从毒在不同阶段病理状态来治疗痛风。
4.2.1 急性期:清热解毒、攻毒散结 痛风急性发作为毒盛,治当清热解毒、散结攻毒,去毒之酷烈、依附、阻塞,急则治标,无须辨整体寒热阴阳。清热解毒即选择土茯苓、山慈姑、生石膏、生大黄、白茅根、土牛膝、肿节风等清热解毒类药物,去其热解其毒,热毒得解,疼痛可缓。在痛风的缓解期亦可为佐使之药。清热解毒之药应中病即止,不可过用,更不能一用到底,虽可快速缓解疼痛但也最伤人阳气。值得注意的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现代多应用在抗癌毒,临床中发现同样对痛风急性期效果明显。
不通则痛,痛风之毒,结聚溪谷,阻塞络脉,痛必剧烈,非大力之品难以奏功。临床中发现,痛风发作应用全蝎、蜈蚣穿筋透节、解毒开瘀,应用蚯蚓解毒热、通经络,能够快速缓解疼痛、肿胀,实为痛风治疗之“特效药”。《医学衷中参西录》[11]曰:“蜈蚣,走窜主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又“擅能开瘀”,《本草纲目》[12]蚯蚓:“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诸热疾,下行故能利小便,治足疾而通经络也。”惟全蝎、蜈蚣有毒,用量不易过大,研末吞服3~5 g,其效最捷;蚯蚓用量宜大,鲜品宜30~50 g,干品15~30 g。全蝎、蜈蚣、蚯蚓等虫类药,历代医家多在痛风石形成的晚期采用,取其搜风通络之功。而笔者在分析痛风病机和临床诊疗过程中体会到,攻毒宜早不宜迟,急性期应用其攻毒效力非凡。究其原因,痛风之毒侵袭溪谷,实已入络脉,应用全蝎、蜈蚣攻毒、搜风通络,又擅开瘀,正是确切之法。始入络脉,即攻毒通络其效彰,及后期结聚成块,则无力矣。
但急性期不宜用通泄、淡渗利尿之品。西医认为痛风为高尿酸致病,中医应借鉴吸收,但绝不能套搬,亦不能入其窠臼。痛风急性发作为毒热阻滞经络,当以“通、清”为先,清热解毒,散结攻毒,“通则不痛”。 西医亦有明确研究[2],痛风急性发作期不适宜用降尿酸类药物,不管是抑制生成类还是促进分解代谢类。痛风在急性期,应用利尿、通泄之品有何影响,还待进一步的研究,但笔者认为在解毒、攻毒之前不宜应用。
4.2.2 间歇期:化湿和毒 间歇期为毒伏,化湿和毒,其为实土,土性敦厚,和解万物。《伤寒论》云:“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脾土健运则可以纳毒、降毒、分解化毒,不仅可以运化水湿去毒之依附,又可降低毒的烈性,促进毒的分解代谢,防其传变而损害它脏。湿本为水,性濡润,易与热结,易聚成浊,弥漫难化。临床上常用陈皮、枳壳、山药、党参、苍术、厚朴、半夏、茯苓等健脾化湿类中药,同时辨证配合宣上通下之品,调畅气血,疏通三焦通道,调和脏腑气机,务以复脾胃运化之枢机为要。
4.2.3 慢性期:温阳化毒、破结开瘀 慢性期为毒结,久病入络,结聚成块,络脉、溪谷为气血灌注末端,流行缓慢,最易伏邪藏毒,尿酸盐最易沉淀析出。现代研究表明[13],尿酸和尿酸盐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较大,易沉积于温度较低且暴露肢体远端的足手耳廓等部位。痛风日久,毒邪结聚成块,难解难化,治以温通,可促进所结之毒消融,气血复通。“阳化气,阴成形”。温阳化毒即是用桂枝、细辛、通草、萆薢等通阳化气,犹拨云见日,未结之毒无以遁形,已结之毒渐化消散。
痛风日久,失治误治,毒凝滞成结块,成为痛风石或者痛风性结石,用土鳖虫、炮山甲、露蜂房、蜣螂、白芥子、白附子、皂荚、胆星等破结开瘀,化顽痰、软坚散结使毒所凝结之处气血得以复流,结节可化。
总之,痛风具有典型的症状、独特的病机,不但能够侵蚀关节,而且可导致痛风石、痛风性肾病等疾病,并与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类疾病相关性明显,危害巨大。在临床上须根据毒盛、毒伏、毒结等不同阶段分期论治,分别建立清热解毒、攻毒通络、健脾化湿和毒、温阳散结制毒等治疗原则。痛风反复,再次急性发作,无论在间歇期还是在慢性期,病机都是毒热再次积聚、阻滞气血,理同治亦同。故无需顾忌其他,尽可按毒盛来治疗;但解毒攻毒应中病即止,不可过用,疼痛缓解即可进入化湿健脾和毒阶段。痛风之毒非一日所成,痛风之治亦非一日之功,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始终应以治毒之害、防毒再生为其治疗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