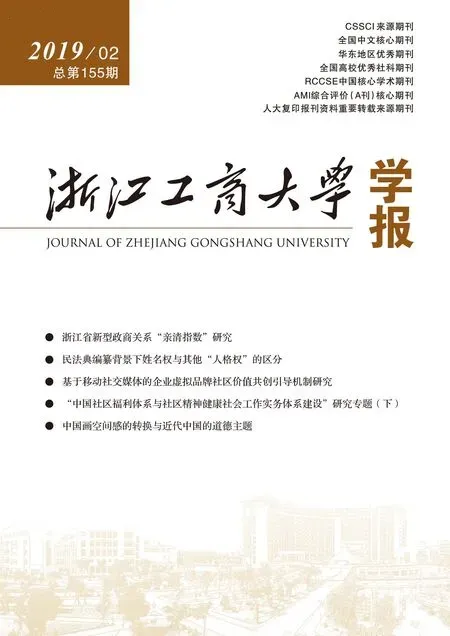论儒家的审美方式
——对孟子性情论的美学阐释
2019-01-04左剑峰
左剑峰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国美学史研究往往从道家和禅宗思想中找出它们相应的审美方式,把道家的“涤除玄鉴”“乘物游心”及禅宗的“顿悟”或“妙悟”视为审美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与西方美学“非功利性”观念有诸多相合之处。然而,当代学者普遍质疑“非功利性”这一信条。例如,柏林特认为西方传统美学中的普遍性、静观、距离、孤立、艺术对象等概念均以“非功利性”为中心,而且这种“非功利性”态度在很多艺术经验中是不适用的,普遍性、静观等对审美的限制也是没有必要的[1]52-59。我们认同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但这样做绝非企图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美学的步伐,而是因为这种批判是合理的、科学的。准此,我们便可以发现儒家思想中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之所以一直被忽略,笔者认为和它与道德不能撇清关系有关。儒家的审美方式就蕴含在孟子的性情论之中。对于孟子性情论,学界一直作为哲学、伦理学的重要课题加以研究,然而对其中所包含的美学问题,尚未被重视和深掘。
长期以来,儒家美学被整体地视为审美自觉和艺术自律所针对的对象,因而被认为是来自外部的对艺术的钳制和束缚,甚至在中国美学研究中成为保守、陈腐、僵化等观念的代名词。这种印象和评价是不恰当的。儒家美学并不限于言志、中和、美刺、载道等诗教乐教内容。儒家审美方式是儒家美学中更具有超历史性普遍意义的内容,它不仅不会对文学艺术构成束缚,反而使艺术的情感表现更为深厚博大。因此,对儒家审美方式的研究既可以丰富儒家美学,还可以改变对它的印象和评价,使它在当今仍表现出活力。
一、 “以情验性”与儒家审美方式
儒家主导的人性论是性善论,它由孟子明确提出来。孟子以道德情感的存在来逆推性善这一结论。
理解孟子性情论的前提是弄清其中“性”概念的独特含义。首先,“性”指人与生俱来的禀赋,这是中国古代各种人性论的通义。其次,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的“性”指人区别于动物的些微特性。再次,人与动物的区别包括诸多方面,而孟子“性”概念又专指人心中的仁义礼智之“根”: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注]文中所引《孟子》均来自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不另注。
最后,从孟子“湍水之喻”中讲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来看,“性”不仅是先验的形式,而且还是为善的潜在动力。傅佩荣指出,性善论中的人性“是一趋向,是一等待被实现的潜能”,“此潜能本身充满动力,表现行善之要求”[2]。可见,孟子“性”概念有四层含义,层层追加限定。如此一来,人性论必然会指向性善的主张。但性善论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证明人性中确有此使人为善之潜在动力。
孟子说道: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孟子·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3]239,它与利害计较和理性思考无关,只要人面临“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便随感而应,率然自生。孟子明确指出了“恻隐之心”是在“乍见”后产生的,因此它不是“性”本身,而是心理经验。另外,孟子又将“四心”称为“四端”。“端”本作“耑”,《说文》:“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端”指已经现实生长出来的部分,并不仅仅是生长的潜能。这也说明,“四端”应属于已发生的现实心理现象,而非人的潜在能力。
朱熹明确地将“四心(端)”解释为情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3]239。具体而言,“恻隐之心”是道德同情心,“辞让之心”指对他人的尊重之情,“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是评价性的道德情感和直觉。四者皆为道德情感,在现实经验中往往又是分不开的,而以恻隐之心为标志。因此,下文所说的恻隐同情之心或仁爱之情,其实指的就是综合性的“四心(端)”。焦循说:“四端一贯,故但举恻隐,而羞恶、辞让、是非即具矣”[4]235。这说明道德情感常连带着道德直觉,甚至可以说,道德情感本身即包含着某种直觉在内。
《孟子·告子上》还有一段与上述内容相仿的文字: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辞让之心”在这里称为“恭敬之心”。对这段话中“情”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根据“四心”为情感,将“情”释为情感;[注]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4页;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1页。二是以“情”“才”在此构成地对举为依据,将其释为情实。[注]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1页;牟宗三:《圆善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页;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0页;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但即使训“情”为“情实”,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情感在孟子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肯认。
上引《孟子》中的文字,皆以“四心(端)”推证“性善”。“四心”何以支持“性善”论呢?朱熹对此解释为“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3]239。也就是说,“情”是“性”的外在表现,“性”为体而“情”为用,所以孟子以用来推证体。清代程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云:“孟子以情验性……如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为仁义礼智之端,谓人皆有之者……若夫为不善,乃其后之变态,非其情动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4]752-753他将孟子论证“性善”的方法概括为“以情验性”。朱熹和程瑶田的解释符合孟子“尽心知性”的观念。
人性作为一种潜在动力难以直接证明,孟子从其最初表现形态——情感入手,通过道德情感逆溯善性之存在。“四心”的产生必有其根由,他排开了一切后天外在的原因(如“内交于孺子之父母”和“要誉于乡党朋友”),也排除了生理好恶上的原因(如“恶其声”),而将真正的根源归结为“性”。故而,孟子特别强调人有“四心”如有四肢一样自然。
“四心”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体,其作用过程可视为一种审美活动。人性仅为先天根据,“四心”又需在对外在情境的感受后,才得以现实发生。而且,它的具体内容也随之体现出所应对情境的特点。《孟子》一书举出了几个道德情感发生的事例。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时产生的怵惕恻隐之情,除了敏感于孺子的危险境况外,还隐含着对无辜幼童将承受的痛苦和毁灭的想象,以及产生“应加以救助”的直觉判断。“乍见”说明外物所具有的感发作用,而且情感的产生过程不同于理性的分析、思索。这种专注的感性心理活动过程就是一种审美。再如,《孟子·梁惠王上》记有齐宣王见“有牵牛而过堂下者”一事。牛将用以衅钟,王“不忍其觳觫”“隐其无罪而就死地”。赵歧注云:“隐,痛也。”[4]83在齐宣王的哀痛悲悯中,有对牛体缩恐惧的敏感,对其无罪就死的想象,以及“以羊易之”的情感决定。若以理性忖度之,以羊替牛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羊也会恐惧畏缩,也属于无罪就死。然而,“以羊易之”乃因齐宣王“见牛未见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可见,审美感受在此成了重要选择依据。
二、 儒家两种情感感发方式
除“四端”之情外,儒家还有“七情”的理论。“七情”即《礼记·礼运》中提到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如果说“四端”属于今天所谓的“道德情感”的话,那么,“七情”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自然情感”。儒家同样重视自然情感现象,要求对它们加以节制和疏导。在儒家看来,自然情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如果对它加以适当制约和引导,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儒家将自然情感的感发当作艺术创作的发生和根本。《礼记·乐记》论及音乐创作说: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成变;变成方,谓之音。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注]参见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8-998页。
这种思想后来进入诗学领域而发展出“感物说”。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再如钟嵘《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由此可见,美学上的感物说源自儒家。
儒家有两种情感感发方式:一是自然情感的感发;二是道德情感的感发。朱熹的弟子陈淳说:
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底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5]。
这里,把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和“四端”统称为“情”,并认为它们是“性”在外在事物的触发下而产生出来的。无论是自然情感还是道德情感都是“感而遂通”的结果,故而均属于审美感受的过程。虽然如此,应注意的是,诗学中“感物说”的内容一般指“七情”或自然情感。
由于自然情感感发不像“四心”感发那样充分体现出儒家独特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只将后者而不将前者视为“儒家的审美方式”。儒家审美方式虽然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被充分自觉,不像自然情感感发那样发展出感物学说。我们今天应该站在美学角度对这种审美方式进行总结。
儒家审美方式所产生的道德情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写到汉末社会动荡,一位饥肠辘辘的妇人将孩子丢弃在草丛间,听到嚎哭声又回头看看,但最终还是流泪走开了。这位妇人说她已没有办法养活孩子了。诗人“不忍听此言”,但也无能为力,只好驱马而去。诗人对白骨蔽野,生民朝不保夕,而“喟然伤心肠”。可以说,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儒家审美方式下产生的恻隐之情。儒家审美方式当然不限于对人事的感受,还包括对自然的同情。例如唐代诗人元稹的《桃花》写道:“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春风助肠断,吹落白衣裳。”桃花这一美好生命物本不能长久,又加上无情风雨的摧残,引发出诗人的怜惜和伤感之情。
上面两首诗中的同情恻隐之心是儒家审美方式的产物,但不难发现,其中也包含着悲伤、哀痛等自然情感。这说明在审美或艺术创作时,儒家两种情感感发方式往往同时发挥作用,使得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通常结合在一起。如前所述,“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人就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说文·心部》:“怵,恐也。”“恻,痛也。”可见,恻隐之心或同情心就是以他人之恐惧为己之恐惧,以他人之痛为己之痛,扩而充之,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己之喜怒哀乐。质言之,同情心、恻隐之心就是物我一体的感受。道德同情心是以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为基础的,是在自然情感上所引发的共鸣或一体关联的感受。所以,自然情感的感发不一定意味着同时伴有同情恻隐之心,而同情恻隐之心的感发则必须以自然情感的感发为基础。这又可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将单纯的自然情感感发作为“儒家审美方式”提供一个理由,即它已经内在地蕴含在“四心”的感发之中了。
“感物”在中国古代诗学中意义重大,但感物所生之自然情感又需要得到疏导和深化。王夫之在诗学上提出了自己的“诗道性情”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明诗评选》卷五徐渭《严先生祠》)古代诗学中的“性情”大多偏指人的喜怒哀乐等七情,但王夫之所谓“性情”则不同,它包括“性”和“情”两个方面。王夫之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则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已”[6]673。一般认为,已发的“四端”是情感,王夫之则认为它们虽是在外物的感发下产生的,却仍是“性”。“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虽其发也近于情以见端,然性是彻始彻终与生俱有的,不成情上便没有性!性感于物而动,则缘于情而为四端;虽缘于情,其实止是性”[6]673。王夫之还发现“性”(“四端”)与“情”(七情)是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固未尝不入于喜怒哀乐之中而相为用”[6]573-574。“盖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其体微而力亦微,故必乘之于喜怒哀乐以导其所发,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7]。离开了“性”的节制和引导,“情”就会走向偏斜;而“性”的力量较为微弱,只有结合“情”才能成其大用。诗不可能表现未发的“性”,而只能表现已发的“性”即“四端”。可见,王夫之“诗道性情”说,其实强调的是“四端”与“七情”或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结合。如果说上文所指出的恻隐之心内在地蕴含着“七情”,体现了道德情感以自然情感为基础的必然性的话,那么,王夫之在这里强调的是道德情感借助自然情感来增强自身作用力的必要性。黄宗羲也主张“诗以道性情”,他区分了“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对后者给予了肯定,并得出结论说:“故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性”指的是什么?“人之性则为不忍”,而“不忍”就是“满腔子皆恻隐之心”(黄宗羲《马雪航诗序》)。由此可见,王夫之和黄宗羲在诗学上主张“诗道性情”,其实质是强调以道德情感来引导和深化自然情感,只是二人均将道德情感称之为“性”而已。
总体看来,儒家非常重视道德情感在生活实践中的意义,古代文人也罕有不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儒家审美方式、儒家对道德情感的重视遂成为古代文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诗人在创作中,一开始着力于表现在自然、社会事象触动下产生的个人的自然之情,但随后又将其普遍化,升华为广博深厚的道德情感。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由个人遭遇的苦痛出发,经由一番倾诉,终而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呼,似乎以此来回应风雨大作的“怒号”。自然情感之所以随后升华为道德情感,其原因在于诗人创作时大多要对相关的词语、意象和情感,在内心进行一番审视。个人自然情感若在反省中得到细味、咀嚼,那么作为抒写对象的“自我”就被“他人化”了,此时可能超出封闭的自恋和狭隘的小我。个人情感染上了对同类人的同情关切色彩。同情不仅可以将他人视为自我,亦可反过来将自我当作他人;而将自我当作他人来同情,又很容易过渡为对他人的同情。
我们甚至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作品本身虽然只是表现了自然情感,并没有升华为悲悯同情的生命共感;但它之所以有价值甚至被普遍传诵,是因为它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读者的内心引发同情。儒家审美方式的存在空间比较广阔,不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创作中,也存在于欣赏者对作品内容的同情反应中。对于艺术家而言,不一定要在作品中直接流露出自己的悲悯同情,而可以单纯抒写自然情感,但要善于通过自己的创造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产生共鸣就会心生恻隐同情之心。从这一点看,并非任何情感都适于艺术表现。诚如19世纪英国诗人约翰·罗斯金所说:“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却不能歌唱失去的金钱。”守财奴失去的是贪婪的对象,因而他的伤痛不具有引发他人共鸣和同情的潜质。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是生命的正当需求,所以她的悲伤就具有了引起共鸣和同情的可能性。王国维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8]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必须具有普遍性,能引起他人的共鸣和同情。
中国古代有“以悲为美”的传统。韩愈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王世贞也说:“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是一合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为什么以喜乐欢愉之情为表现对象的作品难写呢?对此,前人已有出色的解释。明末张煌言在《曹云霖诗序》中说:“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着,沉着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清初陈兆仑在《消寒八咏·序》中说道:“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之浅深别矣。”[注]张煌言和陈兆仑之言,均转引自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4页。张陈二人的解释大同小异,都认为忧愁苦痛的情感具有留驻和沉落的特点,而欢愉快乐之情具有飘散驰越的特点;前者意味深长,而后者余味不足。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些特点恰与它们能否更易于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同情有关。同情需要将他人的情感放在自己内心加以观照和咀嚼。虽然喜乐欢愉之情也是同情的内容,但因为它是飘散性的,难以让人去细味和咀嚼,因此不太容易引起共鸣。反之,由于悲伤哀痛之情是停留性的,能更好地让人去加以细味和咀嚼,故而容易引发共鸣。“以悲为美”的传统暗含着对不同性质的情感在引发欣赏者共鸣和同情上有所差异的规律性认识,也与儒家审美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
由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审美方式对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影响,它所产生的“四端”之情与“感物”所生的“七情”之间有多种结合方式。可以说,儒家对艺术情感表现的影响,除对自然情感加以节制(如“中和”与“发乎情止乎礼义”)外,还有将自然情感蕴含于道德情感之中,用“四端”之情来疏导和深化自然情感,以及将自然情感升华为悲悯同情之心等方法。这种升华既可以体现在作品中,也可以有待于读者来完成。儒家审美方式不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创作中,也出现在欣赏者对作品的欣赏之时。儒家审美方式可以避免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情感走向偏斜,而且还能使它更为广博深厚。
三、 审美作为道德基础的意义
西方传统美学将美与真、善明确分离开的研究方法,在当前不断地遭到质疑。韦尔施说:“在现代性中,理性类型的区分和分界是得到提倡的,这些理性类型被认为是轮廓清楚、内核各不相同。但是,近年来的分析表明,这样做最多是表面看来正确,根本上却是错误的。理性的不同类型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彼此限定,而是在其核心部分表现出纠缠不清和相互转换的状态,从根本上瓦解着传统的分类”[9]。柏林特也指出,“审美价值可以与众不同,却并不与众分离;可以是独特的价值,却不是单一的;可以是重要的价值,却不是纯粹的”[1]21。随着美学致思原则由分离性向连续性转变,审美与道德的关联性成为重要话题。儒家审美方式直接否定了将审美从道德中完全独立出来的纯粹主义和分离主义,显然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感生“四心”是完整道德活动的起始环节。此时,审美与道德尚无分化。对于具体情境,人的情感往往先于理性做出反应。或者说,这是一个尚未进入自觉理性思考和实际行动的阶段,是一个以情感感受和直觉为主导的审美过程。审美在道德活动中的这种基础地位,决定了它对于道德所具有的两方面作用。
其一,充分重视情感感受和直觉作为道德活动起始环节的作用,有利于缓解道德主体内心的冲突。儒家在理论上虽常追溯至人性,但在实践中的依据则首先是道德情感。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批判,不是去指谪对礼的僭越所具有的现实后果,而是叩问季氏心怎能安:“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面对宰我质疑“三年之丧”(父母死后子女守孝三年的丧礼),孔子直指对方内心发问:“女安乎?”(《论语·阳货》)礼在儒家当然是重要的行为规范,但它的背后是道德情感。与此相仿,孟子说道: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
上古之时,有人在父母死后弃尸沟壑,数日后发现虫蛆野兽嘬食,内心刺痛,额头冒汗,不忍正视,于是加以掩埋。孟子认为,掩葬父母的风俗、礼仪大概源自这种情感体验。道德情感往上追溯是人性,往后延伸则是礼法。儒家不仅在本始依据上重视仁爱情感对礼法形成的意义,而且强调它在具体实践中的基础作用,否则遵守礼法因缺乏内在支撑而容易流向虚伪。
敏锐的情感直觉能力具有“左右逢源”(《孟子·离娄下》)的效果。现实情境激起道德情感,直觉则对此情境做出直接判断。对事物的具体感受所得信息,直接体现于情感反应中。道德情感不仅是道德行为的外在动力,而且还决定了行动内容,对具体行动起着框定、指引作用。面对“孺子将入于井”或者见牛觳觫就死,仁爱情感只会支持、引导救援行为,而不支持、引导视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的行为。所以,“四端”既是情又是理[10],它不完全是非理性的。
在审美观照中,人不是去随意玩弄、摆布眼前的事物,现实情境有它自身的召唤结构或暗示力量,它抵抗人的任意反应。上述二例中的情感反应就体现了对象(“孺子”“牛”)的现实遭遇对审美主体内心的影响、启示与作用力。对现实境遇的把握既是道德活动之始,又是审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审美或道德主体对对象所处的现实遭遇的把握,可能比对象(如果是人的话)更合理更恰当。道德同情心一方面具有物我一体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是“旁观者”的心理感受。亚当·斯密说:“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惨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会是什么感觉”[11]。审美主体的同情心体现了“健全理智和判断力”的作用,故而能更客观真切地把握情境。
如果一种伦理学过于推崇理性逻辑,满足于“从一个更一般的义务或义务群到另一个义务的推理”[12]325,那一定会远离现实,甚至得出一些凌驾于生命正当需求之上的结论。康德不正是通过一番严谨的思辨推导而得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撒谎”的结论吗?本来,一切理性推理的根本原理皆源自感性和直觉,但后来的推论可能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儒家审美方式重视人的感性(感知、情感和直觉)的基础意义,避免热衷于纯粹的理性推演而远离现实生命的危险,因而可对过于理性化的道德起补充作用。正如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所说,“没有情感的思维是价值空虚的,它缺乏情感内部的判断提供的意义感”[13]。
当然,完整的道德活动常需要理性分析和推理,惟其如此,行动才有更明确的方向,并采取恰当手段。然而,如果内心道德情感和直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道德活动便不再只是通过外在理由、思辨推理、意志力去强迫人执行。相反,人内心有一种情感驱动力和直觉的要求,这样便极大地缓解了道德实践中内心的冲突和剧痛。弗洛姆把与他人和世界的结合看作是人的内在必然需求,并且认为只有爱才能满足这一需求。他说:“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身不由己,死的必然,人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14]。如果道德过于外在化,只重规范和法则,而缺乏内在的爱和恻隐之心,就不能真正满足与他人结合的内在需求。这或许也是现代人(哪怕是具有道德的人)深陷孤独、空虚,缺乏意义感的原因之一。
其二,作为一种感性力量,儒家审美方式(其中的道德情感和直觉)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判断”作用,对理性化的规范是否与当下情境相贴切保持着敏感,抗拒那些习惯性出现却不适用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如前所述,情感的产生离不开对现实情境的感受,并且其具体内容体现出对情境特性的把握。道德情感的这一特点,在反抗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的非语境化运用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孟子非常重视: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一切礼法规范都具有历史性,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古人。“男女授受不亲”在当时就是被普遍接受的礼法准则。然而,孟子认为这条礼法在嫂子溺水时是不适用的。孟子以浅易的例子说明,墨守成规有时不仅愚昧而且残忍。任何礼法都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才具有合理性,具体实践活动必须因时处宜,善于权变。权变又肇自更微妙的感受和直觉。孔子也非常警惕礼法规范的有限性,因而说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所谓“毋必”“毋固”“权”和“无可无不可”,都意味着礼的相对性。在儒家,知权变比死守礼法要高明得多。“不是简单的外向探索,是人文的、伦理的”[15],由广泛习礼到知权变、掌握更根本的仁道精神,就是一个由博返约、由表及内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往往表现出忽略和逃避复杂的惰性。“我们经常愿意相信一些事实的版本,因为它支持了我们的一些先入之见”[16]。然而,通过感性的关注,能够避免习惯性的道德反应,从而把更多与既定道德规范相矛盾的东西递交理性去思考,甚至使理性一时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和选择。但理性的这种犹豫、不知可否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能避免简单粗暴地看待问题。真正的理性精神必然理性地意识到自身之有限,拒绝做自身创造的观念的俘虏。割断作为源头和基础的外在境域的启示,不去理会内心情感和直觉抵抗的呻吟声,精神世界就会极度贫乏,道德将变得越发陈腐和刻板。应当随时保持警惕,生活总有例外,现实总比对它的理性把握更为复杂。儒家审美方式可以用生活本身来纠正道德,有助于扼制因缺乏了解而粗暴地展开的道德攻击,因而促进道德判断的公正。
很多艺术作品(尤其是精英艺术)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并不在于它演示或贯彻了某些既定的道德观念和规范,而是因为它们揭示了既有道德的有限性、相对性。这样的作品可以唤起欣赏者对道德的有限性的注意,反复经受它们的熏陶,欣赏者就会培养出对道德判断保持警惕的心理。艺术家必须先有所感受和“发现”才能创造出引发欣赏者注意的作品。所以,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都可能存在儒家审美方式的作用。由此可见,儒家审美方式虽然是我们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来的,却是一种普遍性的审美方式。
审美对道德的这两方面作用,其实就是道德的审美化,而这种道德的审美化就是道德的优化。我们在这里论述的“审美化”并不是要否定道德,故而不同于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以审美代替道德(责任、义务和原则)的审美主义。它也与舒斯特曼所说的“伦理学的审美化”不同。舒斯特曼明确表示,伦理学的审美化“不意味着伦理学需要完全反对道德考量,只不过是说,伦理学必须反对道德考量对总体和凌驾一切的要求”[12]325。也就是说,“伦理学的审美化”是在道德之外谋求审美化的伦理生活(好的、幸福的生活),而道德的审美化则是针对道德自身的。
四、 结 语
我们通过对孟子性情论思想的分析,从中发掘出儒家的审美方式。它强调与生命对象联为相互感应的整体,保持彼此的牵动,产生恻隐同情之心。儒家审美方式与道家的“涤除玄鉴”“乘物游心”及禅宗的“顿悟”或“妙悟”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最高的、具有导向作用的三种审美方式。它们均要求发挥本性的作用,在各自所属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儒家审美方式虽然蕴含在儒家思想中,但又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方式。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情感表现,而且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和推广。与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道德也是一种有限的活动。其有限性包括两个明显的方面:一是道德并非完美境界,二是道德规范的相对性。与此相应,我们讨论了审美对于道德活动的积极(促进和推动道德)与消极(对既有道德观念和规范保持警惕)两种意义。对儒家审美方式的这些考察,可以丰富和充实有关“伦理/美学”或“审美伦理学”[注]韦尔施提出建立“伦理/美学”的设想,认为它“旨在意指美学中那些‘本身’包含了伦理学因素的部分”,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关于“审美伦理学”,我国学者陈望衡认为,“既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道德与审美的血缘关系,也可以从比较学的角度,研究道德与审美的异同;还可以从社会效应的角度,研究道德与审美的互补”,参见陈望衡:《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