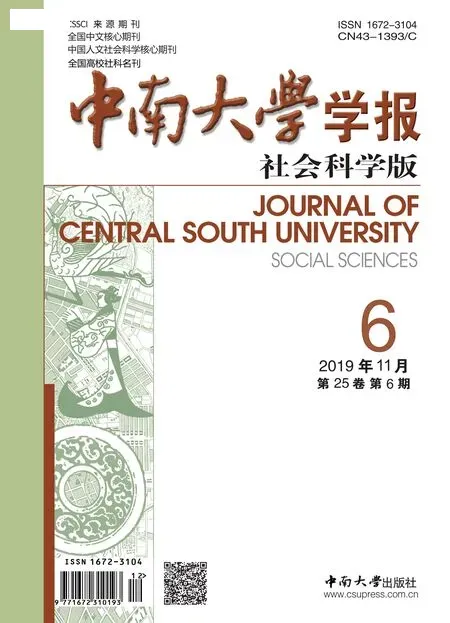“以类为评”:《世说新语》分类体系接受史的新视角
2019-01-04林莹
林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世说新语》分门隶事、以类相从。在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严州校本出现之前,此书的流传全赖抄本,且各本门数略异。除三十六门定本外,还曾有三十八门本和三十九门本①存世。前者如汪藻《世说叙录》载“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1](2b),又王应麟《玉海》引“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八卷”,小字注曰“分三十八门”[2](1048)。后者如颜本、张本二种,“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1](2b)。此二三之后出门类或摘自正史,“显示了六朝以降文人对《世说新语》的增补拟作情形”[3]。
虽云各本略异,但堪称《世说新语》主体的始终是此三十六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这是古代小说较早的分类兼标目②,以“孔门四科”开篇,树立了道可师模的地位③,继而伴随卷次的递增,大抵呈现出立意从褒到贬④、容量由丰入俭的趋势。
正因分门设类不乏主观意味,分类标准为何、条目如何归属,可以大致反映编者的关注重点和价值立场,此即“以类为评”。从评家的实践来看,他们也将某一类目视为一个整体,如元刻本中署名刘辰翁者之评曰“《世说》之作,正在《识鉴》《品藻》两种耳。余备门类,不得不有,亦不尽然”⑤,冰华居士《合刻三志序》亦曰“义庆撰《世说》,妙在《言语》《赏誉》诸条,其他《方正》《文学》,寥寥不足录也”[4]。就具体条目而言,任何一种归置都难以被所有人认同,王思任《世说新语跋》便直言:“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其中顿置不安、征传未的,吾不能为之讳。”⑥可以说,关于这一话题的纷争经久不衰。在明中后期小说选集和《世说新语》风行的背景下,《世说新语》条目不断被摭拾、编入他书,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编者对原书归类的重审与改造。而随时间推移,《世说新语》的“以类为评”逐渐显现出标杆效应,为其续作乃至其他更多作品所借鉴。由此可知,《世说新语》分类体系虽非尽善,然其首创的“以类为评”范式在接受史上影响深远。恰因“以类为评”难平众议,持续数百年的观念交锋不断累积,客观上促使原书的批评思路得以持续深化和开拓,成为一种开放式的、生长型的批评框架。因此,这一特质应当作为“世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关注、梳理和探究。
一、由“类”致“评”:历代评者商榷条目归类的批评传统
条目归置妥当与否,是历代《世说新语》评者聚讼纷如的重要场域。在这方面,元代付梓的首部评本已肇其端。《贤媛》“王右军妻郗夫人”“王凝之谢夫人”二条,分叙郗氏不满夫家对待家兄的态度、谢道蕴不满丈夫的气度,刘应登对此评道:“此二则皆妇人薄忿夫家之事,不当并列《贤媛》中。”此书中刘辰翁之评更着意于此,他评《德行》“晋简文为抚军时”条“复何足于‘德行’”;《政事》“贾充初定律令”条“亦非‘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语甚是,然亦非所谓‘政事’”;《雅量》“庾小征西尝出未还”条“颜色之厚耳,非‘雅量’”;《方正》“向雄为河内主簿”条“憾而已,非‘方正’之选”,“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条“似狎尔,非‘方正’也”。这些言辞说明评者心存有关类目定义与范畴的既定认知。如果说《世说新语》的类目设置和条目归属代表了刘义庆的批评眼光,那么评者所论就是对这种眼光的重审。在此过程中,刘辰翁的批评可谓“破立结合”。除了上述指瑕言论,他也为部分归类建言,如举《政事》“嵇康被诛后”条“也是‘语言’,不当入《政事》”,《雅量》“王戎七岁尝与小儿游”条“当入《夙惠》”。
刘辰翁的批评思路为其后的评本所继承,并逐渐形成一种专属于《世说新语》的批评范式,其中以凌濛初、王世懋之评最为典型。刘应登认为安置不妥的《贤媛》“王凝之谢夫人”条,凌濛初提出“‘忿狷’为是”[5],这无疑与刘应登所言“妇人薄忿夫家之事”的“薄忿”一词隔空呼应。《言语》“会稽贺生”条全文为“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凌濛初评其“甚似‘赏誉’”,亦有其理。《任诞》“王子猷诣郗雍州”条记叙王徽之在郗恢处获见□㲪,下令左右送归己家,“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郗无忤色。”刘义庆原是看重王徽之的率性而为,因此归于《任诞》;王世懋评曰“此见《雅量》乃可耳”,显然偏爱郗恢的不愠自若。刘、王二氏在归类上的分歧,显示了对于人物品性的趣尚之异。
比上述诸家走得更远的是王世贞。王氏为实现全书自汉至明的贯通,择取《世说新语》十之七八,与《何氏语林》十之二三合成一部《世说新语补》。他在《世说新语补》里重置了部分归类,如将《规箴》“罗君章为相”条改隶《宠礼》,与刘义庆的阐释角度截然不同。由于归类行为的主观性,重新归类往往不仅无从消解歧见,反而时常导致更多争论。以《世说新语·赏誉》“王蓝田拜扬州”条为例,此条曰: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王世贞认为王述的陈言浩然正直、合乎礼节,遂改属《方正》[6],凌濛初颇不以为然,坚守刘义庆的归类,曰:“此因有‘名播海内、远近所知’,故入《赏誉》耳,《方正》不类。”清人李慈铭不赞同刘义庆及其拥趸者凌濛初将其置于“赏誉”的做法,也不支持王世贞的“方正”观。在他眼中,此乃“六朝人矜其门第之常语耳,所谓专以冢中枯骨骄人者也。临川列之《赏誉》,谬矣!”[7](247)再以《世说新语·轻诋》“庾道季诧谢公”条为例。此条叙裴启尝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安澄清“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王世贞重视谢安对支道林的欣赏,将之从《轻诋》调入《赏誉》;凌濛初则聚焦裴氏语,评曰“‘目支’一段,弇州采入‘赏誉’,此既是裴郎诳托,不足复存”,彻底驳斥了这一调整。
历代评者围绕归类问题争论不休,本质上是以这一共识为基础的,即归类缪乱不仅是一种误读条目的表现,而且会妨害类目范畴的纯净清晰,甚至导致条目内容与设类标准的两伤。因此,王世懋评判“羊绥第二子”条归隶情况云“此等语,亦伤《雅量》”[8],凌濛初也批评“晋明帝欲起池台”条“乃亦溷《豪爽》之科”。在这方面,陈梦槐的评语尤具识见,当他看到王世贞《世说新语补》将原属《世说新语·言语》的“未若柳絮因风起”条归入《贤媛》时,径斥之曰:“太傅闲怀远韵,晋人中第一品流。当其燕居,问子弟欲佳,车骑答甚雅隽,问白雪何似,道蕴对更娟美。士女风流作家庭笑乐,千载艳人也。弇州以此入《贤媛》,即两伤。”[9]王世贞将谢家风采限于道蕴一人并施以道德视角,确有不妥之处,陈梦槐的批评切中肯綮。另外,对于《世说新语》将“杜预之荆州”条置于《方正》的举措,王世懋早就抱有异议,“杜元凯千载名士,杨济倚外戚为豪,此何足为‘方正’?”陈梦槐对此的评价更加激进,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意,“摹杨济雄俊不肯下人数语,的的如画。入《方正》,则弇州删去便不足惜”。陈梦槐认为,尽管此条笔法甚为可取,但放错类别,以致题意侵损、类目混淆,即便弃之亦无憾。观此种种可知,历代评者是以极为审慎的姿态对待归类的,相关异见的浮现和交汇,既显示了不同的批评角度,也对反观编者观念、丰富条目意涵大有裨益。
二、因“编”审“类”:明末小说编选对分类的调整和开拓
明代中后期,出版业蓬勃发展,小说集的编刊迎来热潮,而彼时也正值《世说新语》因契合晚明世风、得到主流认可而广泛流播的关键时期[10]。职是之故,嘉靖、万历以降的小说集多采撷《世说新语》条目,《舌华录》《初潭集》《情史》《智囊》《古今谭概》《机警》便是其中的典型。对于手握编选权力的文人而言,他们的辑采、标类行为,无不昭示着对《世说新语》分类的重审。众所周知《世说新语》一书虽合丛残小语,然阐释维度甚多,颇难概论其偏重言、事、人三者之何端。刘知几《史通·杂述》将其定位为“琐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视之为“杂录”,四库馆臣归之于“杂事之属”,鲁迅则以之为“志人”小说的开山之作。正因如此,它为彼时小说集的编纂提供了多种定位的可能。总体而言,《舌华录》偏于采“言”,余者重在辑“事”。可以说,这些小说集对《世说新语》条目的重新发掘、归类及评点,构成了“以类为评”的二次实践。
先以万历年间曹臣编纂的《舌华录》为例,此书“所采诸书,惟取语不取事”(《凡例》),所引包括以《世说新语》为首的近百部书,由吴苑分类并撰类目小序,复倩袁中道批评。吴苑对《世说新语》分类的改造体现在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皆有袁氏评点与之呼应。一方面,吴苑细化了《世说新语》的分类,如《排调》的条目大多分流至谐语、谑语,《言语》一门分作慧语、名语、狂语、豪语、傲语、冷语、谐语、谑语、清语、韵语、俊语、讽语、讥语、愤语、辩语、颖语、浇语、凄语等十八类⑦。无论袁评是否认可这种归类方式,对《世说新语》原有分类体系来说,《舌华录》分类的细化确已引发了认知的深化。如“徐孺子”条载: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此条收入《慧语》,袁评曰“若以此入‘辩语’,则无佳致矣”[11](4),大有赞赏之态。“孔融之被收”条,叙孔融之子临危道出名言“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舌华录》将此置于《慧语》,袁评则目之以“丈夫凄语”,与“慧语”的归类相去甚远。在这两例中,吴苑和袁中道对辩语、慧语、凄语三种类别的辨察以及对相关条目的评析,深化了关于《世说新语》“言语”一类的见解。
另一方面,吴苑把《世说新语》“言语”之外更多门类的条目,放在《舌华录》“言”的维度下看待,以此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譬如《伤逝》“王戎丧儿万子”条入《韵语》,舍去王戎的悲戚,唯取山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清韵;《容止》“谢车骑道谢公”条入《俊语》,原书重在“恭坐捻鼻顾睐”之举,虽说袁评也称此“形肖略尽”,但吴苑“俊语”的归类多少稀释了这一细节的重要性,而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物的言辞上来。值得留心的是,袁氏仅偶对《舌华录》的细分归类表示赞同——如《舌华录》将《德行》“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条收入《慧语》,袁评“此处极难转语,非慧口不能”;在更多时候,他往往提出迥异的观点。这从书前《凡例》所云“其中分类有小出入者,袁已笔端拈出,今仍不疑”即可窥见一斑。《舌华录》的编者曹臣一方面尊重吴氏的分类,一方面也邀请读者参阅袁评的观点。如此一来,如果说《舌华录》以“言”的眼光看待《世说新语》,是对其条目内涵的一次开掘,那么《舌华录》里袁中道的评语,则是通过对《舌华录》的批判,起到了二次开掘的作用。具体而言,《世说新语·言语》“孔文举年十岁”条入《舌华录·谑语》,袁氏驳曰“此段乃‘慧语’”,提示读者在谑、慧之间细品“言语”的真意;《世说新语·轻诋》“王丞相轻蔡公”条入《舌华录·谑语》,袁评曰“可入《讥语》”,其解读路径异于吴苑,而更接近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人饷魏武一杯酪”条记杨修著名的释“合”字事,《舌华录》归置《慧语》,袁评曰“不成语”,暗驳了二书给定的正面标签“慧语”和“捷悟”。至于《世说新语·容止》“庾太尉在武昌”条入《舌华录·韵语》,袁评曰“事更韵”;《世说新语·任诞》“刘公荣与人饮酒”条入《舌华录·韵语》,袁评曰“慧人”:此二评语无疑令《舌华录》“惟取语不取事”的理念得以扩容,间接丰富了《世说新语》原书条目的内涵。
同样,其他小说选本亦对《世说新语》内涵的扩充有所助益。如前所述,《初潭集》《情史》《智囊》《机警》诸书若浑言之,均从“事”的维度选编《世说新语》条目;若析言之,则各有切入点和立足点,如《初潭集》以“理”为纲,《情史》以“情”为旨,《智囊》《机警》则展现出以史为鉴的智书风范。这些小说集各自强调的理、情、智主题,不尽合于《世说新语》原来的归类,但也因此使其解读空间更为深广。
“理”的主旨见于李贽《初潭集》。此书是对王世贞《世说新语补》与焦竑《焦氏类林》的选辑,由于《世说新语补》有相当部分源自《世说新语》,《初潭集》也就间接选入不少《世说新语》的条目。李贽将这些条目依照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五伦重新分类,每类之下根据内容或价值判断再作细分。大体上,原书《品藻》一门归于《师友·论人》,《任诞》一门归于《师友·酒人》《师友·达者》,《容止》一门分为《父子·貌子》《父子·令色》《君臣·貌臣》等小类,《伤逝》《汰侈》分别移入《师友·哀死》和《君臣·侈臣》。这种归纳方式对《世说新语》原本的设类来说,既有纵向的细化,也有横向的扩张。例如,《德行》“荀巨伯远看友人疾”条划归《师友·笃义》,在“德行”的范畴内深究“义”的一端,更为精准;《捷悟》所载杨德祖三事归于《君臣·愚臣》,可见李贽对杨修的敏思毫不欣赏,反贬之为“愚”。诸如此类的思路拓展,当归功于李贽关注重心的偏移。《简傲》“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条,记述谢安劝谢万不必拜访王恬,谢万执意而行,果然遭受冷遇。李贽将此收于《师友·知人》,其所谓“知人”重在谢安,而《世说新语》的类目标签“简傲”则重在王恬。《容止》“魏武将见匈奴魏”条即曹操床头捉刀事,刘义庆的归类突出曹操风貌雅望之不凡,李贽置之《君臣·英君》,强调的是曹操对有识人之才的使臣的追杀,他评“驰遣杀使于途”句曰“不得不杀”[12](260),观察重心显然已从外在气度移至思维决策。《黜免》“殷中军被废”条载殷浩书空事,原本重在“黜免”事件,此处归入《君臣·痴臣》,实以“痴”字评价了殷浩应对“黜免”的态度。《世说新语补·雅量》“刘越石为胡骑围数重”条写刘琨清啸吹笳退敌事,李贽评曰“此非雅量,退胡之计也,琨本善啸”,并将之收入《师友·音乐》,这一分类显示了他与王世贞的观点大相径庭。
李贽的归类极具个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一些归类失于牵强,无益于对《世说新语》条目的解读。如将《世说新语·德行》“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条改隶《君臣·正臣》,此条内容本与君臣关联无多,只因其从华、王行为之异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便引申至国家用人的高度,“小人举事不顾后,大率难以准凭,若此,国家将安所用之乎?”他又将《汰侈》“石崇厕常有十余婢”条、《纰漏》“王敦初尚主”条、《容止》“潘岳妙有姿容”条和《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分别置于《夫妇·勇夫》《夫妇·贤夫》《夫妇·贤夫》《君臣·贤相》,皆不知何据。
相较而言,冯梦龙《情史》的设类以“情教”贯通全书,更成体系。书中把《任诞》“阮仲容”条置于《情私》,并在该类结语中宣扬“私而终遂”之可嘉。又把记录韩寿与贾充之女贾午私会偷香的“韩寿美姿容”条归入《情私》⑧,还特在篇末评贾午的追爱之举,甚至宣称父亲为女择婿不如女儿自择其夫,“充女午已笄矣,充既才寿而辟之舍,寿将谁婿乎?亦何俟其女自择也!虽然,贾午既胜南风(原注:充长女,即贾后),韩寿亦强正度(原注:晋惠帝字也),使充择婿,不如女自择耳”[13](202)。此语持论超越,不随俗同声,恰好与《世说新语》所系“惑溺”的贬斥姿态南辕北辙。最可佐证这种“尚情”观的是《汰侈》“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条,冯梦龙从“帝怪而问之”的关键处腰斩,仅保留如下文字,并收于《情豪》一门:
晋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褶,以手擎饮食。
这一归类所指的评判立场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了,有趣的是,此举倒也带来了一种新奇观点,即王武子之奢,乃其性情使然。该类结语所言“丞相布被,车夫重味。奢俭殆天性乎!然于妇人尤甚。匹夫稍有余赀,无不市服治饰、以媚其内者,况以王公贵人,求发摅其情之所钟,又何惜焉”,更是细致地论证了这一观念。
《情史》立意在“情”,冯梦龙编纂的《智囊》及王文禄辑录的《机警》则重“智”。这类智书对《世说新语》条目的重新分类也颇有兴味。《智囊》卷二十七《杂智部·狡黠》录入的曹操四事均源自《世说新语·假谲》⑨。冯氏《杂智部》小序曰:“智何以名杂也?以其黠而狡,慧而小也。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或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14](643)原书类目名为“假谲”,《论语》有曰“晋文公谲而不正”,“谲”即欺诈之意。冯梦龙易“假谲”为“杂智”,固然涵括了“假谲”“正智无取于狡”的消极面,却不摈弃“正智或反为狡者困”“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的积极面,可见他对于“智”认识周全,运筹有道。嘉靖时期王文禄编《机警》一书,自述“生也朴窒,见事每迟”,故将“书史中应变神速、转败为功者,录以开予心”,另于“各条末赘数言以自警”[15](1)。其书同样收录了《世说新语·假谲》的条目:
王羲之幼时,江州牧王敦甚爱之,恒置之帐中眠。敦尝先出,羲之犹未起。钱凤入,敦屏人言逆节谋,忘羲之在帐。羲之觉,备闻知无活理,乃佯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睡。敦言毕方悟,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见吐,信之,乃得全。沂阳子曰:羲之早慧,故能脱虎口,至亲何益哉?是以君子贵豫远恶人也。
篇末“沂阳子曰”便是王文禄的评论。正如冯梦龙对曹操的“杂智”有所肯定,王文禄对王羲之的“急智”也击节赞叹,誉之为“早慧”,录之以“自警”。冯、王二氏之说与《世说新语》的归类指向相去甚远,构成了一种对话。
以上分述明末诸书从“言”“理”“情”“智”等角度对《世说新语》条目展开的重新审读。诸书不约而同加以选评的少许条目,是值得深究的绝佳样本,兹举三例予以说明。其一,《世说新语·汰侈》“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条,原本归类意在批评石崇的奢靡作风。《古今谭概》将此收入《鸷忍》,首要斥责石崇的冷酷残暴,铺张问题倒在其次。不同于刘义庆、冯梦龙的负面视角,《舌华录》将之改隶《豪语》,评价对象不再是石崇,而代之以后半段“固不饮,以观其变”的主语王敦。主人劝酒不成连斩三人,王导劝王敦从命,后者却大言不惭道:“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在吴苑眼中,这样的洒脱是最大的亮点,当以“豪语”之称为其加冕。有趣的是,袁中道的评语“有此主人,亦有此客”,则兼顾了石、王二氏的言行,意味深长。其二,《世说新语》“王安丰妇”条写王戎妻以“卿卿”相称,原归《惑溺》,显然蕴含道德上的指责。《舌华录》《情史》与此迥异,前者入《谐语》,付之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后者归《情爱》,并在结语里大赞王戎之妻云:“情生爱,爱复生情。情爱相生而不已,则必有死亡灭绝之事。其无事者,幸耳!虽然,此语其甚者,亦半由不善用爱,奇奇怪怪,令人有所借口,以为情尤。情何罪焉?”进而借题发挥,叹惋史上为污名所困的红颜,剑指亡国的真正原因,“桀、纣以虐亡,夫差以好兵亡,而使妺喜、西施辈受其恶名,将无枉乎?”这类崇尚情爱、为情脱罪的言论,与最初的“惑溺”说针锋相对。其三,《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原书“言语”的归类重在孔融对祢衡骂曹的评论,“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初潭集》改入《师友·豪客》,重点移至祢衡,并含钦慕揄扬之意。《古今谭概》编进“矜嫚部”,结合部首小序所云“谦者不期恭,恭矣;矜者不期嫚,嫚矣。达士旷观,才亦雅负,虽占高源,亦违中路。彼不检兮,扬衡学步。自视若升,视人若堕。狎侮诋諆,日益骄固。臣虐其君,子弄其父。如痴如狂,可笑可怒。君子谦谦,慎防阶祸”[16](232),可知冯梦龙并不关心孔融言语,亦不赞赏祢衡举止,仅举之以为鉴,劝诫君子谦恭为本,切莫恃才轻慢、招惹祸端。
综上所述,明末小说集在编选过程中,实际上借用了《世说新语》“以类为评”的范式,与《世说新语》“以类为评”的既定面貌进行了充分的对话。其结果是,原书的分类体系在众声喧哗的评点或以行代言的分类中得到新的开拓,其条目的内涵也收获了角度各异、别出心裁的阐释空间。
三、“以类为评”:对于“世说体”及其他更多小说的标杆效应
评者围绕《世说新语》归类的争鸣之多、诸书对《世说新语》分类的改造之盛,无不说明了《世说新语》分类体系的影响之大。而作为这种影响源头的“以类为评”特质,反过来又成为影响的表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强大的标杆效应。
其一,“以类为评”的标杆效应最直观地体现在 “世说体”小说在设目和归类上的追摹。有学者指出,“世说体”小说对《世说新语》分类体系的效法,包括“完全模仿”(如明代《兰畹居清言》《明世说新语》,清代《明语林》《玉剑尊闻》《明逸编》,民国初年《新世说》《新语林》)、“基本依托”(宋代《唐语林》《续世说》《南北史续世说》,明代《何氏语林》)、“门类生发”(明代《儿世说》,清代《女世说》)和“作者自创”(明代《南北朝新语》)四种类型[17]。这批小说直至民国初年犹延绵不绝,其中不乏《西山日记》《玉堂丛语》《琅嬛史唾》《芙蓉镜寓言》《异闻益智丛录》等未在书名上透露规摹意图的作品,可谓不遑枚举。“世说体”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此处仅从“以类为评”的角度,略陈一二例证。
崇祯朝张墉编纂的《竹香斋类书》,又名《廿一史识馀》,取《史记》以下二十一史之佳事隽语成书。此书近仿《焦氏类林》,远承《世说新语》,对《焦氏类林》五十九类“或仍或去,数衷于焦。而独详政事、干局、兵策、拳勇者,愧世所应有而不有,补痴顽、鄙暗、俗佞、贪秽者,恶人所应亡不应亡也”。此书分类不止步于形式上的效法,书前《发凡》中的“分部”一条,对《世说新语》的条目归置提出了批评,“临川《世说》,以谢公妒妇侧《贤媛》,甘草丑人列《容止》”。卷四《长厚》“赵咨以敦煌太守免选”条记述盗贼为孝所感、惭叹跪辞事,眉端缀评曰“辰翁有言:‘两贼亦入《德行》之选’”[18](624)。观此可知,无论是编者张墉,还是评者项声国,均对隐藏于这一分类体系背后的“以类为评”范式相当熟稔。茅坤评《何氏语林》“言语”上“何义方言不虚妄”条亦曰:“可入《方正》。”[19]而前述合《世说新语》《何氏语林》二书为一的《世说新语补》也承袭有迹。在此书中,新录的非《世说新语》条目同样得到了与《世说新语》原文同等的待遇,印证了本文前两节所论的双重“轨道”——因具体归类而引发纷争,借小说编选而调整分类。“梁伯鸾少孤”条曰:
梁伯鸾少孤,尝独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鸾及热釜炊,伯鸾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之。
此条被何良俊归入《德行》,王世贞保留了这一分类。李贽却在“灭灶,更燃之”之旁批“无理,丑甚”⑩,待其编写《初潭集》,便顺手将之调入《夫妇·合婚》类。再对比其他小说集的处理方式,《舌华录》收归《狂语》,袁中道评曰“有道学气”,分类者强调的“狂”和评者提点的“道学气”如同小径分岔,并不一致。《古今谭概》却视其为迂,入“迂腐部”。这些评论无一与何良俊最初归类时所持的嘉奖态度相同,均以崇真祛腐为底色,挖掘出条目的全新内涵。
其二,从传统上并不认为属于“世说体”的作品来看,“以类为评”的标杆效应亦不容小觑。明人祝彦辑《祝氏事偶》,他自叙对《世说新语》进行分类的凭据是“自正史外旁及稗编,惟据事同耳。但错出无伦,姑取《世说》诸目分隶之,‘目’所不该,复括之曰‘部’,以隶其后”[20](209)。《王太蒙先生类纂批评灼艾集》一书是王佐将《灼艾集》的嘉靖初刻本重新分类而成,书中分类体系效法《世说新语》由褒到贬的“价值递减”原则,并直接采用识鉴、雅量、文学、栖逸、容止、企羡、赏誉、品藻、箴规、巧艺、轻诋、忿悁、惑溺等部分《世说新语》类目。《古今谭概》⑪分迂腐、怪诞、痴绝、专愚、谬误、无术、苦海、不韵、癖嗜、越情、佻达、矜嫚、贫俭、汰侈、贪秽、鸷忍(附“绝力”数则)、容悦、颜甲、闺诫、委蜕、谲知、儇弄、机警、酬嘲、塞语、雅浪、文戏、巧言、谈资、微词、口碑、灵迹、荒唐、妖异、非族、杂志等三十六部,不仅其数量与《世说新语》相同,部分类名亦有《世说新语》类目的印记。并且,此书所选《世说新语》条目的归类去向,也能清晰地映射出沿袭路径——原属《纰漏》的内容入“谬误部”;刘伶脱衣裸形、王徽之雪夜访戴、桓伊横笛三弄等原书《任诞》名段,一并汇入“越情部”。
其三,更为抽象也更为重要的标杆效应体现在“以类为评”思想的内化。古代文学的类分思想萌蘖于汉赋,设目分类的实践经由《文选》肇始、《皇览》等类书奠定[21],但多以题材类型作为分类依据,不具备价值评判的性质。及至《世说新语》成书,受其成书时代评骘风潮的影响,才另辟蹊径,开启了这种暗寓批评的分类方式。“以类为评”基于两个前提:一是认同书籍的设类立目包含了价值判断,二是认定条目的归类方式蕴藏了编者深意。前论“世说体”和“非世说体”诸书当中模仿《世说新语》分类体系而新设的门类,就是经由形式上的效法,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了“以类为评”的精神实质。
实际上,“以类为评”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这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浙江图书馆藏本《智囊补》作为《智囊补》原刻本的增订版,于“发凡”处有曰:“各条有原刻在某卷,今移载某卷者,皆出先生详定,即同卷中前后,亦多所更置,读者将前刻细心对阅,应知自有经纬。”[22]这般“移载更置”的“经纬”,即“以类为评”理念之所在。冯梦龙也曾在《笑府》卷三“吏借卓”的条末评道:“或谓余曰:‘古称四贱,曰娼优隶卒,吏不与也。子伸丞史于《古艳》,而附吏书于《世讳》,有说乎?’余应之曰:‘有,无官不贵,无役不贱。’”如是自述,足证这般归类之婉而多讽,仅在归类 之举中便暗藏指斥贵官贱吏的微言大义,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前引王佐《批评灼艾集》一书,为《识鉴》类的“正统中”条附眉批云:“此条应在《相 术》。”[23](42b)此评表明,关于识鉴、相术的分野及条目的真正指向,评者胸有成竹。清人曾衍东所撰小说集《小豆棚》,在卷十四“郝骧”条之末出自评曰:“此当入《果报》类。存之实,则删之更净。”[24](240)此书编次者项震新将此条归在“淫昵类”,作者特地在评语里提出调整归类的建议,是因为“淫昵”太过强化艳情意味,很可能令读者忽视其寓劝惩于果报的初衷。诸如此类重视归类、寓以批评的举措,都可追溯至且归功于《世说新语》首创的“以类为评”范式。
在有明一代对《世说新语》和“世说体”作品的大力推崇与梓行之下,明清两代小说集中的这类例子不少。虽然“以类为评”终究无法一统众议,也不尽是得宜且有益的(如王金范删定《聊斋志异》,将原书之大半分为孝、悌、智、贞、义等二十五类[25],总体上即无甚可观),但应强调的是,这一范式为寻绎作者或编者心目中最为关键的观看角度和批评立场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后世的评者议论和编者重审,赞同也好、驳斥也罢,不断交汇,推动了批评视角的深化与开拓,丰富了最初批评思路的既定面貌,推动“以类为评”成为《世说新语》分类体系的重要特质和重大贡献。“以类为评”既是一种开放式的批评框架,不断邀请异代读者走进跨时空的对话,也是一种生长型的理论范式,容许文本的意涵在时间的河流中得到滋养,渐次充盈,与古为新。
注释:
① 或谓有四十五门本,所据即董弅本跋语“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潘建国据汪藻《叙录》引刘本跋语指出,“所云‘四十五篇’,当指第十卷所载四十五事,而非指《世说新语》全书分为四十五门”,参见《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86-97页。
② 汉代刘向《新序》《说苑》,应劭《风俗通义》等具有部分小说特征的作品,今虽分类标目,然皆经宋人编订(前二书为曾巩,后一书为苏颂),初版是否已有标目尚不可考。
③ 今人赵西陆评曰:“孔门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世说》分门,盖规此。”参见周兴陆辑著《〈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本文所引《世说新语》原文皆据此书。
④ 有学者以“价值递减”概括排序原则,参见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8页。
⑤ 见《品藻》首条批语,明末凌瀛初刊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八卷,国家图书馆藏。此书汇有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三家评(刘辰翁评语真实性存疑,因非论述重点,本文不作区分)。最早录有二刘之评的《世说新语》,当为元至元二十四年八卷本,日本内阁文库藏,然彼处未载此评。为行文简便,本文所引评语仅于首次援引时注明出处。
⑥ 见张懋辰汇评本《世说新语》序跋。今人论之者如“《世说新语》以记人为主,记事为副,故其分门亦以人为准。然细别之,其分类之标准,甚不一致。有以人之行为为准者,如德行门、言语门、政事门、文学门等;有以人之性情为准者,如方正门、雅量门、豪爽门、任诞门等;有以人与人之关系为准者,如规箴门、宠礼门、轻诋门、惑溺门等。头绪纷纭,界域混淆,故事中多有分置不当之处”,参见马森《世说新语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1959年硕士论文。
⑦ 此举不免有分类过细之嫌,诚如《颖语》小序所言:“颖之于语,无类不有,惟谐、谑、讥、辩之类居多。然四语已有部领,即四语中有具颖者而颖部无与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谐、谑、讥、辩之语,斯成颖语矣”,参见曹臣《舌华录》,陆林校点,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10页。
⑧ 此处实则直录自《晋书·贾充传》,《晋书》又从《世说新语》而来。
⑨ 《世说新语》中另有一则曹操事,冯氏认为不足采信而未录入正文。他在此四则后注曰:“《世说》又载,袁绍曾遣人夜以剑掷操,少下不着,操度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此谬也。操多疑,其儆备必严,剑何由及床?设有之,操必迁卧,宁有复居危地以身试智之理!”参见冯梦龙辑《智囊》,缪咏禾、胡慧斌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⑩ 李贽批阅王世贞删定本《世说新语补》,并选取部分条目与《焦氏类林》的一部分合编成《初潭集》。带有李贽批语的《世说新语补》后被他人改题《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出版,书中批语确出其手,然非本人授意刊行。
⑪ 此书也受到了《太平广记》分类的影响,“《太平广记》的92大类中除了以事件分类外,已有以人性缺陷为纲目的较多内容,如奢侈、谄佞、谬误、诙谐、嘲诮、嗤鄙、酷暴等门类”,参见徐振辉《编纂高手 评论大师——从〈古今谭概〉看冯梦龙的编辑成就》,《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106-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