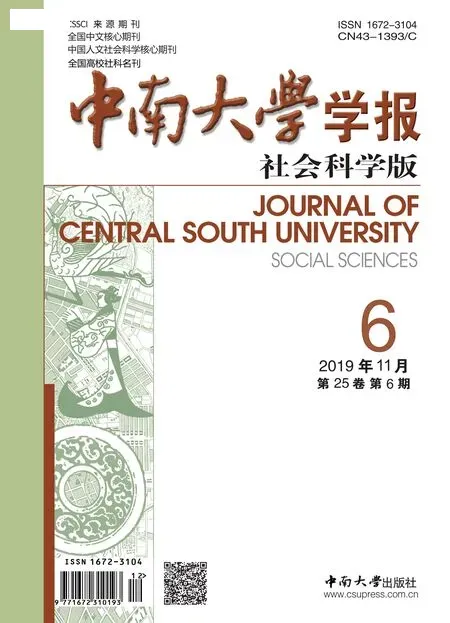“最A不过”与“再A不过”结构的来源与演变
2019-04-25张金圈
张金圈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一、前言
汉语中的“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是两个表达极性程度义的常见框架结构,其中的“最”“再”和“不过”是固定成分,A 是可变成分,由形容词充当,整个结构的语义相当于“极其A”,例如:
(1)歌唱,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1998年《人民日报》)
(2)荣德生说,“老先生是最清高不过的,别说支票金条决不肯收,有人送书画古董还被他扔出来呢。”(1994年《作家文摘》)
在现代汉语中,这两种结构里的“最”和“再”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自由互换,因此人们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并记为“最/再A 不过”。
关于这两种结构的来源,目前学界有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最/再A 不过”是由明清时期同样表极性程度义的“A 不过”结构通过添加“最/再”而来的。赵新说“普通话中已不使用‘A 不过’,而必须在形容词前加上‘再’或‘最’,变成‘再(最)A 不过’的格式”[1](75)。太田辰夫指出清代语料中的“~不过”可以表示“最……”的意思,也有在“不过”前面加上“最”的[2](165)。杨煜认为“A 不过”格式中的“不过”已经定型为后附成分,表示程度高,通常粘附在形容词后面,之所以在A 前加上“再/最”,可能是类推的作用,“不过”既可以粘附于形容词,也可粘附于形容词性词组,并且“再”有程度加深义,“最”是程度副词,所以加上“再/最”可以起到强调凸显的作用[3](36)。
第二种观点认为,“最/再A 不过”是由“N1 最/再+A+(也)+A+不过N2”这种含有最高量级假设意义的紧缩复句经过成分移位、成分省略、话题化和主语化等句法语义操作形成的。沈家煊最早提出这一假设,他用下面一组例句来论证该假设:
(3)a.你再和气也不过范家老奶奶。
b.你和气不过范家老奶奶。
c.范家老奶奶,你和气不过她。
d.范家老奶奶,和气不过她。
e.范家老奶奶真是(再)和气不过。
沈先生认为,a 句中的“不过”还是一个词组,主要意义是“不超过”,但因为出现在“再……也”的格式中,所以便有了“程度最高”的意思。b 句里的“不过”也可以分析为动结式的可能补语,“范家老奶奶”仍然是宾语。c 句“范家老奶奶”前移充当话题,“不过”失去了后面的宾语,但还留下一个复指话题的代词“她”。d 句又省略了主语“你”,到了e 句,复指代词“她”消失,话题“范家老奶奶”变为主语。此时,“不过”也就从短语变成了一个表示高程度的附着词[4](35-36)。
雷冬平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5],但并不完全同意沈先生的推导过程。他指出:沈家煊[4]推导“最/再……不过”格式形成的例句是“范家老奶奶……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儒林外史》)。此例所包含的格式是“A 不过”而不是“最/再A 不过”,这容易让人误解“最/再……不过”的形成是在“A 不过”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推导过程中涉及“最/再”的添加、省略然后再添加,整个推导过程如果一直保留“最/再”的话则不够顺畅。因此,雷冬平根据《红楼梦》中的“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这一用例拟测了如下逻辑推导过程:“凤丫头再巧巧不过老太太” →“凤丫头再巧不过老太太巧”→“凤丫头再巧不过老太太”→“老太太再巧不过”。其中,第一个箭头代表的推导过程属于句法移位,其动因是“直接成分尽早识别原则”导致的谓语后移;第二个箭头属于语义推导,承前省略相同性质的成分“巧”;第三个箭头代表的是话题化和主语化的语义句法推 导[5](115)。
比较、分析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点认识:其一,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重视历时语料的分析。他们发现,从出现的时间上看,“A 不过”结构在先,“最/再A 不过”结构在后,因此很自然地得出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而来的观点。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更注重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推导“最/再A 不过”的产生过程,有意无意地忽视历时语料的详细考察。其二,不论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都不自觉地将“最A 不过”和“再A 不过”等而视之,认为它们是同一结构的两个自由变体形式,不加区分地考察其产生过程与机制。
本文坚持从历时语料出发,对这两种结构的来源与演变提出新的认识。笔者认为,虽然在现代汉语中“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在表义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二者却有着不同的历史来源。其中,“最A不过”来源于明清时期表极性程度义的“A 不过”结构,而“再A 不过”则来源于“N1 再A 也A 不过N2”结构。二者异源同流,演变成现代汉语中表达极性程度的“最/再A 不过”结构。
二、“最A不过”的来源
(一)从“V 不过”到“A 不过”
赵新对近代汉语中的“不过”补语句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分析。他认为,“不过”补语句始见于宋代,宋元时期只有“V 不过”(即核心为动词)形式,可以表达可能、结果、状态等语法意义,其中可能补语表达的意义又可以分为“表示不能完成、不能实现、不能达到”“表示不能再持续”“表示不能胜过、不能超过”和“表示不能产生或具有”四种,分别举例说明如 下[1](70-71):
(4)我若横说,你又跨不过;我若竖说,你又跳不出。(《五灯会元》卷第18)——可能补语,表示不能完成不能实现不能达到。
(5)当时是皇亲葛彪先打死妾身夫主,妾身疼忍不过,一时乘忿争斗,将他打死。(《关汉卿全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可能补语,表示不能再持续。
(6)燕燕己身有什末孝顺,拗不过哥哥行在意殷勤。(《关汉卿全集·诈妮子调风月》)——可能补语,表示不能胜过不能超过。
(7)他两个的冤魂也放你不过。(《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可能补语,表示不能产生或具有。
(8)见扑鱼的,遂叫入酒店去扑,扑不过,输了几文钱。(《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结果补语。
(9)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关汉卿全集·感天动地窦娥冤》)——状态补语。
赵文指出,表结果的“V 不过”用例不多,和可能补语的差别仅在于语境不同;而表状态的“V 不过”都是“被V 不过”的形式,如“被逼不过”“被劝不过”“被羞辱不过”等[1](72)。笔者认为,这两种用法与表示不能持续的可能补语用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可以用“可能”来概括所有“V 不过”结构的语法 意义。
到明代时,“V 不过”结构依然使用广泛,并开始出现“A 不过”结构,例如:
(10)公子逃去两日,东不着边,西不着际,肚里又饿不过。(《二刻拍案惊奇》卷22)
(11)我在此闷不过,出外去寻个乐地适兴,晚间不回来也不可知。(《二刻拍案惊奇》卷21)
(12)这雪娥气愤不过,正走到月娘房里告诉此事。(《金瓶梅》第11 回)
(13)再三拷打,打得皮开肉绽。李吉痛苦不过,只得招做“因见画眉生得好巧,一时杀了沈秀,将头抛弃”情由。(《喻世明言》卷26)
(14)你又不在家中,没有一个知我心的,我冷落不过,故此将就容纳了乞儿。(《醒世恒言》卷23)
赵新将这种用在形容词之后的“不过”视为程度补语,认为其功能是“补充说明行为状态所达到的程度很高”[1](72)。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赵文并未使用常见的“性质状态”这一表述方式,而是改用“行为状态”。虽然作者并未刻意强调这一点,但笔者却认为,相较于“性质状态”,“行为状态”这一表述方式更为精准地概括了上述用法的本质。早期的“A 不过”中的A 大部分都是表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如上述例句中的“饿”“闷”“气愤”“痛苦”“冷落”等,而心理到底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行为,有时很难说清楚。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将“饿”标为形容词,而《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也将“饿”收录其中;《现代汉语词典》将表示生气的“气”标为动词,而将“气愤”标为形容词。也就是说,这些早期的“A 不过”都与“V 不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比下面例(15)—(19)中的“V 不过”与上文例(10)—(14)中“A 不过”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加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15)身边并无财物,受饿不过,少不得学那两个古人:伍相吹箫于吴门,韩王寄食于漂母。(《警世通言》卷22)
(16)亦且心下有事,焦焦躁躁,那里睡得去?闷坐不过,做下一首词。(《二刻拍案惊奇》卷9)
(17)这惠祥在厨下忍气不过,刚等的西门庆出去了,气狠狠走来后边,寻着蕙莲,指着大骂。(《金瓶梅》第24 回)
(18)姚大受痛不过,叫道:“老爷亲许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警世通言》卷11)
(19)且说筑玉夫人晚间寂守不过,有个最知心的侍婢叫做如霞,唤来床上做一头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34)
以上几例都是“V 不过”,属于赵新所说的“表示不能再持续”的可能补语用法。他认为,这类“不过”补语句的动词多具有忍受或坚持的意义,“V 不过”表示行为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1](71)。某种行为状态不能忍受、不能坚持,语义上已经隐含了“该行为状态的负面程度极高”的意义。沈家煊也指出,“程度最高”的意义是根据“不过量准则”和常识推导出来的隐含义,即“忍受不过去”的事情一定是负面程度极高的事情[4](35)。所以,从例(15)—(19)的用法发展出例 (10)—(14)的用法是很自然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A 不过”中的A 大部分都是表示负面状态的形 容词。
一旦“程度极高”的语义固定在“A 不过”这一结构中,A 就会逐渐突破早期的表心理行为状态和感情色彩上的限制,开始接纳表其他性质状态的中性甚至褒义色彩的形容词。这种用法的“A 不过”在明代还非常少见,但到清代就已经比较普遍了,例如:
(20)况且小娥有心机,申兰平日毕竟试得他老实头,小心不过的,不消虑得到此。(《初刻拍案惊奇》卷19)
(21)那月娥是个久惯接客乖巧不过的人,看此光景,晓得有些尴尬,只管盘问。(《初刻拍案惊奇》卷2)
(22)他专教人练硬功夫,癞团经、龙吞功,厉害不过的。(《七剑十三侠》第53 回)
(23)我那表嫂是个和气不过的人。(《儒林外史》第53 回)
(24)进得门来,一条甬道,都用云石砌得光滑不过。(《乾隆游江南》第1 回)
(25)讲到老弟你了,不但我信得及你是个学问高不过,心地厚不过的人;我是怎么个人儿,你也深知。(《儿女英雄传》第32 回)
(二)从“A 不过”到“最A 不过”
赵新认为在“A 不过”前边加上“最/再”就产生了“最/再A 不过”结构,但他并未解释原因[1](75)。杨煜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在A 前加上“再/最”,是为了起到强调凸显作用[3](36)。雷冬平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最/再A 不过”与“A 不过”两个结构不存在衍生关系,因为无法解释“最/再”的出现,二者的形成有着不同的来源[5](115)。因此,他完全撇开“A 不过”结构,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最/再A 不过”的来源。笔者认为,杨煜[2]和雷冬平[5]都正确地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又都忽视了另一个方面。“A 不过”结构表示程度极高,为了强调、凸显这一意义,在前面加上同样表示极性程度义的副词“最”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解释的;但“再”却不一定,因为“再”本身并不能表达极性程度义,所以从“A 不过”到“再A不过”确实是无法解释的。
历时语料表明,“最A 不过”在十八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而“再A 不过”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这种时间层次上的不一致也显示二者来源上的不同。下面是“最A 不过”的早期用例:
(26)只要凭据写的结实明白方妥,胡大爷也是最精细不过的人。(《绿野仙踪》第17 回)
(27)昨年又请了个吴先生,是江南人,于营伍中事,一点梦不着,且又最疲懒不过。(《绿野仙踪》第28 回)
(28)苗三爷是大爷最厚不过的朋友,问他那心,还不如个婊子哩。(《绿野仙踪》第53 回)
(29)黄天霸跟得日久咧!不知他是最奸不过的坏骨头。(《施公案》第106 回)
(30)好在县太爷是个最清不过的青天,将来不致使你含冤负屈。(《施公案》第378 回)
《绿野仙踪》成书于十八世纪中期,《施公案》现存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道光四年(1824)刊本,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这两本书中,都只有“A 不过”和“最A 不过”,没有“再A不过”。
在稍晚些的语料中,“A 不过”前边还可以加上其他表高程度义的词来凸显强调极性程度义,例如:
(31)蒋福那东西顶坏不过,恐怕他未必就此干休。(《官场现形记》第5 回)
(32)这种狗最是娇嫩不过,经不起摧残,一着地,哀号一声,滚了几滚,四脚一伸死了。(《孽海花》第27 回)
(33)一些邻居以及家中的庄汉都过来叫喜,阶下乐鼓齐作,堂前灯烛辉煌,十分热闹不过。(《续济公传》第194 回)
雷冬平未区分“最A 不过”和“再A 不过”,认为它们都来源于“N1 最/再+A+(也)+A+不过N2”结构[5](115)。笔者认为,就“最A 不过”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的困难。事实上,雷文的具体分析基本都是针对“再A 不过”进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解释的局限性。
首先,“N1 再A 也A 不过N2”(“你再巧也巧不过她”)是一种通过N1 量级变化的无穷性来凸显N2程度高的表达方式,这种说法及与之类似的“N1 再A也不如N2(A)”十分常见;而“N1 最A 也A 不过N2”(“你最巧也巧不过她”)的说法则非常少见,在雷冬平举的例子中也只有“最亲亲不过夫妇”一个[5](114)①。这种情况在历时语料中同样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再A 不过”,在同期的语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若干类似于“N1 再A 也A 不过N2”的用例,但在整个清代的语料中,我们却没有发现与“N1 最A也A 不过N2”相关的用例。其次,例(31)—(33)的说法更难以从“N1 顶/最是/十分A 也A 不过N2”之类的结构发展出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A 不过”(而非“再A不过”)是在原本就表达极性程度义的“A 不过”结构前加程度副词“最”而来的(而非来源于“最A 也A不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A 不过”本来就可以表达极性程度义,为何还要在前边附加高程度义副词“最”呢?这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考察语料发现,“A 不过”中的A 大部分都是双音节形式,从而形成一个由两个基本音步组成的“2+2”稳定结构;单音节形容词充当的“A 不过”结构独立性较差,除非构成对举形式(如例(25)),因此为了保证由单音节形容词充当的“A 不过”结构的稳定性,说话人便可能在前边附加上一个语义相宜的单音节副词“最”,从而形成一个“2+2”的音步组合。其二,可能由于方言的差异,某些地域的说话人对“A不过”结构表达的极性程度义感受不明显,因此便又在前边附加表达高程度义的副词“最”(前加“顶/最是/十分”也是同一道理),从而使这种极性程度义更加显豁。
三、“再A不过”的来源
关于“再A 不过”结构的来源,笔者同意沈家 煊[4]和雷冬平[5]的观点,即认为“再A 不过”与明清时期表示极性程度义的“A 不过”之间不存在衍生关系,前者是“N1 再A 也A 不过N2”结构通过移位、省略、话题化和主语化等句法语义操作而生成的。下面笔者将结合历时语料对这一演变过程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雷冬平曾举到《红楼梦》(成书于十八世纪中叶)中的一个例子——“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他认为该例就是“N1 再A 也A 不过N2”结构,“最/再A 不过”正是在这种用法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即:“凤丫头再巧巧不过老太太”→“凤丫头再巧不过老太太巧”→“凤丫头再巧不过老太太” →“老太太再巧不过”[5](115)。
通过分析语料,笔者认为《红楼梦》中该例句的“再”并不像“N1 再A 也A 不过N2”中的“再”那样表示“无论怎么”等让步假设义,而是相当于一个转折连词。“汉典网”(http://www.zdic.net/z/15/xs/518D.htm)中“再”的一个义项即是“表示转折,相当于‘却’、‘也’”,举例为《红楼梦》中的“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怄的人难受”。除此之外,《红楼梦》中还有如下“再”表转折的例子:
(34)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第22 回)
(35)宝钗道:“你只怨我说,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后的形景。”(第34 回)
(36)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第77 回)
所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凤丫头凭他怎么巧,也巧不过老太太去”。虽然该例句中没有出现表程度增加义的“再”,但它的确表达了与“N1 再A 也A 不过N2”相同的凸显最高量级的让步假设义。在笔者调查的语料中,没有发现“N1 再A 也A 不过N2”结构的实际用例,但表让步假设的“再……也……”结构从明代到清代确实一直存在着,例如:
(37)只拣足色细丝,或积三分,或积二分,再少也积下一分。(《醒世恒言》卷3)
(38)中宗也叫:“老元勋苏醒!”由你叫时,再叫也叫不醒。(《薛刚反唐》第96 回)
其中的“再”都表示假设的让步,相当于“无论多……”“无论怎么……”[6](85)。《儿女英雄传》中还有这样一例:
(39)但是嬷嬷爹嬷嬷妈怎么重也重不过老爷太太去;也重不过家里这个大局去。(《儿女英雄传》第36 回)
其中的“怎么重也重不过老爷太太去;也重不过家里这个大局去”就相当于“再重也重不过老爷太太去;再重也重不过家里这个大局去”,这说明,“N1再A 也A 不过N2”的说法在清代时期的汉语中是完全可以存在的。
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的语料,发现“再A 不过”结构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例如:
(40)我金荣胆量是再小不过,经不住被吓。(《续济公传》第224 回)
(41)他本是西湖灵隐寺的一个疯和尚,那知他却然是佛前知觉金容罗汉转世,道行是再大不过。(《续济公传》第234 回)
(42)心里只是想,哪晓得兰儿再灵活不过,早把缰绳一拎,坐下的胭脂马就靠拢过来。(《西太后艳史演义》第5 回)
(43)原来这位旗大爷,再贪财不过,再好色不过。(《西太后艳史演义》第13 回)
坑余生所著《续济公传》是我们所见的最早使用“再A 不过”结构的文献。据林辰研究,自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先后顺序的济公故事续书,其中“四续”约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续”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坑余生所著乃“六续”和“七续”。由此可知,例(40)(41)中“再A 不过”的用法最早也应在1908年之后才出现[7](95)。
“再”修饰形容词时只能表示程度增加[8](643),本身并不表达极性程度义,因此“再A 不过”不可能是在“A 不过”前直接加“再”产生的。它只能来源于“N1 再A 也A 不过N2”这种含有极性程度义的无条件让步假设句。在《儿女英雄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用法:
(44)何小姐这才放手,说:“滑再滑不过你了!也不知真话哟,也不知赚人呢!”(《儿女英雄传》第32 回)
(45)我们德州这地方儿,古怪事儿多着咧!古怪再古怪不过我们州城里的这位新城隍爷咧!(《儿女英雄传》第22 回)
例(44)中的“滑再滑不过你”的底层结构应该是无条件让步假设句——“再滑1 滑2 不过你”,由于该句表达的核心信息是“你滑2”,所以当要凸显述位成分“滑2”时,将其前移话题化,就形成了例中的“滑2再滑1 不过你”;同理,如果需要凸显的是主位成分“你”,则将其前移便形成了“你再滑1 滑2 不过”,两个相同语素紧邻合并,便形成了“你再滑1+2 不过”。可以将这一推导过程概括如图1所示。

图1 “你再滑不过”结构的推导过程
根据太田辰夫的研究,《儿女英雄传》成书于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年)[9](222)。也就是说,“N1 再A也A 不过N2”结构出现的时间早于“再A 不过”,这也是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的必要前提。
四、“最A不过”与“再A不过”结构的合流与微殊
(一)“最A不过”与“再A不过”结构的合流
虽然来源不同,但由于“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都可以表示极性程度义,且形式高度相似,所以逐渐出现合流的趋势。到现代汉语中,二者在句法语义功能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比较下列例句:
(46)a.所以,夫妻间昵称,叫“老伴”,最恰当不过。(《读者》(合订本))
b.这句已流传几十年的名言,放到黄东华烈士身上,再恰当不过。(2000年《人民日报》)
(47)a.那通常不是什么珍馐百味,而是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张小娴《把天空还给你》)
b.在中原乡村,手擀面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饭。(1998年《人民日报》)
(48)a.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行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法轮功”反人类、反科学和反社会的罪恶本质。(新华社2001年2月份新闻报道)
b.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的共同立场。(2000年《人民日报》)
(49)a.虚荣和私欲是孪生兄弟,这在张宗玲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不过了。(1994年报刊精选)
b.在这里,婚姻和抚育的密切关系,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读书》)
由上述例句可见,“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都可以自由地充当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互换以后完全不影响语义的表达。因此,前人都不自觉地将这两种结构视为自由变体形式并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进行讨论②。
(二)“最A不过”与“再A不过”结构的微殊
虽然“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两种结构在形式和功能上高度相似,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相同,它们仍然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句法形式和使用频率上。
从句法形式来看,“最A 不过”存在“最是A 不过”“最为A 不过”和“最最A 不过”等变体形式,而“再A 不过”没有对应的“再是A 不过”“再为A不过”和“再再A 不过”;相反,“再A 不过”可以加入“也”字形成“再也A 不过”和“再A 也不过”,而“最A 不过”没有对应的“最也A 不过”和“最A也不过”。例如:
(50)可是吴声豪却说,“惊梦”里幽会那一段,最是露骨不过的。(白先勇《游园惊梦》)
(51)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概括整个考研过程,“This is one step—choosing a goal and sticking to it—changes everything !”这句话最为恰当不过。(网络语料)
(52)几乎全部的俄国文学能为英国读者读到,颁发给她一个荣誉称号才是最最恰当不过的呢。(《读书》)
(53)这几句话的用意再也明白不过。(金庸《天龙八部》)
(54)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比喻工人作家邢绍忠所走过的文学道路,是再适合也不过了。(新华社2001年2月份新闻报道)
我们认为,这种形式上的差异与二者的来源不同有关。“最A 不过”是在原本就表示极性程度义的“A不过”前加高程度副词“最”产生的,所以可以在“最”后再加上仅起补足音节作用的“是”“为”或为了进一步凸显程度义而重复“最”;而“再A 不过”是由“N1再A 也A 不过N2”经过移位、省略等句法语义操作演变而来,“再也A 不过”和“再A 也不过”等用法正是源形式中的“也”遗留造成的,可以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
两种结构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异可以按照句法形式的不同分成两类来考察:一类是“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后加“了”的情况,一种是不加“了”的情况。
当“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后不加“了”充当各种句法成分时,二者在使用频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再A 不过”共出现603 例,“最A 不过”出现391 例,二者的比例约为1.5∶1。
当“最A 不过”与“再A 不过”后加“了”时,在句法上主要充当谓语或系词“是”的宾语。此时,二者的使用频率存在极大的差异。在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再A 不过了”共有362 例,而“最A 不过了”却只有42 例,二者的比例接近9∶1。
笔者认为,“最A 不过了”与“再A 不过了”在使用频率上的巨大差异也与其来源有关。两种结构中的“了”都是传统所说的“了2”,而“了2”的主要语法功能就是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8](351),这与“再A 不过”的源结构“N1 再A 也A不过N2”中隐含的程度无条件变化义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再A 不过”后更容易加上“了”。由此也可见“保持原则”在语法演变中的强大力量[10](19-20)。
五、结语
语言的历时发展就像河流一样,既有支流的合并又有干流的分叉。原本相同性质的成分可以变成不同的成分,原来不同的成分也可能合而为一。在现代汉语中,“最A 不过”和“再A 不过”两种结构的功能完全一致,形式也高度相似,因此研究者常常将其视为同一结构的自由变体,并想当然地以为它们也有着共同的来源,恰如一般人想当然地认为现在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群众都是一脉相承的炎黄子孙。共时层面的同质性掩盖了历时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可能性。通过全面深入地分析历时语料,我们发现“最A 不过”和“再A 不过”两种结构其实有着不同的来源,“最A 不过”是在明清时期表示极性程度义的“A 不过”结构基础上,为了凸显强调程度义而前加高程度义副词“最”而产生的,所以它可以有“十分A 不过”“万分A 不过”“顶A 不过”“太A 不过”等相关形式和“最为A 不过”“最是A 不过”“最最A 不过”等变体形式。而“再A 不过”则是由“N1 再A 也A 不过N2”这一表极性程度的无条件让步假设句经由移位、省略、话题化和主语化等句法语义操作演变而来,所以它可以有“再也A 不过”“再A 也不过”等变体形式。二者在产生年代上也有一定差异,“最A 不过”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而“再A 不过”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在现代汉语中,二者的句法语义功能逐渐合流,但形式上仍有细微差异,“再A 不过”在使用频率上更占优势。
语法化是一种考察语法演变的理论和方法,一些学者将其分成历时语法化和共时语法化,其中共时语法化研究又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是考察当前较短时间内发生的语法演变,虽然某个语法化过程只有几年至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但研究者仍注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与语法演变之间的关系;另一个角度则完全撇开具体的时间顺序,转而从逻辑顺序上解释某个语法演变的过程和机制,其分析过程强调逻辑上的合理顺序,而不重视语料出现时间上的绝对先后顺序。在缺乏历时语料的情况下,这种以逻辑先后代时间先后的做法有其必要性,而且严格、合理的逻辑分析得出的先后顺序也应该是与时间上的客观先后顺序相一致的。但是,在具备充分的历时语料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尽量避免这种以逻辑先后代时间先后的做法,当二者的分析不一致时,我们应该首选从历时语料分析得出的客观时间先后顺序。
注释:
① 雷冬平还提到“最毒不过妇人心”这一用法,认为其完整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事物最毒(也)毒不过妇人心”→“事物最毒(也)不过妇人心毒”→“事物最毒(也)不过妇人心”→“最毒不过妇人心”[1]。笔者认为,“最毒不过妇人心”与“最毒也毒不过妇人心”没有结构上的联系,“最毒不过妇人心”应该是“妇人心最毒不过”的修辞性表达(比较“新嫂嫂最乖不过”(《官场现形记》)),而“妇人心最毒不过”则是由表极性程度的“妇人心毒不过”直接加“最”而来的,也就是说“最毒不过妇人心”中的“最毒不过”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最A 不过”结构。“最毒不过”与“妇人心”之间类似于同位关系,即“最毒不过的是妇人心”。
② 有意思的是,由于两种结构形式和功能上的高度一致性,有的学者即使在声称研究某一种结构的情况下,也会不自觉地在举例中出现另外一种结构。例如吴芝欣、谭晓平只以“再+X+不过”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时却无意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而一般我们说‘他最聪明不过了’,并不只是以其他同学为参照,而是根据我们心中的标准所作的主观评价和客观上对该事物的比较分析”[11](63-64)。李泉主编《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Ⅱ)》第18页将“再……不过了”作为一个语法点,笔者在为留学生就该语法点举例讲解时,也会下意识地说出“最……不过了”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