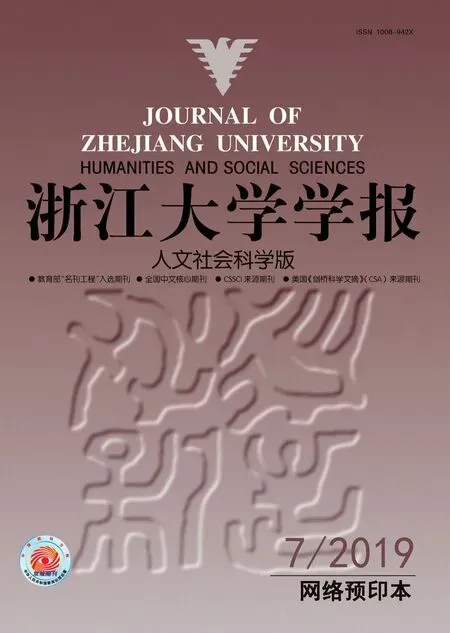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2019-01-03吴涵昱
吴涵昱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一、 问题的提出
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是保险法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明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是完善被保险人保护的前提。
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我国学者对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解读可以“关系人地位说”加以概括。具体来说:投保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负担保险费给付义务;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事故发生时因受损失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1]35。然而,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一些分歧:有观点认为,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同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1)此类观点参见李玉泉《保险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王伟《保险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还有观点认为,只有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而投保人可以解释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或者替代被保险人办理保险的保险活动参与者(2)此类观点详见宋耿郎《论保险法上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之权利义务》,载《保险学刊》2011年第27期,第87-109页;谢克《保险法视野下被保险人权利问题研究》,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2页;游源芬《关于保险当事人与关系人之异议——与〈保险学原理〉一书商榷》,载《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34-38页。。那么究竟哪个观点更合理呢?
如何科学认识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事关保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分配及其正当性。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二、 被保险人合同关系人地位的反思
在我国保险法学界,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一直是学界通说。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依照传统民法,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合意,一方的要约经另一方的承诺,即当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合同始能成立。而从保险合同订立的实然层面观之,达成保险合意的双方不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并非缔结保险合同的主体,却因保险合同的订立而享有保险合同上的独立请求权,其与保险合同有经济利益关系,故可将其视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投保人则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这样的定位虽然符合民法理论,但从保险合同的实然层面观之,却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首先,一般民事合同的当事人享有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却因为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构性差异而只承担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并不享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2]30。与此相反,被保险人虽未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却享有合同项下的请求保险金的权利并可根据自己的意旨将保险金让渡给受益人(3)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受益人的指定或变更均须依被保险人之意思,换言之,受益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系经被保险人转让而取得的,因此该项保险金请求权本质上仍是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这显然不完全符合民事合同中合同当事人与合同关系人的标准。
其次,从《保险法》的具体规定来看,尽管投保人被认定为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仅为合同的关系人,但是我国保险立法赋予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数量却明显多于投保人。在权利方面,《保险法》赋予被保险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4)参见《保险法》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同意权(5)参见《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四条。这两条分别规定了普通人身险与死亡险中被保险人的同意权。及对同意的撤销权(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被保险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和投保人撤销其依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作出的同意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保险合同解除。”、单方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7)参见《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8)参见《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三款:“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在义务方面,《保险法》规定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后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时的通知义务、向保险人提供资料的协助义务、维护保险标的安全及事故发生后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损失的义务。反观《保险法》对投保人权利和义务的设置,仅体现在《保险法》第十五条的投保人合同任意解除权、第十六条关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第二十一条的通知义务、第二十二条的协助义务以及第三十五条的缴费义务。被保险人作为一个合同关系人,法律对其权利义务的规定竟如此之多,这在一般合同中是难以想象的。且在权利的性质上,有些权利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合同关系人所应拥有的权利的界限。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被保险人享有同意撤销权,该权利行使的法律后果与合同解除一致。换言之,被保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对保险合同进行实质性的干预,这是“合同关系人说”根本不能解释的,因为通常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对合同的存续行使权利。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保险合同是一种将不幸集中到某一个体身上的危险通过保险的危险分担法则分散给社会公众而使之消化为无形的特殊合同。而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恰恰是保险合同分散风险、补偿损失、防灾防损功能最集中的体现。具体而言,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当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必然会因此而遭受财产或利益上的损失,保险人通过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使其能够重新购置财产、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以达成保险目的。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合同的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虽然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当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遭受损害之时,其本人或家庭必然会遭受重大的经济影响,需要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以弥补其损失[3]14。由此可知,保险合同是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的,被保险人才是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该特征直接造成了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构:投保人虽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人,但其在合同成立后仅享有保险合同项下有限的、经约定才有的部分权利,其当事人的地位具有限缩性的特征。而被保险人虽然不一定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但因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保障其在法律上所承认的利益,故而被保险人虽是合同关系人,但其权利和义务具有扩张性的特征,实际上已与合同当事人并无二致。因此,单纯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妥当。
三、 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重构: 实际当事人
(一) 合同当事人: 理论上难以自洽
既然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关系人并不妥当,那么是否可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的当事人呢?笔者认为,直接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当事人在理论上恐难以自洽。
其一,被保险人不是订立合同的主体。诚如前述,达成保险合意的双方不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虽然在订立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等特定保险合同的情形下,投保人对保险标的进行投保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然而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的同意与作为合同成立要件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要约表示接受,并不能同日而语。一方面,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的同意只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人格尊严及生命安全,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发生所采用的必要防范措施,实为政策性考量的结果,与意思表示并无直接关联。另一方面,许多保险也并非一定需要被保险人同意方可投保。何况在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方可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同意并非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而仅仅是效力要件。综观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进行投保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不外乎两种情形:(1)《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为与其不具有特定亲属关系及劳动关系的人投保人身保险的,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该人身保险合同无效。(2)《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从上述两个条文的文意看,此处所称的“被保险人同意”仅是保险合同的效力条件,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并不构成影响。由此可以反推,被保险人的同意并非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虽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能够成为合同当事人的,并不一定必须参与合同的订立,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有些主体虽未参与合同的订立,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合同当事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的法定的合同概括承受及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买卖不破租赁”。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情形与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状态均有所区别。因为上述情形均存在一方退出合同关系、另一方进入合同关系并承受合同项下所有权利义务的情形,而保险合同中并不存在这一情形。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而为二的情形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权利义务上存在天然的分离。因此,欲以法定的合同概括承受及“买卖不破租赁”这两个典型例子来阐述在订立合同时未做出意思表示的第三人也可成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难以达到证成效果的。
其二,代理理论无法解释被保险人的合同当事人地位。有学者认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可以将投保人解释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而将被保险人定义为保险合同当事人[4]36。然而,依据民法代理的理论,代理人通常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活动的,而最终的法律效果归于被代理人。按此原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也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然而依据《保险法》,投保人依然是缴纳保险费义务的承担者。因此,民法上的代理理论难以圆满解释《保险法》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
其三,无因管理理论也无法解释被保险人的当事人地位。有学者认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投保人的行为系属无因管理。在保险领域,风险的转移虽为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但是如果风险个体以外的人愿意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投保,此举不仅不违背保险制度的社会风险管理本质,且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障(9)参见窦玉前《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研究》,黑龙江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4页。。然而《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付的“必要费用”。按此规定,若投保人系被保险人的无因管理人,则其应有权向被保险人请求支付必要费用。而在我国及域外保险法中均未见此等规定,也没有发现过此等做法。因此,无因管理理论也难以解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关系的实然状态,以无因管理来诠释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逻辑上无法成立。
(二) 实际当事人: 现行法律框架下可选择的一种变通方案
如前文所述,将被保险人定义成合同关系人与被保险人在保险法中实际所享有的核心地位及所拥有的权利义务相矛盾,将其定义为合同当事人又存在民法理论上的困境,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呢?笔者认为,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实际当事人概念并对被保险人予以实际当事人的定位,可能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而所谓的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是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但其所拥有的实际地位、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已经相当于合同当事人。
首先,实际当事人的引入及其定位符合法学变迁的规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法律应该与时俱进。对法学而言,新生事物的出现意味着需要对既有法学概念进行重新检验,以消解因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新的价值冲突。而从法的经济分析来看,现行的法律典章制度是先前微观个体互动汇集加总的结果,在特定的时点上体现了一定的均衡[5]44-46,因此,法律的变迁应是渐进式的,即面对社会变迁,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处理新出现的法学疑难:捍卫原有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但不能死守教义,在外围概念上可以松绑,以便当社会发展到新的均衡时能够较大幅度地修改法律典章制度[5]45-54。事实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为了满足日益变化的商事交易的需要,早就开始突破传统民法概念的藩篱,进行了概念和理论的创新。例如,商事代理(如经理权)的代理范围与传统民法不同,其不完全取决于本人之意思,而是主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而民法中的意定代理原则上依照本人的意思发生[6]20。依照民法学说,意定代理是扩展本人的意思自治,补充延长其“手足”的必要手段[7],体现了本人的私法自治权。而在商法背景下,这样的理论就无法完全解释商事代理的权利来源。又如商事留置与传统的留置在条件上也有所不同:传统民法的留置权对债与留置物之间的牵连关系要求较高;而在商事留置中因商事主体交易频繁,留置物与债权难以一一对应,为排除牵连关系的举证困难,商事留置权与债权不受同一法律关系制约[8]84。再如,公司法中的“实际控制人”这一概念,就是应因公司发展的实践而在公司法中引入的新概念。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在一般的情形中,能够控制公司的通常是公司的股东,但在公司中也会存在非股东对公司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实际控制公司的情形。因此,法律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对非股东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地位也进行了认定。商法是开拓者,而非守成者,其生命力和价值在于鼓励、保障和规制具有营利性的商业交易,法律逻辑和概念体系则处于次要地位(10)商法体系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扩充性,与市场经济运行高度契合。商法必须不断适应新的交易形式,因此始终没有形成闭合的体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参见赵旭东《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43页、46页。。保险合同作为特殊的商事合同,在认定这种特殊商事合同中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之时,也应当对传统的民法概念进行变通,否则在理论上将陷入困境。如前文所述,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保障的对象,在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虽然在现有理论上被保险人难以被定位为合同当事人,但根据其实际的重要性,可以借鉴公司法中“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将被保险人认定为实际当事人。这样的认定既不会冲击传统的概念体系,也应因了保险制度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并符合法学变迁的规律。
其次,实际当事人概念的引入与定位并不违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相反,这一定位与保险法的立法意旨高度契合。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对被保险人是这样定义的:“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这一条款中,并未明确说明被保险人只是合同关系人,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合同关系人仅是目前学理上的一种见解。而且,从该款的文意看,既然被保险人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那么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更能体现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特点。更何况,从我国保险法体系设计来看,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实际上并不享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其所承担的义务在数量上也少于被保险人。投保人的重要性不如被保险人尚且能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核心主体,其法律地位更不应低于投保人。因此,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也是可行的。
再次,将被保险人定位为实际当事人可从域外法中找到相关参照依据。在域外法中,英美保险合同法一直采用二元主体的模式,即保险合同的双方主体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被保险人既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负担保险费的给付义务;又是受保险合同保障之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当然,英美的二元模式有其历史文化的原因。在保险制度发展初期,大多数人购买保险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被保险人自己就是缔约主体,自无须加以区分,且西方国家社会的典型特点系个体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较强,亲属之间的联系较弱[9],人们通常不会干预他人事务,为他人买保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第三人利益购买保险的事例也逐渐开始增多。为了适应这种情形,英国保险合同法于“二元模式”基础上,另以制定法形式通过在财产保险中约定“loss payable clause”条款、在人寿保险中指定第三受益人或转让保险单三种方式为“利益第三人契约”提供法律依据(11)参见窦玉前《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研究》,黑龙江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3页。。而对“利益第三人契约”采取宽大态度的美国,其保险合同法架构之原则和例外则与英国保险合同法并无多大差异,只是在保险实务上,亦有称人寿保险之当事人为申请人,而称以其生命为保险对象之人为被保险人,但此为少数情况(12)同上。。由此可见,英美法国家并未因为他人投保的需求而改变被保险人、保险人二元主体的架构,被保险人依然是合同的当事人。这与英美法系注重实践多于概念体系的传统是相关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利益的所有者,是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英美法对被保险人地位的定位正是基于被保险人在实践中所实际具有的功能以及重要性。英美法灵活性与实用性的特点值得我国法律借鉴,其二元主体的模式也为被保险人实际当事人的地位提供了域外法的参照依据。
总之,实际当事人的定位既能体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特殊性,又不至于破坏传统民法的理论体系。“实际当事人”在字面上更能体现被保险人的核心地位,而“合同关系人”则无法体现该主体的重要性。在内涵和功能上,实际当事人的定位也能为法律进一步加强被保险人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四、 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立法实现
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被保险人的权益保护。诚如前述,在理论上被保险人应当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然而理论上的定位并不能保证被保险人在现实交易中的权益不受损害,因此需要法律予以保驾护航。虽然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有了一定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建立在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的理论基础上的,这就导致了法律对被保险人的保护依然不够充分,被保险人的核心利益在实践中屡受损害。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确立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理念,在以被保险人为实际当事人的认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立法。
(一) 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赋予了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当然不成问题。但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而为二时,如果投保人可不通知被保险人而任意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则会使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落空,这显然会对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严重侵害。2015年11月25日颁行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回应,根据该条规定,当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时,被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人的解除行为无效。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磋商权,以便使被保险人有机会替代投保人继续履行保险合同。然而,该条依然只是在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关系人的基础上稍微增加了对被保险人的保护力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保险人利益受损的问题,因为该条对投保人解除合同前的通知义务、被保险人的介入权等均没有明确规定,而在投保人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境下,规定被保险人的介入权与投保人的提前通知义务恰恰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被保险人的介入权是指被保险人在接到投保人欲解除合同的通知之后有根据自己的意志加入原保险合同关系,取代投保人而与保险人形成保险合同关系的权利。之所以有必要规定被保险人的介入权,首先是因为在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情境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已经破裂甚至反目成仇,投保人未必愿意让被保险人继续享有保险保障(13)例如离婚的一方解除对另一方的人身保险,在这种情境下,双方关系恶劣,投保人不一定会同意让对方继续享有保险保障。。如果投保人拒绝与被保险人达成合同地位让与的合意,则被保险人对原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就会落空,这对被保险人是十分不利的。其次,被保险人介入权的赋予并不会损害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利益。一方面,被保险人介入权的赋予,使本来应当解除的保险合同关系因被保险人的介入而继续承续,保险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继续缴纳保险费,这对保险人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对投保人而言,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利益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需要继续缴纳保险费;二是可以获得保险单项下的现金价值。对于第一项利益,被保险人因介入而成为保险合同新的投保人,自然应由其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对于第二项利益,法律可以规定,若被保险人行使介入权,则其须承担向投保人支付保单现金价值的义务以平衡双方的利益。
而通知义务的设立之所以有必要,乃是因为投保人很有可能在被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形下解除合同致使被保险人没有时间介入保险合同并支付对价以取代投保人的地位。而法律加设通知义务可以让被保险人有时间采取措施并行使介入权,以保护其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然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并未对此予以规定。
事实上,如果继续维持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的定位,则该制度也很难再向前推进,因为被保险人并非合同的当事人,法律赋予被保险人介入权并规定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会面临理论上的困难。具体而言,被保险人的介入权本质上系属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抑或是对投保人任意解除权某种程度上的限制。而合同关系人不同于合同当事人,其在合同中的地位弱于合同当事人,即便其在利益上与合同相关,也无法对合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干预。法律也很难仅仅因为顾及合同关系人的利益而去限制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如若确立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的地位,则被保险人在合同解除之时介入合同关系在理论上就能够成立了,因为此时被保险人的地位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法律为了平衡合同主体间的利益而赋予其介入权,并不会违背传统的理论认知。且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合同当事人在行使权利之时不得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也必须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投保人在行使解除权之前对被保险人负有通知义务,被保险人有权行使介入权替代投保人继续维系保险合同的关系,均存在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应当基于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的地位赋予被保险人对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介入权,即投保人在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时,应提前通知被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愿意以支付退保金或继续缴纳保险费的条件参与到原保险合同中来,则应尊重被保险人的意愿,以保护被保险人的期待利益。
(二) 中止与复效制度的完善
基于人身保险长期性、储蓄性等特点,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规定了人身保险合同的中止和复效制度,但这些规定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方面存在明显缺失。第一,《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根据这一规定,在投保人未缴纳当期保险费且超过宽展期的情形下,保险人不能以诉讼的方式追讨欠缴的保险费,也不能直接终止合同,而只是使保险合同的效力暂时停止。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人身保险合同的缴费期限较长,投保人难免因主观的疏忽或客观的苦衷使其保险费的交付有所延误[3]193。应该说这一规定对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该规定并不周延,缺失了有关保险人催缴保险费义务的规定,这极易使被保险人的权益受损(14)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了催告,但这并非保险人的义务,且也没明确催告之时应当告知其不缴纳保险费的法律后果。。因为在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身保险合同缴费期限内,投保人迟交或忘交保险费当属常见现象,若保险人怠于催缴,再以中止为由拒赔,则被保险人的利益必然受损。何况在保险合同关系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往往欠缺法律知识,他们未必知道欠缴会产生保险合同中止的法律后果。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分离时,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和,投保人接到通知后故意不缴纳保险费,被保险人对此毫不知情,其利益也会受损。第二,《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虽然规定了保险合同中止后两年内投保人可以申请复效,以尽可能保证原有保险合同的延续,但保险合同的复效须满足“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并达成协议”这一前置条件。这就将复效的主动权完全交到保险人手中,极有可能使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落空。虽然《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对此问题有了回应(15)《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保险费的,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确拒绝的,应认定为同意恢复效力。”,否定了协商机制,使得保险人拒绝复效的权利受到限缩,然而,对于复效时投保人是否要承担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是否有权申请复效等与被保险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依然没有规定,保险人仍有可能利用这些空白而拒绝复效,从而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上将被保险人视为合同关系人而造成的,因为依照传统理论,既然被保险人仅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则法律只需稍稍兼顾其利益即可,不必对其利益太过关注,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才是优先需要顾及的。倘若采用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的理论定位,将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保险合同保障的核心,则上述问题就可避免。既然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则其理应享有申请复效的主体资格;在保险合同中止之前,保险人理应负有催缴保险费并说明后果的义务,且该义务不但要向投保人履行,也需向被保险人履行,以防止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和或投保人故意不缴纳保险费致使被保险人无法维持保险保障等情形的发生。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核心地位并保障其利益,应在保险合同的中止制度中增加关于保险人催缴保险费并说明后果的义务规定。在复效制度中,应对投保人在复效时是否要承担告知义务做出明确规定,并明确被保险人申请复效的主体资格以充分维护其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这样的修改能够更加体现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以及保险合同核心主体的地位。
(三) 团体保险受益主体的限制与契约转换权的设立
我国现行《保险法》欠缺团体保险中对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规范。团体保险的目的在于推行员工福利,并为员工提供经济保障,因此,团体保险应以被保险人权益作为保护的重点。然而,就目前保险立法来看,这方面的规定严重缺失。一方面,我国《保险法》中并没有明文设置受益人的指定或变更应排斥团体单位的条款,这极易使投保团体险的企事业单位以被保险人指定或经被保险人同意为借口,将本当属于被保险人及其家属的利益通过所谓的“经被保险人同意或指定”而归属于该团体本身,从而侵害被保险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国《保险法》未赋予被保险人契约转换权,即当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成员与团体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后,被保险人有将团体人身保险合同转换为个人人寿保险的权利,该缺失无疑会使作为团体成员的被保险人利益受损[10]119。
在被保险人既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又是保险合同核心主体的理论定位下,上述规则的完善也会有更强的理论支撑。一方面,应借鉴域外法的经验(16)美国有一些州的法律已经规定了团体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保险法》就对此进行了规定,参见La.R.S.22:176(10):″Conversion on termination of eligibility. A provision that if the insurance, or any portion of it, on an individual covered under the policy ceases because of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or of membership in the class or classes eligible for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such individual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issued to him by the insurer, without evidence of insurability, an individual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 without disability or other supplementary benefits, provided application for the individual policy shall be made and the first premium paid to the insurer within thirty-one days after such termination.″ La.R.S.22:176(11):″Conversion on termination of policy. A provision that if the group policy terminates or is amended so as to terminate the insurance of any class of insured individuals, every individual insured at the date of such termination whose insurance terminates and who has been so insured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prior to such termination date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issued to him by the insurer an individual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 subject to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as are provided by Paragraph (10) of this Section, except that the group policy may provide that the amount of such individual policy shall not exceed the smaller of (a) the amount of the individual’s life insurance protection ceasing because of the termination or amendment of the group policy, less the amount of life insurance for which he is or becomes eligible under any group policy issued or reinstated by the same or another insurer within thirty-one days of such termination and (b) two thousand dollars.″完善团体保险规则,排斥团体投保人作为受益人的资格;另一方面,确立团体保险解除情形下的投保人或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及被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以维护团体保险下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 投保人伤害被保险人后果的修正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款明显与保险合同保护被保险人的功能不相符,因为从保险事故的偶发性原则来看,保险人所承保的应系意外事故,而非被保险人主观可控的事故[11]22。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为一人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造成的伤害非被保险人主观可控,保险人不应当免责。况且此事故系投保人造成,然而最终受损的系被保险人,有代投保人受过之嫌[12]12。出现此问题,笔者认为,还是由于我国法律只将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而没有将被保险人定位为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法律应当进一步区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的情形,规定在此情形之下,投保人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时,保险人仍应当承担保险金责任,不应当让无辜的被保险人为投保人的过错承担后果。至于投保人的过错,可由法律另行规定进行调整。
(五) 被保险人倾斜保护原则的确立
我国《保险法》对被保险人保护不周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并未确立被保险人保护的核心原则。这与被保险人只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地位的理论认知不无关系。虽然我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了最大诚信原则,对保护被保险人能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然而其并未直接强调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无法直观地体现立法者保护被保险人的意图以及被保险人实际当事人的地位。
具体来说,最大诚信原则强调保险合同当事人应当从自身出发,最大限度、竭尽所能地遵循诚信要求去缔结合同、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权利[13]95。其最初含义是“一种主动性义务,即投保人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投保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14]55。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为此提供重要佐证。该法第17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合同;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他方可以撤销该合同。”第18(1)条规定:“根据本条规定,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必须向保险人披露其所知的一切重要情况。被保险人被推定为知道在通常业务过程中他应当知晓的每一情况。若被保险人未进行此种披露,保险人可以撤销合同。”由此可见,最大诚信原则在其确立之初主要是基于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诚信原则也开始逐渐增加对保险人最大诚信的要求,兼顾被保险人的利益。例如在20世纪的美国,投保人的披露义务开始限缩,被保险人在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之时被赋予了请求赔偿的权利,这充分体现了最大诚信原则内涵的转变[15]12。目前,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核心规则主要包括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保证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弃权和禁反言,逐步加大了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增加了对被保险人的保护。
从最大诚信原则的变迁可以看出,其最初目的是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也只是兼顾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被保险人的保护并非该原则最主要的意旨。最大诚信原则并未体现对被保险人的重点保护,而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恰恰需要法律给予倾斜保护。
首先,保险合同系典型的附和合同,它由保险人单方制定,且内容冗长而复杂。保险人有时会使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充斥其间,一般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本难以理解。即便保险人用了简单通俗的语言,其内容也无法被大部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理解[16]13。而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并没有充分的动机去充分阅读保险合同,因为他们知道哪怕阅读了这个合同也无法改变其中某一条款,他们只有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的权利,而无部分修改的权利[16]13。
其次,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也决定了其履行顺序较为特殊,通常系投保人先缴纳保险费,然后等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人才能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保险合同这种履行上的特殊性决定了被保险人在遭受损失之前并不会特别关注保险合同的内容,而只有在遭受损失之后才会关注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加之保险条款具有附合性、技术性等特点,如果仍按照一般的合同原则来处理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争议,则极易使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合同约定内容的牺牲品,所谓的合同自由便成为保险人侵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自由。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被保险人保护的现实需求以及理论上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实际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保险法》中确立对被保险人倾斜保护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类似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的原则。消费者倾斜保护主要是指立法过程中应设置有利于消费者权利、增加生产者销售者义务和责任的条款,这样就使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上不相称的力量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17]99。由于保险服务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种消费类型,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本质上是消费者,故而也应受到法律的倾斜保护。法律原则能够起到指导立法过程、指引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弥补法律漏洞、指导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功效,如若在《保险法》中确定被保险人保护的原则,则对被保险人的保护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五、 结 语
近年来,虽然我国立法开始重视对被保险人的保护,但在加强被保险人保护的立法趋势之下,理论上对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认知也应进一步深化。将被保险人认定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可以为立法者对我国《保险法》中一些规则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在此之前,被保险人合同关系人地位的认知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有失周全,就算发现其利益受损,鉴于理论体系上的障碍,立法者只能部分兼顾其利益而不能给予其更加完善的保护。被保险人实际当事人地位的确立将打破原有对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认知,对被保险人权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当下我国理论界对被保险人的关注依然不够,如何以法律为手段更好地发挥保险合同分散风险、保障被保险人的功能,激励保险行业形成诚信的氛围,依然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