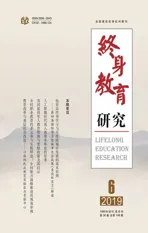中山文化教育馆与“中山符号”的构建和传播
2019-01-03□彭冉
□ 彭 冉
1932年冬,孙中山之子、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1891—1973)在上海的住处(哥伦比亚路22号,今上海番禺路60号)召集政界、知识界部分名人商议筹建中山文化教育馆,并于次年3月12日,在南京中山陵园举行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大会。在会上,孙科申明该馆将“罗致国内学者,潜心研究以阐明中山先生之主义与学说,以树立文化之基础,以培养民族之生命,同时亦即以此为中山先生留文化上永远之纪念”①。总的来看,中山文化教育馆实践了其宗旨,在“中山符号”的学理化构建及社会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层面强化了社会对孙中山的崇拜。
虽然中山文化教育馆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当事人的日记、口述等相关材料对此却鲜有提及,学界对之也甚少关注。迄今为止,以中山文化教育馆为研究对象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它们或侧重梳理中山文化教育馆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史实,或研究该馆与当时文化环境的关系,或聚焦《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及其背后的人脉关系、党派色彩等。②鉴于此,本文转向新的探索空间,尝试探讨中山文化教育馆对“中山符号”的构建及其社会传播问题。
一、中山文化教育馆之建立
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此后十年,国民党政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中国国民革命已由消极的破坏阶段进展到积极建设时期”[1]4。与此同时,日本侵华程度不断加深,强化“国族”认同及普及中华传统文化观念成为时代主旋律。但是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社会文化基础却异常薄弱,“大多数国民,其智识技能乃至生活方式均尚滞留于极顽旧之境遇中,民族之老大落后,已无可自讳”[2]2。在孙科看来,当时的文化环境不但未能发挥孙中山思想在普及中华文化上的引领作用,相反马列主义颇为流行,影响到了国民党政权的主流价值观,“社会科学的书籍多受其影响,有识之士佥认有重振三民主义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必要”[3]。基于对这一时期社会形势的分析,孙科认为,“对于中山主义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进而作客观的、理智的研究”[1]4,应当建设一文化机关,使其“负有指引全体国民实践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之使命”[2]1;换言之,即以社会教育的方式普及三民主义。因此,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建立,不仅为了满足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要求,还与民族危机背景下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有关。概言之,加强对中山主义和“中山符号”的社会传播,实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基本宗旨。
1932年11月至次年1月间,孙科在上海的住处召集马超俊、黎照寰、梁寒操等人,先后召开了6次谈话会并达成共识,认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基础不甚坚固,三民主义阐扬尚显不足,因此导致青年思想缺乏领导,甚或“步入歧途”①,应当立即着手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筹备过程颇为顺利,至3月7日为止邀请到签名发起人逾三百余人。[4]17这份发起人名单中既有国府主席林森及诸多政界要人,如孔祥熙、于右任等,也包括执牛耳的学界闻人,如蔡元培、马寅初等。1933年3月12日,中山文化教育馆在紧张的筹备后,在南京中山陵园举行成立大会。成立典礼借总理逝世纪念大会为契机,遍邀国府要人和党部要员,与会来宾达五百余人[5],还邀请了明星电影公司进行有声影片摄录。[6]此后,孙科又在1935年3月12日,再次在中山陵园举行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两周年暨新屋落成典礼[7]6,以扩大声势。时人谓“冷落之东郊,乃顿呈车水马龙之观,热闹情形,为全国运动会后所罕见”。[8]各大重要报刊如《中央周报》《申报》《东方杂志》《时事月报》等均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和评论。
中山文化教育馆由于得到孙科庇佑,前期发展十分顺利。抗战军兴后,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该馆只得辗转流离于广东及澳门等地。据谢放推测,最迟至1947年年底,该馆已经终止了相关活动。[9]目前并无可靠史料揭晓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最后结局,不过该馆图书馆所藏的丰富资料虽历经战乱仍得以保存,并于1949年后被陆续运往台湾,现存于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
二、中山文化教育馆与“中山符号”的构建
1.“中山符号”的塑造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认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由再现体、对象及解释项构成,且符号与其对象、解释项之间存在着一种三元关系。[10]也就是说,符号可以通过形体传达符号对象的讯息,这就是符号的意义。事实上,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一直致力于“中山符号”的塑造,以神话孙中山形象。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孙中山陵寝——中山陵的建设。中山陵作为一个开放的纪念空间,其设计的造型、用料乃至台阶、景观布置等皆蕴含着丰富的“中山”意义。李恭忠认为,在国民党的努力下,中山陵负载着整个国家的记忆和认同,成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11]除了中山陵以外,国民党还致力于将“中山符号”渗透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随处可见的总理雕像、总理遗像,甚至地名、路名、公园等皆以“中山”或者“三民主义”等孙中山遗产关键词命名,“中山符号”得以镌刻在民众生活的各个缝隙,逐步走向日常化。以至于时人抱怨:“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称‘中山民国’”,“将‘亚细亚洲’改称为‘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12]
国民党塑造“中山符号”的目的在于消费和垄断其政治价值,通过对“中山符号”的继承以获得政治地位,以此谋文化统治之便。但客观地说,国民党早期对“中山符号”的塑造仍有缺憾。由于国民党早期对孙中山的形象宣传皆以其革命精神和革命实践为载体,注重孙中山对既往“非正义”势力的抵抗和破坏,从而导致孙中山成为“革命”的代名词,而“革命”则往往意味着“破坏”和“暴力”,这从中山陵修建时南京地区的谣言即可见一斑:当时民间盛传修建中山陵需要以幼童灵魂奠基,家长多在小孩身上缠五色旗或红布以“避祸”,谣言逐渐蔓延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最终政府不得不出面辟谣。[13]此次事件当然与民众愚昧不无关系,但是细究起来,恐怕与孙中山形象以及民众对领导人身后事的认知关系更为紧密。此外,国民党极力构建中山符号的神圣性,在宣传过程中未免有些操之过急,方式简单粗暴不说,还一再强调孙中山形象的不可亵渎性。例如为了修建中山路、中山公园而占用民众农田甚至祖坟等与民众产生冲突,甚至还在一些中山公园的篱笆外加一层铁丝网,以防民众涂画等亵渎行为,无形中将民众与神化的孙中山进行了区隔,“瞧着令人悚然而惧”[13]。正如陈蕴茜所总结的:国民党对“中山符号”的构建追求的是一种霸权,让人们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符号暴力。[14]虽然从传播学角度看,信息越简单、渠道越直接,传播效率越高,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初期中山符号的传播以及借助中山符号巩固政权,但是随着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简单粗暴的宣传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宣教环境,甚至容易出现“回飞镖效应”④。中山文化教育馆与以往的“中山符号”塑造有所不同,其致力于对“中山符号”的学术化、理论化研究和阐释,着重构建孙中山的“学术”形象,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理论先锋。
2.中山文化教育馆对“中山符号”的外化塑造
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未抛弃外化的“中山符号”塑造,这主要体现在其名称、成立日期以及馆址选择等方面。在第一次关于建立“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谈话会中,孙科即提出该馆既然“纪念总理致力于文化与教育事业,名称当以中山文库或中山文化馆等为宜”[4]31。12月4日的第三次谈话会中,委员会正式确立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名称。随后又以“中山文库”的名称命名该馆出版的世界名著译丛。除了名称与“中山符号”靠拢之外,孙科还竭力将中山文化教育馆与中山文化、中山纪念相联系。中山文化教育馆自1932年11月孙科等正式发起倡议,到1933年3月12日举办成立大会,仅用了3月余。该馆之所以仓促成立,皆因为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党国政要闻人将齐聚中山陵园举办纪念活动。中山文化教育馆将成立大会选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其意图除了方便短时间内悉数召集政要及知识界闻人之外,同时“即在本馆成立之意义上亦多一重光荣之纪念”[15]6。孙科不仅将馆的成立与声势浩大的总理纪念紧紧联系在一起,还特意致函中央及南京市各有关机构,请求在中山陵园内建馆,以使馆与“紫金山庄严壮丽之中山陵,互相辉映”[15]57。1933年9月27日,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致函中山文化教育馆,同意划拨陵园内“白骨坟”一带为建筑基地,并于1934年1月5日正式签订租地约书。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一向严格控制土地使用,即便是党国要人身后能否葬于陵园内亦有严格规定。而中山文化教育馆却得以在寸土寸金且管理严格的中山陵园成立,并以极其低廉的租金购地建设(每年仅四十八元一角五分国币),由此不难窥见国民党政府及孙科的政治意图,即借助中山陵园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将中山文化教育馆与国家性、社会性的“中山符号”捆绑在一起,将“中山符号”附着在该馆之上,赋予其无可比拟的正统性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将中山文化教育馆与丰富的中山含义捆绑在一起,不过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创立的外在的显见价值,而对“中山符号”的学理性构建则是其内隐的重要旨趣。这个构建过程是通过该馆的相关出版、研究等活动完成的。
3.中山文化教育馆对“中山符号”的学理性构建
出版是中山文化教育馆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据相关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间,该馆即投入58 000元用于出版工作,占年度总支出的35%以上。该馆出版图书的准确数字已难考证,不过据1974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印的“代管中山文化教育馆图书目录”显示,彼时中山文化教育馆馆藏中西文图书约28 556册,其中以中山文化教育馆为名义编辑或者出版的中文图书约有79种。⑤这个书目大致能够反映中山文化教育馆所出版图书的基本信息。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图书中,关于中山思想、中山精神遗产的阐释和宣传占了很大一部分。该馆通过“命题征文”“资金支持”等方式,编辑出版了“中山文库”“党义丛书”“建设丛书”“公民丛书”“民众科学丛书”等一大批出版物,并资助了总理遗教研究、三民主义研究等研究成果的出版工作。这些出版物皆以研究中山思想、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构建国民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这些出版物从学术、理论的角度构建孙中山的学术形象,以丰富孙中山的“国父”形象。
除了出版图书之外,中山文化教育馆还出版了许多定期刊物,包括《时事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后更名为《中山文化季刊》)以及《T'ienHsiaMonthly》(即《天下月刊》,亦称《天下》,下文皆以《天下月刊》为称)等。这些期刊有特定撰稿人,也接受自由来稿。在期刊内容方面,除了对时事的介绍和探讨之外,还刊登了许多对“中山文化”或者孙中山思想的议论文章。例如,对中山分权论在政治学上的地位的讨论[16]、对孙中山革命学的讨论[17],以及对孙中山“革命的人文主义”特征的讨论[18]等等。据现有资料的检索显示,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山文化季刊》和《时事类编》中以“中山”或“总理”为题名,并与孙中山直接相关的文章数量共有18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孙中山思想和革命实践的内涵及其对文化事业、抗战事业的重要意义。
《天下月刊》杂志是英文月刊,旨在向英语世界宣传中国,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天下月刊》的发刊词中,孙科说,“已故总统孙中山先生最爱的箴言之一便是‘天下为公’。……创办《天下月刊》正是为实现‘天下为公’这一目标而做的朴实努力”[19]。宣传中山文化,传播“中山符号”为该刊的办刊宗旨之一。在实际操作中,《天下月刊》除了对日本侵华暴行、中国新生活运动及建设运动等政治形势和社会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译介之外,还宣传介绍孙中山的思想,例如在第5卷第4期中即有一篇P.C.Huang与W.P.Yuen合写的文章《TheAllegedInfluenceofMauriceWilliamonSunYat-sen》(中译为《莫里斯·威廉对孙中山的影响》)。文中质疑了莫里斯·威廉所声称的对孙中山的影响,还重新梳理了孙中山思想与布尔什维克以及民主思想的关系,对于孙中山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该刊名称所蕴含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以及“the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即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机构的标注,本身就是对“中山符号”的直接宣传。《天下月刊》杂志共发行56期,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具学术品味的英文杂志”[20]。在当时中西方话语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下,《天下月刊》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地主办一份面向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思想文化类英文刊物”,打破了“西方‘独语’的局面,彻底改变了中方作为整体长期‘缺场’的状态”[21],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宣传孙中山的重要窗口。
除了出版工作之外,中山文化教育馆还直接聘请研究人员,或者以资金支持的形式进行各类研究工作。前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中山研究及各项社会调查研究为主,该馆的总结报告指出,在1933年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搬离首都,共开展的研究工作达28项之多,其中以孙中山思想或三民主义理论为题的研究即有9项,包括“孙中山哲学体系的研究”“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研究”“实业计划之理论与实际的研究”等等,均以研究课题的形式对孙中山思想内涵作进一步阐释。研究成果形成了各类研究报告,并部分地刊印发行,例如《总理事略》《总理遗教索引》等。⑥抗战爆发后,馆内研究和出版工作皆集中到抗战方面,出版了大量抗战特刊、抗战丛刊,以研究敌情、讨论抗战对策等。抗战胜利后,中山文化教育馆将研究工作划分为民生、民族、民权三个研究组,研究专题包括“三民主义的民族论与文化论”“三民主义的民权学说与政治制度之研究”“实现民权之三民主义的方法与程序”“中山先生之民生哲学与经济学说”等,将孙中山三民主义与当时战后亟待振兴的新社会相结合,寻找建国出路。在当时馆内复员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依然出版了《三民主义国家建设原理》《总理民权学说体系》等研究报告。以上研究工作皆将孙中山思想或三民主义理论与时事相联系,是对孙中山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学术化过程。
通过研究、出版、调查等活动,中山文化教育馆构建了与雕像、陵园、公园等物理性的中山象征截然不同的“中山符号”,同时也区别于既往扁平的、直白的大众宣传模式,以内涵建设使得“中山符号”更加立体化。换言之,中山文化教育馆对“中山符号”的构建体现在思想文化层次,是一种学理层面的建构,而受众也更偏重“有闲阶层”,甚至是“有文化”的民众。
三、中山文化教育馆与“中山符号”的传播
皮尔斯认为,符号代表客体或解释着头脑中的所指事物,并区别了三种基本符号:图像符号——与其所代表者相似,索引符号——与其代表物有某种联系,象征符号——任意或约定俗成地与其所指物相联系。符号是人们能够借以进行抽象的某种方法。因此,中山文化教育馆借助中山陵园,以及以“中山”命名等形式与“中山符号”进行捆绑,形塑了“中山符号”独特的空间。同时,它还将“中山符号”抽象化,使其蕴含在其出版品以及各种研究、调查、教育工作和活动之中,从而构建了孙中山的学术形象,将“中山符号”内涵学理化。借助于以上种种努力,中山文化教育馆极大地拓宽了“中山符号”的社会传播范围。
上文提到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大量出版物,限于资料原因目前无法准确统计其总数,但其影响范围可从定期出版物的发行数量上略见一斑。该馆创办之初,限于经费、人力等因素,出版发行皆委托书店代理,随着后期出版物逐渐增多,遂组织成立专门发行处。发行处成立后,该馆发行自主权扩大,得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广告费用,采取种种措施以推广出版物。例如扩充各省市及国外分售处,聘约各大商埠个人推销员,特约全国邮局代收定户;同时,馆方还联络了各大报纸及各著名杂志交换刊登广告和宣传文字,极大地改善了出版宣传工作,使得各刊销数均有惊人之进展。[15]49以《时事类编》为例,每期销数从一开始的3 000册增长至6 000册,即便如此也还是“不敷供求”。[15]49自1937年以特刊形式出版后,第1期初版的3 000册两天内便销售一空,又再版8 000册,仍然供不应求,最后“再版至四次之多”。[22]由此可见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力之大。尤其在国民党政权加大对新闻出版事业管控之时,中山文化教育馆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成为当时最“安全”的出版机构之一。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出于政治因素考虑,曾有一段时间以发行国立中央研究院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出版物为主。[23]政治权力对文化出版行业的大力审查,使得其他出版机构和刊物噤若寒蝉,却促进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物的影响范围。
该馆出版物发行如此顺利,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最主要还是得益于其较高的出版质量。彼时,该馆各类出版物获得了业界及“有文化”民众的较高评价,在各自领域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例如,坊间皆认为《时事类编》在“当前国内出版物中,是唯一的优良的供给研究国际问题资料的期刊了”[24]。其在当时出版界的地位“不敢说是已经造成了出版界权威的地位,对于研究国际问题和关心世界大事的人们对于本刊却不能不人手一册”[25]。梅汝傲在总结中引用林语堂先生在一篇英文论文的说法,称《时事类编》在中国出版界的性质和地位“等同于英国的‘活时代’(Living Age)”,而《活时代》是世界上很有历史,很负盛名的刊物。[26]至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在当时出版界的地位,则为“纯学术性亦为当时国内最具权威之一流刊物”[27]。
定期出版物以其快捷性、时效性等优点,得以迅速传播,使得中山文化教育馆迅速在国内出版市场内占据重要位置。实际上,中山文化教育馆对“中山符号”的传播范围并不仅限于国内,还包括海外。在馆务刚刚正常运转不久,馆内同仁即认识到国外对孙中山的认识尚嫌肤浅,“皆注重于私人琐屑之生活,偶有论其学说者,亦多隔靴搔痒,甚或妄肆攻击”[7]17,应当加以宣传,以纠其视听。因此,孙科委任徐卓英等人,将孙中山的生平及其思想学说翻译为英文著述,以销海外。再佐以上文提到的《天下月刊》,图书与杂志相互依辅,促进了中山研究的系统性发展和深度拓展,扩大了“中山符号”的影响范围,增强了孙中山思想的海外影响力。基于该馆出版品的较高质量以及巨大的发行量和发行范围,说孙科欲以“中山符号”垄断当时的文化市场绝非向壁虚构。[28]总之,中山文化教育馆依靠巨大的出版发行量所累积而成的影响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山文化和“中山符号”的社会传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中山符号”宣传管道。
除了出版物形式的宣传之外,中山文化教育馆还举办“中山奖学金”评比及征文等活动,扩大“中山符号”在大学知识青年中的影响力。中山文化教育馆为“提倡学术,发扬文化,奖励科学之发明,与专门之著述”[29],组织专家委员会,于1933年至1936年间评选、颁发了两次中山奖学金。第一次奖学金以“救济我国农村方案”和“暑假计划与工作报告”为题;同时还奖励自然科学竞赛,奖金总计4 000元。征选范围为国内公私立大学及专门以上学生。公告发出后,仅前两项报名登记者就有208人,虽然最终交卷的只有91份,但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未因此减少奖金数目,相反还加录了名额,“以期普及”。[30]1935年该馆举办了第二次中山奖学金评选活动,奖学事项为自然科学考试竞赛,以物理学为主,分考试竞赛和征文两部分,奖金总额4 000元,总奖励人数达68名。[31]此外,中山文化教育馆还与国立武汉大学工科研究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合作,设置中山奖学金以资助研究生学习工科研究课程,国内大学或独立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生皆可报考。[32]这些资助和奖励惠及人群为高校表现优异的学生,得到了高校的普遍欢迎,尤其是获得奖金的学校皆在校刊上进行报道。客观地说,举办奖学金和征文活动,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关注与研究,同时也有效地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加强了“中山符号”的传播。
总的说来,中山文化教育馆以其独特的宗旨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在“中山符号”学理化构建及其社会传播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限于史料,中山文化教育馆在对“中山符号”传播中的受众反应暂时无法揭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历史作用值得学界重新审视、评估和再研究。事实上,除了对“中山符号”的传播之外,中山文化教育馆还在教育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化发展、国际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战时致力于民族文化保存、战时文化宣传方面,“有力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和信心”。[33]
四、结语
与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等“官修”文献机构不同,中山文化教育馆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党义宣传”的羁绊,有较大的伸缩空间,更利于从文化层面构建与传播“中山符号”。从这方面来看,中山文化教育馆吸引了一大批知识人投入到中山研究中,包括杨幼炯、谌小岑、胡继纯等,他们划分不同的研究小组和专题,“集众人之力量,作有计划之推进”⑥,从而使得中山文化教育馆与同时代其他文化研究机构相比,在出版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具有明显优势,形成了“中山符号”稳定的传播网络。同时我们还须看到,中山文化教育馆除了其出版印刷品在外在形式上体现的“中山符号”以及内容上的“中山”含义之外,其所支持的社会调查、征文、奖学金等活动,兼顾了普通群体以及作为党国基础的高校学生群体,使“中山符号”的社会影响面大为扩大。正如陈蕴茜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对于“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中山路”“中山公园”等时间、空间的大力宣传与塑造,是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话语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在微权力领域的运作。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研究和宣传亦是如此,只是其触角主要伸向了“有闲阶级”和“有文化”的民众群体。
当然,孙科对“中山符号”的大肆宣传,不排除夹杂其个人借助“中山符号”在国民党政治体制中争取“话语权”的意图,不过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传播孙中山思想,建设国民党政权下的主流文化根基。显而易见,孙科以中山文化教育馆为依托,着力于“中山符号”的学术化、理论化构建,强化了三民主义的文化传播,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政治文化塑造。
注 释:
① 中山文化教育馆缘起章程(1933年,此处档案内标注日期为1936年应为有误),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80111-00001-003,第4页、第3页。
② 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谢放,《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影响——以中山文化教育馆为例》,被辑于《岭南近代文化与社会转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捷硕士论文,《中山文化教育馆与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山大学,2011年;高萍萍,《孙科创建中山文化教育馆》,《档案建设》2012年第5期;吴小燕:《〈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及其党派色彩考察》,《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千野拓政著、朱晓进译,《胡风与〈时事类编〉》,被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家出版社,1992年;彭发胜,《向西方诠释中国〈天下月刊〉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
③ 对于国民党如何塑造“中山符号”、构建孙中山崇拜,并以之争取政治利益的研究,Liping Wang《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Yue Du《Sun Yat-sen as Guofu:Competition over Nationalist Party Orthodoxy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和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等研究论著中已有深入论述,此不赘言。
④ 罗伯特·K·默顿用“回飞镖效应”描述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以与作者们所意料的相反的形式对宣传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宣传没有起到宣传者所希望的效果,甚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罗伯特·K·默顿著、唐少杰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774—784页。)
⑤ 这个书目应当远远低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实际编印、发行的图书数量。原因有三:(1)中山文化教育馆图书馆为内部研究人员使用,不对外开放,因此致力于搜罗其他出版单位出版的书籍,本馆书籍是否都在图书馆存档应当存疑;(2)中山文化教育馆图书馆在战时、战后几经辗转,先后搬往重庆、广东、澳门等地,图书恐多有遗失;(3)笔者统计仅以“中山文化教育馆编”或出版发行为“中山文化教育馆”为关键词进行统计,但实际上的图书目录编印中有许多“中山文化教育馆编”的书目并未显示,这部分书多由其他出版单位印行,而其书册上依然有“中山文化教育馆”字样。例如陈培玮、胡去非编《总理遗教索引》,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虽在版权页写明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编辑,但在图书馆目录中没有写出,故未被统计在内。
⑥ 国立中正大学概览校历及中山文化教育馆十周年工作概况以及呈报校务工作计划报告之有关文书(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档案号:五-5534,第8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