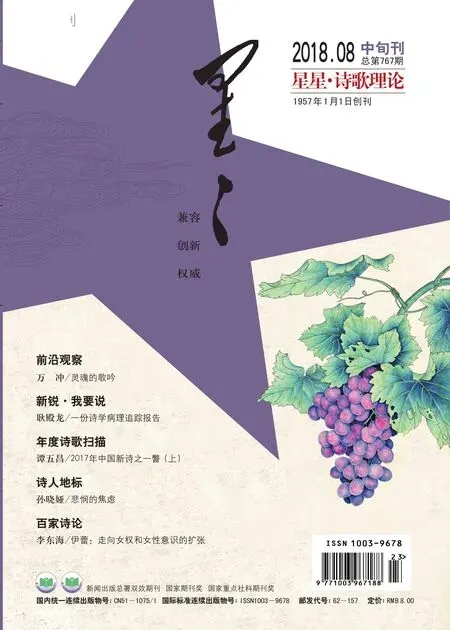2017年中国新诗之一瞥(上)
2018-12-30
众所周知,2017年恰逢中国新诗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这在诗歌界是普遍公认的历史事实。缘由国人身上普遍潜藏的百年时间情结,从本年初至年底,各种与“新诗百年”话题有关的诗学论坛、研讨会与诗歌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举行,可谓接踵而至,热闹非凡,包括两岸四地在内的成百上千的诗人、评论家与学者均参与其中,构成本年度最具标志性的诗歌事件与诗坛景观。对于中国新诗所经历的百年历程以及百年中国新诗所取得的成就,在诗人、评论家与学者们之中虽然不乏批评与质疑之声,但总体上肯定新诗百年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在诗坛内部还是成为主流性的意见。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与“新诗百年”话题有关的诗歌活动均带有对新诗的一段历史进行世纪总结的色彩与意味。与此相对应的情形是,在2017年,罗门、余光中、屠岸等享誉海内外的诗坛大家相继辞世,以象征性的方式宣告自身的诗歌生涯已经成为一段历史,而这也成为新诗百年境遇的一种隐喻:新诗百年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翻篇了,可供人缅怀,新诗的下一个百年的旅程,业已悄悄开启了。百年时间范围内的辞旧迎新,无疑给所有热爱新诗的人们带来一种不乏美好意味的怀旧与伤感情绪。正是在此心态下,罗门、余光中、屠岸等与世纪同行的老一辈诗人在2017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年份的先后逝世,在广大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通过微信、微博等高科技平台表达对前辈诗人逝世的哀思。不少人还以写诗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对已逝诗人的深切缅怀之情,例如学者朱寿桐专门创作了悼念性诗作《悼罗门》,该诗对罗门的诗人形象、精神气质给予了简洁、生动、恰切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诗人陆健则创作了悼念性诗作《秋天的树叶飘在一片心田——写给余光中先生》,该诗以质朴、真诚而深情的语调,表达了一个晚辈诗人对一位前辈诗人的艺术认知与命运认同,该诗以情与思的真挚与深刻打动人心。总之,新诗百年的时间情结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潜存令2017年度诗坛上那些重要的人与事,带上了一层编年史的色彩,值得人们长久铭记。
综观2017年的中国新诗创作,它与往年的创作面貌与格局并无明显的变化,依然在平静中呈现出勃勃生机。从宏观的诗歌美学与价值取向的层面着眼,可以把2017年度的诗歌创作大致归纳成9种写作向度。下面试分别简要论述之。
向度之一:现实关怀写作与人文关怀写作
中国的诗人们在写作中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直接将现实问题作为表现题材与书写对象,从中展示出诗人们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传统自《诗经》《楚辞》时代开始,时至当下依然绵延不绝,甚至称得上发扬光大。
与往年相类似,不少诗人对当下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作出及时反应,他们以诗歌为载体,进行了深度介入式的现实书写。环境污染与生态保护问题是不少诗人的现实关怀焦点问题。郭新民的《雾霾倏然散去》与盛华厚的《雾霾随想》以近几年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为作品题材,两首诗整体上缓慢近乎沉闷的节奏,颇为有效地传达出诗人内在的苦闷心情。前者以假想“雾霾倏然散去”的戏剧化场景的想象性描写,与作品结尾“雾霾未曾散去”的现实形成对比,凸显了现实本身的无奈与沉重;后者则以雾霾现象对城市人们情感与精神生活的慢性污染为表现主旨,让读者对雾霾之于人类的危害性效果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简言之,前者偏于外向,后者偏于内向,是这两首雾霾题材诗作的区别所在。梅黎明的《分别》反映的是当今时代最为棘手的社会现象: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诗人精心选择了春节期间在外打工的农村妇女与儿女分别的一个场景,对之进行了客观而简洁的叙述,典型的细节描写将诗人深厚的同情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了。吴昕孺的《拆》直面今日中国社会普遍性的拆迁现象,诗人以借古喻今的讽刺性手法,对漫无节制的拆迁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性后果,表达了沉重的忧患意识。赵天饴的《当一切都乱了的时候》则针对旅游景点文物遭遇偷盗与变卖的社会乱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批判立场,与吴昕孺的《拆》颇为相似的是,该诗也是运用了借古喻今的讽刺性手法,显示出一定的思想力度。钱轩毅的《驻守在城市的乞丐与雕像》以某种对比和寓言性的手法,对在城市中流行的“乞丐现象”表达了真诚的忧虑与反思。车延高的《苦难》揭示的是当下许多青年人无房无车且婚姻毫无着落的苦难生存境遇,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语言形象、生动而辛辣,富有艺术表现力度。
与前述诗人对社会现实问题所持的批判性意向不同,一些诗人对社会现实则表现出正面性的肯定态度与担当姿态。例如,舒喆的《十里春风不如你》对发生在本土的一桩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给予了热情的讴歌,情调风格明亮、热烈、激昂,给人以正能量的感染效果。郭思思的《云上贵州的彩虹》描叙了贵州遵义高速公路全线贯通的动人场景,诗人以欢快、自豪的语调表达了对于家乡美好现实与发展前景的无限喜悦之情。柳必成的《秦岭如此这般说》采用诗人自己化身为秦岭的拟人手法,通过独白的方式,以巧妙的构思,突显了秦岭进入高速时代的历史豪情。与此相类似,罗鹿鸣的《地铁,从我楼下经过》采用白描般的方式,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到处修建地铁的情景予以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作品的情绪基调欢乐而明朗。刘晓平的《在辽飞集团》叙述了作者参观军机生产车间的见闻与感想,欢快、高亢的语调渲染出诗人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热情,属于典型的主旋律叙事。与此类似,姜念光的《秋天的军旅》描叙了人民军队沙场秋练兵的盛大场面,精确有力的修辞,豪迈昂扬的气势,彰显出诗人的英雄主义姿态与爱国主义情结。而周庆荣的《鸡年往后》则以散文诗的方式,对2017年(农历鸡年)中国社会发展蓝图给予了充满理想主义彩色的展望,作品直抒胸臆,格局阔大,立意高远,可谓气势昂扬,催人振奋。
由此可见,上述诗人们在其诗歌写作中是怀有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精神的。当然,还有部分诗人在其诗歌写作中,其思想主旨从现实关怀层面进一步深入到人文关怀层面,例如,晓音的《我对面的人群》由己及人般的联想到周围人群的生存困境,诗人对他人的关怀态度令人感动。黄芳的《对饮》在一幕世所常见的好友与亲人之间的对饮与对谈的场景描叙中,揭示了人们“丧父”之后精神上无所皈依的痛苦状态。乐冰的《有时候我们甚至连一只蚂蚁都比不上》则将关怀的目光投注在人类自身卑微的生存处境方面,这种自我的精神觉醒令读者产生深深的心灵共鸣。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诗人将其人文关怀向度的写作延伸进文明思考的层面,其文本中往往存在着文明与愚昧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比如,刘川的《忏悔》以自己小时候恶作剧地拧掉蜻蜓的脑袋为忏悔动机,巧妙地把没有脑袋的蜻蜓与今日大街上许许多多“没有大脑”(没有自己思想)的庸众作比对,反映出诗人骨子里对大众精神麻木状态的深沉忧虑与启蒙思想。而严力的《一百米》则以寓言式的表现手法,对世界范围内的不文明形象进行了委婉而有力的揭示,其文明忧思具有难得的深广度,促人警醒。在此必须稍微提及一下的是,在具体的诗人文本中,现实关怀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存在程度不同的叠合关系。
向度之二:日常口语写作与底层写作
与一批诗人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关注民族与人类命运、体现人文精神关怀的宏大叙事写作追求不同,有一大批诗人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生存的日常生活叙事美学原则与口语化写作,这一诗歌写作向度自进入21世纪以来日趋显明,这是大众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优势地位的必然结果。原则上说,所谓的日常口语写作包括日常生活叙事美学原则与口语化写作两个层面的含义,二者存在着逻辑上的对应与重合关系,它与学院化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形成了美学趣味与文化立场上的对立态势。客观而理性地来看待,日常口语写作自然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价值,因为它是对社会上普通人(而非社会少数精英)思想情感状态与审美趣味的诗性表达。在日常口语写作向度上,一部分诗人倾向于日常生活叙事,追求质朴、亲切的审美风格,另一部分诗人则倾向于口语对书面语进行文化解构的先锋写作立场,展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趣味。当然,这二者在具体的诗人文本中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叠合关系。
侯马与伊沙作为日常口语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他们惯常在诗歌文本中展现其解构主义的文化立场与美学趣味。2017年,侯马的口语短诗《饺子》叙述了一位囚犯因为没有醋而拒绝狱警送来的除夕饺子,不合常情的行为,夸张的修辞,呈现出一种冷幽默的艺术效果。伊沙的《在母亲的遗像前为父亲的祈祷词》写诗人在母亲的遗像前所带有的具诅咒意味的祈祷话语,与祈祷父亲延年益寿的良好心愿,构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令人忍俊不禁。幽默与反讽,可以说是许多口语诗作的共同审美元素。例如,马非的《童话》叙述了诗人青年时代因为经济困难而把简陋的办公室当成婚房的一段苦涩经历,至结尾处,凭借当今年轻人的不可理喻,作者自诩他和妻子属于童话中的人物,反讽的效果顿时呈现。黄海兮的《人身佛像》叙述了诗人自己登山拜佛的一段真实经历,结尾处凡人与佛神位置的暗中置换与人为错位,彰显某种荒诞意味。
桂杰的《喂鸭人》以城市居民为了消遣而争抢着去公园喂鸭的现象为表现题材,该诗的结句关键词“收获”暗藏讽刺含义,超越了传统的意蕴。
不少诗人的文本从审美形态的角度来看虽然也属于日常口语写作范畴,但并不以解构主义为写作目标。准确地说,诗人们是运用鲜活、亲切的口语来对自己所亲历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艺术化的叙述,从中提炼出生活的诗意。例如,梁平的《一次晚餐的感觉》描叙了诗人在一次晚餐上享用韩国烧烤的情景,幽默的口语运用与生动的情景再现相得益彰,令人赞赏。吕约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从未消失》描叙了诗人的老母亲在自己园地里种菜,老父亲为老母亲送饭的温馨场面,质朴、生动、简洁的场景描写,幽默、俏皮的人物对白,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对热爱生活的中国老年夫妻的动人形象,让人过目难忘。李强的《特别的你》以绿树与诗歌比喻自己的女儿,鲜活、美丽、可爱的女儿形象与活波、明快、轻盈的语言叙述互相映衬,有力地传达出大地般深厚的父爱主题。胡建文的《我在大学教书》则以质朴无华的语言描叙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大学教师的生活图景,其中精心设计的青蛙鸣叫的细节描写,顿时令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田园的诗意。
有些诗人在日常口语写作中,兴趣点已经不在于书写自身的经历,而是重点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即使是书写自己的经历,也把自己作为社会底层的“草根”人物来看待,此即人们通常所谓的底层写作。海讯在其散文诗作《草的耐心》中对于草与泥土的关系描写,以及对于草的低微与坚韧的重要特性的揭示,鲜明地呈现出底层民众的形象与品质。正是在底层写作这一向度上,熊曼的《农妇的哲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大地(泥土)般诚实品质的农妇形象,她坚信埋在土里的事物“是可以信赖的”,因为“它们终年在低处|闪烁着泥土的本色”。王彦山的《我的父亲王传亮》则使用质朴自然的语言,采用叙述
人物情节片段的方式,为我们真实地勾勒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父亲形象。王长征的《走进王府井》运用自叙传的手法与话语,通过叙述自己走进王府井的见闻与感想,展示出了一位“北漂青年”的生存窘境与精神状态。而林之云的《吃早饭的保安》则将目光对准一位吃早饭的保安,诗作对底层出身的保安吃早饭的动作与声响给予了原生态般的细节描写,生动而传神,使读者在如临其境中感悟到底层人民的知足常乐心态。柯桥的《光阴慢》以简洁、传神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农妇砍柴的场景,刻画出这位农妇年迈无力、孤苦无依的悲惨形象,诗人的情感深藏不露,但令人动容。许敏的《地铁,打手机的女人》抓住城市生活中一个经典性的场景,作品将关注点集中于一个在地铁上打手机的乡村妇女,通俗易懂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刻画出这位独闯城市的乡村妇女形象,诗作的结尾含蓄而鲜明地表达出诗人对这位乡村妇女的深切同情。马海轶的《桑吉卓玛》用略带幽默的口语,以某种反讽性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底层藏族妇女困窘糟糕的生活境况。黄梵的《广场舞》则对近些年在城市普通居民中颇为流行的广场舞给予了重新的认知与评价,诗人对广场舞进行了形神兼备的描写,通过自己对底层民众娱乐方式一种充满悲悯情怀的突然理解,来呈现诗人的底层关怀精神。庄凌的《年关》用小说的笔法生动地勾勒了一幅农民工回乡过年的图景,诗人对故乡的认同情感与中国经验水乳交融。衣米一的《水花》则是对一位城市底层妇女投河自尽的悲剧情景给予了生动、空灵、有力的艺术表现,诗人的悲悯情怀与性别认同情感有机交融在一起,令人无限动容。
向度之三: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
与当下的日常生活叙事诗歌写作美学潮流相对接,一批诗人从现实叙述的层面转向记忆叙述的层面,即诗人们热衷对于个人记忆中的人物、地方与事情进行诗性叙述,让日常生活叙事充满审美情感色彩。
不少诗人将对亲人的回忆作为诗歌的素材与表现内容。例如,梁尔源的《菩萨》以诗人晚年的祖母为书写对象,通过祖母与菩萨之间一段自言自语的对话及相关场景的简洁描叙,生动地刻画出老一辈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田禾的《葵花》以明亮的笔调描写了诗人父亲栽种葵花的一个记忆片段,作品丰富的想象背后传达出了诗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热情。林莉的《守岁记》则以细腻、温馨的笔调描叙了自己昔日与父亲一起守岁的快乐时光,物质匮乏的时代与诗人内心的丰盈构成一种微妙的对比。同样是书写与父亲有关的回忆,念琪的《六月里》以跳跃的语言、诡异的意象,还原了一段充满父爱气息的南方青春岁月记忆。第广龙的《埋了父亲》则以直面痛苦记忆的莫大勇气,用锥心刻骨的本色语言,叙述了自己亲手埋葬逝去父亲的心路历程,令人震撼。
还有一些诗人将童年记忆作为作品的表现内容。例如,张执浩的《补丁颂》以作者穷困的童年经历为记忆书写内容,“补丁”这一恰切意象的选用与诗人的怀旧情感互为映衬,作品成熟的修辞展现出它不俗的艺术品位。商泽军的《蝙蝠》选择“蝙蝠”这一具有乡村文化禁忌色彩的意象,以此叙述并呈现诗人童年时代一段灰暗的生命记忆。许耀林的《老家的大水坑》以故乡的大水坑为回忆对象,在朴实的语言叙述中,诗人对于故乡对于童年的眷念情绪跃然纸上。杨廷成的《回家》以诗人童年记忆中的双亲形象以及自己对于父母亲的血缘深情为表现内容,作品质朴无华的语言与掏心掏肺般的情感诉求,读来感人至深。汪剑钊的《爱情的丧家犬甩不掉一个悲伤的尾巴》则以诗人自己一段不幸的爱情婚姻为回忆内容,精妙的比喻与老到的修辞有效地升华了作品悲伤的情绪。阿毛的《我看见》、李云的《渡口——水路》、倮倮的《回声》、夏花的《要冷就冷到骨头里》、马志刚的《李红星的枪》,则以诗人们自身的一段生命经历作为记忆书写的内容,其艺术风格或灵动,或细腻,或深沉,或奇特,或冷峻,各具特色。有些诗人的地域情感记忆颇为出众,例如王晖的《长沙记忆》与徐小泓的《北京深蓝》均是以自己居留过一段时间的大城市为抒写对象,两位诗人分别抓住两座城市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与蓝色天空为情感寄托载体,娓娓道来般的叙述与浪漫唯美的意象营造,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阅读印象。
还有一批诗人,在写作中将关注的目光从个人记忆转向民族历史,展开历史想象性或历史记忆性的书写。也就是说,他们是侧重以民族历史的集体想象或集体记忆为表现内容的,体现出中国诗人身上源远流长的历史情结。
一些诗人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潮流、风云激荡与时代风尚作为表现内容。李少君的《民国的黄昏》由诗人一次黄昏散步中的情景联想,凸显出其优雅精致的怀旧情绪。艾明波的《松花江》以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为时代背景,诗人以情深意切的言说方式,为我们定格了一段屈辱的民族记忆。李荣茂的《有轨电车》则以“有轨电车”这一极具年代感的交通工具为切入点,将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记忆叠加在一起,令人百感交集,复杂难言。程步涛的《突围》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人民军队在强势敌人的围困下,悲壮突围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具有宏大叙事的美学特色。还有一些诗人,则将怀古的想象性目光,回溯到数百年乃至千年以前。例如,鲁若迪基的《马帮》对几百年来活跃于边地的具有神秘色彩的马帮生活给予了质朴、生动的叙述,李东海的《班超从戎》则将目光投往千年以前的汉代英雄班超身上,明快大气的节奏凸显出历史人物的英雄气概,林汉筠的《船语》以南北朝的杰出水利专家郦道元为追慕对象,诗人运用超越古今、亦真亦幻的手法为读者呈现了自己在船上敬拜古人的幻觉情景。张民的《古人》在千年的时间范畴之内对古代民间侠客的形象进行了生动的虚构与刻画,语言流畅而气势充沛。邓涛的《酗酒的李白》展开了对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饮酒解愁的经典场景的想象性描述,诗句朴实而有力,堆雪的《酒泉醉酒》称得上是对邓涛的《酗酒的李白》的呼应之作,诗人对李白在酒泉醉酒的历史传说给予了艺术化的描写,意境优美,韵味醇厚。舒然的《明月是李白的蓝色情人》以李白诗歌中的经典意象“月亮”为诗思激发点,体现出女性诗人的唯美情怀。胡勇的《蓦然回望》则对李白其人其诗进行了历史想象性的整体描叙,赞美的语调贯穿全篇。彭志强的《在石壕:磨刀的人》以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为书写对象,这是一位当代诗人对古代诗人的致敬行为,诗作刻意营造的词语想象力值得称道。杨克的《在瓦口关品茗》也以在瓦口关品茗为契机,对盛唐时代的一段人文历史展开了优雅的想象,情绪张弛有度。黄恩鹏的《鹳雀楼》以唐诗中的经典意象为诗思激发点,在历史与现实的千年叠合想象中,凸显出诗人沉重的忧患意识。彭惊宇的《射雕英雄梦》以金元时期群雄争霸的局面为历史背景,充满西域文化元素的词语与意象的运用,使得诗人的叙述别具一番动人的情韵。育邦的《南田生活指南——过刘基故里,兼致慕白》以明朝一代贤臣刘基为缅怀对象,古典性的意象与优雅从容的节奏,恰切地表现出诗人的怀古意绪。高璨的《魔术》则将怀古的目光投注于遥远的诗经时代,该诗对古典诗句的化用与现代意识的含纳,有其可圈可点之处。此外,刘剑的《高崖上的土陶》与周占林的《山顶洞》则将诗人们的历史怀旧情结延伸进对中华文明沉思与赞美的层面,诗思辽远,境界阔大,而有些诗人甚至还将对历史文化的崇古与怀旧情结扩展至华夏以外,例如欧阳白的《葵花》就对19世纪欧洲天才画家梵高的一生进行了角度别致的追思与评价。
当然,诗人们的个体记忆书写与历史书写某种程度与现实书写存在同一性,它们是互为补充的。诗人们往往通过历史情结来表达其现实关怀精神。总之,个人记忆写作与历史想象性写作展现了个体记忆、个人情感、历史记忆、集体情感在诗歌写作中的独特地位与特殊魅力。
向度之四:生命写作与人性写作
所谓的生命写作,是指诗人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或者说,诗人在叙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重点呈现其生命体验,生命意识成为其诗歌文本的核心内涵。诗人生命体验的纯度、深度与独特性,成为考虑持生命写作向度的诗人文本优劣的重要尺度。
2017年度的中国诗坛,涌现了一大批生命写作的优秀诗歌文本。树才的《虚空》表达了诗人对于虚空这种极端生命状态深入骨髓的体验,返璞归真的语言,袒露灵魂的叙述,给人以持久的心灵感动。童蔚的《感恩节》着力表现诗人的感恩心态,诗作采用某种对比手法,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营造出一幅奇幻动人的灵魂图景。华清的《迷津》设置了一幅“他”与“你”之间讲述与倾听的人物关系与情节场景,诗人在流畅、生动、神采飞扬的语言叙述中,重点揭示了倾听者“你”对于讲述“他”的人生经历的深刻感悟,倾听者“你”最终灵光闪现般的生命觉悟令人怦然心动。安琪的《鸦群飞过九龙江》以质朴、生动的笔触描叙了作者自己化身为乌鸦混迹于鸟群飞跃故乡河流的想象性场景,这种对自我形象的“抹黑行为”背后流露了诗人一段沉痛的生命经验,读之让人感觉无限酸楚。潘洗尘的《恶性的一年》以记实的手法叙述了诗人过去一年来遭遇的种种人生磨难,叙述者平静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调加深了诗作的悲情色彩。高兴的《泪》与潘洗尘的《恶性的一年》所表达的负面性的生命体验相似,但诗人省略了悲情故事的叙述,直接以“泪”的意象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笔墨俭省,效果动人。若离的《人生》对于自己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际进行了不加掩饰的叙述,女性沉痛生命经验的真率表达别具一份打动人心的力量。师力斌的《中科院力学所微雨中捡枣》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作者于一个微雨天气在中科院力学所捡枣的情景,诗人联想到当今世界难民成群,自己却无法将枣子等食品“递给饥饿的兄弟”,此种感同身受式的人道主义情怀,无疑能够唤起读者深深的心灵共鸣。刘立云的《第一场雪》叙述诗人在雪景中怀念逝去的父亲,雪花的寒冷与人心的寒冷互相映衬,情景交融,令人印象深刻。田湘的《我终于替代父亲》通过诗人与亡父之间进行一场想象性的精神对话,“我终于替代父亲”的亲情话语背后所透露的父子情深,可谓感人肺腑。与此类似,海湄的《有一天梦见父亲》叙述了女诗人自己梦见亡父的亦真亦幻的动人情景,诗作所表达的阴阳永隔的冷酷无情体验,无疑可以刺痛读者的神经。此外,一批具有生命写作性质的诗歌文本品位不俗,审美情感与艺术风格各具特色,例如《日月湾的夜晚》的忧愤(雨田),《赠梦——》的空灵(大卫),《这冰雪的天地》的沉痛(潘红莉),《攻心术》的机智(谭畅),《给这个世界一点暖》的温馨(雁西),《诗人小镇怀上命中的诗歌》的清新(爱斐儿),《弯弓在弦》的洒脱(远心),《从此以后》的深情(茂戈),《疼痛》的真诚(胡刚毅),散文诗《乡音,是孤独的最佳救赎》的质朴(皇泯),等等,均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阅读印象。
有一些诗人,则在生命意识彰显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勇敢地进入到人性书写与探讨层面,剖析自己或他人真实而复杂的灵魂状态。现举部分文本为例进行简要点评:叶延滨的《让人捧着》通过披露社会上有一类人喜欢让人捧着已经变成僵尸的虫草的非正常现象,对人类品行的劣根性表达了诗人委婉而有力的讽刺态度。潇潇的《这个世界的残缺》以人们对世界的普遍性抱怨、愤懑、诅咒态度为观察点,通过敏锐的思考与犀利的语言,揭示出“这个世界的残缺”其实要归因于每个人身上的坏毛病,这种对于人性缺点的认知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王霆章的《插入内心的时光之刃》以时光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磨损现象予以了诗性叙述,诗作所运用的矛盾修辞,恰到好处地展示出诗人自己灵与肉的冲突,人性书写的深度由此彰显。毛惠云的《仓央嘉措的悲伤》以想象历史的方式,表达了诗人对于一代情圣仓央嘉措追求世俗情爱的人性化理解。吴海歌的《照镜子》用现代性的语言与意象方式,表达了诗人对于衰老发自灵魂的深刻恐惧。度母洛妃的《叫醒自己》用矛盾修辞的方式,在精神的虚空与清醒之间,诗人意欲清醒,但实质上陷入了非理性的纠结状态。瓦刀的《三重门》运用某种寓言性的手法,对诗人自己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与神秘性,给予了艺术化的呈现,发人深思。而樊子的《失眠》与戴潍娜的《临摹》则采用情景假设、自我对白等戏剧性手法,对于诗人自身灵魂的内在丰富性与复杂性状态给予了比较精彩的揭示与呈现。
向度之五:神性写作
所谓的神性写作是建立在生命写作与人性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对生命写作与人性写作在情感层面的高度提纯与无限升华,神圣性、庄严性、超验性,可以视作神性写作的基本而重要的审美特质。神性写作向度自新时期以来一直绵延至今,它对诗歌写作的大众化与世俗化美学趣味予以必要而有力的反拨,这对于净化诗坛精神环境,维护诗歌美学生态的平衡格局,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一观点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经常提及)。
坚持神性写作向度的当代诗人数量不菲,而且多为优秀乃至杰出的诗人(例如吉狄马加、大解、寒烟、杜涯、谭延桐等),2017年度,李南、王黎明、阿信、刘以林、石厉、姚辉、祁人、牛放、肖黛、唐成茂、南鸥、西可、冉冉、徐柏坚、马启代、牛红旗、扎西才让、李永才、马培松、冷先桥、王琪、超侠、王立世、萱歌、曹谁、孔占伟等一大批诗人,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风格不尽相同、整体艺术品质优良的神性写作诗歌文本。其中,李南的《现在,曾经》以先抑后扬的手法,叙述了诗人自己由一位无所顾忌的女生转变成一个对某些事物保持敬畏之心的成熟女性的心灵历程,朴素、简洁的语言,真诚、庄重的语调,彰显出作品内敛而饱满的情感力量。王黎明的《尘世的一天》以新颖、恰切的比喻,展示出诗人对于一天不同时辰敏捷、到位的理解,该诗结尾对尘世的超越意向顿时将作品升华至神性境界。阿信的《秋意》以山中之王老虎的视角来打量秋天的事物,结尾表明它要止息一切雄心,服从最高秩序的召唤,作品构思精巧,立意深远。刘以林的《鸟》描叙了人与鸟之间一种奇妙的心灵互动关系,诗人天启般的非凡想象与作品呈现的神奇境界相得益彰。石厉的《在白鹭洲散步》以一种诗人仰望神鸟的姿态,对白鹭的形象进行了高度的美化与神化,优美的想象铸就了高迈的境界。姚辉的《悬崖》以落日作为观察与描写对象,诗人从悬崖的角度书写了落日的不同形象,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具悲凉色彩的太阳情结。祁人的《题西岭雪山》以西岭的雪花作为书写对象,诗人想象的优美与雪花的轻盈构成一种对称关系,作品所传达的圣洁情感引人进入超凡脱俗之境。与祁人的《题西岭雪山》相类似,牛放的《留一块干净的冰雪》是以喜马拉雅山的冰雪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诗人以崇敬、虔诚的心态与语调,表达了对于人类最后一块神圣纯洁家园的守护愿望。肖黛的《水的秘密》以追溯人类生命起源的姿态,歌颂了水、生命、美、伟大的寂静等非凡的事物,体现了诗人对神秘与神圣之物的内在敬畏。唐成茂的《肩膀上的春天》叙述了作者一种空前绝后的爱情体验,诗中用了长江、天上等意象来表达诗人对于爱情纯洁脱俗、永恒如同天堂的精神诉求,超验的想象与虔诚的情感水乳交融在一起。南鸥的《雕刻时光》对一个死者的身体状态进行了细致、生动的场景描叙,诗作结尾神性的在场展现了诗人对于高端精神境界的自觉追求,殊为难得。而西可的《上天梯》则是诗人运用原始思维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上天梦想,巫术般的想象力与魔幻般的情景描写,使得这首短诗体现出典型的神性写作特质,读来意味深长。
此外,李永才的《飞鸟与上帝的谈话》、冉冉的《夜幕合围之前》、徐柏坚的《浮世清欢》、马启代的《大雪》、牛红旗的《有的雪变成了粮食》、扎西才让的《绿度母》、马培松的《豹》、冷先桥的《在蒙古高原听天神轻语》、王琪的《稻花开了》、萱歌的《横断山》、曹谁的《昆仑墓酒》、孔占伟的《远山上的雪》等一批可以归属于神性写作的诗歌文本,在艺术想象力的出色、情感体验的纯粹与虔诚、境界的静穆、神圣与辽阔方面,都各具特色,值得一提。总之,神性写作为读者提供了各种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情感体验以及多姿多彩的超现实艺术图景,为当下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道绚丽庄严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