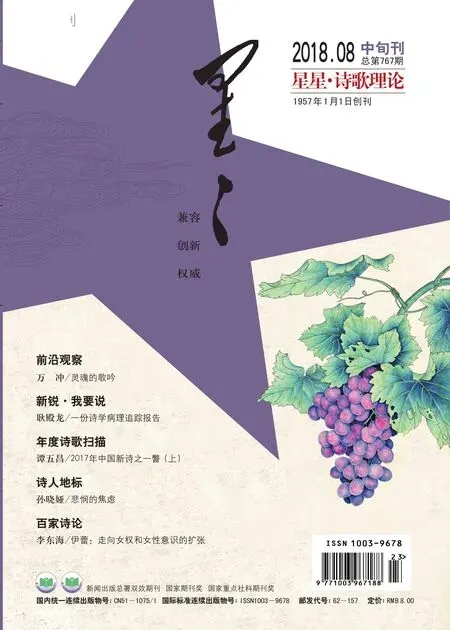生命不是无尽的,而生活是
2018-12-30
生与死是创作永恒的主题,幸福与苦难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并行不悖的。蒙田曾说过“人生的终点就是死亡”,对于死亡的好奇则从幼年开始持续人的一生,对生死没有概念的儿童也会提出“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然而有过死亡经验的人自然再也无法重复他的经验,人们也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旁观之中面对死亡并进行想象。对于某一个普通个体来说,直面死亡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目标与过程,无论是面对自身或是他人都存在着基本的恐惧。
这一期“新现实”的诗歌也有多首涉及到了死亡书写,而诗人则又一次成为了这种死亡的旁观者。这些诗歌注重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对于旁观者所留下的深刻烙印:“而不时砸我身上的落叶/我真的不敢说出,它们像谁谁谁//我怕我一出口,它们/就会变成一记记当胸的重锤”(《林中漫步》),当富有力量的语言将亲朋离去的冰冷体验赋予落叶时,轻飘的落叶也变得有千斤重,残酷地敲打着人的神经;而这种情绪又是极为克制的,正是因为无法宣泄,才“不敢说出”。“父亲的坟就在地头上/母亲有时候会抬起头/朝父亲这里望一望”(《雨点》),生与死的界限是如此暧昧,却又如此分明且无法逾越;当时间冲淡悲伤之后,对已逝之人的怀念便成为了因为生存而必要的劳动间隙的那么一眼。但死亡尽管是个人的终点,却并非他人的终点,生活仍然是以其原本的步调继续:“松树长了起来,杉树长了起来//那些,坟头的草/也长了起来”(《火灾》);而死者,也留下了寄托与安慰:“亲朋好友说遍了爬到金鸡林/对死去多年的表叔说”(《表婶》)。
生活是永远持续又无法摧毁的,在庞大的生活面前,个体的死亡也坍缩成了他人的又一场苦难,而苦难拦不住生活的脚步。孟松的《像棵韭菜我有痛哭一场的冲动》以一种卑微的沉重笔调书写这种苦难:“兄弟,你的昭通挨着我的宜宾/就像苦命挨着苦命”,像元业《魔术师之死》中的那句“——‘命运不可更改’,有人说出这句话/就哭了。”昭通与宜宾两座城市的存在如此坚实,正如大山般的苦命沉重又不可转移。诗人无比通透却又悲哀地看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以韭菜自比:韭菜这种植物“苟活于乡村的田边,地角/从来的身份就不会是园子里的主角”,“而尘世这片园子里/你我又何尝不是,一棵棵韭菜?”可或许作为韭菜本身都更为轻松:“如果锋利还痛快些/而你我遭遇的不公却常常是一把钝刀”。就是因为钝刀般的命运,生活才没有被拦腰截断,尽管被痛苦所洗礼,像虽不是主角可生命力蓬勃旺盛的韭菜一样野蛮生长;在“痛哭一场”过后,还是要持续下去。
比起这样些许浪漫化的痛苦,组诗《农历的村庄》则用一种冷峻的笔调描述所发生的事实细节,诗人也鲜少表露情绪,而是如刀刃将面包一般的生活剖开,赤裸裸地将充满空洞的截面暴露在读者眼前:“去年一斤一元多喜悦的萝卜/今年怎么就变成七分钱的可怜了”“大嫂知道工钱没要上/但大嫂不知道/侄子的右手也让搅拌机咬了指头”,“咬”字就将搅拌机这具冰冷的机器化作一只张牙舞爪的巨兽,将他撕咬与吞噬。正如“新现实”这个名称所表现的,或许许多城市中的读者已经距离这样的生活太过遥远,可这几句却又能使读者切身地读懂遥远的生活现实:细节与状态是不同的,但内核是相同的。琐碎却又沉重的细节最后也构筑成近乎荒诞的诗意:“他是想叫城里人都变成兔子/那样他今年的萝卜一定不会悲伤”“油让汽车拉走了/那老井谁也没动/怎就没水了”。尽管如此,生活却还在继续——怎么能不继续呢?
当然,在无尽的生活之中,也不仅仅只有苦难。在这一期沉重的基调之上,胖荣的组诗《幸福书》就是光明的点缀。同样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细节,咀嚼起来就是最真实的滋味,比如鸡蛋一般破壳初生的太阳:“这个清晨/地平线上的太阳/也刚刚剥好”,又比如在路上一个安逸惬意的瞬间:“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它们纷纷张开了翅膀/我爱人间,这片刻的宽容”,比起人间片刻的宽容,不如说是诗人在无数平凡瞬间中抓住的那个诗意的闪光点,朴实而清新,也是在生活道路上可以松一口气的悲悯。《捉迷藏》则一下子将气氛拉入了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那些幼稚的回忆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某个不起眼的位置始终陪伴:“我睁开眼,回过身/这些年,只有它们/一直看着我”。
诗人需要细腻敏感的内心,也需要坚韧不折的意志,而生活永远是诗意的直接来源。这一期的作品无可保留地展现现实或许过于压抑,但它们也都透露出超越一切并持续的生活意味。在这样庄严的观照中,我们仍可以透过诗投以人文关怀:正如苏轼所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