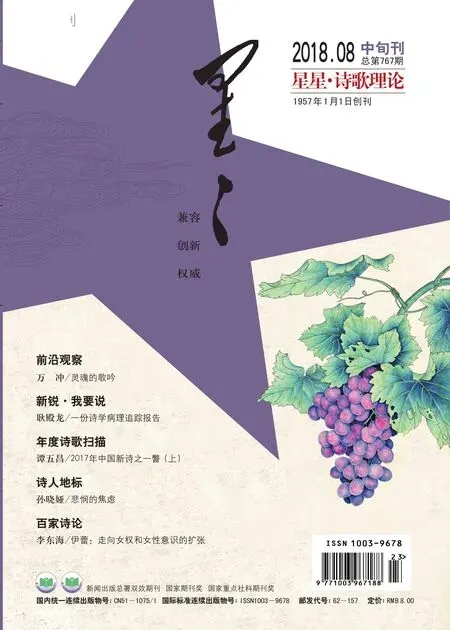生命存在的诗性哲学表达
——评龚学明诗集《白的鸟 紫的花》
2018-12-30
一个人在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很难避免那种在内心摇荡的恍惚感觉。我想,诗人龚学明也是这样,他呈现在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清晰的,但也有恍惚变形的一面。惟其如此,他所触摸到的并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经历,也在“碎片的形式”中隐藏着更深一层的人生感叹。我以为,他的诗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也正在这里。一首感人的诗是唤起读者叩问生命存在的一个小小切口,通过这个切口,读者看见的不仅是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是读者感同身受的一片风景。这片风景中的花草树木都浸润着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同时也感染着读者的情感和情绪。龚学明的诗呈现的是一种节制的情感之美。他不把写作中的激情完全湮灭在技巧和修辞的铺排上,而是把写作中的激情做到充分的内在化,使他的诗又显示出一种丰盈之美。比如,《寻找父亲》写父亲去世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团好看的雪/在他的头顶上飘动/在他的脸上,总开着一朵微笑的花/他步子轻盈,从不与道路相争”,就把死亡带给亲人的惊骇和痛苦写得相当节制,而这种节制在诗中是必要的,带给读者的恰恰是一种至爱深情的体验。
显然,一首诗的情感张力也正在这里,在失去亲人的大哀大痛与形式的克制之间,一首诗的深度不是来自情感的直接表白,而是深蕴在情感的节制中。《在冰河上》也是这样,龚学明写得非常克制,似乎是在犹豫,或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样的情景很像一个病重的人:/——身体渐冷/白鸟飞临,是否是前世的女人来召唤//我宁愿喜欢那阳光下的白。/它不同于野芦花的白,或者会哭的白幡/它在讲述一种起死回生的语言
这是诗集中龚学明为病中的父亲写的第一首诗,基调是悲郁的,诗中的声音显得低抑而哽咽。他在为父亲的病情担忧,尽管江面上有阳光照临,但他笔下的白色江鸟仍然散发着不祥的诡异的气息,把诗人的心绪不可抑制地引向对死亡的联想,却又抑制住悲痛的过分释放。尽管诗中布满不祥的暗影,却是诗人掩抑在内心的产物,并不显得悲怆,就像阳光下的雪影给人并不可靠的幻觉。一首诗的美学形式是情感和修辞的综合,需要把情感赋予恰当的修辞,才能形成一首诗的内在深度。
闻一多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在情感激烈时不宜作诗,而是要等到情绪相对平静下来,“记得的只是最根本最主要的情绪的轮廓,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象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尽量充分具象化[1]”,新月派诗人尊奉“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就在于理性对情感的调适可以保证诗美的健全,避免情感的泛滥对诗美的削弱。无疑,龚学明是深谙此中玄妙的。他力图把情感克制在含蓄的形式上,既做到诗中有我,又不刻意把诗中之我格外放大,避免不加节制的直抒胸臆,而是把情、景、意融汇在自我的胸臆中。中国的古典诗歌中 “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抒情传统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也有所继承和发展,一些新诗经典名篇也得益于此。我想,龚学明也有此一方面的自觉意识,他的情感表达方式有一种出于理性的自我克制,又把自我克制处置在情感的诚实上,有其自觉的用心之处。
情感表达在诗歌写作中居于核心的位置,诗歌的修辞和形式要素都是情感的载体。一首诗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就在于恰当的情感表达,而恰当的情感表达又是修辞和形式要素在整体上的协调统一。不过,对很多诗人来说,这恰恰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一个诗人缺乏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意识,或是缺乏探索的动力和功力,他的写作就会落入贫乏的窠臼,也就谈不上有值得期待的创作前景。诗歌的修辞和形式技巧并不是主题内涵的附属物,而是诗歌的本体性元素,诗歌的主题内涵只有通过恰当的修辞和形式技巧表现出来,才能使诗歌获得稳定可靠的意义视域。就此看来,诗歌的修辞和形式技巧内在于诗歌本体,而诗歌本体尽管是一个混沌的形体,却又是修辞和形式技巧的内在转化,因此,在诗歌写作中,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应该是诗人的责任。
我注意到,在龚学明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他对修辞和形式技巧的探索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很注意运用西方诗歌中的隐喻、象征、悖论等手法,又在诗歌的结构中锲入自我的内在心象,因此,他的一些诗歌需要反复阅读方可领会。比如,他的《在地铁的尽头》:
穿行于涂绿的表情
时而经受黑色的暗示
时而,有透明的诱惑
(玻璃总很无情)
戛然而止的变故
让余下的参与者目光迷离
尽头,对于没有准备的人
需要一场细雨般的微惊
而我,喜欢这些冷静的
句点
这么快,将我从一个眼神
带到另一种飘忽
比如秣周路终点
从闷热、逼仄,到空旷和酣畅
在没有路的地方
到处都是路。雪随意地覆盖
如果是春夏
这样的尽头,花朵拥挤
湖面喧哗,说话的柳树
不说话的石头,像在谈诗论画
此诗写乘坐地铁的感受,很容易写得单调而流于无趣的情境描述,但龚学明却把视点落实在情绪的变形和变异上,把乘坐地铁时情绪的起伏变化扭曲在适度的陌生感上,而这正是对诗意的强化和提炼,用地铁空间上的拥挤和无序对照人们情绪上的躁动和恍惚。显然,这是直接的描摹达不到的效果,其中透露出来的象征意义也更耐人寻味。此诗有一种整体象征的辐射强度,对细节的描摹有很强的暗示性,而这些细节聚合起来,就是结构上的整体性,象征的意蕴就是从结构中溢出来的,需要做整体上的把握。
龚学明诗中的意象也值得注意。意象是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对应物,是一首诗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意象往往是和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联系在一起的,形成整体上的表达效果,可以使一首诗的内涵更沉潜,也更丰富,在形式上也显得新颖别致。诗人唐湜说得好,“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Mind)与最虔诚的灵魂(Heart)化为表里的凝合[2]。”意象不是纯客观的物象,而是和诗人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心象,也是一个诗人真诚的体现。从一个意象中,可以发现诗人的个性禀赋和他对生活的态度,但寻找一个合适的意象并不容易,对诗人的审美敏锐是一大考验。龚学明的诗讲究意象的贴位,把意象安置在极妥当的位置上,诗中的意象疏朗有致,避免意象的过度拥挤和无序越位,这是其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读龚学明的诗,不难发现,他对意象的处置是极其用心的,很少空置一个意象而无特定的意义指向,注重一首诗中不同的意象之间的意义关联,每一个意象都在一首诗的总体情境中与其他意象产生互动效应,因此,一首诗中的意象就像树根紧紧抓住泥土,而在泥土的下面又相互扭结在一起,带给读者一种稳妥而又不无歧义的阅读愉快。
这种对意象之间的张力处置,龚学明做得相当到位,几近不露痕迹,刀锋颇为老道。比如他的《我抚摸一棵老树》:
天太冷,我外出捷行。
一条发白土路
老树孤零零站立。只有骨头
细长,灰黑
没有穿鞋子脚趾向下,紧扣
泥土。我禁不住停下,打量
双手抚摸僵硬树身
我的父亲有树的颜色
手无鲜花,脸色暗淡
沉默寡言一如此时的树
没有飘曳叶子
我记起给父亲擦身时,枯瘦手臂
像没有泛青的树枝;
我给父亲洗脚
忍不住抚摸他的小腿
伤心它已退回,干枯的冬天
此诗由一棵老树联想到病中的父亲,诗人随景生忧,他的情绪是低郁的,但没有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诗中的意象传达出来的,显得自然而又带着冬天季候性的压抑,流露出诗人对父亲病情的担忧。诗中的意象老树、骨头、脚趾、泥土、手臂、小腿等,在诗的总体情境中都具有某种相似的属性,趋向一种暗淡与冷寂的情采,与冬天的环境氛围是一致的,但也有一种内在的热度,诗人的心理波动隐然可见。这些意象又是扩散性的,既是诗人情绪的扩散,也是诗人想象的扩散,由此及彼,由物及人,在意象的转换中,触及到某种深层的哲学内涵,包含着诗人对生命存在的深沉思考。
在龚学明的诗中,意象都是带着他的生命底色的,不仅与他的生命体验圆融一致,而且大都运用得极为妥帖。一个诗人的写作功力,大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意象的选择上。一个恰当的意象实际上是诗人与神性的相遇,沈从文说得好,“生命具神性”,生命并非外在于神性的自然之物,而是内在于神性的自为自在之物,意象的功能在于把这种神性呈现出来,在神性的光辉中抵达生命存在的本质。龚学明诗中的意象往往都含有饱满的情感,从这些意象的内核中可以发现一个诗人热烈的衷肠。意象是诗人个性的投射,在某种程度上,意象可以看作是诗人的心理或情绪病灶,透过诗中的意象,可以发现诗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微妙处置。龚学明的情感表达方式还是偏向内敛的,他的诗中多采用色彩相对暗淡的意象,即使色彩本身明亮的意象,也在他的诗中往往转化为另一面的暗淡或似乎磨损后的形迹,从中可以见出一个诗人隐藏于内心的某种犹疑和审谨。我想,他对现实的态度大概是存在主义式的,观察现实的眼光有忧郁的一面。
龚学明的诗歌从总体上看具有先锋的底色,却又显示出回归传统的趋向。换言之,他的诗歌避免炫耀一副先锋的面具,而是内蕴着一种先锋艺术精神,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中国诗歌传统的表达方式,讲究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对极端性的先锋写作保持清醒的克制。实际上,先锋与传统的杂糅和扭结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才能形成一首诗的张力结构,使一首诗耐读,值得回味。比如《南京,南京》:
在南京,我成为一名诗人/经常泪水涟涟/我的疼和城市的痛相连/现实和记忆一次次受伤/我的青春期如此粗暴/一朵没有设计的花/在厚重的城墙下 在阴影里/结出异果
诗的语言有某种陌生化的效应,但并不晦涩,大体没有超出常规语法的边界。同时,龚学明追求语感的畅通和内在的层次性,把词语丰沛的活力展布在多样化的句式中,“龚学明注意文气的控制,注重句式的打磨——包括长句子的运用,以及修辞的陌生化。句式的平和沉稳,凝重澹定,充分折射出主体纯熟的诗学功底,尤以深情的诉说、理性的展示、睿智的评判,形成自身独有的诗歌语感[3]。”当然,对诗歌来说,语言的梗结有时恰恰是一种诗性的流畅,在诗中恰当地延滞,也可以带动张力感的深层渗透。这可能也是龚学明在以后的写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总体上看,龚学明的诗集《白的鸟 紫的花》在主题上追求一种诗性的哲学表达,他没有停留在对生存体验的哲理性表达层次,而是试图从更深处挖掘生存体验的复杂内涵,实际上关切着人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追问,诗人的迷惘和思想冲动都落实在自我的真切感知上,大都显得凝重深刻。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诗人用诗的形式进行表达,尤需避免带上概念面罩的逻辑程序,否则就会导致诗意的弱化和匮乏。九叶派老诗人郑敏说,“诗与哲学是近邻。”确实如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是一首诗可贵的品质,尽管诗与哲学是关于存在与世界的不同语言,却可以调适在充满个性化的写作中。在龚学明的诗中,似乎可以发现存在主义的哲学背景和哲学影响。他写父亲从生病到去世的那些诗,就具有相当浓厚的哲学意味,在诗人的日常叙事中,既有父子情深的场景呈现,也包含着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即使他写花的那些诗歌,实际上写的还是人和生命,他所揭示的是生命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不过其中的人生感喟隐藏得更深而已。龚学明的诗在艺术形式上有自己的匠心,他似乎与当前的诗歌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有利于他进行独立的探索。从他的创作所展开的前景来看,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