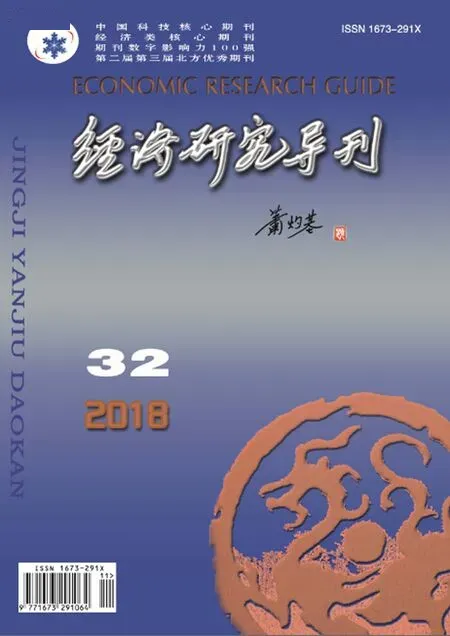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及绩效研究评述
2018-12-07蒋劭妍
蒋劭妍,韩 雪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37)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时,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锐减和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种种迹象表明,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长久化。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可以用来调节各方利益关系,使经济主体之间达到激励相容,最终起到改善生态质量的作用。
一、生态补偿的内涵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以及2000年后北方肆虐的沙尘暴使人们认识到需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观点。生态补偿由单纯向破坏生态环境者收费发展到对生态环境保护者进行补偿[1,2](王金南,2006;赵雪雁,2012)。生态补偿是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3](毛显强,2002)。我国生态补偿政策及实践已扩展到森林、草原、海洋、流域、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工程等多个领域。国际上,生态补偿是基于正外部性的环境付费(PES),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自愿的生态服务交易[4](R.Muradian,2012),至少要有一个服务的购买者和服务提供者,而且服务供给者能满足供给条件,补偿生态服务内容具有明确定义和可测度性[5](Wunder,2005)。纵观各位学者对于生态补偿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补偿是寻找生态服务产品在生产、消费和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利益不均衡、交易成本过高的领域,通过制度安排使受益方付费、受损方得到补偿,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生态补偿机制及理论基础
生态补偿机制指生态补偿制度的组成和运行,即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生态建设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由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渠道和方式以及补偿资金筹措、管理及分配等组成。众多学者运用自然环境资源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公共品理论、产权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补偿机制中补偿主体与客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进行了探讨。
(一)生态补偿主体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等三大特性,而准公共产品不同时具备该三大特性或在某一特性上存在瑕疵。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属于公共产品,因此,此类生态服务的补偿主体应是政府,公共财政补贴是其主要渠道。Sarah Schomers(2013)对457篇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发现绝大部分生态补偿都有政府参与其中,政府或是作为中介组织帮助私人主体完成生态服务交易,比如配置环境产权、建立谈判机制、实施监督,或作为生态服务购买者直接进行交易[6]。
而对于生态准公共产品是可以根据科斯定理来界定的,通过初始产权的明确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允许双方通过市场机制达成补偿协议。其中有政府在获得生态系统服务量总额的情况下,进行初始产权分配,引导建立配额交易市场[7-8](王军峰,2011;胡鞍钢,2002)。此外还有在成本收益博弈中明晰环境资源产权。Engel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印尼的森林资源管理付费案例中,PES让社区更愿意获得森林资源产权,与伐木公司产生冲突,通过讨价还价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解决产权模糊下生态环境付费问题[9]。
(二)生态补偿方式
外部性理论为生态补偿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环境资源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使用成本-收益法。对于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正外部性行为,通过奖励使其收益内化。对于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赔偿使其内化[10](刘学敏,2004)。
1.政府主导生态补偿。庇古理论和科斯理论则进一步指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政府路径和市场手段。庇古认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私人边际收益受损失,需要政府提供补贴弥补。正外部内化常用的政府手段有财政补贴、政策优惠、项目支持,也有间接的实物补贴、就业培训、技术指导等。而对于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征税或赔偿使其内化[11-12](Available N.A.N.,2001;Koskela E.,1997;温作民,2001)。政府主导型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或征收生态税[13]。
2.市场主导生态补偿。而科斯则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实质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双方产权界定不清,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要通过初始产权的界定及允许产权交易,就可以将外部性内化。一是私有业主签订协议。Abecasis R.C.(2013)分析印度尼西亚保护区潜水旅游经营者与农户之间签订的珊瑚礁租赁协议,禁止在这些地点进行捕捞、运输和锚定,由私人业主通过直接支付系统直接补偿农户的经济损失[14]。二是通过中介支付。吴水荣(2009)研究发现,哥斯达黎加的水电公司为获取稳定的水流,提供当地非政府组织为上游的私人林场主补偿森林经营和再造林的部分成本[15]。三是政府引导的开放市场,如碳配额交易、水权交易。四是间接市场支付,如森林认证。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设计生态补偿契约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效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吕雁琴(2013)分析了新疆煤炭资源开发中政府、煤炭企业和矿区居民三者在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下的博弈[16]。李国平(2014)研究了政府和农户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设计最优的激励契约,并分析了不同信息状况和农户类型对契约效率的影响[17]。
(三)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服务机制及成本理论为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有物质生产、调节气候、调蓄水量、净化水质、生物多样等,其中除了物质生产可以通过市场价格计算出价值以外,其他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都难以直接量化,需要借助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推算。具体方法有影子工程法、生产成本法、替代法,其中气候调节功能通过计算生物量求得固定二氧化碳(碳税率法)和释放氧气的价值,蓄水和调洪价值是通过存储相同体积洪水所需的工程造价来估算(影子工程法)的,生物栖息地通过修建同等规模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成本来替代价值(替代法),降解污染物功能价值根据同等污染物需要污水处理厂净化耗费的总费用替代(替代法)(欧阳志云,1999);除此,还有生态足迹法,通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差值计算生态补偿标准[18]。
另一类方法是成本收益法,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和土地发展权等。其中,有以替代生计的收益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也有以农民现实收入与预期发展目标收入之间的差距作为生态补偿标准,还有选择与研究区域发展条件相似的地区作为参考的,比较地区与保护区之间地方财政收入、农民收入、城镇收入的差异,估算研究区域发展权的损失来计算补偿补偿标准[19,20](徐晋涛,2004;于金娜,2012;陈江龙,2012)。另外,也有以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和支付意愿的。杨光梅(2006)对天津七里海湿地采用二分式CVM法进行意愿分析,分别统计了年均补偿(生态补偿)和征地补偿两种方式下的意愿水平[21]。么相姝等(2017)应用支付卡和Heckman模型分析赣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22]。
三、生态补偿绩效测度
国外生态补偿主要采取生态服务价值支付(PES)的形式,相应绩效的研究也多以案例研究为主,虽然研究方法先进、科学,但研究对象仅针对某一类指标(比如生态环境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较少涉及生态补偿综合指标。另外,应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范式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还是环境、生态领域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一)基于成本有效性的生态补偿绩效测度
传统经济学理论下,研究者倾向于成本有效性是生态补偿效率的衡量标准。Biner(2004)认为,自然资源保护中成本有效性评估从制定何种生态保护方法的产出成本节约、生态补偿项目进行管理的执行成本节约,以及相关过程中的决策成本节约[23]。徐晋涛、徐志刚(2004)通过评估退耕地块的瞄准效率,比较退耕地块机会成本与国家提供补贴之间的差异,来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成本有效性。
(二)基于效率的生态补偿绩效测度
生态补偿绩效是个复杂的系统,就如何测度政策综合效益,梳理文献后可分为几种方式:一是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分析法(AHP),建立分层指标并确定指标权重,通过政策实施前后的评价得分与权重乘积量化政策实施效果。邓远建(2015)针对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评价,构建了指标体系,得出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24]。二是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倾向值匹配方法测度绩效。徐大伟(2015)运用熵值法对2009—2012年经济、社会、生态状况相近的27县综合生态绩效进行计算,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政策绩效有效性进行评估[25]。三是DEA数据包络法,以投入或者产出为导向测算出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刘炯(2015)分析东部六省财政间生态补偿政策效果时,根据拟合值对初始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发现调整后的环境支出综合效率有所提高[26]。
四、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我国的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单一,需进一步研究扩大资金来源的渠道。一是可以将利用自然资源获取经营利益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都纳入补偿主体,对其征收生态税。二是研究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充分利用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通过购买交易途径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三是现有的补偿标准多以现金为主,补贴标准也过于粗放,无法与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匹配。以退耕还林为例,生态补贴的标准只是是否退耕,而对于林木成活率、生长状况并无考核标准,导致还林的效果难以评估和衡量。因此,未来可以对生态服务标准进行深入研究,考虑不同机制下形成的补偿标准或服务价格。四是我国市场型交易的生态服务产品还十分匮乏,准公共品的市场交易机制也还不够健全。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哪些生态服务产品符合市场交易的条件,政府应如何明晰生态服务品的产权、如何降低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