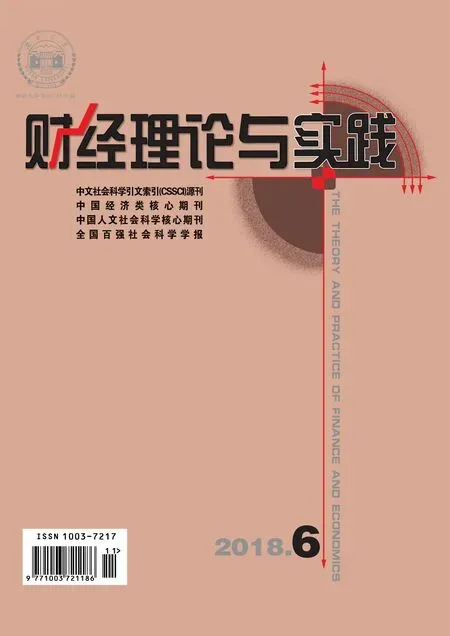政府职能转型与媒介效应述评
——以电子政务为例
2018-12-06张利平
张 利 平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日渐兴起的传媒融合给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伊契尔·索勒·普尔将媒介融合定义为“模式的融合”,他认为这种“模式的融合”主要通过两种形式模糊了媒体间的界限,即“过去为不同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一个媒体提供;过去为一种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不同的媒体提供。”[1]随着媒介融合的加速,包括微信、微博、各类手机APP、政府网站等在内的新媒体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履行其职能的重要载体,各级政府纷纷构建基于自身需要的电子政务平台。数据显示,政务外网已建成我国最大的统一政务网络平台,覆盖范围不断延伸。截至2016年6月底,政务外网已接入中央政务部门和各省及计划单列市相关单位130家;已连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14个地级市(地区、州、盟)和2538个县(市、区、旗),地市级和区县级覆盖率分别达到94.6%和89.5%。衡量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已经由2003年的全球74位上升到2016年的63位[2]。
本文把电子政务的媒介效应(media effect)界定为“各级政府利用电子政务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的媒介传播效果”。媒体参与在我国政府职能发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张锐昕和杨国栋(2012)认为,电子政务和政府职能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政府职能是目的,电子政务是手段,后者为前者服务,两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主从关系[3];但丁香桃认为,媒体发展冲击了政府信任的基础,进而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职能[4]。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我国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媒介效应的理论发展、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结合我国当前电子政务发展现状,提出此领域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方向。
二、政府职能:从传统政务到电子政务
(一)转型中的政府职能
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到国家干预主义(state interventionism),再到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的转变。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崇尚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能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 solution)。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进而,斯密认为政府的职能之一在于“建设和维护某些私人无力办或不愿办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5]近代以降,西方理论界的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取代了市场自由主义,尤其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对政府职能界定发生很大转变,认为由于“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有必要运用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与供给进行调节,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职能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凯恩斯后续的追随者大致继承了他的国家干预的思想。当代西方政府职能理论中,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出现了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6]。在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权力从某些领域中有计划地撤出是我们构建“服务型”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产业日益融合的传媒业
在现代政府职能朝着高质高效转型的同时,在微观传媒领域发生的媒介融合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趋势。科技的发展促使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社会领域,极大降低了公众的信息获取的成本并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席卷全球的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自媒体把传统传媒产业带入到一个各类媒体日益融合的“全媒体”时代[7]。Spyros M(1995)较早讨论了信息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给社会和公司组织带来的冲击。比较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之后,他预测“信息革命会在20年内达到工业革命实现的水平,并给人们的购物、娱乐和社会服务等带来彻底的变革”[8]。Gareth L (2002)分析了卫星直播(direct broadcasting by satellite,DBS)这一近年在英国和欧洲兴起的传播方式的融资渠道、运营、本土内容和多元化选择等,讨论了这一传播方式在公共服务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三)电子政务兴起
传媒业的融合发展促使电子政务(e-government)成为一个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研究热点话题[9]。国内外电子政务发展阶段的划分存在很多不同流派,例如欧委会的“四阶段论”、联合国和美国行政学会(NU/ASPA)的“五阶段”论、Clay Wescott提出的“六阶段论”等等[10],其中较有影响的有Davide A和Annaflavia B(2014)等提出的电子政务兴起“三阶段论”。他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中心导向”时期(government-centric paradigm)。这一时期政府在电子政务上面进行了大量投入,最大限度地提供线上公共服务;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借助ICT行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获得效率和效用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首要考虑目标[11]。21世纪初,电子政务发展进入“公众中心导向”(citizen-centric approaches)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政府部门以公众需求和关切为导向,重新组织他们的服务内容,使公众从电子政务发展中获益。2010年以后电子政务进入第三阶段,公众和政府部门的边界日渐模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在二者间“联合设计、联合交付”。这一“新公众驱动式”(new citizen-driven model)电子政务建立在新技术变革和日益开放的公共数据基础上,正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12]。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大致处在与发达国家同一时期,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体现了我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后发优势。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首先提出了建设全国行政首脑机关办公决策服务系统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案,并在全国政府系统推行办公自动化,2001年又制定了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建设的五年规划。按照这一规划,我国将建立起以“三网一库”(政府机关内部的办公业务网、办公业务资源网、政府公众信息网和电子信息资源库)为基本架构的政府系统的政务信息化枢纽框架[13]。当前,电子政务在我国的发展已经由当初的单纯依托PC端的单向网络浏览和搜索的Web 1.0时代进入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平台,能实现互动功能的Web2.0时代。信息技术和传统媒体业态的发展革命性地改变了我国政府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空间,政府履行职能的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三、电子政务中的媒介效应
媒介的融合和迅速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公共部门自身的,也有对私人部门的,本文主要关注基于政府职能的需要即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媒介效应。这种媒介效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媒介效应与微观组织和个人的政府信任
电子政务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提高公共部门服务效率的有力工具。基于Web2.0基础之上的电子政务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公共信息查询、公共事务办理等方面提供了便捷通道。公众信任是政府职能及其办事效率基础。Rousseau等 (1998)将信任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包括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积极期望[14]。Min等(2015)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公民信任的前因、形成及在实际公民参与行为中的变化趋势。他们调查数据来自使用政府社交媒体服务的韩国民众,结果表明,公民的政府信任可以扩展为对社交媒体和实际行为的参与意向[15]。Gregory等(2016)考察了公民对电子政务网站和公共部门社交媒体账户的使用与他们对公共部门信任度的满意度和看法之间的关系[16]。总体上看,电子政务的发展增进了私人部门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但国内经验研究显示,其影响在不同的群体中存在异质性。
(二)媒介效应与选民政治
媒介融合发展对选民政治的影响是近年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Chunfang C(2011)考察了媒体偏见与媒体对投票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温和派选民中,报纸对那些更有可能受到其影响的选民更有效果。这些调查结果表明,选民在竞选期间确实依赖媒体获取信息,但这种依赖程度取决于偏见的程度和方向[17]。Amedeo P和 Florian S(2015)建立了一个将媒体竞争与政治参与联系起来的框架。媒体报道了候选人竞选公职的能力,以及通过他们的选择来争夺观众的能力。只有当告知候选人能力对他们的群体来说影响足够大时,公民才会关注媒介报道,经验数据表明媒体报道可以增加或减少投票率[18]。Kevin A和Martin J等研究了新闻传媒对政治精英们的影响。他们发展了一种所谓的“战略反应”的理论(strategic responsiveness),即当选民关注时,当选代表更有可能注意选民的偏好,因此,新闻媒体对立法行为的影响在临近选举时最为明显,并取决于选区的党派组成[19]。Jimmy C和Wing S利用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后认为,在一个选民对公共政策缺乏足够了解动机的情况下,媒介可以通过两类媒体对选民行为施加影响,第一类媒体是直接报告政党提出的政策,现代媒体中,这一策略较少被采用;第二类媒体涉及从新闻背景分析到对重要公共政策的评价,这类媒体消息证伪困难,因而容易被操纵[20]。
(三)公共部门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
Scott G和Konstantin S(2014)提出了一个正式的政府管制媒体的模式,以阐明不同国家和时间媒体自由度的差异。他们认为大规模政府媒介宣传减少了政府和私人媒体的偏见,但增加了政府将私人媒体国有化的动机[21]。María-Dolores G (2016)认为,社交媒体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办法,以提升政府透明度,增加公民参与和协作决策或改善公共服务的机会[22]。
四、电子政务媒介效应的评价
(一)政府信任、公共社交媒体和电子政务因素:Gregory A P模型
1. 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满意度。一般说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一个必要特征,而且是有效和高效的[23]。Gregory A P基于对特定地方政府——汉城市政府(the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简称SMG)的分析,把政府公信分为能力(ability)、仁爱(benevolence)和诚实(honesty)三个维度,对这三个方面的积极评价有助于公民对公共部门的意图和行为抱有积极的期望,从而使公民最终信任他们的政府。
2.政府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多公共部门把社交媒体作为增进与居民交流和增进联系的方式[24-26]。社交媒体的形式众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微博、推特(Twitter)、微信公众号、脸书(Facebook)、Youtube等等众多形式。一般而言,由于社交媒体强加给用户的格式限制,信息通过电子政务的某种传播形式传播得越频繁,信息往往更短、更模糊。例如,微博和社交网站经常对帖子的长度设置限制。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例,公共部门使用社交媒体可能是向某一地区的居民提供当地公共卫生诊所免费注射流感疫苗的最新情况,同时也将他们引导到诊所的网站获取更详细的信息(Aizhan T等,2017)。公共部门拥有的社交媒体数量越多,越容易增进与公众的交流。
3.电子政务网站平台。相比社交网站,电子政务网站可以有效地传递出一些更详细更深入的信息[27]。电子政务网站的发展潜力就在于它能迅速传递深入具体的信息给公众。通过公开大量的详细信息,电子政务网站被认为有助于减少政府和公民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并提高公民对政府行为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的理解[28]。电子政务建设越完善,越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
综上所述,Gregory A P模型主要通过经验数据研究政府信息通报中的详细程度如何影响公民对其公共部门的评价。研究结果澄清了公开披露信息与公民对其公共部门的评价之间的复杂关系,表明通过更具体的电子政务形式公开披露政务信息通常对公民的政府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通过电子政务形式传递的信息有利于积极影响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这些发现为不同形式的电子政务与公民对其公共部门的评价关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但其研究没有审查通过电子政府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传播的信息内容,因而可能影响公民对其公共部门的评价的准确性。
(二)政府信任与媒介效应:Min J P模型
政府职能的履行是通过众多政府的分支机构具体社会管理职能实现的。受众对某一特定社交媒体的信任会传导到这一社交媒体拥有者及其同盟,有关这种媒介外溢性(spills over)的传导效果的经典理论主要有“认知平衡论”(cognitive balance theory)和“认知失调论”(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两种。认知平衡论认为,社交媒体用户在对社交媒体和他们在这些平台上所遵循的品牌的态度上力求和谐平衡, 这意味着那些在社交媒体上高度信任的人将这种感知传递给他们在平台上所遵循的品牌[29];同样,认知失调理论预测,那些不信任社交媒体品牌和托管品牌的人,要么放弃平台,要么在社交媒体上忽略不可靠的品牌。因此,由于这些认知和社会过程,人们对社交媒体服务的信任有望转移到社交媒体托管的品牌上,平台上的用户也会紧随其后[30]。电子政务兴起后,实践表明,政府机构电子政务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对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信任感总体上是正相关的[31,32]。
基于上述研究,Min J P发展了政府信任理论,其贡献在于他们将来自社交媒体的政府信任分成:机构主导型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过程主导型(Process-based trust)和特征主导型(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三类具体类型。这三类信任类型都有助于借助媒介效应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该理论为研究政府社会媒体使用信任的前因提供了贡献,同时它也为信任的结构成分提供了综合的视角。但不足的是,研究信任因素与媒介效应需要对不同类型人群进行严格划分,他们个性特征和对媒介的反映存在个体异质性。例如,从Facebook中建立的政府信任在其他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渠道中(如Twitter)可能因媒体和通信系统的特性而不同。
(三)电子政务媒介效应测评的经验方法
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电子政务媒介效应进行测评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较有影响的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电子政务评估报告体系(UN E- Government Survey)、埃森哲咨询公司体系、布朗大学世界电子政务评估体系、早稻田大学评估体系和欧盟的评估体系。上述评价方法各有特色,指标的选取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广泛影响力[33]。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采用调查数据对我国电子政务的效果进行研究,目前采用的较多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层次分析法(AHP方法)。层次分析法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对某一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效率进行实证分析[34,35];(2)结构方程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简称SEM)。SEM是用于讨论隐变量(也叫结构变量)或潜在变量与显变量(也叫观测变量)关系以及隐变量与隐变量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焦微玲(2007)运用该方法对上海市电子商务公众满意度的评价研究[36]。(3)因子分析和DEA方法。该方法建立在投入产出研究基础之上,典型研究成果有陈岚(2010)结合因子分析和DEA方法,对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 个省级政府电子政务效率进行的评价,并分析了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相对有效性状况[37]。
总体上看,上述测评方法各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所采取的技术路径和指标选取也有较大差异,观测值的可获取性和指标的可比性还不统一;另一方面,传媒日益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日益融合,电子政务的表现形式呈现多元化趋势,现有的评价方法指标较多局限于地方政府网站或少数的APP上面,数据获取渠道还比较有限。对电子政务的媒介效应评价目前尚没有全国范围内普遍认可的指标体系和广泛接受的评价方法。
五、研究与展望
由于技术的进步,公共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公开披露了更多的信息,但信息公开披露对公民对其公共部门的评价的影响还存在争议。首先,内容上的细微差异也可能影响公民对其公共部门的评价;另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内生性和变量偏差。现有文献大多根据横断面观测数据,缺乏特定的时间顺序变量,因此排除了因果逻辑。此外,虽然考虑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影响,但一些未观察到的变量也有可能对结果产生偏差。今后研究应注意利用不同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以便更好地研究不同形式的电子政务与公民对政府的看法之间的关系。
此外,本文所讨论的信任因素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都需要对不同人群等个人特征进行严格的分析。因此,需要对twitter、facebook和网站等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政府信任对社交媒体的一般影响逻辑。并且,为了概括本研究的结果,应通过跨文化研究进行验证。虽然在验证假设时,政府信任和预期绩效都被用作控制变量,但本研究中提到的政府信任需要更严格的界定,同时也要考虑性别和年龄等不同的个体特征。
在经验研究方面,限于指标的获取性和评价方法的局限性,目前国内还没有一种电子政务评价方法被广泛接受。构建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媒介效应评价体系,并对现有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优化,推进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