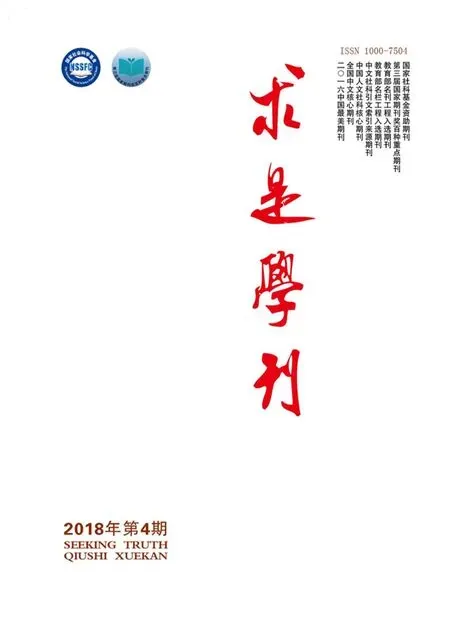权利、损害与损失①
2018-11-28道纳尔诺兰徐铁英竹译
[美]道纳尔·诺兰 徐铁英,王 竹译
一、导 论
考虑到本文对术语之价值的持续关注,我从为后文将展开的这三个概念划定其暂定的定义来开始本文的研究。当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权利”(rights)的时候,我指的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作为法律权利的请求权利(claim rights),与法律义务对应,②Hohfeld W.N.,“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1913)23,Yale LJ,,p.16,p.32.例如一项鼻子不挨打的权利或一项要求另一方合同当事人履行其债务的权利。澄清“损害”(damage)的含义正是本文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目前仅指出一点即可:当我提及“损害”时,我指的是对一个人的受到保护的利益的干扰——典型的有身体或心理损伤,以及财产损害——这将为提出过失侵权法上的请求提供依据。最后,我用“损失”(loss)指“一个恶化的抽象概念”,也就是说,遭受一项损失相当于使遭受者承受“不利差异”(detrimental difference)。
暂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些术语,我将在下文解释为何选择将注意力放在损害和损失之上,而非与其无甚差异的“伤害”(harm)与“损伤”(injury)。对此,简单的回答是:在我看来,赋予“损害”“损失”这两个词以意义较为简单,它们与那些在日常语言中被使用的字词是相通的,这样有助于走进那些在解释与理解过失侵权法的时候发挥有益角色的概念。相比之下,在我看来,正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伤害”与“损伤”缺乏那种让我们在这一特定情境下达至有益的概念的潜力。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证明的论断,然而我还是会主张,使用“伤害”“损伤”来研讨过失侵权法的核心难题是,正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这两个术语产生的概念是如此之宽泛,以至于无法被用来在该情境下划出有益的区分。简言之,我的论断是:对于一名过失侵权法律师而言,“损害”与“损失”的术语确实要比“伤害”与“损伤”更加趁手,因为它们的识别性更强。
二、权利与损害
本文在这一部分的论断是,损害的概念是看似可行的以权利为基础展开分析的过失侵权法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之所以作此论断,原因有二:其一,若干权利理论研究者已尝试将过失侵权案件中的损害要件降等,将其从不法行为(wrong)本身的要件转化为决定不法行为之可诉性的一项条件。其二,即便是那些并未公然走上这条路子的权利理论研究者,要么也表达了对损害要件的疑问,要么干脆完全无视它。
在这两种做法当中,第一种尽管为少数派,然而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并由Nicholas McBride与Roderick Bagshaw有力地表达出来。①McBride,N.J.,and Bagshaw,R.,Tort Law(5thedn,Pearson Education 2015)esp ch 5.从根子上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过失侵权法中的不法行为,到底是指将他人置于对其身体完整性、财产等的干扰的不合理的风险之下,还是指过失地令此等干扰发生。依据后者,干扰是不法行为本身的要件,到底怎样的干扰是必需的(“损害”要件的本质)才是分析的核心;相比之下,依据前者,上述问题便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至多仅仅涉及一项不法行为的可诉性,而该不法行为是否存在与此无关。我之前已说明,基于多项原因,前一种观点是无法接受的,②Nolan,D.,“Deconstructing the Duty of Care”,(2013)129 LQR,p.559,pp.561-564.它等同于说我们都拥有对抗任何其他人以避免被暴露在某些类型的风险之下的充分权利,此处无须重复其理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依据前一种观点,一个损害概念同样是必需的,确定的理由有一项,还有第二项可能的理由。说一个损害概念是不可或缺的无可争辩的理由是,存在(依据这种观点)一项采取合理注意而作为的义务支撑起了过失侵权法,它取决于可以合理地预见到被告的行为将导致原告遭受(视情况而定)身体伤害、精神疾病或者财产损害,原告在其被损坏的时候具有充分的利益。③See McBride,N.J.,and Bagshaw,R.,Tort Law.,cit.,ch 6.依据这种观点,损害之所以重要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它或许可以决定由被告不合理行为所构成的不法行为的可诉性,尽管它实际上是否成立取决于McBride与Bagshaw在说到可诉的“损失”或可诉的“伤害”(harm)时到底指的是什么。④就其对可诉性的探讨,see McBride,N.J.,and Bagshaw,R.,Tort Law.,cit.,ch 10.
权利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更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失侵权案件中的不法行为指的是过失地伤害了另一个人,那么在这种观点看来,“损伤”或“损害”的发生因而是被告的不正当行为的核心——于是也是描绘由该行为侵犯的权利的核心。然而,在这些权利理论研究者的作品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承认损害概念,显著的趋势是使用“损伤”这个词,而非“损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同时也将这个词作为“不法行为”的同义词来用。为了简短起见,对该观点的探讨将限于两位声名卓著的权利理论研究者的作品,也就是对过失侵权法进行了持续的观察研究的Allan Beever与Robert Stevens。
我们从Stevens开始。我们会发现,他确实承认了这里所说的意义上的损害概念,然而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并非就该概念本身提出,而是就在这个情境下使用的“损害”用语。下面这段文字概述出了他的立场:
对于那些笃信财产损害与人身伤害为损失的种概念的人而言……证明损害的要求并非是一项证明损伤的要求,而是一项证明伤害的要求,于是权利便从叙事中消失了。滑腻腻的用语“损害”抹去了伤害与它所造成的损伤之间的差异……①Stevens,R.,“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Oxford,Hart Publishing,2007,p.121.
Stevens通过援引一项司法判决中的损害定义来构筑其观点,即损害的用语非常“滑腻腻”,该定义称损害为“一个抽象的恶化的观念,或是身体上的,或是经济上的”,②Stevens,R.,“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cit.,p.121,引用Lord Hofmann在Rothwell给出的定义。而这个概念曾被我用来界定“损失”。分解这段话后,我们可以看到,Stevens将“伤害”等同于(我的术语体系下的)“损失”,他还将“损伤”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法性”(wrongfulness),于是,对“损伤”的处理必然造成放弃基于权利的分析立场(rights-based analysis)。最后,我们看到“损害”这个用语摇摆不定地悬在“损伤”与“损失”之间。且将“伤害”与“损失”等同视之的做法是否适当的疑问放在一边,我们面对的是接受一个被封装在公开谈论的“财产损害与对人的损伤”之中的“损伤”或“损害”概念的价值,然而在抓住该概念的时候也存在更倾向于“损伤”这个词而非“损害”的明显趋势。
由于我在这里的论断是一个“损害”的概念乃是任何基于权利来分析过失侵权法的必要组件,看起来,我与Stevens之间唯一的歧见是用语之别,因为他似乎接受这个论断,只不过较之“损害”,他更倾向“损伤”的用语。虽然如此,用语的清晰准确正是文本的核心主题,于此用语的问题是有意义的。那么,哪一个词可以更好地把握这里的这个概念:“损伤”还是“损害”?在我看来,答案当为后者,因为我认为“损伤”是一个不稳定的词汇,“损害”则没有这个问题。请回忆一下,“损伤”这个词在法律意义上可具有的两项含义:“侵犯他人的法律权利”(即一项不法行为)或者“伤害或损害”。③SeeBlack’s Legal Dictionary,cit.,p.905.由此断定,在过失侵权法的情境中,“损伤”这个词实际上正是悬在这两个含义即“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摇摆不定。Ste⁃vens的观点至少对他而言,“损伤”是具有一项特定含义的说法并不能对此等不稳定性做出回应,因为在他自己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两个二选一的含义之间游离不居。在以上提及的这个进程中,例如,对“损伤”这个词的后两种使用似乎意味着一个不法行为,与此同时Stevens在同一篇文章中称过失侵权法中的注意(duty)是“一个不去损伤的注意,而非一项不暴露于损伤的风险之下的注意”。④Stevens,R.,“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cit.,p.118.如果“损伤”这个词意指“不法行为”,该论断便显得十分古怪,如果它指的是像“损害”一样的东西,就能够讲得通了。相比之下,虽然我可以无困难地接受“损害”这个词语在当前的背景下被当作“损失”的同义词对待,然而这并非因为“损害”这个词在一般意义上的内在的含混不清,而是由于一个更加显著的未能认识到损失与损害两个概念之间差异的凌乱马虎而导致的。倘若该差异获得了认识,相关用语使用恰当,那么存在于“损害”这个词当中的含混不清便可轻易祛除。
Beever的作品亦为类似问题所困扰。他在分析过失侵权法的时候似乎故意地避免使用“损害”这个词,⑤尽管如此,至少有一项例外:see Beever,A.,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Oxford,Hart Publishing,2007,p.485.(又一次地)倾向于使用“损伤”。然而同Stevens一样,Beever也是在“损伤”这个词的两项含义间游离。在一个核心段落中,⑥Beever,A.,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cit.,p.211.他论证说损伤的真正的法律概念为“对一项法律权利的侵犯”(易言之,一项不法行为)。然而在这部作品的另一处,Beever却似乎在一个更加限定的损害或者伤害的意义上使用“损伤”这个词,他在那里谈到被告是否造成了“原告的损伤”,①Beever,A.,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cit.,p.414.或者当他说起依据矫正正义,“问题在于在被告的过失行为与原告的损伤之间是否存在恰当的规范关联”。②Beever,A.,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cit.,p.138.于是和Stevens一样,在术语上选择“损伤”而放弃“损害”导致了困惑与混淆,这再一次——这次是含蓄的——表明,对“损害”的拒绝并没有反映出对与我之前描绘的轮廓相符的一个损害的基本概念的抛弃(例如,Beever毫无困难地承认,为了证立被告实施了一项不法行为,原告必须证明该被告“损害了他对之具有一项权利的某物”③Beever,A.,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cit.,p.218(重点为后来所加).)。
就权利与损害之间的关系可作出两点结论:其一,某人间或会碰上某些情形,在其之中“损害”这个词实际上被当作(就像“损伤”)对权利的侵犯的同义词使用,易言之,一项不法行为。需再次指出,这样的用法将遭受抨击,当“损害”坍缩进“不法行为”之中时,损害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别于过失侵权行为的原因区分性因素的功用便失去了。其二,对于过失侵权法中的损害概念而言,损害是由某人承受的理念是固有的(因此我们总是说原告的损害)。现在,损害与原告之间的这一关联显然在人身损伤的场合毫无困难:此刻,原告遭受损害,因为是她的身体完整性或者精神健康因为被告的过失行为而减损。然而,在财产损害的场合,要在原告与损害间证立其关联之必要,要求我们不仅去证明一个特定的财产物品遭受了其功用或价值减损意义上的“损害”,此外还要证明原告对于该案所涉财产具有充分的利益。④See McBride,N.J.,and Bagshaw,R.,Tort Law.,cit.,pp.166-168.此刻,我们不在到底要求什么利益的问题上耽搁时间,可能有多人对于受到损害的财产具有充分利益——寄托人与受托人——以至于可以提起诉讼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背景之下的“损害”是一个与人有关的规范概念,而非一个与特定的物质实体有关的事实概念。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当然可以说原告的身体或者小汽车被“损害”了,然而支撑起一项过失侵权上的诉求的损害是一个更为无形的概念,是对一个人的受保护的利益的某种形式的干涉。
三、权利与损失
Robert Stevens在其专著《侵权行为与权利》中称,一项不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的权利在理论上是可以获得认可并由法秩序执行的,这也清晰地意味着,在他看来,这样的一项权利无法恰当地(rightly)获得法院的认可,因为只要这样去做,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法官去回应政策问题,而这将令他们偏离“对司法裁决之作成所设下的政治与技术界限”。⑤Stevens,R.,Torts and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37-378.然而在此后的一篇文章中,Stevens却采取了另外一条进路,声称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事实上在概念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论证如下:
一项不法行为或者损伤,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发生,尽管某些不法行为是可重复的,例如诽谤,或是持续性的,例如侵入他人土地。当D违反了其对C承担的不去为x的义务之时,他便对C实施了一项民事不法行为。因此,谈论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并无意义。如果损失发生了,它是违反义务的结果;它无法导向D负有义务去做或不去做什么的定义。⑥Stevens,R.,“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cit.,p.119.
Stevens的立场转变无甚说服力。在Nicholas McBride看来,他在前面这段话中的论证说不通,因为从一项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中的事实中,并不能导出讨论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结论。“如果A负有一项不对B造成损失的义务”,McBride如此论证,“那么这项义务恰恰就在A的行动使得B恶化的那个时间节点上被违反了”。⑦McBride,N.J.,“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cit.,p.363.此外,在McBride看来,Stevens的论证难以与其坚持认为过失侵权法所施加的义务乃是不去造成损伤的义务,而非暴露在风险之下的义务的观点相容,因为(就像McBride所言)“一项不去对某人造成损伤的义务与一项不去对某人造成损失的义务的结构完全相同”,因此难以解释Stevens为何打算承认前一类的义务能够存在,而后一类却不行。①McBride,N.J.,“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cit.,pp.363-364.同样地,在评论收录了Stevens经修改过的文章的文集的时候,Sandy Steel称“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无法成立的”的观点“令人惊诧”,于是他怀疑“许多人……将就这一理念产生怀疑,即‘损失’的概念无法——作为一项概念上的律令——列入一个人的主要的法律权利或者义务的行列中”。②Steel,S.,“Book Review”[2014]CLJ 466,468(评论Nolan/Robertson).相反,评论者认为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的可能性早于Stevens而提出的例子是,see Priel,D.,“A Public Role for the Intentional Torts”(2011)22 KLJ,p.183,p.198.
在此,我希望能够阐明Stevens的一项不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无法成立的这一论点的真相,并且梳理出它对过失侵权法——以及更一般地对私法——的影响。本人的论证结构十分简明,它立基于两项相互独立的主张之上,基于二者的真实性,可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结论。它们是:(1)一项不法行为(易言之,对一项权利的侵犯)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2)一个人由于另一人的行为遭受了损失与否,无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确定。因而可断定,造成损失不可能是一项不法行为,因而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是不可能的。
两项主张中的第一项,即一项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对此当无争议,McBride在其对Ste⁃vens展开批判的时候也没有对它发起挑战。毕竟,将一项不法行为构思为(用Peter Birks的话)“世上发生的一个事件”③Birks.P.,“Right,Wrongs and Remedies”(2000)20 OJLS,p.1,p.5.相似然而不同的一项主张,see Descheemaeker,E.,“Mapping Defamation Defences”(2015)78 MLR,p.641,p.646(“侵权法的任何诉因均与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件相关”).肯定没错,而世上发生的一个事件显然发生在——或者至少开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在此之外,我们可以向那些立基于一项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这一设想的那些法学理论指出,诸如,普通损害赔偿的估测要参考财产价值在不法行为发生之时的降低这一财产侵权的原则。
那么,一旦接纳了一项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命题,我们转过头看第二个命题,即一个人由于另一人的行为遭受了损失与否,无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确定。请回想一下我们正在这里使用的损失的定义是“一个恶化的抽象概念”,以至于遭受一笔损失对于遭受者而言达到了“不利差额”的地步。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是否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确定A的行为造成了B的“恶化”。从直觉出发,我们感到可以如此。以一个例子说明:假设A的过失驾驶造成了一起交通事故,而B的腿因此折断。此刻我们能不能自信满满地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时,A的行为使得B的境况恶化了?长话短说,答案是否定的:将A造成B死亡的情形放在一边(这产生了一些我们此处无须应对的难题),说A的行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使得B的境况恶化了从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嗣后事件(later events)是否会就A的行为对B的利益的作用产生影响。比方说在该车祸案中,如果B在发生车祸的时候正在驾车驶往机场赶飞机,而这架飞机在起飞时坠毁,乘客无一幸免,那么假若A未曾过失驾驶的话,B必将死于空难?在这一假设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车祸之后的最近的时刻A的行为使得B的情况恶化了,但是一项嗣后的事件(飞机坠毁)将推翻这一确信。
无法在某一刻确定A的行为是否已经使得B的境况恶化这一点,使法院试着在纯粹经济损失的过失侵权案件中,去鉴别出原告在什么时候承受了所谓的“损害”那一刻遇到的难题所揭示。在这类案件中,A的过失行为使得B在经济上的境况恶化了的主张构成了诉权的基础,这里的经济损失并非一项单独的不法行为之结果,比如过失地造成人身损伤或财产损失。在这样的案件中,无法区分损害与损失,因此如果我们使用“损害”概念,它就会塌陷入损失之中。而且法院在这些案件中坚持认为,诉因的出现,就像在其他的过失侵权案件中那样,仅仅发生在原告遭受了“损失”的时候,这意味着为了限制责任之故,他们必须准确地指出B是在哪个精确的时间点上由于A的行为而在经济上恶化了。然而,基于我之前已经指出的原因,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原因很简单:压根儿没有这么个时间点。结果(毫不令人意外地)只是有关在纯粹经济损失案件的责任限制问题上的一堆混乱不堪、令人困惑的案例法,之中毫无清晰的原则可言。
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A是一名财务顾问,他过失地建议B去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投入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基金当中,而不是建议后者选择更加多元的、高低风险搭配的投资渠道。在此情形,毫无疑问不可能精准确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B的境况因此恶化了。作出投资的一个月后,由于其投资的价值降低,可能看起来好像他的境况发生了恶化,然而假若基金之后反弹又如何?该人在两个月后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请注意我的主张并不局限于在一些“纯粹经济损失”的案件当中,或许根本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说A的过失行为是否已经使得B在经济上的境况恶化了,我主张的是作此判断无论何时从来都是不可能的。A的过失使得B在经济上的境况恶化了的遗嘱受益人的案例或可有助于理解,比如White v Jones案,①[1995]2 Ac 207.B在这里是被遗嘱指定的受益人,由于律师A的过失行为造成遗嘱人的意思未能在其过世之前载入遗嘱,于是他失去了本可以取得的遗产。尽管即使在本案中能够想象A的过失行为最终没有使得B的境况恶化的情形,例如依据当前遗嘱而受益的人不愿意接受这笔遗嘱人实际上欲留给其他人的遗产,因此将其赠与给B。
对于“B是否由于A的行为而遭受了损失无法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确定”的命题有两点异议,然而它们均无甚说服力。第一点异议是,我们在这些案件中应当在某种程度上限缩B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车祸案件中,我们将损失界定为断掉的腿以及损毁的汽车。由于在车祸发生之后,并未发生其他事件可以变更如下事实,即B由于A的过失承受了一条腿的断掉,难道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却不能说B因为A的过失行为遭受了损失吗?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可以这么说,然而这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这里说到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用“遭受损失”来指“境况恶化”,那么一项不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判断不能通过将(我的术语意义上的)“遭受损失”的含义替换为“承受损害”来反驳。
第二点异议如下:在车祸与遗嘱人本来属意的受益人这两种情形中,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可以说A的过失行为使得B的状况恶化了,然而确实存在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点上我们至少可以说这非常有可能确实发生了?既然民法是在证明标准的或然性平衡(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standard of proof)之上运作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B当作已经在那一刻遭受了一项损失,正如同我们将对待B就好像他由于A的过失行为而遭受了损害一样(但是彼时“是”相对于“否”可能性确实更高)即便我们并不能确定他的确遭受了?为了说清这点异议不能成立的原因,我们需要区分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与我们以为的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现在,A的过失行为要么导致了B的腿断掉,要么没有造成该结果,然而我们彼时无法知晓是或否。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像或然性平衡标准这样的技术来解决这个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乃是十分恰当的。然而此处正在作出的论断是: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是不可能的,因为一项对权利的侵犯(或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然而无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确定A的行为是否事实上使得B的境况恶化了。以及某事事实上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相对于我们是否会将某事当作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并非一个可以通过或然性平衡来解决的问题,无论它是确实发生过,还是没有。
不仅如此,我们现在可清晰地看到,McBride的异议并未对Stevens的“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是不可能的”论点发起攻击。请回想他的第一点异议,即并不能从一项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的事实中,得出谈及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结论,因为一项不去给B造成损失的义务将在“当A的行为开始使得B的境况恶化的那个时刻”被违背。①McBride,N.J.,“Rights and Other Things”,in Nolan D./Robertson A.(ed),Rights and Private Law,cit.,p.363.然而像已经表明的那样,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时刻。McBride的其他异议同样没有什么说服力,那也就是Stevens所称的过失侵权法所施加的义务乃是一项不去损伤(injury)的义务,而一项不去造成损伤的义务与一项不去造成损失的义务“恰恰具有相同的结构”,因此很难说明为何其中一种义务能够存在,而另一种却不能。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McBride是如何得出这两种声称的特定的义务具有相同的结构的结论的,以至于接受一个存在上的可能即意味着接受另一个存在上的可能。无论如何,一旦将(“损害”意义上的)损伤与损失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很显然,Stevens的观点并无矛盾可言。
那么,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不可能成立的这一判断又具有怎样的含义呢?就该问题开展思考的一个妥适的起点或许可以从强调对该判断的三点限定开始。首先,该判断仅涉及什么能够作为(being)一项不法行为(以及,什么能够作为一项权利),因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法律依靠是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去构造一项不法行为的可诉性,此刻,该不法行为看起来似乎造成了原告的损失。的确,在一些耳熟能详的例子中,法律以这种方式来限制不法行为的可诉性,例如在就欺诈起诉之时,得证明欺诈者给你造成了损失这么一条规则;还有诽谤者一般具有可诉性这条规则,只要原告承受了“具体的损害”。由于当前的这项不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谎言或诽谤依赖于它或者于此刻被发出——这一项技巧与这里所作的判断是匹配的,尽管在这些情形中,“损失”概念内在的偶然性依旧有可能导致若干难点,例如确定诉权发生的精确时间。
用来限制我的前述判断的第二点是,被这项判断排除出去的唯一的一类权利是一项不遭受损失的权利(a right not to suffer loss),这里的损失被界定为某种程度的“恶化”。可见这项判断并不影响其他类别的权利在概念上是否可能,我也并不试图去就可为法律承认的权利的范围设定其他限制。举例说明,这样的话,一项A不去过失地切断对B的工厂的电力供应的权利并不被前述判断排除出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出现并非不法行为的一项关键特征,如若该权利受到侵犯,那么就可以精确确定一个不法行为发生的特定时间。
最后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作的判断涉及的仅仅是法律有能力承认的权利的范围,而非责任的范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法院或者议会设置一条责任规则,依据它,责任的存在取决于B遭受了损失,因为这条规则并不依赖于B因为A的行为,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被说成是恶化了(在某种消极的意义上)这一假定。
只要牢记这几点告诫,“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这一判断的含义于是就显得更加清晰起来。其中最显著的一项含义就是,一项不会因为他人的行为而不遭受所谓“纯粹经济损失”的权利不可能存在。对于那些笃信过失侵权法建立在权利之上的人而言,这为该类损失在英国法中不获赔偿的一般规则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解释。然而还是得(再次)强调,这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并不存在一种权利——正如一项令自家工厂的电力供应不被切断的权利——可以为落入迄今所提到的不赔偿规则范围内的经济损失提供救济,②确实,或是经济损失已经在过失侵权中获得了承认的情形,然而这却并不能以被告在先对原告承担责任为依据而得到解释。轮廓清晰的唯一的例子是当代英国法中的White v Jones,这里被侵犯的权利必定是顺着这一项权利的边界,即一项不被过失地剥夺对一笔打算给他的遗产的权利。当遗嘱人死亡之时,这样的权利便遭到侵犯,在该案件中诉因确实是在这个时候受到判决认可而成立[Bacon v Howard Kennedy(a firm),PNLR,1998(4),p.1].(请注意我并不是在对此等权利的存在大加赞扬,而仅限于指出,在这类案件中,这是唯一一种有根有据的权利类型)。同样不能由此推断出,法律就不能设置一条责任规则,在特定的情形下允许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
与这个判断有关联的一个含义是,纯粹经济损失不获赔偿规则的最主要例外——即A对B承担了相关的责任的情形——只能与过失侵权法的权利分析(a rights analysis)协调起来,除非在这类情形中,B所承受的经济损失并不定位在违法性问题本身,而只是定位到一项在早些时候犯下的不法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上(假定是A过失的行为因而违背了依合理注意行动之义务的那个时刻)。既然合同违约的不法行为并不取决于对损害或损失的证明,那么这里的分析便与较早的“违约损害赔偿之诉”(assumpit)学说(它同样影响了现代合同法)中的责任承担理念的起源是一致的,同时,它与在过失侵权中责任(li⁃ability)产生于责任的承担(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的那些情况的共同之处,至少不亚于它们与过失侵权法的其余情形之间的共同之处的这个熟悉的论点发生共鸣。
我并非首个指出在这里谈及的纯粹经济损失案件的原告并非“权利”的研究者,然而之前就该观点提出的论据是循环的,又或者说,它们(至多)建立的不过是一个较狭隘的命题,即此类案件中的原告并无财产权利。我们在此似乎遭遇了两个难点(它们紧密相连):第一,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似乎将权利设想成是由过失侵权法设定的——过失侵权法本身认可此等权利——或者说其存在独立于过失侵权法,这一概念可很好地在Beever的过失侵权法的“权利基础”的用语中得到表述①Beever,A.,Rediscovering the Law of Negligence,cit.,pp.61-70.(仿佛这个“权利基础”与过失侵权法分得开似的)。如果这些学者使用的“权利”(同我一样)指的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请求权利(claim rights),那么这样的将过失侵权法与作为其基础的权利的分离就说不通了,因为一项请求权利——从一项规范的受益者的立场出发,就法律的意义提出的一项主张——与它自己的规范是不可分的,因而亦与该规范构成其一部的法律也是不可分的。第二,这些学者中至少有一部分,似乎是在将这个论据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或者说逻辑上无法辩驳的主张提出来的,而实际上该项主张以一个过失侵权法的特殊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为前见(本质上是康德意义上的权利)。相形之下,这里正在提出的主张绝无循环论证之嫌,它也不以过失侵权法的任何特别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为前见。它只是一个我从两项假定出发从而必然得出的结论。如果这两项假定均为真,而这项结论确实是必然从它们那里得出的,那么这项主张本身必然为真。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尽管我无意将“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论断在私法上的所有可能具有的含义讲清楚,这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一论断的涵盖面不限于过失侵权法。举一个例子,试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存在一项由于合理地信赖他人的允诺而不因此遭受不利(detriment)的权利,这项权利曾被论证成允诺(或衡平)禁反言学说的根基。既然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确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赖已经是不利的,那么这种权利也就无法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允诺禁反言学说就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rights-based):比方说,可能是这样的,即允诺的给出,在受允诺人身上产生了一项该项允诺将被遵守的权利,然而未遵守允诺的不法行为只有在受允诺人信赖该允诺而行动之时,或者当此等信赖看上去可能是有害之时,才成为可诉的。即便沿着这条路子展开的权利取向的分析被认为不足以令人信服,对允诺禁反言学说——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将是一条责任规则(lia⁃bility rule),它的主要内容是:如果B合理地信赖A从而对自己不利,那么A便有责任去确保B不遭受此等不利,二者似乎正是Ben McFarlance所论证的构成某些允诺与所有权禁反言案件之根基的允诺-不利原则的主旨。②McFarlance,B.,“Understanding Equitable Estoppel:From Metaphors to Better Law”(2013)66 CLP,p.267.再一次地,一项这类的责任规则与此处正在作出的论据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正如McFarlance说明的那样③McFarlance,B.,“Understanding Equitable Estoppel:From Metaphors to Better Law”,cit.,p.294n.)在这样的分析中,允诺人并无义务——因而对受允诺人不享有权利——直至法院的判决作出,于是这条原则并不依赖于在概念上是否可能存在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
四、损害与损失
从前文当中,很容易得出我认为损害(作为过失侵权诉因的一项要件)与损失是两个根本迥异的概念,在本文的这个部分,我希望展开这一论断,与此同时,还有损害的存在不能以损失之存在为前提的论断。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损害与损失是两个根本迥异概念的论断看似有争议,因为在著名判决中对损害所作的界定将其等同于损失,意指因为被告的过失行为而“恶化”(或是遭受了某种“不利”)。此外,法官与学者时常在这个语境下互换式地使用“损害”与“损失”的两个词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发觉根本性的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一开始就不相信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不情愿对损害和损失进行区别对待的态度令人惊讶,尤其是想起二者在日常语言中的大相径庭的含义之时,在我看来,此等情形亦在私法中有(或应当有)其反响。
即便如此,我的损害与损失是两个根本迥异概念的论断是一个法律论断,因此我必须在法律的层面上证成它。而对法律进行更为细致的检验,该论断愈发显得符合现实。损害与损失之间的根本不同最清楚地在房产损害案件中展现出来,在这里被认为遭受了损害的人(因而具有诉权)并没有遭受损失,同时遭受了损失的人却被认为并未遭受损害(因此没有诉权)。试想一个例子。一幢房子由于A的过失造成的震动而受到了损害,B为房屋主人,而损害(也就是价值的降低)只是在B已经将房子出售给C之后才暴露出来。在此情形,B被认为是遭受了“损害”因此对于A享有一项诉权,而C——他才是境况很可能会恶化的那个人——却不被认为遭受了损害,因此无法起诉。与此类似,货物的出卖人能够在其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之前就对其造成的损害提起侵权之诉,即便此时风险已经转移给了买受人,①The Charlotte[1908]P 206;The Sanix Ace[1987]1 Lloyd’s Rep,p.465.反之,买受人(真正遭受损失的人)却无权起诉。②See egLeigh&Sillavan v Shipping Co,The Aliakmon[1986]AC,p.785.
面对这样的例子,人们可以争辩说,将过失侵权责任建立在损害而非损失之上有可能产生强差人意的结果。然而我们应当牢记,还有一些第二顺位的原则可以用来抚平这些坎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保险人代位财产所有人就被保险财产主张赔偿的权利。像这样的一些原则与本文提出的论断和谐相处。此外,我并不是要争辩说过失侵权责任不能(甚至不应当)被建立在损失而非损害之上,我只是想说,将其建立在损失之上将引发一个责任规则的分析(a liability analysis)而非一个权利/义务式的分析。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需要概括地在这两条路径中二选一,因为虽然理论上它们能够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于是救济要么以损害要么以损失为基础——然而在实践中这样做肯定会导致无法接受的结果:比方说,这样做将使得被告在前段讨论的案件中承担双重责任。当普通法国家的立法者与法院决定去允许过失侵权案件中的请求以损失而非损害为基础时,应将其铭记在心。
它把我引到一个相关的论断,即如果损害概念与对过失侵权法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分析是相容的,那么损害的存在绝不会以损失的存在为前提。这一论断可从我已作出的其他论断中容易地推出。一项不遭受损失的权利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一项不会遭受损害的权利并不可能引起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而只有在若损害的存在以损失的存在为前提时才会如此。更一般地说,如果对一项权利的侵犯发生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只要损害的要件对于一项过失侵权法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分析而言不可或缺,那么一个人承受了或是没有损害肯定是可以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上确定的。
且将在纯粹经济损失的案件中使用“损害”会出现的困难放在一旁,当前为法院使用的损害概念显然是符合这些认知的。当然,在实践的层面上,准确指出原告遭受了损失的那个时刻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背景下的诉讼时效案件显然设想这一时刻确实是存在的,而在纯粹经济损失的背景下,确定这样一个时刻的尝试所造成的一系列判例法的问题中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努力。过失侵权法中的损害的时间确定(time-specific)本质在The Starsin案①Homburg Houtimport BV v Agrosin Private Ltd(The Starsin)[2003]UKHL 12,[2004]1 AC,p.715.的分析中被揭示出来,该案中有过失的装载方式使得多种货物在航运过程中逐渐变质。英国上议院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失侵权的诉因一劳永逸地在货物首先遭受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损害之时产生,且只有在该具体时刻对货物具有权利的人(而非那些在航运的较晚的时刻取得了此等权利的人)有权利提起侵权之诉。该项“一劳永逸”原则同样适用于人身伤害赔偿案件。
虽然如此,在财产损害案件中,对基于权利的分析,损害的存在决不能以损失的存在为前提的主张,可能具有一项潜在的意义非凡的含义,因为这将推导出无论A的过失行为是否对B的财产的市场价值造成了影响这一事实,并不能决定B是否遭受了过失侵权法上的请求意义上的损害。这是因为市场价值的降低是损失的一种形式(“恶化”),它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一样共同具有偶然性这一特征,这显然是因为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可随时间而波动。举例说明,假设A(一名街头涂鸦艺术家)未经B同意便在后者收藏的19世纪山水画上“签下大名”,显著降低其市场价值。但是让我们假设A随后成名成家了,以至于几年后这幅画作的价值大涨,如今其价值远高于它没有被“签名”时。如果这里的损害的存在取决于A的行为一般地或是明确地降低了这幅画的价值,那样的话压根儿就不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以至于可以声称该幅画被损害了,这在A的行为的效果对于B的财产的市场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案件中确实是通常情况。
结果表明,当我们在过失侵权的背景下界定“财产损害”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例如,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司法判决对财产损害作出的定义即“物理上的改变,它使得该物件用处更小或者价值更小”②Hunter v Canary Wharf Ltd[1997]AC 655,p.676(Pill LJ).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依据这样的检验标准,物理上的改变对财产的市场价值的实际作用具有决定作用。尽管其间的差异十分微妙,可以接受的另一项定义(它在刑法中的损害背景下被使用③See egR v Whiteley(1991)93 Cr App R 25,pp.28-29(Lord Lane CJ).)则是“物理上的改变,它削弱了财产的价值或功用,”④对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财产损害概念的运用,seeRanicar v Frigmobile Pty Ltd[1983]Tas R,p.113,p.116(Green CJ);Douglas,S.,“Actionable Interferences: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hattel Torts”,inDegeling and others(n 53),p.90.See al⁃soLosinjska Ploviaba v Transco Overseas(The Orjula)[1995]2 Lloyd’s Rep,p.395,p.399(Mance J).(将犯罪测试标准描述为过失侵权情境下的一个切题的指引)。《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一个对“损害”下的定义式“损伤、伤害;例如对物的物理损伤,像减损其价值或有用性”。,只要它被理解为这样一类的物理上的改变,它倾向于对于像本案中的财产物品的价值或功用具有消极作用。因为第二项定义将关注点从这个特定的改变对这个特定物品的价值的实际的作用上移开了,它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项改变发生的那一刻,财产遭受了损害。因此,在山水画的例子中,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这个乱涂会减损其价值,我们能够说在19世纪山水画上的涂鸦倾向于具有此等效果。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压根儿不去谈论价值,而是聚焦于作为一个自足概念的“削弱”,意思是该案中的物品由于过失行为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好(less good)的物品。比如在山水画案件中,这幅画在涂鸦被加上去的那一刻就被削弱了价值,很简单因为相较于曾经的样子,现在的它成了一幅不那么好的山水画,如同打断某人的腿使得这条腿不那么好了,以及在别人的车上划痕使得这辆车成了一辆不那么好的车一样。
结 论
第一,我的论断不是否定损失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损失的概念在评定损害赔偿金额的时候是有价值的,而我们也看到了,它有时候被用来确定一项不法行为——该行为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它——的可诉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损失”的概念当然能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概念的精确参数也在学者的分析中获得了有益的探讨。
第二,无论如何,我都不应当被指控为暗示“损失”相较于“损害”而言较次要或者不那么具有根本性。相反,在事物的宏观框架下,一个人的整体福利自然比一扇被打破的窗户或者被打断的胳膊意义更加重大。问题仅仅在于,损失的本质决定了这个概念本身无法用来构建我们相互之间互负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尽管法制史方面的考察可以大幅提升我们对现行法的认知,无论是作为学者、实务工作者还是法学学生,然而我们不应成为历史的奴仆,而应当努力使我们的规范进步,从而让未来的法律优于过去的法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提炼或是抛弃那些已不再适宜的学说,这方面的一个佳例是本身可诉的不法行为(per se)与证明了损害才可诉的不法行为这一古老分类。这里使用的词“损害”实在是滑腻腻的,它有时候指的是我使用“损害”所指称的那种意思(因此损害是不法行为的一项要件);有时候它又指我使用“损失”这个词来指称的意思(因此遭受损失是不法行为的可诉性的一项条件);而又有一些时候它什么意思都没有,比如在私人侵扰的侵权行为中,损害在这里不过是对土地的利用和享用的实质性干扰这一核心理念的同义词(因此并没有添上什么东西)。
第四,审慎而一致地使用法律术语的重要性。无须赘言,我并不期待大家就这样接受我在本文中对损害和损失所下的定义。然而,我确实认为可以合理地期待立法者、法官与学者将来在使用法言法语的时候做到始终如一,并且至少考虑一下,例如,互换式地使用像“损害”“损失”“损伤”“伤害”这样的术语到底合不合适,换句话说,分别赋予哲学术语以离散的含义是不是更加有益呢,希望这将有助于澄清讨论中的规则、原则与论点。漏洞百出的术语使用既是漏洞百出的思辨的结果,同时亦为其原因。
最后一点,我写下本文所欲达成的目标其实是相当朴实无华的,那就是澄清若干被私法学人用来论述各自主题的概念的性质及其界限(或许,有时候,稍具一点野心,确定并探索私法学人可得如此使用的若干概念)。尽管如此,否认我在本文中做的这一类“概念调整”工作的重要性将是一个错误。相反,我希望自己已经表明了小心地界定我们使用的不同概念间的边界可以极大地有益于私法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