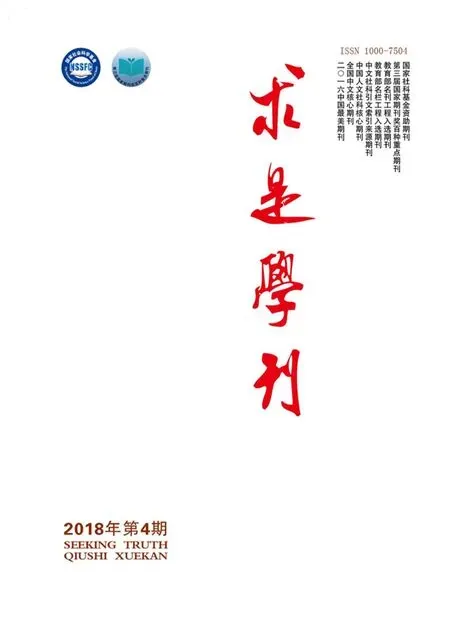非经典文本的程式化写作:以谢榛七律送别诗为例
2018-11-28颜子楠
颜子楠
基于一个长期的经典化过程,在现今的文学史框架下,学界对于中世诗歌的认知已经非常成熟,针对诗歌文本的分析方法也较为完备,从传统的文献考证、知人论事、文以载道、情景交融、诗史互证,以及受到西方学术影响的比较文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阐释方式,乃至于现今比较流行的地域研究与文化研究。然而相比较而言,对于缺乏经典化过程的近世诗歌文本,现今学术界的研究似乎还未能超越“文学史书写”的阶段。与此同时,由于近世诗歌的数量太大,且“经典诗学面对占绝对数量的非经典作品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学界针对明代“非经典文本”的系统性的分析也较为缺乏。①本文中“中世诗歌”“近世诗歌”“经典诗学”的概念均援引自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新的、针对非经典文本的分析角度,对明代诗人谢榛(字茂秦,1499—1579)的七律送别诗进行个案研究,思考非经典文本本身的特性,以及在明代文化环境下诗歌写作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性与实用性。
正如张剑所关注的,“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倾向,与近世诗学观念、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变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②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近世诗歌的另一特点是“程式化倾向”。所谓“程式化倾向”主要体现在诗歌文本层面,即创作情境的近似、表现内容的趋同、文体风格的模仿等,而“程式化”往往最为直接地体现在诗人写作技巧的“僵化”,也就是作者对于某些固定的写作程式的一再重复,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因此,本文即专门研究诗歌文本所展现的“程式化”问题,尝试分析谢榛留下的大量非经典诗歌文本。然而以非经典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还是有必要先从经典文本切入。谢榛作为明代“后七子”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人,其生平、社交、诗学等方面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①现有关于谢榛的研究成果,以李庆立的贡献为主。李庆立在其2003年出版的《谢榛全集校笺》的附录中有一个较为详细的索引。见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22—1426页。2003年之后的研究成果关注的重点依旧是谢榛的诗学思想,这些论文大多可以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上找到,但由于数量较多,在此无法一一援引。最近的有关谢榛的专著是赵旭:《谢榛的诗学与其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其他关于明代诗学研究的著作中也有许多与谢榛有关的论述,如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等。整体看来,学界主要讨论的问题大多围绕着谢榛的生平交际和诗学理论而展开,唯有张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从谢榛的山人身份出发,讨论了其诗歌创作行为和社会活动的一系列问题,见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首尔:新星出版社,2003年,第73—79页、第98—99页、第126—127页、第144页、第146页、第151—152页、第190—192页、第206页。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谢榛最为“经典”的一首七律送别诗,进而揭示经典文本与非经典文本之间的关联,并思考谢榛诗歌创作行为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性与实用性。
一、明代“最好”的七言律诗之一
从诗歌体裁来看,后世的文学批评家大多赞赏谢榛的五言律诗而非七言律诗,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七言律诗大多有应酬的倾向。②李庆立:《谢榛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299—302页。谢榛的七律总数约有六百首,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写给特定的读者的,有比较明确的社交功能——他的很多诗题都包含有他人的姓名、官职以及“送”“寄”“酬”等字样,甚至会明确记录下写作的具体时间、地点与目的。许学夷(1563—1633)对于谢榛的应酬诗作非常反感,③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19页。但对其与行旅、送别相关的律诗则持有相对较为积极的态度:
严沧浪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愚按:茂秦五七言律、绝,其妙处正在于此。今人不惟厌其诗,且厌其题矣。④许学夷:《诗源辩体》,第421页。
作为清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沈德潜(1673—1769)对于谢榛五、七律的观点与许学夷大致相仿,同时,他于《说诗晬语》中提及了有明一代“最好”的两首七律,其中一首便是谢榛所作:
谢茂秦古体,局于规格,绝少生气;五言律句烹字炼,气逸调高。集中“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人吹五更笛,月照万家霜”,“绝漠兼天尽,交河荡日寒”,“夜火分千树,春星落万家”,高、岑遇之,行当把臂。七言《送谢武选》一章,随题转折,无迹有神,与高青丘《送沈左司》诗,并推神来之作。⑤沈德潜:《说诗晬语》,《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沈德潜在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的《明诗别裁集》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送谢武选少安犒师固原因还蜀会兄葬》
天书早下促星轺,二月关河冻欲消。白首应怜班定远,黄金先赐霍嫖姚。
秦云晓渡三川水,蜀道春通万里桥。一对郫筒肠欲断,鹡鸰原上草萧萧。
(沈德潜注)将题意逐层安放,一气转折,有神无迹,与高青丘《送沈左司》诗,三百年中不易多见者也。⑥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6页。
谢榛的《送谢武选》被沈德潜看作是明代最好的两首七律之一。当然,《送谢武选》是否为明代最好的七律可以进一步讨论,然而此诗在明代七律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却毋庸置疑。本文即从这首《送谢武选》开始,在以下三小节中分别讨论这首诗的诗题、颈联和尾联所反映出的写作程式,进而延伸到针对相同类型的非经典文本的分析。
二、分割诗题与线性逻辑
毫无疑问,沈德潜对于《送谢武选》的解读是非常准确的,即这首诗的写作方式就是“将题意逐层安放”在四联之内——我们可以先将诗题中所有的动词提炼出来,即“送”“犒”“还”“会”,并以每一个动词所从属的短语为单位,将诗题分割为四部分。与之相对应的,这首诗的每一联分别阐述了诗题中的一部分(一个动词短语):首联写谢榛“送”谢东山(字少安,号高泉子,1541年进士,当时可能于兵部武选清吏司任职)出京,颔联假设谢东山在固原(今宁夏境内)“犒师”的场景,颈联假设谢东山顺道“还蜀”时能够看到的景色,尾联再次假设谢东山“会兄葬”时候的心态——这首诗的四联完全按照线性顺序将诗题的四部分呈现出来。
由于沈德潜强大的诗歌鉴赏话语权,《送谢武选》或许可以被视为一首被沈德潜“经典化”的作品。不过当他的观点被接受之后,似乎后世很少有人继续发展此种分析方式来讨论谢榛其他的七律作品——换言之,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似乎并不在意这首诗所展现的“将题意逐层安放”的现象是否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送谢武选》成为一个特例,一个可以让人赞叹的、拥有奇妙结构的佳作。①关于前人对于《送谢武选》诗作的其他几条评论,可参考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第476—477页。陈书录同样赞同沈德潜的观察,也认为这首诗在谢榛的诗集中属于“个别精品”,见陈书录:《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17—318页。然而,这恐怕只是经典化所产生的幻象而已。如果我们深入阅读谢榛的诗集,用同样的角度来观察谢榛全部的七律,就会发现这种“将题意逐层安放”的现象实际上并不罕见:
《冬夜宗考功子相宅同张比部士直、钱进士惟重饯别方行人仲安使阙里,便道还蜀》
虚堂秉烛共开樽,岁晩梅花发禁园。南北交情今夜醉,江湖别思几时论。
天边候雁逢燕使,雪后春泥过鲁门。家在涪川暂归去,万峰回首隔中原。②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第471—472页。本文所引谢榛诗歌皆出于此版本,下不另注。
这首诗的题目依然可以被分割成四部分,即提炼出动词“同”“饯别”“使”“还”(动词“便”字在此从属于“还”字)。从诗句的内容来看,这首诗的首联强调的是宗臣(字子相,1525—1560)、张士直(生卒年不详)、钱有威(字惟重,1550年进士)、方正修(字仲安,1550年进士)、谢榛五人“共开樽”和“岁晚”,以照应诗题第一部分的“同”和“冬夜”;颔联描写的是“饯别”的场景;颈联是在假设方正修从北京前往山东阙里的路上会遇到的情景;尾联则是在假设方正修“便道还蜀”时的状态。与《送谢武选》非常相似,谢榛在创作这首《冬夜宗考功》诗的时候同样将诗歌的四联按线性顺序来照应诗题的四部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诗题都是可以被准确地分割为四部分的,诗题可以被分为三部分的情况较为常见,而线性逻辑的呈现在诗题中含有“兼”字的作品中尤其明显:
《送马汝瞻暂还夏县,兼讯乃弟子端》
王门贳酒慰平生,浮世宁求著述名。千里自嗟仍老计,十年相见又离情。
月明上党时虚榻,云白中条秋满城。有弟最良心自远,莫教宦迹似难兄。
《送王大参明甫之秦中,兼寄张方伯子文》
岛夷能御待论功,歌起渔樵吴会同。兵甲威名悬海上,旌旄行色入关中。
金城远抱山河地,宝气犹存秦汉宫。君见张衡正秋兴,三峰欲赋两争雄。
《送别张佥宪肖甫之颍州,兼忆徐太守子与》
浮云蓟北叹相违,旧社词人各是非。谪后两迁心事定,醉中多赋宦情微。
黄花含笑孤秋色,白雁离群几夕晖。颍上有怀徐干远,建安风调迩来稀。
《送翟逸人之京,兼寄张太史叔大》
别来几梦汉江干,瘦马长驱道路难。行李三秋云共远,飘蓬千里岁将残。
黄金旧使燕台重,白雪今知楚调寒。独有高情张学士,故人北去好相看。
以上四首诗在结构上的共同特点是:前两联描写诗题的第一部分,即送别的对象;颈联专注于诗题的第二部分,即对象所要前往的地区(谢榛在颈联对于景物描写的程式化倾向将会在下一小节中予以阐述);尾联转向诗题的第三部分,即“兼讯”“兼寄”“兼忆”之人。由于诗题能够被分割的部分较少,谢榛在前两联的位置才能更为充分地针对送别的对象进行描述——或许诗题被分割得越多,则越限制了谢榛在写作逻辑层面的创造力,而那些不太能够被分割的诗题,反而能给予谢榛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此外,分割诗题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送别”题材。在谢榛的诗集中有很多社交、应酬类的作品,而这类作品的题目往往会写得非常详尽,因此诗题便可以被分割成更多的动词短语,例如这首:
《十四夜即席呈应职方瑞伯,因忆去秋是夕同瑞伯归自盘山复酌潞阳官舍,时北虏已走三河慨然赋此》
去年遥自蓟城回,旷逸堪怜越客才。驿柳清秋还并辔,潞河良夜坐传杯。
青山别后边烽起,明月歌中胡马来。今夕相看感离乱,西风吹雨不胜哀。
如果按照动词来分割的话,这首诗的题目甚至可以被划分为八部分:“即”“呈”“忆”“同”“归”“酌”“走”“赋”。将这八部分放入诗歌的四联中对应分析:“即”字和“呈”字在诗中没有体现;“忆”字、题目中涉及的人物“应职方瑞伯”(应云,字瑞伯,1541年进士)和时间“去秋是夕”反映在首联;二人从盘山“同”“归”的行为反映在颔联出句,在潞阳官舍“酌”的行为则在颔联对句;北虏“走”反映在颈联;谢榛“赋”诗的行为则在尾联中予以表达。
由此可见,当诗题本身拥有很明确的叙述性时,谢榛会倾向于按照诗题的叙述顺序来安排诗句的具体内容——无论题目可以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在作品中展现出的诗题与内容严谨对应的线性逻辑(即沈德潜所说的“将题意逐层安放”)正是谢榛写作的一个基本程式。当然,诗题能够被分割的部分越多(诗题中的动词越多),其内容与诗题的对应及其线性逻辑便越明显;反之,线性逻辑则越不清晰,以至于很难被读者发现。这也就是说,写作的线性逻辑或许也存在于那些诗题简短的作品中,例如那些仅仅可以被分割为两部分甚至是无法分割的诗题,如“赠某人”“寄某人”“答某人”等。但是,也正是由于诗题太短,因此无法将其作为诗句的参照系——如果我们再要试图证明线性逻辑普遍存在于谢榛所有的作品中,恐怕便是有生搬硬套的过度阐释之嫌了。
总而言之,谢榛在送别诗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交诗的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写作程式,即按照诗题叙事的线性逻辑来书写诗歌的内容。反向思考这一问题,拥有这种线性逻辑的作品或许能够从侧面证明,谢榛的写作行为是先确定诗题,然后按照诗题写作具体内容的——也就是“命题作文”的写作程式。律诗依照题目而写、逐层铺展的程式化写作方式并非谢榛独有,这在前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曾有所体现,尤其是“应制”“应命”“应教”之类的作品。不过,谢榛对于这种写作方式的运用似乎更为刻意,其适用范围也更广,且更符合他自己所宣扬的诗学理念。例如,谢榛《四溟诗话》中刻意强调的写诗不需要先“立意”,这或许意味着谢榛更倾向于按照诗题所表达的意思顺势创作诗句。①谢榛对于“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颇多不满,相关分析见赵旭:《谢榛的诗学与其时代》,第193—195页;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第470—473页。
三、时空转换与代入视角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送谢武选》的题目与内容的关系入手,揭示了谢榛在送别诗中所展现的一种写作程式(且这种写作程式不仅仅局限于送别诗)。在这一节中,我们由《送谢武选》的颈联入手,即“秦云晓渡三川水,蜀道春通万里桥”两句,揭示谢榛在送别诗的中间两联中经常运用的另一种写作程式,即对于时空转换的刻意强调以及代入旅人视角的写景习惯。
一般来讲,谢榛在送别诗的诗题中至少会写明两项信息:人物的身份和前往的地点。当然,有一些诗题也会包含更多的信息——正如《送谢武选少安犒师固原因还蜀会兄葬》,以及以下这首诗题很接近的作品:
《送蹇武选子修使秦中便道还巴郡》
都亭离宴对斜晖,万里星轺岁暮归。蜀岭云低迎昼锦,巴江草绿换春衣。
天连上国书难达,山断中原梦不违。南北严兵当此日,岂容常掩故园扉?
如果按照上一节中的方式阅读这首诗,我们首先会发现线性逻辑的缺失,原因是诗题中的第二部分“使秦中”在作品中并没有明确地展现,作者只是简略地谈到“万里星轺”——首联言及“送”蹇来誉(字子志,更字子修,号文塘,1518—1596)离京,而颔联便直接是在描写他“便道还巴郡”的状况了。值得注意的是,谢榛在《送蹇武选》的颔联所运用的描写方式是为了展示一种旅人在行旅途中的行进动态。在“蜀岭云低迎昼锦,巴江草绿换春衣”两句中,出句强调空间的变化(动词“迎”字),而对句表现时间的推进(动词“换”字)。参照《送谢武选》的颈联“秦云晓渡三川水,蜀道春通万里桥”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其运用的写作程式是一致的(出句动词“渡”字和对句动词“通”字同样表现了时空的变化)。①有其他版本录为“蜀道春随万里桥”。
谢榛的送别诗往往很关注空间和时间的转变,表现了他对于行旅过程的重视,而重视行旅过程则引发了对于“路”这一概念的强调。仔细阅读谢榛送别诗的颔联或颈联,我们会发现他比较执着于描绘行旅路上所见的景物,例如以下九个例子:
马经三辅雪霜后,路出五陵松栢西。(《送张别驾赴秦中》颔联)
旗影极天开驿路,剑光终夜照边楼。(《送田户曹子仁督饷秦中》颔联)
两迁薇省秦中路,一望岷山塞上云。(《送孟方伯存甫之关中》颔联)
天开鸟道三秦外,地入蚕丛万岭西。(《送张给事仲安擢蜀中参政》颈联)
使节天边云渺渺,王程春暮草萋萋。(《送宋行人进之使太原、潼关诸郡》颔联)
北极云开燕道路,中原天划晋河山。(《送陈参政汝忠还任太原》颔联)
驿骑先飞秋草路,使旌高卷夕阳天。(《送张户曹茂参募兵真定诸郡》颔联)
马经滹水鱼龙避,霜下恒山道路清。(《送杨侍御按真定》颈联)
关开涿鹿云连树,路出蜚狐雪满城。(《送李给事元树奉使云中诸镇》颈联)
综合看来,谢榛对于行旅路上的景物描写大致有四个规律:其一,谢榛习惯描写旅人在路上行进的状态,且尽量将其动态化,这也就是强调了出句和对句之间的空间转换;其二,由于受到线性逻辑的影响,谢榛在出句中所展示的空间往往是距离旅人的出发地较近的,而在对句中所展示的空间则是距离目的地较近的——如此一来,两句之中空间的变化就代表着时间的推进;②由于中文没有具体的“时态”概念,因此如果诗人要想表达时间的变化,他或需依靠虚字的介入,或需依靠描写空间的变化。其三,谢榛所写的旅途中的景物,是通过一种代入旅人视角的方式观察到的,即谢榛假设旅人在行进途中能够看到何种景色;其四,景物描写缺乏细节。
由于前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他诗人的作品,因此暂时无法准确判断以上四个规律是否为谢榛独有的特点。然而,通过对比梁有誉(1519—1554)、宗臣(1525—1560)、徐中行(1517—1578)三人的七律送别诗,仅就描写行旅过程而言,三人并不像谢榛一样有意识地强调“时间空间转换”和“代入旅人
杜约夫问曰:“点景写情孰难?”予曰:“诗中比兴固多,情景各有难易。若江湖游宦羁旅,会晤舟中,其飞扬轲,老少悲欢,感时话旧,靡不慨然言情,近于议论,把握住则不失唐体,否则流于宋调,此写情难于景也,中唐人渐有之。冬夜园亭具樽俎,延社中词流,时庭雪皓目,梅月向人,清景可爱,模写似易,如各赋一联,拨摩诘有声之画,其不雷同而超绝者,谅不多见,此点景难于情也,惟盛唐人得之。”约夫曰:“子能发情景之蕴,以至极致,沧浪辈未尝道也。”④谢榛:《四溟诗话》,第63—64页。
在这段对话中,谢榛更明确地将写作的题材与方式结合在一起讨论。在保证效法“唐体”的大前提下,他尤其认为在写作“江湖游宦羁旅”这一题材时,务必要着重写景,因为在这种题材下,写情要比写景更难把握尺度。由此,这也可以佐证谢榛在写作送别诗时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偷懒取巧、追求便利的心态。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谢榛在创作送别诗的时候是要代入旅人视角的。谢榛实际上不可能看到行旅之人真正会看到的景色,因此,他只能通过想象来描绘这些景色,而谢榛所能想到的景物,也都是很空泛的——似乎他只能想到那些雷同的驿道、山峰、白云、树木而已。⑤谢榛在谈及如何快速创作大量作品的时候,曾经说过“景出想像”的创作方式,详见谢榛:《四溟诗话》,第91页。这有可能是因为谢榛一生的踪迹局限在京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一带,⑥李庆立:《谢榛研究》,第19页。并没有太多接触不同风景的行旅经验。既然谢榛想象中的景物都差不多,那么如何在不同作品中区分不同的行旅路线呢?恐怕只剩下那些用来点明时间和空间的词了。因此,我们会在谢榛送别诗的句子中找到大量的指示时间和空间的名词,例如“春”、“秋”、“冬”(“雪”)、“夜”(“月”)、“暮”(夕阳)等,以及一系列的地名。
地名的使用在谢榛的送别诗里是极为频繁的——他无意对景物进行细致的描写,但同时又必须尽可能地将不同的行旅途径做出区分,那么,借助不同的地名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区分不同行程的方式。此外,正像前人已经讨论过的,使用地名是一种快捷地模仿“唐体”的方式。⑦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26页。地名是一种直接而又视角”,而唯一相似的是,梁、宗、徐三人的送别诗中也没有细致的景物描写。①梁有誉:《兰汀存稿》卷四至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123—174页;宗臣:《宗子相集》卷七至卷八,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313—403页;徐中行:《徐天目先生集》卷七至卷十,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271—450页。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谢榛送人前往西北内陆地区的诗句,而这些例子尤其缺乏景物的细节描写。假设我们删去诗题和诗句中的所有地名,以及那些与季节特征相关的词,我们会发现剩下的景物是很空泛的,无非是一些“山”“天”“云”“草”“树”“旗”之类的概括性的名词。②同理,当谢榛描述江南地区景物的时候,一般会用“江”“帆”“海”“月”“云”“草”“树”等概括性名词,但组合变化似乎要比描写西北内陆地区的词更丰富一些。那么为什么谢榛只运用这些相对空泛的描述,而不去观察更为细致的景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诗歌审美的个人偏好,而谢榛对此的认知在其《四溟诗话》中有着很明确的表述:
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③谢榛:《四溟诗话》,《四溟诗话·姜斋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4页。
从一方面看,谢榛不喜欢追求“实”的效果,且倾向于使用概括性的言语来描述景物,也就是描绘“远景”——他甚至认为“含糊”即是美。这应该是谢榛模仿盛唐诗风的一种方式,即使用精炼的语言描写景物的宏观性质而非微观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或许更暗示着一种取巧的描写景物的态度——既然景物“难于名状”,那么与其费力气描写以达到“逼真”的效果,不如描写得“含糊”一些更为省事:模糊的承载历史、文学、文化的方式,例如以上所涉及的“三辅”“三秦”“滹水”“涿鹿”等,都是唐人诗作中经常使用的汉代的地名。但凡阅读到这样的词,读者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与其相关的秦、汉时代的故事,抑或是前代诗人尤其是唐代诗人的相关题咏——即便是无法联想到具体的故事或诗句,读者也能够模糊地感受到地名所附带的文化底蕴。因此,从审美效果来看,读者的思绪或许会被诗句中的地名所引导,进而发展为对于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体悟(当读者有了这种体悟,或许就会认为这首诗写得很美了)。
综上所述,本节讨论的是谢榛在创作送别诗时往往在首联点明“送别”的主旨,继而在颔联或者颈联以代入旅人视角的方式,描写他人在行旅的动态中可能看到的景物,同时强调空间的变化和时间的推进。然而这些景物的描写大多是空泛模糊的,且往往需要借助地名来表现不同行程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文本表现形式并非意味着谢榛修辞能力的局限性,这反映了谢榛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模仿唐体的,也暗示着谢榛写作时可能拥有的追求便利的心态。如果我们再度反向思考这一现象,地名的使用、对于行旅过程的描述,本质上都是为了照应“送别”这一主题而存在的,因为谢榛一定会在诗题中明确地指出送别的对象(大多时候会写明官职)和他所要前往的地方。这样看来,似乎谢榛在创作送别诗的颔联和颈联的时候,其思维的核心是如何让诗句尽可能地契合题目,即考虑并描绘其送别的对象是如何到达目的地的。
四、替人抒情与假设场景
在了解了谢榛写作颔联和颈联的大致程式之后,让我们再次回顾《送谢武选》的尾联,“一对郫筒肠欲断,鹡鸰原上草萧萧”,展开关于谢榛送别诗的尾联中所表现出的第三种写作程式的分析。这两句的写法依然是代入旅人视角,即假想出谢东山在看到故乡景色的同时怀念已经逝去的兄长的场景。尽管出句“肠欲断”的主语在行文中被隐匿了,但很明显,句子的主语是谢东山——谢榛想象谢东山会在那样的场景中产生悲伤的情绪。而此句的妙处恰恰是主语被隐匿的现象——这样一来,谢榛似乎也是在暗暗地表达他对于谢东山的处境是感同身受的,而“肠欲断”或许在不经意间也变成了作者谢榛所要抒发的情绪。
由于中文诗歌语言的特点,隐匿主语的情况普遍存在,而正是得益于主语的隐匿,抒情的效果往往能够达到最佳。一旦主语被隐匿,作者笔下所创造的写作对象的情感便很容易与作者自身的情感混杂在一起。因此,替人抒情与自我抒情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皇甫水部道隆谪大梁,诗以寄怀》
闻君遥自楚天来,一到梁园见赋才。揺落旧曾悲屈宋,寂寥今复吊邹枚。
黄河荡日寒声转,嵩岳连空远色开。何事弟兄俱谪宦,西风愁对菊花杯。
(谢榛注)其兄子循谪开州。
尽管并不是明确的送别诗,这首诗的颈联同样是在想象皇甫濂(字道隆,1508—1564)在前往大梁的途中能够见到的景色。尾联由于隐匿了主语,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在“愁对菊花杯”。一种解读是谢榛做出了一个假设,即其送别对象皇甫濂想到其兄皇甫汸(字子循,1498—1583)同样被贬,因而发愁;另一种解读则是谢榛想到皇甫弟兄双双被贬而发愁——这依旧是一种感同身受、替人发愁的写法。
谢榛在七律的尾联中不仅会替他人表达负面情绪,也会替他人表达正面情绪,尤其是在那些送人前往边疆地区的作品中,比如以下六个例子:
豪侠从来多慷慨,几人钟鼎勒奇勋?(《送吴将军北伐》尾联)
丹凤城高天咫尺,壮心时拂宝刀尘。(《送李别驾宗器北上》尾联)
谩说请缨平百越,行看仗策静三韩。(《送许中丞伯诚镇辽阳》尾联)
班固为郎宁久滞,还期北去勒燕然。(《送张户曹茂参募兵真定诸郡》尾联)
计日楚才封事上,君王深见九边情。(《送李给事元树奉使云中诸镇》尾联)
不信赏功贫郡邑,封章拟报圣王知。(《送张明府召和之边》尾联)
当谢榛写诗送别的对象前往边镇地区,谢榛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军事的成就或者帝王的赏识,进而对其进行正面的期许或赞美,借此暗示自己替人振奋的情绪。
非常显而易见的是,以上涉及的这些负面或正面的情绪是很笼统的,且都是谢榛基于人情常理揣测而来的。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经颇为自得地记录,他在一日之内代作送别诗二十篇,并向他人介绍自己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
夫欲成若干诗,须造若干句,皆用紧要者,定其所主,景出想象,情在体帖,能以兴为衡,以思为权,情景相因,自不失重轻也。①谢榛:《四溟诗话》,第91页。
在短时间内创作大量作品,谢榛并不需要有任何实际的感动或者具体的经验,只需要按照想象来描写景物,按照常理来揣测他人心态即可——这就是他所说的“景出想象,情在体帖”。而谢榛大部分送别诗都有“应酬”的性质,即在他人升迁、贬谪、转任之际写诗赠予,这些作品中所表达的情绪往往都是程式化的,因为谢榛很有可能完全不了解其人官职变动的前因后果,甚至是与其完全不相识——谢榛也只能依照常理揣测他人的情感。这样一来,在谢榛的笔下,大凡贬谪之人,情绪都是愁苦的;大凡升迁之人,前景都是积极的;大凡前往边疆之人,心中都是有抱负的。
然而谢榛并没有在每一首送别诗的尾联都替人抒情,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准确地揣测某些人物在转任时具体的心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谢榛只能采用更加“含糊”的处理手段,即假设其人到达了目的地之后,会在某一个场景中做某一件事情。那么在谢榛的想象中,旅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一般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其一,其人会“回首”或“遥望”,一般是朝向京城方向:
渐老江州白司马,建章回首隔重云。(《送白户曹贞甫之三河》尾联)
回首风尘迷北望,几逢燕使问京华。(《送毛明府伯祥之羊城》尾联)
共道转输非旧日,帝京遥望朔云秋。(《送田户曹子仁督饷秦中》尾联)
沈约未须裁八咏,倚楼时复望长安。(《送沈郎中宗周出守顺庆》尾联)
定知丰剑归君后,遥望长安北斗边。(《送朱参政之豫章》尾联)
其二,其人会与谢榛“相忆”,有时候是相互的,有时候是单方面的:
宦游莫惜梅花信,岁暮长安定忆君。(《送符主簿之蜀》尾联)
东林尚忆谈禅处,月满松庭共夜分。(《送孟方伯存甫之关中》尾联)
鸣琴尚忆天涯客,莫待梅花始寄声。(《送刘明府朝宗之瑞安》尾联)
芳杜青时定相忆,赤湖桥上寄双鱼。(《送太仆卿李钝甫之滁州》尾联)
南都赋就应相忆,明月孤樽坐夜阑。(《送龚侍御性之赴南都》尾联)
其三,其人务必要“登高”或“赋诗”,且往往是在秋季:
宋玉三秋还有赋,谁同华岳一攀跻?(《送宋行人进之使太原、潼关诸郡》尾联)
壮游共拟磨崖赋,海岱秋高木叶丹。(送许克之下第归历城》尾联)
江山自此増颜色,漫向高秋独赋诗。(《送莫宪副子良督学贵州》尾联)
山灵暂尔留旌节,独立西风赋武夷。(《送章行人景南使闽中》尾联)
胜地且留何逊赋,春风应见贾生归。(《送何进士振卿谪乐平少尹》尾联)
简单来讲,谢榛一般会在送别诗的尾联揣测他人心态并代替他人抒发情感,而当谢榛不知道应该抒发哪种情绪的时候,则会采用假设场景的方式,描写他人到达之后可能会做的某件事情。
总的看来,谢榛送别诗的尾联与颔联、颈联在思路和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也会有线性的倾向。当谢榛在颔联或颈联代入旅人视角,描写他人在旅途中可能看到的景物,其在尾联则依旧会代入视角,描写他人到了目的地之后的行为。而且无论是颔联、颈联和尾联,都是谢榛依据常理想象与揣测出来的场景。这种写法的基本原则便是假设自己处于他人的状态下观察景物并思考问题。如果说得更夸张一些,或许谢榛根本不了解、也无须了解他的送别对象在离别时的具体的想法。我们甚至可以把谢榛送别诗的创作逻辑看成“谢榛送别谢榛前往某处”——前者是真实的谢榛,而后者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谢榛想象与揣测的成果,是纯粹的艺术性的创造,没有丝毫的真实性可言。
五、读者意识与偿还诗债
通过文本分析,以上三节依次揭示了谢榛送别诗中三个相对固定的写作程式。首先,从诗题与诗句的对应关系来看,谢榛的线性思维是比较明显的。其次,在首联扣题之后,谢榛往往在颔联、颈联想象旅人在前往目的地的路途中所能看到的景物,强调行旅空间的改变和时间的推进,但这种景物想象大多都很空泛,因此他需要借助地名来区别不同的行程。最后,谢榛在尾联会习惯性地推测旅人的心态,替人抒情,但有时他也会假想出旅人到达目的地之后所处的一个场景及其将要做的事情。因此,谢榛的送别诗从原则上讲是以虚构为主体的,而出现这种虚构是因为他写作送别诗的主要目的是社交和应酬——谢榛或许并不太了解他所送别的对象,很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听闻某人要升迁、转任的消息,然后便写诗送别。①这也就是说,如果想通过谢榛的送别诗(或者其他类型的交际诗)来构建谢榛的社交网络,还是有较大的风险的。当然,并非谢榛所有的送别诗都是遵循这几种写作程式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那些数量相对较少的非程式化的作品中,被送别的人物与谢榛的关系是较为熟络的,因此谢榛比较了解对方的真实行为或想法,这样在写诗时也就不需要完全遵照以上这些相对僵化的程式了。
由于暂时还没有关于明代其他诗人送别诗写作程式化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本文因此也无法过度地强调谢榛的程式化写作所具备的唯一性。然而通过与梁有誉、宗臣、徐中行三人的七律送别诗对比,最为直观的感受便是谢榛诗作中的线性逻辑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仅是诗题与诗句相对应,谢榛在中间两联与尾联中运用的代入视角、替人抒情的方式,及其诗歌整体所表现出的时间线性推进,在梁、宗、徐三人的诗中几乎无法找到。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认定,在谢、梁、宗、徐几人之间,谢榛七律送别诗的程式化程度较为严重。②谢榛诗集中七律送别诗的数量要远大于另外三人同类作品的数量,因此诗歌材料的基数较大,也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发现谢榛写作的程式化倾向。
谢榛特殊的山人身份应该是其诗歌创作程式化程度较为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明代的山人指的是那些游走于四方公卿门下,以文学或其他方面的技能干谒权贵,并以此为生存之道的一个特殊群体。③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第29—33页。山人大多交游广泛,谢榛的状况尤其如此,他往往借官僚权贵升迁转任、寿辰宴会、子孙诞生等机会写诗干谒。④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第187页。凡是此类情境下创作的诗歌,其创作行为本身被赋予了极强的社会性与实用性,诗歌的内容则往往更加关注其预期读者的感受,而非作者自身的情绪。
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来看,具有干谒性质的诗歌同样也需要作者的自我表达,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务必要契合其预期读者所处的情境,即作者在创作时必须拥有极强的“读者意识”。谢榛在写作七律送别诗时,他的读者意识是很明确的。其代入视角和替人抒情的写作方式正是为了让其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产生一种最为直接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谢榛在下笔时写的是“你如何如何”,其读者在阅读时自然而然便会以“我如何如何”的视角去阅读了。除此之外,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及的“家常话”和“官话”,以及“堂上语”“堂下语”“阶下语”的差别,都是他重视读者感受的旁证。①谢榛:《四溟诗话》,第66—67页、第105页。
同样是由于布衣山人的身份,谢榛的生计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他的写诗能力,而写诗则被认为是他的谋生工具。②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2—313页。谢榛在王府作为幕客,经常需要在宴席上代主人即时赋诗,或者在主人的要求下按时完成并上呈固定数量的诗作。他在《四溟诗话》中就曾记录自己在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快速创作的经验:
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饯于郭北申幼川园亭。赵王枕易遗中使留予曰:“适徐左史致政归楚,欲命诸王缙绅辈赋诗志别,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诸体二十篇,以见邺下有建安风,何如?”予曰:“诺。明午应教毕,北首路矣。”③谢榛:《四溟诗话》,第91页。
此外,钱谦益(1582—1664)在《列朝诗集小传》转引潘之恒(1556—1622)《亘史》中的记载,谢榛死亡的直接诱因是他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写一百首贺寿诗:
逾二年,(谢榛)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至八十余,投笔而逝。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5页。
无论谢榛是否是因为写诗而累死的,其作为布衣山人,经常需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创作,这种状态和其他那些具有官僚身份的诗人(例如后七子中的另外六位)是完全不同的。
参考艺术史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对于文徵明(1470—1559)绘画的研究:绘画、书法甚至是诗文都是在“人情网络”的社会框架下生产并流通的,是可以被看作是“礼物”和“商品”的结合,对于文徵明而言,很多画作的产生是源于社交的压力,而非出于艺术家的天性自发创作的。简而言之,艺术创作不是为了纯粹的艺术追求,而是为了偿还欠下的人情“雅债”。⑤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IX—XIX页。对于生活在同时代的谢榛而言,其诗歌的创作未尝不可被放置于同样的社会框架下进行阐释。谢榛的诗歌所具备的社会性与实用性极其明显,其创作行为往往也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有着偿还“诗债”的意味:
凡诗债丛委,固有缓急,亦当权变。若先作难者,则殚其心思,不得成章;复作易者,兴沮而语涩矣。难者虽紧要,且置之度外。易者虽不紧要,亦当冥心搜句,或成三二篇,则妙思种种出焉,势如破竹,此所谓“先江南而后河东”之法也。⑥谢榛:《四溟诗话》,第66页。
谢榛于短时间内创作大量作品有着较多的实践经验,然而在其《四溟诗话》中我们终究无法得知谢榛是如何具体地构思的;只有通过分析其诗歌文本的程式化,我们才能够看出哪些固定的程式有助于谢榛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诗作。在诗题与诗句之间放置线性逻辑相照应,在颔联或颈联的出句与对句之间放置时空转换,在尾联放置一个假设场景;一旦掌握这些固定的程式,谢榛则不需要担心诗歌的篇章构架,只需要更专注于具体字句的锤炼即可。而谢榛《四溟诗话》中关注的重点恰好是对于具体字句的锤炼,甚至“有时竟致只顾字句而不顾全诗”。⑦宛平:《四溟诗话校点后记》,见谢榛:《四溟诗话》,第133页。
余 论
当柯律格不无遗憾地认为他无法准确地构建文徵明的“画作风格(画成何样)与其制作之社会情境(为谁而画)的关系”,①“当时或许太过天真,以为真有可能建立画作风格(画成何样)与其制作之社会情境(为谁而画)的关系。很快地,我便清楚意识到这无疑是缘木求鱼。”见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第V页。本文则尝试揭示谢榛的诗文风格(写成何样)与其制作之社会情境(为谁而写)的关系。通过针对非经典作品的文本分析,我们从谢榛的送别诗中发现了种种程式化的倾向。进一步分析,“代入视角”和“替人抒情”是因为谢榛在创作时拥有较强的“读者意识”,而“线性逻辑”“时空转换”“假设场景”则是谢榛“偿还诗债”时比较有效的手段。总而言之,无论是“读者意识”还是“偿还诗债”的概念,都脱离了经典诗学的审美范畴,进而揭示了非经典诗歌文本是如何与具有社会性与实用性的创作行为相互勾连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种针对非经典诗歌文本的程式化研究推而广之,其最直接相关的便是社会学与经济学框架下的诗人行为模式的探讨。当诗人的行为模式趋向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时,其对于自身能力和文化资本的运用,把诗歌文本的生产与现实资本的交换相勾连,或许才是诗歌创作的原始动机和终极目标。简而言之,当我们继续对近世诗歌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时候,相比于针对某些诗人和作品的经典化,我们是否应该更加注重构建一个以非经典文本为主导的文学史框架,进而强调以社交、应酬为主的诗歌作品的社会性与实用性?甚至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在已经被传统的“经典诗学”所统治的中世诗歌的文学史中,我们对于诗人主体性的过度关注和推崇,是否已经误导了我们对于那些诗歌作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价值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