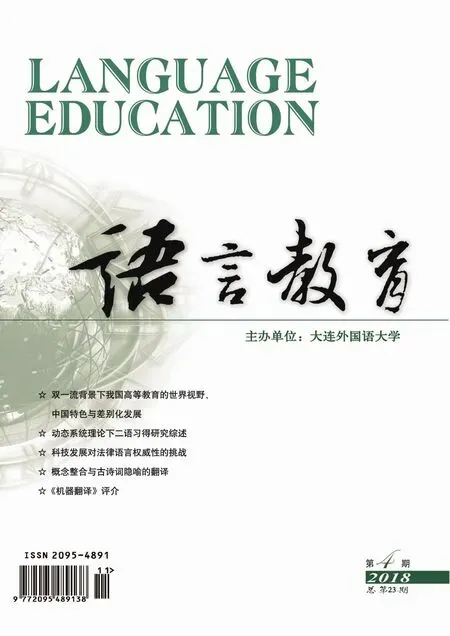“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
2018-11-28曹丽红陈文铁
曹丽红 陈文铁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连)
1.引言
近年来,反常规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①“Unnnatural narrative”一词,国内学者大多译为“非自然叙事”。笔者从“科学性”和“可读性”术语翻译原则角度,认为这个叙事学术语应译成“反常规叙事”更合适。为此,作者专门撰写了关于这个术语翻译的原则一文,并期待与读者见面。研究是叙事理论中令人兴奋的新课题(Alber&Heinze,2011∶1)。“反常规叙事学已经成为叙事理论中最振奋人心的新范式,是继认知叙事学之后最重要的新方法之一”②但是对于成立“反常规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这门学科,学界尚有争议,“反常规叙事学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Bundgaard et.al,2002:15)。(Alberet al.,2013∶1)。以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Jan Alber)、亨里克·尼尔森(Henrik Nielsen)、斯特凡·伊维尔森(Stefan Iversen)、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等为代表的西方叙事学家们对此展开了大量探讨,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反常规叙事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除了对反常规叙事的定义有多种看法外,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是后现代主义文本中“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而对于早期叙事中已经“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研究甚少。这是因为反常规元素在后现代主义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和激进。其实从历时角度看,“后现代主义的反常规情节和事件并不是崭新的现象,因为早期的叙事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反常规元素”(Alber,2011∶42)。由于早期叙事作品已经成为文类规约,读者在阅读时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反常规元素,所以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此类已经“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可以说“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是推动叙事学和文学史发展的一股被忽略的力量,理应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此本文的研究焦点是“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那么什么是“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什么是“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如何解读反常规叙事使之常规化?“常规化”的解读对文类发展有何意义?本文将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2.反常规叙事的定义
首先,到目前为止关于“叙事”的定义均侧重于“自然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反常规”的元素。“自然叙事”(natural narrative)与“反常规叙事”相对应,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将“自然叙事”定义为“自然的口头故事讲述”(Fludernik,2002∶10)。《牛津英语词典》(OED)将“反常规”(unnatural)定义为“与自然的、常规的、或与期待的不一致;非常规的、奇特的”(尚必武,2015∶96)。
对于“反常规叙事”这一术语的定义,叙事学家们则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反常规叙事学不是同质一元的理论流派。尽管反常规叙事理论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但它也是多元的、杂合的和多声的思潮,学者可以从多重研究视角来分析和定义反常规叙事”(Alber&Heinze,2011:1)。
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是最早研究反常规叙事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小说中存在不同的表现模式,即摹仿、非摹仿和反摹仿。摹仿的作品是指摹仿非虚构作品,试图通过某种可供辨识的方法来描绘人们关于世界的体验,例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非摹仿的作品可能发生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遵循这个世界的规约,或者这类作品把超自然的元素添加到摹仿的故事世界中,比如神话、童话、超自然小说等非现实主义作品;而反摹仿的作品则同摹仿(现实)相悖并产生陌生化的场景、物体和事件等,于是文本中会出现大量不可能的时空现象、因果倒置,以及对抗自然化与常规化要素的叙述行为等等,这类典型作品如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等。理查森进一步提出,“不同于非摹仿的特质,反常规实际是由反摹仿构成的,因为反摹仿违背传统的摹仿惯例,并凸显不真实的本质”(Richardson,2011∶34)。
尼尔森认为反常规是“偏离自然的范式,即口头叙述”的叙事(Alber et al,2012:373),他认为反常规叙事是虚构叙事的一个子集,其中的叙述时间、故事世界、思维再现及叙述行为等会表现出物质上、逻辑上、记忆上和心理上的不可能性,或是较之于真实世界故事情境的不可信性。
伊维尔森的定义则聚焦于故事和情节之间难以理解的冲突,即“向读者展示故事世界的规则与故事世界中的情节或事件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和读者的表面理解是相反的。”(Alber et al,2013:6)
而阿尔贝指出,反常规叙事是“在逻辑上、物质世界中和对人力而言不可能发生的场景或事件(Alber,2016:1)。也就是说,反常规叙事违背了统治着物质世界的法则、众所周知的逻辑准则和人类知识与能力的标准界限等,从而展现的叙述场景在真实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以上定义来看,叙事学家们对“反常规叙事”采用了“多重定义”,这也是强调术语本身的多元性(Alber et al,2012:351)。但是无论如何定义,反常规叙事中包含极端的、怪异的、不真实的、不合逻辑的因素,它是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越界。
2.1 “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
“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并不意味着“自然化”(naturalized),“常规化”就是解读反常规使之转化为读者认知范畴的一部分,但它们依然含有“反常规性”(Nielsen,2011:85)。只是读者不再对“反常规”元素感到陌生或疑惑,而是能够理解这种反常的故事世界。因为“读者把反常规元素划入了特定的文类规约中,即把这种异常现象嵌入到合适的话语环境中”(Alber,2016:49-50)。这些反常规的叙事已经转化到人们的认知领域,成为人们叙述表达时常见的习惯。
“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在文学史上数不胜数。从话语层面上看,典型的‘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有19世纪的第一人称现在时叙事,此外还有全知叙事、自反式叙事、同故事叙事等等(Alber,2010:131)。开始时,这些叙事读起来似乎令人奇怪,我们也很难下定义。而今天,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第一人称现在时的叙事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读者在阅读时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这种新的形式和技巧也随着时间变得“常规化”了。
从故事层面上看,我们熟知的有动物寓言中的动物可以说话;史诗、传奇、哥特式小说以及奇幻叙事中可以出现魔法;我们可以看透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的想法;我们还能接受科幻小说的时光旅行等等(Alber,2016:50)。弗鲁德尼克所谓的“寓言、魔幻、幻想和超自然”文本,包括上述的早期先驱式的文本都属于“常规化”的反常规文本。读者倾向于将这些“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视为文类规约。
2.2 “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
反常规叙事不仅包含“常规化”的叙事,还包含相反的未成为常规化的叙事。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常规叙事中的某些现象成为常规化的叙事,但仍有一些叙事,依然令读者感到突兀、奇怪。阿尔贝还划分了极具陌生感并使人疑惑的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反常规元素,和早期作品中己经逐渐演变为重要文类特征的反常规元素。“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是那些依然令读者产生奇怪的、不安的认知感受的叙事。按照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谢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y)的看法,这些不可能的场景和现象给读者造成的疏离感和迷惑感表明“这种文本仍然具有陌生化效果”(Shklovsky,1965:12)。
从话语层面上看,话语本身是为了建构故事或表达故事的,但是在反常规的文本中,话语不再为故事服务,而是为话语自身服务,话语颠覆或消解了故事。例如,叙述者会说,“今天下雨了,今天没有下雨。”这样的反常规叙述行为给读者理解文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读者无法用现有的认知模式理解故事,这样的叙事仍属于“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从故事层面上看,反常规叙事建构在物质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中,通过展现不可能的叙述者与故事场景、非现实的人物、反常规的时间或拟人化的空间,解构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叙述者、拟人化的人物,还有读者对现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比如先锋实验小说以及后现代主义叙事等就是典型的“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它们将不可能元素集中化、激进化,文本中充满了令读者感到奇怪、陌生或不寻常的场景或事件,超越了读者的认知范畴。
2.3 反常规叙事的“常规化”解读
既然反常规叙事的话语是反常的,故事世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对于那些习惯于阅读自然叙事的读者而言,不免会有陌生感、新奇感和疑惑感,同时还面临着解读这类文本的困惑。那么读者会如何阅读这类反常规叙事?
阿尔贝等学者提出了反常规叙事的“常规化”解读观点。既然我们始终受到自身认知结构的约束,那么我们也只能在认知范围和模式的基础上应对反常规叙事。读者在阅读包含不可能存在的故事的文本时,其首要任务在于阐明反常规是如何激发我们创造出超越真实世界知识的认知模式,使得我们认知的模式接受那些不存在的事物,从而让这些“不可能”成为我们现实中的可能。其次,读者需要回答反常规是如何看待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袁德雨,2016∶54)。也就是说,反常规叙事是根植于我们真实的世界。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读者的“认知”就是媒介,解读尚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就是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过程。正如在阿尔贝看来,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叙事仍然表现的是故事世界,而不是构建纯粹抽象形式的话语、文字或转向诗歌的封闭式写作(Alber,2016:46)。在最基本的阅读模式中,无论叙述的文本结构有多奇怪,它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交际行为中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就是“某人在试图表达某事”——不管这个“某事”可能是什么(Alber,2016:46)。他还将人性化图式应用于文学文本:即使最奇怪的文本,也与人类或人类的关切以及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关。的确如此,在“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中,我们依然能辨别出世俗的元素。例如,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空间和时间坐标,以及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某件事情。因此,反常规叙事仍然会“投射出一个世界,不过是部分的或不连贯的(Mckeon:1987,151)。
那么读者应该如何解读反常规叙事使之常规化呢?这就需要读者的认知充当媒介。一般来说,读者基于弗卢德尼克的“体验性”或“‘现实生活体验’的拟摹仿”,使“反常规”转化为“常规化”的过程,就是读者解读反常规叙事、恢复认知平衡的过程。根据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说法,读者在面对费解的文本要素时,可以唤起熟悉的认知模式使这些要素自然化,“如果我们不希望在碑文前目瞪口呆,那么必须要回复和归化那些奇怪的、正式的、虚构的东西,使其回到我们正常的视野范围内”(Culler,1975:134)。弗卢德尼克也认为:“通过‘叙事化’(narrativization)的过程,即‘一种通过求助于叙事图式来归化文本的阅读策略’,读者就可以利用认知要素理解文本的断裂与奇异之处(Fludernik,2002:43-46)。她还指出,规约属于文类、社会关系、惯例。阐释反常规叙事则需要遵循某些文本阅读的规约,借助于我们熟知的并且大量使用而被规范化了的套话、类别或场景(Fludernik,2012:367)。因此,当读者在反复接触文本中的反常规现象时,通常会调整阅读模式,逐步接受不可能的场景或事件,把“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解读转化成“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
当然,有些学者对于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提出异议。尼尔森、伊维尔森、理查森等学者不赞成解读反常规叙事。尼尔森认为,许多文本经过自然化的解读后,其中蕴含的含混而独特的意义都消解殆尽了(Nielson,2014:256)。他提出“反常规化阅读策略”(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建议不要一味诉诸真实世界的阐释模式,而是应该将目光转向虚构艺术本身。但我们得承认,常规化还是未常规化,都是反常规叙事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常规化”和“反常规化”解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两者皆可的选择(尚必武,2016:5-16)。
3.解读“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的意义
阿尔贝指出,“当物质世界或逻辑上的不可能性转化为一种新的感知模式时,那么一种新的文类就诞生了”(Alber,2011:43)。文类意味着“种类或类型”,“一种文类就是一种文学”(Mikics,2007:132)。“文类就是有关辨别和分类的问题:把事物组织到可识别的种类中去”(Frow,2005:51)。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nislaw Lem)认为,“静态模式下的故事讲述属于文学惯例,违背这一惯例则有助于文类的进化(Lem,1985:123)。从历时的角度看,在英语文学史上,从古英语史诗到后现代主义,各种文类层出不穷,如史诗、中世纪奇幻故事、18世纪的物件叙事、奇幻的超自然叙事、含有读心术的现代小说、包含不可能的时间的科学小说等等①本文提到的文类都是阿尔贝意义上的“亚文类”(subgenre)(Alber,2011:43)。,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阿尔贝认为反常规叙事的‘常规化’是推动新文类塑形和文学史进程的一股被忽略的推动力量(Alber,2012:373)。解读反常规叙事使之常规化将不断推动文类的创新和发展。
在史诗方面,以古老的基督教诗歌《十字架之梦》(The Dream of the Rood)为例,叙述者通过做梦的形式与十字架对话(Swanton,1970:1-78)。在叙述者“满怀悲痛/久久凝视救世主之树”时,十字架竟开口说话。文学的拟人化在古希腊文学中早已出现,而十字架自康斯坦丁大帝后也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但以十字架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欧洲文学似乎还没有先例。诗作的主体部分是十字架的独白,其中关于耶稣受难的描写生动深刻,是全诗精华所在(肖明翰,2011:11)。当然无论现在还是过去,物质世界中的十字架都是不可能说话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诗歌中出现会说话的叙述者就逐渐被读者接受,也促进了这种文类的形成。
而中世纪的奇幻故事,从广泛的民间故事体裁中脱颖而出,它的特点有“魔幻变形、巨人和侏儒、年轻女性被囚禁或被诅咒、盛大的成年仪式等等”(Mikics,2007:116)。由此可见,它和超自然关系密切,涉及到物质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力量,并超越了科学可见的宇宙。当这种奇幻故事出现时,读者则予以“常规化”解读,并逐渐接受在小说世界中可以存在的超自然力量。在阿尔贝看来,可以假设这一“常规化”的过程开始于中世纪之前,因为超自然力量早在古英语史诗时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如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古代阿拉伯、印度、波斯等的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等等。(Alber,2011:47)。因此对古英语史诗的超自然场景和事件的“常规化”解读,推动了中世纪奇幻故事体裁的形成和发展。
还有在18世纪流行的连环小说或物件叙事这一文类中,作者创造的讽刺性叙事大多不是人类叙述者,而是没有生命的物件。在本文看来,正是动物寓言的常规化推动了物件叙事的发展。马克·特纳(Mark Turner)指出“会说话的动物是一种明显的融合现象,在儿童文学中十分常见”(Turner,2002:13)。例如早期的伊索寓言包含许多“会说话的动物”,它们谈论和嘲笑人类的错误。这种会说话的动物早已常规化并转化到读者的认知范畴中。当读者遇到“物件叙述者”时,就会利用已有的认知参数,以动物叙述者为范本,逐渐接受小说世界中的物件叙述者(Alber,2011:50)。所以对寓言故事的“常规化”解读推动了物件叙事这一文类的形成和发展。
奇幻的超自然叙事这一体裁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中世纪的神话故事和之后的玄幻小说都充斥着大量的超自然元素。“鬼魂、吸血鬼、狼人、巫师等超自然生物以及预言、符咒、占卜等超自然事件在物质世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Ronen,1994:55),这都属于反常规元素。“中世纪的神话故事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规化”现象了,读者已将其转化为基本的认知模式”(Alber,2011:52)。当中世纪的超自然叙事逐渐成为常规化的叙事时,后期奇幻的超自然叙事则在此基础上加入反常规元素,并使之集中化、激进化,从而变成新的文类形态,促进了文类的创新。
同样的例子还有现代小说中的读心术、科幻小说中不可能的时间等,这些文类都是在常规化解读之后得以创新和发展。从宏观来看,后现代主义中的反常规场景和事件的创新和发展也得益于对反常规叙事的解读,因为后现代主义“把这些‘常规化’的反常规现象集中化和激进化,使得叙事文本再次变得特殊并产生陌生化的效果(Alber,2016:437)。”因此换言之,解读反常规叙事使之常规化有利于文类的创新,“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就是推动文类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4.结论
尽管反常规叙事发展相对晚近,但是在引发叙事学界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批评与争议。学者们对反常规叙事进行了多重定义,并将反常规叙事分为“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和“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对于“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读者不再感到陌生或疑惑,而是很容易接受它们就是故事世界的一部分。对于“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读者可以扩展认知范畴,把“未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解读为“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同时,解读“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对文类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例如史诗、中世纪奇幻故事、18世纪的物件叙事、奇幻的超自然叙事、含有读心术的现代小说、包含不可能的时间的科学小说等文类的发展都离不开“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常规化”的反常规叙事是叙事领域的重要命题,目前研究还远远不够,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进一步展开,以后再撰文深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