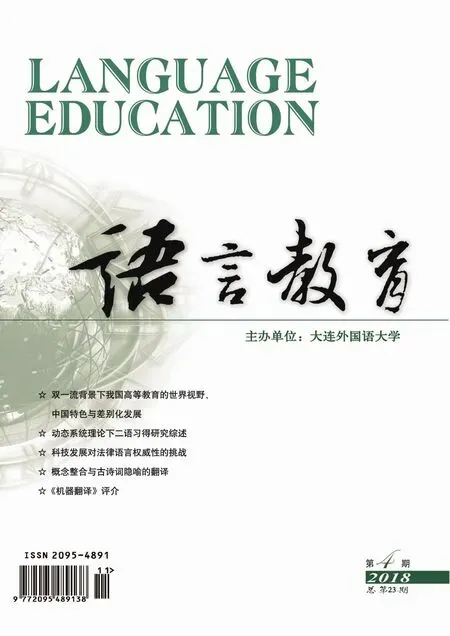战争法庭语境下的翻译行为研究
——《战争法庭中笔译证据与口译证言:拉锯战》述评
2018-11-28郑东升
吴 娜 郑东升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地区爆发战争,国际社会力量前往战事前方收集证人证言开展调查,之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在联合国提议下成立,对战争罪行进行审判,历时长达24年(1993—今),共计审判161名罪犯,450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该刑庭结合英美普通法系的对抗式审判与大陆法系的纠问式审判程序,惩戒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人权。
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战争法庭中笔译证据与口译证言:拉锯战》(Translating Evidence and Interpreting Testimony at a War Crimes Tribunal:Working in a Tug-of-War)(以下简称《拉锯战》)就是以前南斯拉夫刑庭审判为背景,剖析翻译如何影响审判,实现法律正义。作者艾伦·伊莱亚斯-布尔萨奇(Ellen Elias-Bursac)是哈佛大学前教员兼文学译者,在前南斯拉夫刑庭担任六年多译审,积累了大量法庭翻译素材。结合自身经历,作者从翻译从业者的角度审视国际军事法庭及其庭审的运作机制,对比前南刑庭翻译人员与普通从业者面临的不同挑战,阐释翻译对前南刑庭庭审过程的影响,进而为国际庭审提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2.内容简介
除前言外,本书分为两部分,即“译员”和“法庭”,共八章。前言简要介绍前南刑庭的发展历程和参与审判的各方人员构成,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陈述本书的整体架构。
第一部分为“译员”,下分三章,即从业者(practitioner)、翻译行为(practice)和实际问题(practicalities)。
第一章“从业者”交代翻译人员的相关情况。作者分析了前南刑庭发展历程中翻译从业人员构成与数目的变化,阐释了其不可或缺的文化使者身份及其肩负的职业责任,剖析其成为前南刑庭译员的动因。作者还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译员在前南刑庭最有意义和最具挑战的经历,探讨了外界对译员以及译员对庭审当事人的偏见问题。
第二章“翻译行为”探讨前南刑庭的语言服务运作机制,以及为应对挑战而制定的相应策略。前南刑庭语言服务部门(Conference and Languages Service Section)为庭审各方提供语言服务。作者分析前南刑庭将英语和法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原因,举例说明法语在庭审过程中与英语不平等但极为重要的地位;阐释为何将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统称为B/C/S(Bosnian/Croatian/Serbian),以及不采用被告或证人语言进行庭审记录的原因;陈述了前南刑庭口笔译两种职位的交融与人员流动机制,重点剖析处于庭审各方对抗焦点的口译员的身份、权利、职责等,凸显其显身的特性,探讨庭审口译标准。解释语言服务部门笔译人员因大量证据被法庭采用、庭审数量增多、时间限制等因素承担的超强工作负荷,出现重复翻译问题,激励前南刑庭出台系列翻译相关政策,优化翻译管理流程,设立检方翻译部门(DVU)分担工作负荷,确立追求准确易读的翻译标准。笔译审校工作职责让译员免于卷入庭审各方对抗性争辩,避免当庭讨论译文,节约庭审时间。
第三章“实际问题”聚焦影响庭审的翻译相关流程,即语速放慢请求(slow-down request)、纠错(error correction)与注解(annotating)、种族歧视语(ethnic slurs)翻译。语速放慢请求在多个国际法庭审判中均有使用,但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作者概述庭审过程中口译员请求律师或证人放慢语速对庭审的影响,列举发出此类请求的情形、功用和表现形式。纠错是多语法庭的翻译例常。作者在对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等国际法庭译审纠错流程后,详述前南刑庭核实备忘录(verification memoranda)在笔译文本纠错中的效用,即有效缓解庭审各方对翻译施加的压力,保持独立身份;简要介绍口译小错误纠错澄清(clarification)流程,包括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误听、误译、误解现象,强调能及时纠错且不影响庭审结果即为有效的翻译。作者梳理了几类允许笔译标注的情形,避免译员对除民族歧视语以外的文化进行注解。通过分析Balija(穆斯林:歧视语)等民族歧视语的翻译和法庭对Siptar(阿尔巴尼亚人)一词是否为民族歧视语的界定,强调此类语言的翻译应结合历史渊源,凸显前南刑庭语言服务部门作为翻译机构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焦点,在前南刑庭与庭审各方保持既独立又合作的地位。
第二部分为“法庭”(The Courtroom),下属四个章节,分别从庭审各方即证人、检察官、辩护方和法官的视角审视口笔译过程。
第四章“证人”(The Witnesses)重点关注证人在审判过程中与翻译相关的三个问题,论述译员如何因证人反供而被迫显身。证人多为来自战事国家的受害者,他们不通晓英语和法语,证词的收集和庭审作证过程完全借助翻译人员。作者首先介绍调查阶段证词的采集方式以及人们对此方式的批判;开庭准备阶段为帮助证人重温其当初被采集的证词,译员将英语证词回译成证人母语。因证人出庭作证一方面受到被告方的恫吓、侮辱,另一方面回顾不幸将再次造成精神创伤,迫于其出庭作证面临的种种挑战,庭审时证人对调查阶段收集的证词或认可,或纠正小错,或以翻译问题为由全盘推翻证言,诬陷译员篡改证言。战后审判是语言的战场,证人成为辩护双方律师通过询问进行意义磋商的介质。
第五章“检方”(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通过问询相关词汇的翻译进行意义磋商,寻求正义。“asanacija”一词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Srebrenica massacre)相关案件中多次出现,然而该词在英语和法语中均没有意义对等词。检方通过梳理作战报告及其它大量证据得以确认该词的含义,但前南刑庭译员并未确定译文。在庭审中检方又多次问询证人及被告该词的含义,而译员不得不就各方的解释给出不同译法。同一词语的不同译法使检方与法官透过语言表象了解该词的言外之意,即大屠杀。
第六章“辩护方”(The Defense)聚焦如何采取语言相关策略推进案情。一方面,检方在庭审中有举证责任,辩护方则力在对证据提出合理怀疑。辩护方通过监控译文,利用其语言优势进行强势交叉询问,引导证人作证的言辞或译员的译文措辞,淡化其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进行自我辩护的被告人依据“平等武装”(equality of arms)原则,要求前南刑庭语言服务部门提供大量材料的译本。当该要求无法得到全部满足时,被告便以此为由妨碍庭审进程。此外,被告在交叉询问过程中诱导译员披露保密信息,抑或质疑作证译员的证词可信性,使证人失信,以此提出合理怀疑。
第七章“内庭及前南刑庭遗产”(Chambers and the ICTY Legacy)梳理了法官的职责及其如何介入庭审翻译过程,并总结了判决书所体现的语言与翻译相关问题。多语庭审翻译给法官审判带来诸多挑战,同时对翻译难点的讨论亦能引起法官关注,深入审判案情难点。判决书体现庭审哪一方在语言拉锯战中获胜,败诉方多以翻译不当为由提起上诉,其中判决书和上诉判决书中出现的两类频率最高的翻译相关词汇为纠错和程序问题。作为前南刑庭遗产,判决书中所体现的法律原则对今后的国际法将产生深远影响,而判决书中对翻译问题的阐释有力地支撑了判决结果。
第八章“结论”从翻译视角审视前南刑庭成功与否。作者归纳概括前南刑庭庭审翻译机构对译员的塑造和影响,比较庭审翻译与其它翻译如文学翻译间的异同,阐释译员与其它庭审各方间不可避免的拉锯战,并概述前南刑庭处理翻译相关事宜时的不足之处和成功经验供国际刑事法庭借鉴,推进战后国际法发展。
3.评论
前南刑庭审判过程中,各方通过语言进行权利之争,而为各方提供语言翻译服务的译员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利拉锯战的焦点。《拉锯战》阐述了前南刑庭审判中译员采取的翻译实践策略,揭示译员的翻译行为对审判的影响。为加强对庭审的有利影响和降低不利影响,译员竭其所能维护各方权利,提供合格翻译服务,保障公正判决,实现法律正义。与普通译员相比,前南刑庭机构译员具有独特的身份,其翻译行为表现出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翻译原则、道德规范和翻译制度等方面。
第一,译员翻译行为受庭审具体语境的限制,遵循准确、简洁、一致、严肃等翻译原则,维持其机构译员的客观独立身份,避免卷入控辩双方拉锯战。
准确性原则:庭审是一场语言的战争,法官定罪量刑均依据以文字和语言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和证言,译员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保持绝对中立,提供忠于原文且准确的译文,不得对原文进行修饰、省略和编辑(Rigney,1999:85)。然而,前南刑庭译员主要分为口、笔译员两类,因其翻译形式不同,译员对准确的定义亦不同。笔译译文在庭审过程中实时显示在电子屏幕上,为实现视觉等值(赵军峰,2015:59),笔译译文更倾向于直译,但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用自己的语言阅读与理解,翻译时不能字对字翻译(赵军峰,2015:59),而应在直译与可读性间取得平衡。而于口译员而言,语言转瞬即逝,译员无法做到原文的全部还原,故准确不等同于逐字译(verbatim),对信息一定程度的整合是允许的。当目的语词汇缺省时,口译员为保证译文准确,多采取模拟发音,当庭解释词汇含义,而非简单地用目的语中的概念替换源语中的概念(Sarcevic,1997∶147),避免因概念的不对等而影响审判。
简洁性原则: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更好理解译文,普通语境下笔译员通常对陌生文化内涵进行注解,但由于法律文件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翻译过程切忌因一味追求“达”和“雅”而做随意解释性翻译(张法连,2009:72),前南刑庭坚持少注解原则,避免译员过多注解主观的理解,维持庭审客观公正。这些翻译策略与方法适用于前南刑庭庭审,同时也为之后法律译员提供借鉴,更好地在维护法律客观公正原则与翻译的准确达意间寻得平衡。
一致性原则:法律术语是法律概念的具体指称,法律体系的不同必然导致法律概念不对等,术语不一致或缺省。前南刑庭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累积不同法系的法律术语,制作英、法语和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间概念不对等的词汇表。因对模糊的法律陈述进行解释的权力属于法官,译员应避免对某一法律术语做出价值判断(屈文生,2009:89),这些术语通常经当庭讨论方确定涵义。一经制词成表便能保证术语在多个案件、多次庭审过程中仍保持意义统一,无需就该术语进行屡次争辩,节约庭审时间。在专业性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具备从事术语工作的能力,利用术语学理论知识解决术语翻译问题,即术语能力(王少爽,2011:69)。与普通情境相比,刑庭语境对译员的术语能力水平具有更高的要求。
严肃性原则:前南刑庭审判属于特殊用途语言情境,除交际功能、法律考量外,语用因素亦影响翻译策略(Sarcevic,1997∶5)。庭审中同一译员以同声传译形式为各方提供口译,在询问和交叉询问阶段,控辩双方律师因时间压力,常与证人的语轮间没有间隙,甚至重叠。为避免对听众(法官与检察官)造成困惑,译员需在语轮转换时进行话语标记。为保持法庭审判的严肃性,译员仅在语轮前加Q表示律师提问或者A表示证人回答,不对音色进行变声处理,避免不必要的语用因素添加,保持严肃的语体风格。
第二,前南刑庭审判中,译员在道德规范的制约下为抗辩双方提供翻译服务,确保每一方均享有平等的翻译权利,在各方间的拉锯战下显身。
无论是开庭前法官的例行致谢和赞扬,被告方的批评,抑或是译员当庭指正语言问题或出庭作证,均凸显了口译员无法隐身的身份特征。战争冲突情境下,翻译已然由语言转换活动升级为权力等级体系中复杂的社会实践,卷入冲突的各方为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努力呼吁同情以获得对他们行动的支持,以及对他们声明的敌人的谴责(穆雷 王祥兵,2014:80-81)。前南刑庭译员多来自战事国家,一方面拥有对祖国的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又受雇于前南刑庭机构,翻译过程中要保持绝对的独立和相对的忠诚。庭审各方当庭就证据材料进行激烈辩论,证据原文尚且具有争议性,加上有时目的语与源语并不直接对等,这就决定了译文的暂行性(provisional nature),且证明性的语言是法官量刑定罪的依据,故检方与辩护方就译文的措辞进行争执,就意义进行磋商,使译员成为拉锯战的焦点。囿于庭审的特殊要求,前南刑庭译员的身份从调查阶段的隐身到当庭的显身,地位上经历了巨大转变。然而,译员的显身却引起人们对翻译道德要求即保密性的质疑,为此前南刑庭制定翻译政策规定译员可不出庭作证,极大程度保证译员不被卷入对抗,避免对译员保密性职业道德的挑战。此外,译员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庭审,如译员对歧视语注解引起法官的足够重视,正义得以伸张。此类研究对其它战争法庭译员作用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为保障提供高质量庭审翻译服务,译员遵循前南刑庭机构制定的系列翻译制度,规范翻译行为,避免在拉锯战中被庭审各方所利用。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等制度规范和优化语言和翻译相关庭审流程;口、笔译服务外包,减轻译员工作负荷;文件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Document Management)成立,有效杜绝证据重复性翻译,节省资源;在继续沿用同声传译技术的基础上,采用视频监视器实时显示庭审记录,及时纠错,避免翻译错误影响审判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继续向前发展,调查阶段还可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采集证人证言,避免审判过程中证人推翻证词;语音识别技术可代替人工进行庭审笔录,应用于未来多语法庭庭审。
4.结语
《拉锯战》一书语言朴实,通俗易懂,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但在内容与表述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作者在表述上不够严谨,比如,法语作为工作语言是否当庭实时记录,作者前后表达自相矛盾。其次,作者未就翻译对庭审的影响做历时性研究,如本书内选取的某些案例审判长达17年之久,期间译员是否更换,如作更换是否对庭审有影响,作者并未提及。此外,前南刑庭判决书对战后国际法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本研究只是总结了判决书中高频出现的翻译词汇,未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亦未从法律角度审视判决书的意义。
概言之,本书有理有据,案例详实,采用全新视角审视多语法庭运作机制,运用真实案例文本诠释翻译与庭审的相互影响及作用,拓宽了多语庭审的研究视阈。另因前南刑庭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审判结合体,践行的翻译政策可供中国大陆涉外法庭借鉴。本书不仅可作为一般读者了解多语庭审及翻译的入门级教材,还可引发研究者深入思考,譬如:对比前南刑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翻译实践与政策的影响;探究中国大陆法庭与前南刑庭情形下翻译行为和作用的异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