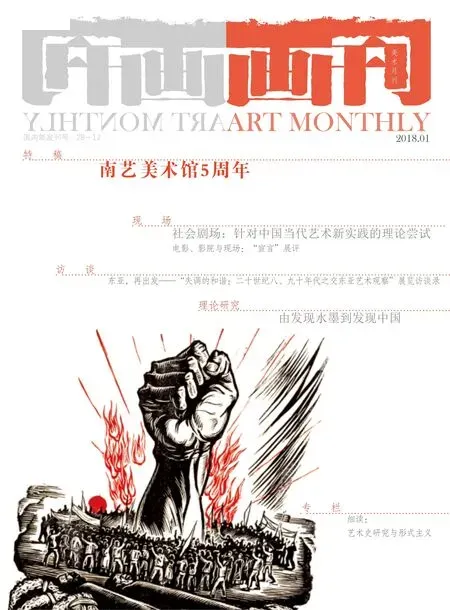由发现水墨到发现中国
2018-11-28冀少峰
冀少峰
谈起水墨,自然和中国联系起来。发现水墨,亦是发现传统,更是发现中国。作为最代表民族根性的传统文化的符号礼仪,再没有比水墨更能沁入中国文化的深处,水墨俨然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观念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方式,水墨艺术的发展被赋予了关乎中国画的未来的使命,特别是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更成为关乎中国文化跻身世界文化之林的一种文化战略。虽然透过水墨艺术的发展看到中国文化心理上的矛盾、无奈、挣扎,甚至是分裂,更感知到由水墨到传统文化由边缘重返主流的急迫,但深层次的是在发现中国,不断寻找“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其实在迈向现代性的多元发展道路上,当代文化的传承不是把水墨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水墨和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对水墨与传统进行创造性诠释,发现传统的普遍性内涵并进行新的诠释改造,进而穿透传统迷雾为现代性设置的种种迷雾,走出一条中国道路,这才是发现水墨、发现传统直至发现中国的价值所在。
探寻水墨艺术不断被发现的历程,不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之变局,中国由传统社会急剧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不仅仅是新旧观念的冲突,亦是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冲突,更是中国在急剧完成现代性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在地”现代化过程。当我们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时,当我们从一个农业国逐渐向新型工业国家转型时,当我们日渐脱离乡土社会而高扬城镇化步伐时,这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都市文化的兴起、观念形态的更新、大众文化的流行、图像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全球化的冲击,都使得水墨艺术和水墨艺术家不能孤立于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思潮的更替之外。而置身其间的文化传统又构成了发现水墨的背景,意即水墨艺术所面临着的传统,一方面它带有强烈的农耕文明特质,这种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发现水墨的强烈羁绊;另一方面,1949年到1976年的“毛式”传统,浓烈的社会主义经验视觉叙事和题材决定论,还有就是第三方面的传统,即1978年以后的邓小平传统,亦即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传统,水墨艺术正是在这些传统的浸淫中一步步挣脱出来,寻求到了一条自我融入当代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系统中。特别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不仅开启了全面的市场化道路,也彻底终结了计划经济模式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窘境。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不仅使水墨获得了发现与解放,它必然开启了水墨获得发现与解放以后水墨艺术的新时代,而对水墨艺术的发现,亦是对传统的发现,更是对发现中国、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想方式的开启。
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一个历史节点的话,不难发现,水墨在这个阶段的探索不仅弥漫着强烈的求新求变特质,从中亦可找寻到水墨艺术走到现代水墨的视觉表达路径。
现代水墨与传统水墨(主流、体制内)的最大区别,或者说这一阶段的水墨方式是通过向西方的学习,特别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艺术为参照,它吸收的是西方抽象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手段和方式,采用拼贴、错置、挪用、变形,以水墨拼贴和平面装置的形式,强化制作感,消除手画的痕迹,除了纸与墨,传统的技术基本上派不上用场,这样传统的笔墨趣味和题材模式就被破坏和消解得无影无踪。传统的笔墨标准也被扩大和改写,现代水墨还注重的是一种风格的建立与范式的确立。这也导致大多数水墨艺术家基本上陷在了现代主义情理中,致力解决的问题也主要是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这种和现实生活始终处于一种隔膜状态的现代水墨虽然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方式,但却始终难以进入当代水墨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的生存境遇的表达的这么一个境界。现代水墨作为现代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得不处于一种悖论的发展逻辑中——夹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中国社会的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珍惜与留恋;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一种面对现代性的焦虑,即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艺术家注重将社会意识、问题意识融入到艺术创作中时,而大多数水墨艺术家却仍然热衷于对传统的语言媒介问题提出问题,较少从当下文化问题中寻找水墨艺术的对位性。于是空洞的、玄而又玄的观念口号和冷漠的图式躯壳,在无法融入当下的文化背景时,只能游离于社会现实与精神生活之外。现代水墨的“大部分实验的重点都放在语言的可能性上,即基本上是遵循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形式主义路线,尽管它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整体上仍然与中国现代(前卫)艺术的发展同步,也就是说,就像中国现代艺术在不长的时间把西方现代艺术演示了一遍一样,水墨画的实验也几乎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同一个模型,但是要慢半拍”(易英《实验水墨的可能性》,《学院的黄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477页)。“慢半拍”一语道破了水墨的实验并未能和开放的社会发展同步,其语言的实验似乎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循环,而用现代的语言形式重新阐释传统,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承接与延续,这必然导致现代水墨既旁落于前卫文化,又旁落于当代文化。水墨媒材与信息时代构不成一种对应关系,因而必然决定了现代水墨的一种尴尬处境。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现代水墨一直遭受着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前卫性的批评家认为他们与西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等过于接近,而抽象主义在西方已是十分成熟的早期的现代主义流派,现代主义在西方其实已经走向了尽头,因而,在艺术史上不具有冲击力和语言的新颖性;另一种批评来自水墨画内部,认为他们舍弃了传统水墨画的笔墨精华,舍弃了形象,只是在玩形式主义的游戏”(殷双喜《城市·水墨·现代性》,《艺术生活》,2009年第1期第21页,福州大学)
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以来,伴随着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大历史、大政治的时代已成了明日黄花。它的彻底终结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种个人与时代命运相连的大时代的苦忿悲情与宏大叙事已成为过去。对于21世纪而言,体制内与体制外已不再有区别,官方与民间也少了些对抗,地上与地下的界限也消弥了,空间秩序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社会制度。当代人们再谈论这个阶段的当代文化发展状貌时,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么一种倾向,即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因为自1990年以来,在中共政治文化里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再中国化”又意欲何为呢?其实,“再中国化”就是要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能量。而作为民族文化符号与礼仪的水墨艺术无疑又是“再中国化”在艺术领域的表征。也可以说,水墨艺术往往被赋予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使命。但究竟哪种水墨具有这种历史担纲呢?在此,笔者认为,发现水墨(当代水墨)则是以当代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水墨有着一种颠覆与超越。它不仅仅是在媒材样式与观念形态上,更深层次讲,它其实是试图重新建构一个新场域,这个场域就是一个关乎“中国画”的评价标准和教育体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水墨(当代水墨)并不是结果,它实际上是在“再中国化”的讨论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水墨艺术又向何处去的问题。它的真正意义则是提出了水墨艺术在未来的可能性。但活跃、冲动与丰富,特别是夹杂其间的混搭、多义与多元,新的中国性无疑又构成了2000年以来水墨艺术获得解放以后的关键词和视觉叙事路径。
发现水墨之后便是发现传统,而解放的水墨超越了把水墨作为中国文化精粹和代表的理想,超越了对水墨的种种约定俗成的规范,破除了笼罩在水墨艺术头上的种种清规戒律,破除了水墨的基本规则,打通了水墨艺术进入当代的途径。于是,这种解放了的水墨形态无疑被放到了一个日益开放与多元而又充满着活力的当代文化背景中。它不仅导致水墨艺术家对水墨艺术的一种再理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的视觉思考与表达融入到当代文化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在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发现水墨到解放的水墨,已悄然地把架上水墨的概念解构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方式,它以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国际性、颠覆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水墨艺术的“慢半拍”的窘境。它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并开始蔓延到各种艺术方式中。于是,传统的某些元素成功地转换为当代情怀的表达。解放的水墨无疑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找到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并愈来愈以一种差异性的民族身份参与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水墨解放带来的突出变化,在“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中,则体现为三个背景和五个方面。
一、三个背景
当代水墨艺术究竟要适应的社会现实呈现出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表征呢?抑或说为什么参加“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艺术家们的水墨叙事能代表时代水墨的发展方向呢?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来看,改革开放的30年,恰恰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激烈变化的30年,使得水墨艺术不可能孤立于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思潮更替之外,参展艺术家们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亦导致他们的水墨表达不能不带有某种经典性、风向性和未来性。
构成参加“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艺术家成长的背景的文化传统有三,第一,他们一方面面临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很显然此种文化带有强烈的农耕文明特质,而传统水墨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农耕文明的表征;另一方面,他们又浸淫在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背景中,此种传统亦称之为“毛模式传统”,“毛模式”造就了这代人的深沉、凝重、理性的思考特征。于视觉表达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宏大叙事的激情,苦难与悲情意识往往成为其视觉叙事的主调。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亦是新时期以来的邓小平模式,即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传统。正是这三方面的传统,构成并完善着参加“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艺术家们的成长路径。由此,我们亦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文革”和“改革开放”则构成他们主要的视觉表达路径,在他们的视觉叙事所呈现出的对历史的反思、文化的批判,特别是充斥其间的社会主义经验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记忆,则唤起了一代人共有的集体记忆。但难能可贵的是,弥漫其间的精神的召唤,文化的重建与利用,都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惑,则昭示出他们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关怀;在他们视觉表征的背后,他们有意识地建构了自我的图像体系;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对传统进行批判和扩充。
二、五个方面
(一)与水墨有关的装置与影像
装置艺术的当代特质也使其成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主要表现,而其特点就是一是要有空间和体积。传统意义上的水墨强调卷轴、把玩、留存久远,但装置艺术则可以在做完之后马上消除,并不追求永恒和不朽。而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消弭,水墨的语言特性在当代社会批判精神中的消失与重构,都引发人们对水墨与装置间的结合所产生的水墨解放形态进行讨论。而网络化的生存现实和科学技术与多媒体手段的介入,虚拟化的精神体验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于是一种无笔无墨的水墨表达,如设计水墨、光影水墨、影像水墨的出现,使水墨表达开始从架上走到架下,从纸介质走向综合媒材,从二维转向了三维,从静态走向了动态。这不仅改变了水墨艺术的展示方式,在阅读方式和审美习惯上也是一个颠覆性的变革。
(二)非水墨艺术家的水墨情怀与表达
发现水墨重要的并不是水墨,不是材料,而是观念的呈现。一些成熟艺术家在新的叙事情境下,在强调自我原创性的基础上,愈来愈注重立足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彰显当代文化特征。由于他们没有水墨的包袱,反而在探索水墨新的可能性上做得更加开放与自由。
(三)水墨新意象
仍有部分艺术家一如既往地坚持架上水墨探索,仍然坚持用架上水墨作为应对艺术与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用于表达的仍然是传统的媒材,但它和传统水墨有着截然的区别,即它是当代的社会生活在当代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关注的是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存境遇:它有着当代艺术一贯的问题意识,彰显着一种追问精神,体现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直入当代艺术的堂奥。
(四)科技与奴役
数字时代的水墨其实隐含着一个深刻话题,就是科技与奴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水墨获得解放后面对科技的发展所必然面对的现实。它带来的水墨解放方式则是科技越发达,对水墨奴役的色彩越强烈。但其深层内涵不言自明,就是在科技背后有奴役、水墨背后有自由,水墨的解放及不断走向广阔的公共空间,其实解放的何止仅仅是水墨,它揭示出的是水墨背后人们精神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更是中国价值、中国经验的体现。
(五)微时代的水墨新方式——微叙事、微体验、微表达
由发现水墨到发现传统,直至水墨的解放在70、80后们身上的表现更为直接。而70后、80后们既能敏于时代变迁,又能从自我的生存体验出发,他们以一种浪漫、幻想,抑或是梦游与妄想,置身于一个虚空的网络化的生存现实,他们营造的是属于自我的话语空间。特别是在微博、微信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艺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图像的逼真动人,手机阅读的快捷便利,当数字开始挤压文字,界面不断欺负纸面,读图日渐代替读字,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个体方式展开对社会的一种微抵抗。他们用自我内在的激情,真实记录着我们生存的社会现实,又通过自我的一种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微叙事来消解宏大叙事,用微体验去消解社会主义经验,用微表达终结了一代人的集体主义经验和集体主义记忆。微时代的水墨,仍然折射出的是艺术内在形态和新一代艺术家心态的深刻转变。这不仅仅是视觉图像的转向,更是微时代的一代青年对激变的社会现实所作出的激情思考和视觉想象。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发生激烈变化的同时,激变的社会必然迫使他们作出自我思考和判断。那么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社会的变化问题呢?因为微时代所带来全球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以及从中出现诸多不曾遇到想到的问题,仅仅依靠现成的知识储备、思想储备难以回答。因此,新一代艺术家敏锐地抓住了微时代的文化脉搏,又非常机敏地针对微时代的文化问题,作出了回答。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微时代的水墨正是水墨获得解放走向未来的憧憬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