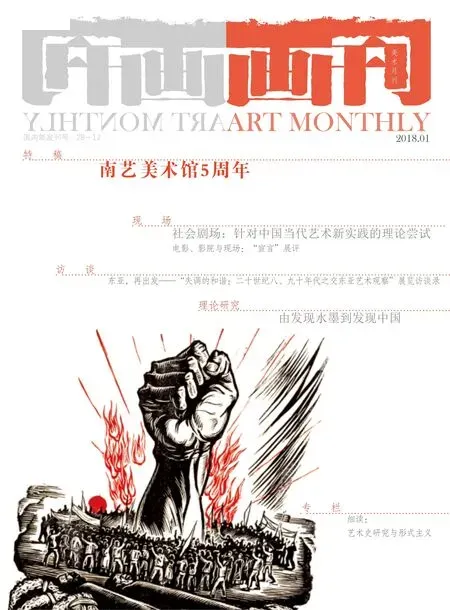打造身体:18世纪俄国肖像画中被造就成“他者”的自我
2018-02-02阿利森
[美]阿利森·利
我们喜欢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敏锐地感受到衣着的重要性——这是有意义的。我们觉得穿衣打扮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受到个人收入的限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居住的地方——但我们也感觉到衣着关乎于主观的、消费主义的选择,一个个人追求的问题,是一个阶级条件可以被掌控、甚至有时被克服的领域。然而,在其他的时代,衣着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也没有很大的调停余地。我们今天把这件事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常常认识不到文化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打造意义的劳动”,即我们建构的主体性——它的渊源和发展,以及它所遭遇的困难。本文的目的是把服装作为打造身体的手段来加以研究——这种打造同时也发生在身体内部。由此我建议对历史上一个怪诞时期的文化产品进行筛查——这个时期现在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潮流转向的时刻——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比得上18世纪的俄国在身份的外在表现上的投入。

左·图1 《埋葬猫的老鼠》俄国卢布克版画 1860年代

右·图2 《玛丽娜·姆尼舍克皇后肖像》 西蒙·博古休维兹(Szymon Boguszowicz) 1606年
几乎恰好在新世纪之交,即1700年1月4日,沙皇彼得一世(Peter the Great,现在为人所知的称谓是“彼得大帝”)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军队人员、政府官员和商人必须舍弃传统的俄国服装,改穿欧洲风格的衣服。几个月后,他定下了实施新着装政策的最后期限,其中也包括对女性的着装要求。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项法令直接要求商人、步兵和火枪手全部穿西方服饰。手艺人被规定只能为男士制作法国或撒克逊大衣和德国马甲,为女人和女孩则只能制作西式裙装、帽子和衬裙。法令中所规定的阶级如被发现穿着俄国传统服饰则会遭到罚款。
再怎么强调这次全方位的巨变对于俄国精英阶层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17世纪的俄国肖像画展示了俄国人已经穿了几个世纪的做工复杂的长袍。事实上,俄国男士和女士的穿着十分相像,只不过女士的头饰近乎完全盖住了她们的头发,保守又松垮的长袍遮住了她们的身体,只有脸和手露在外面。最初的法令颁布后过了几年,到了1705年,彼得甚至进一步下令男性要剪掉胡须。那些不想遵守这项法令的人将不得不每年按照他们的职业地位缴纳一笔税费。
但我们如何从艺术史的角度评价这次变革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理解那个社会中剃掉胡须、改装易服的人们的感受呢?这个国家正急迫地向现代化趋近,渴望在世界舞台上被认真对待。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我关注的是在君主的钦令下改装易服是如何从外向内地重塑了这些俄国人。独裁的易服政策以一种尤为令人恐惧的方式让俄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创造了一种“部分确定的身体”或“隐式身体”——这几乎在一夜之间让俄国公民对自己产生了陌生感。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他者性”?如果有,我们又该用什么来衡量?我想:那个时代的肖像画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基本的事实,而这是同一时期的任何其他文化产品都不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这些事实称之为调停或升华,或者更为乐观地说,将其称之为转化。
在这里,俄国的形式主义者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对我们有所助益——在讨论服装变革这个问题时,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所需要的是吸取欧洲日常生活的形式,同时对这些形式保持一种外在的、与之格格不入的俄国人的态度。俄国人不应该变成外国人;他仅仅是应该表现得像一个‘外国人’……”因此,对于洛特曼而言,这是一个相异性程度的问题。俄国人所需做的就是在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进行调整。我在本文开头所引的那句“陈词滥调”或许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最直白的表现——在这些俄国人的例子中,衣服确实造就了他们。俄国人所穿的新式欧洲服饰对其穿戴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详尽地确定他们在社会等级制中的位置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还显示了一种新奇的深度。现在俄国人不仅继承了其与生俱来的文化,还是一种贵族的杂合物——通过着装融合了西方欧洲文化的特征,也由此通过他人的认同来彰显他们自己。这种“杂合性”使得俄国的上层阶级不仅自己对自己感到陌生,还成了他们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俄国民间版画“卢布克”(Lubki,亦称lubok,是流行于俄罗斯的一种版画,主要描绘在文学、宗教和民俗中流传的故事,是一种较常见的装饰品。——编者注)(图1)证实了这种内在的陌生感——洛特曼称其为“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这项法令使得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得具体可感,将农民与绅士截然分开,使得阶级结构有了一个统一的符号体系。
正如学者安·琼斯(Ann Jones)和彼得·史达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在他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所做的精彩研究中指出的,将着装视为身份的物质标识的危险在于服装与身份是可以分开的。在那个年代的肖像画中,画家以奇怪的方式凸显了塑造和消解一个人的形象这样的日常行为。
在17世纪中叶的肖像画中(图2),肖像画家常用的一个技法——让模特做手势表示要裸露衣服包裹下的躯体。但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个真的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她们的姿势凸显了其时西方服饰的表演性特征。她们的手和微微裸露的感觉是一种深层符号学的核心所在——代表了失调、偏差以及不一致。这种手势与遮掩的手势非常不同——后者在彼得的法令颁布之前的一些女性肖像画中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那些年的肖像画中描绘的很多男性和女性还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缺乏完成性的、或实在的肉体存在感。让我们看一看这幅瑞孚纳·普拉斯柯福亚·伊万诺娃(Tsarevna Praskovya Ivanova)的肖像(图3)。在应该有一处凸出锁骨的地方没有锁骨,她瘦削的形体因此偏离正道,变形了。她的脸以45°侧向一边,身体微微向右倾斜。摆出这样的姿势后,她脖子上本应至少垂直划过一抹阴影,来表现皮肤下紧致的筋腱。然而画面上只有她空无一物的白色胸部;貂皮衬里的斗篷滞重地垂下来,将她围住。看上去她好像并没有真的穿着这件衣服,而更像是这件衣服被放在她身上,附着到她不能被称之为身体的身体上——与其说是穿在身上的衣服,不如说更像是风景。
这种肉体存在的缺失也以其他方式被模仿。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衣服的装饰性元素,我们是不是甚至连人物躯体从哪开始、在哪结束都分不清楚?这里的明暗对比常常如此强烈,以至于造成了身体消失这样的极端后果(我所说的身体消失并非指胳膊和腿,而只是指人体躯干的轮廓——这在画面上被微妙地抹除了)。画中的人物在没有主体的环境中被赋形;最终是衣服使他们成了被观看的对象。这个时期的画作展示了我所称之为“斯拉夫的西方主义”(Slavic Occidentalism)的内容——即吸取感觉格格不入的西方主题和风格,这标志了俄国的他异性,改变了意在建构一种具象化的整体的艺术反应,而与此同时,艺术家和国民都在力求掌握和拥有一种并非属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这些人被彼得大帝的世界所笼罩,他们是没有实体的主体,屈从于西方现代化的物质性——只有依靠把自身变成物质对象的能力才能获得身份和地位。

图3 《瑞孚纳·普拉斯柯福亚·伊万诺娃肖像》

图4 《叶卡捷琳娜二世》 安特鲁波夫 1766年
进一步来说,请注意画中人物是怎样经常被一层一层的衣服包裹起来的,尤其是皮草。你可以认为这证明了俄国冬天的寒冷,或者说这只是财富的展示,但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皮毛不正是另一种皮肤吗?皮草对于这些模特来说似乎起到了双重作用——既是一层保护,又是通向内在的“斯拉夫”(Slavic)本土传统的障碍。但是这些衣服也是纯粹的西方式幻想。无可否认的是:画中对它们的描绘着意于官能感受——所有那些奢华的天鹅绒、精致的蕾丝和锦缎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而皮肤在这里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一片模糊,它在触感上的特征被抑制,以营造一种非物质化的肉体性——这种肉体性否认在皮肤下的血管中有流动的血液。在“斯拉夫”和“西方化”之间存在着互换,存在着竞争。在这场战役中,肉体成了一种拜物教似的崇拜对象,这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通过使皮肤看起来像是“人工做成的”,这些肖像画强化了身份与生俱来的“塑造”和“消解”过程,而这正是“斯拉夫的西方主义”的体验。
事实上,那个时期的男女都煞费苦心地把皮肤弄得看上去像是“假的”。甚至在16和17世纪,俄国女性就在脸上抹厚厚的粉,擦上鲜艳的胭脂。但这种一以贯之的做法与西方服装、假发和珠宝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令人吃惊的效果。女性(有时也有男性)把铅白和蛋白混合而成的膏状物涂抹在皮肤上——18世纪理想的肤色是要接近瓷器的那种白色。为了不损坏化妆品涂层,人们不经常洗脸,所以他们的脸跟面具一样。当时的外国来访者,例如1783年住在俄国的英国官员彼得·亨利·布鲁斯(Peter Henry Bruce)注意到了这种做法。他写道:“俄国的女性……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作是长得很好看……如果不是因为那种涂脸的荒唐习俗的话,她们把太多的东西涂在了脸上,可以说她们在脸上遮了一层覆盖物来藏起了她们的美丽。”
像这样的同时代人的讲述说明了“斯拉夫的西方主义”的杂合性——实行西方的做法(化妆),但又结合着俄国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把西方标记为“他者”。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洛特曼对那个时代的分析——即俄国人吸收了欧洲的形式,但同时对这些形式仍然保持疏远的态度。那个时代的肖像画证实了这种二重性:它们展现了俄国人在假面式化妆上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那些曾经是自然状态的东西进行的“仪式化和符号化”。在这种双重化的过程中,在这个从日常事物中建构出符号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现代性的快速发展。在帆布上用颜料画出的人物本身也是化过妆的——这种结合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史学家通常所认为的现代主义的根基。而这通常不被看作是艺术创作的一个方面——直到19世纪60年代马奈(Manet)和印象派画家开始消解幻觉主义和实际创作方法之间的界限。
但我们已经在像安特鲁波夫(Antropov)和尼基丁(Nikitin)这样的俄国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现代性的开展——他们笔下抹着胭脂、擦着粉的俄国美人已经开始消解人物和背景之间的联系了(图4)。这些俄国肖像画中的某些地方已经直接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消融”(dissolution)和“偶然”(contingency)的观点。从这些作品的非空间性,以及皮肤化解到织物中的特点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立体主义创作中对身体进行分解的先兆,还有就是凸显现象感知的碎片化本质的做法(既包括对这种本质的描绘,也包括对这种本质的直接体验)。我们看到外在的身体化解成了各种表面,一系列的自我除了创造出表象之外别无作为。这些肖像画在某些方面如此真实,从而消解了画中的自然主义——这与隐藏在它们创作过程背后的经验的本质相关。这些肖像画具有深刻的预言性,而它们所预测的未来令人恐惧。这些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是被建构起来的;它们说出了荒谬模仿的,那个时代的真相。
因此,这些肖像画在那些年份出现并非巧合——那些年正是卓尔·瓦曼(Dror Wharman)所定义的现代自我诞生的年份。在他看来,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见证了对于个体身份的新看法的成熟,这种看法用新发现的个体性和独特的表达能力来定义自我。瓦曼认为:这个根本性的改变为“自我的现代化”(the modern regime of selfhood)打下了基础;我们在肖像画中看到的正是这个改变所带来的动荡。对于18世纪的俄国来说,效果的微妙不是艺术的目标。极度的矫揉造作标志着俄国登上了西欧的权力舞台,也标志着创意交流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他者性”的东西。在这个体系中,身体具有了寓意——这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真实的人变成了可以被同位置换的珠宝——确实,人们对于用来当珠宝戴在身上的微型肖像的狂热追求凸显了真实的人在那个时代是怎样变成了符号。这些男人和女人变成了是可以互换的,被客体化和物质化了——像旧胸针或手镯一样被戴在身上。经历了这些变革的俄国公民变成了物质对象,为了国家利益而被操控,被用来展示炫耀。他们是彼得大帝手中的证据,用来证明俄国准备好了接受西方世界的认真对待。俄国人将不再被视为“野蛮人”。
彼得大帝像皮格马利翁(Pygmalion)那样雕刻了新的俄国的“伽拉忒亚女神像”(Galateanwoman)用以展示给欧洲。或许这样一个形象在这里最适合。彼得大帝乐于被描绘成这样一个形象。1723年,拉斯特雷利(Rastrelli)接受委托制作了一座彼得大帝的半身像,其右侧有一个细节表现彼得大帝化身为皮格马利翁在塑造这个新的女神(图5)。欧洲作品经常强调伽拉忒亚女神的女性特征,但在这件作品中,她不是裸体的,出现时已经身着铠甲。她的形象只完成了一半,仍与她存身其间的岩石连在一起,却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
因此,对于在彼得大帝的法令下改穿西方服装的俄国人而言,穿西式衣服就意味着被沙皇塑造,就如同伽拉忒亚被皮格马利翁塑造一样。这意味着接纳对“自我”的新的构想,但同时也意味着意识到一种“杂合性”——这种“杂合性”从那时起就一直折磨着俄国。彼得大帝的服装改革是历史的一个单一瞬间,但以后还会反复上演。布尔什维克(Bolshevik)革命后的几年间,像乌拉迪莫·塔特林(Vladimir Tatlin)这样的艺术家们受命为理想的苏联公民设计新的“制服”。而像留玻芙·波波瓦(Liubov Popova)这样的其他俄国先锋派成员则被要求将他们的创作能量从抽象绘画转到织物设计上来——织物设计将使新的苏联公民能够把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穿”在身上。

图5:《彼得大帝半身像》 拉斯特雷利 1723-1730年
但1700年是那个启发后来的时刻。彼得大帝的着装改革是让身体成为一种工具的首次实验——这个工具由国家掌控,以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而肖像画中展示的被描画的身体恰恰证明了这种接触与交流的成功。在这些肖像画中,“他者性”和“外来性”成了构成“自我”和“本土性”的组成部分,由此消解了文化二元对立的极端性,创造出了新的文化认同,即“斯拉夫的西方主义”。18世纪的肖像画家捕捉到了这种二元性——即当时“自我”被塑造成了“他者”。从身体为了戏剧化地呈现模特而摆姿势的方式,到衣服过于装饰性的特征;从皮肤被去除肉体特征以及被同化成织物到面具似的化妆效果——肖像画家展示了身体如何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极具挑战性的层面上被利用:从外向内发生作用。这个现代俄国的意象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被推销,俄国精英阶级的身体以及记录这场变革的肖像画家都在从事这种推销。在这种文化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艺术家被雇用——一个模仿与消费的新社会在此诞生了。
(译/高尊 校/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