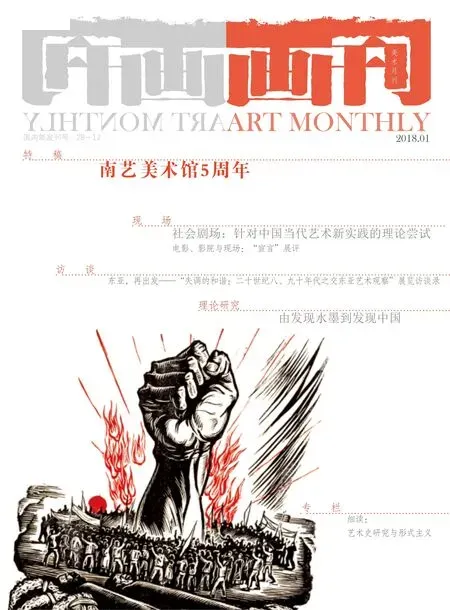为一种水墨的辩护
2018-11-28王春辰
王春辰
我们必须以一种态度来对待水墨,必须以一种在今天需要反省的态度来认识水墨,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对待水墨的态度上改变自身的偏见和傲慢。
首先是让真实的水墨回到人间,不再加给水墨一种不可能的、想象的文化复兴梦幻。无论我们有怎样辉煌的水墨绘画历史,但都不应因此产生出水墨是中国艺术的代表的错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让水墨回归水墨、回到人间,是指我们能够真正地认识到水墨是艺术的一种方法,围绕它所生发的哲学理念和美学,都是为了让水墨丰富起来,而不是因此说水墨天下无敌,具有唯水墨而独尊的傲慢。
事实上,从事水墨研究与创作,如果摒弃了傲慢的态度,就不会纠结在水墨可以或不可以开放、水墨是不是故步自封这样的狭隘中,同时在今天的语境中,也不会将水墨摒弃在当代艺术创造的进程中。
水墨创造的路径,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同期其他艺术类型的比较以及水墨自身的演化,我们该回到一种平和而严肃的态度上了。
经过20世纪以来的艺术风云变幻,经过历次关于水墨的争鸣和讨论,越来越清晰的是水墨有自身的独立语言系统,有自身的独立美学原则。我们常常是拿另外的艺术参照来分析、对比水墨艺术,进而得出水墨发展的不足和困局。没错,水墨画的不好确实造成了水墨的萎缩和困顿,这是由因循守旧、技艺不精所致,而非是水墨的缺憾;这也是对于水墨绘画的理解力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所致,而不是水墨内在的美学原则失效了。
在文化的逻辑上,水墨自然会发展、会变化和改变,同时它需要受到外部的刺激来激活自身的语言创造力。由于它的历史悠久、各种语言笔法成熟,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它创造力的怀疑,常常以没有创造力的水墨绘画来指代全部的水墨绘画,以部分趣味恶俗、笔墨低劣的作品来指向水墨的应有高度和水准。
对于水墨及其形成的绘画艺术,不仅仅是画家手上功夫要提高,就是眼力也要绝对的高级。看画就怕眼力一般,甚或很低,那肯定无法区别出什么样的水墨绘画好,什么样的不好,最怕仅仅靠门派、地位、名气在那里绕语言游戏。后者事实上造成了对水墨绘画艺术判断的失误和见识浅薄。对水墨绘画艺术的研究和理解应该分出不同的类别。纯粹进行文字研究的,那么就让它对水墨文本的历史进行梳理、解释,还原的是它的文字故事,但在这里它无法关涉水墨绘画艺术之妙,甚至这样的文章洋洋洒洒,引经据典,纵横宏论,但难以点评绘画的水准和差异。这样的历史研究,以文字取胜,它可以将水墨绘画的历史讲得头头是道,但对于水墨的高下、功夫深浅、语言的驾驭却隔靴搔痒,全不在实处。
如果我们看一下20世纪的水墨绘画一直看到今天,就会发现多少的文论、文字都是匍匐在画家的名头之下,并未有论者的眼力真见,受时俗、人云亦云所限,要么大唱赞歌,要么唱衰水墨。
能论中国画(水墨)者,绝对是用情怀的人,近世对中国画大作评价的人无不是看到了世界的图景,感叹中国画的不作为,视为衰弊,如康有为奋笔疾书道:“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败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争哉?……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1]这是他出游欧洲,看到了众多西方绘画后的感慨之言,颇多警世语,即便今天读来,又何尝没有说到位。但康有为仍然期盼国朝有奋力追求绘画新貌之人。
晚清对“四王”的贬斥不断由革命家提出,陈独秀更是痛斥道:“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2]在这里,西方写实是参照系,是引起国内革命者愤慨的比照。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持相同看法:“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3]他们皆是以写实具象这一技术来比较中国画并认为这是中国画的弊端。
如果说,20世纪头10年的康有为、陈独秀对中国画的批评还是来自革命家的政治立场,那么到了20年代,一批艺术家发出了改良的声音,比一味否定就来得艺术化。如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郑锦就说:“画法亦应打破历代帝王御用物之谬见,而不复为旧法所束缚。自由发达,共策进行,取各国之所长,补向来之所短。其道固自有在也。”留学法国的徐悲鸿尽管说了他的恩师康有为一样的话“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但他的艺术观又让他讲道:“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4]这些都是以艺术之道来改良中国画。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艺术家看到的中国画弊病比政治家要明确,提出的是改良方法,而不是决然否决。岭南派画家高奇峰也持综合改良之论:“乃将中国古代画的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比兴、抒情、哲理、诗意那几种艺术上最高的机件,通通保留着;至于世界画学诸理法,亦虚心去接受。”[5]出现这样的改良论,与最初面对西洋高超的写实绘画的那种惊慌失措的反应不同了,艺术家有了距离感,有了足够时间去思考,所以心态平和起来。对于传统和古代,黄宾虹指出:“画不师古,未有能成家者。……盖艺术之事,所贵于古人者,非谓拘守旧法,固执不变者也。”[6]这些20世纪上半叶的前贤之论多是痛感不思进取的水墨状态,而画家以自己的魄力去践行新的水墨创作时,他们付出了几倍的汗水,甚至不被理解,如黄宾虹者。
水墨是物,而人是活的,对于水墨的各种态度都是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的态度并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水墨是死的,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但水墨在近代以来确实有僵化、达不到应有的水准的普遍现象,甚至今天也并不例外。这百年来的各种水墨观点和态度主要是以不同的他者视角来测评水墨,形成相互矛盾的认识和态度。阵营不同,所持论据就不同;水墨的评判权力变成了各种非艺术的权力与体制的较量。一方面,我们期待好的水墨创作的出现;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对水墨充满了偏见;又一方面,那些烂的水墨、差的水墨到处横行,无忌地肆虐,特别是多少不怎么样的水墨不过是脱了一层身份的皮在呼风唤雨。这些都是与水墨生命的本质无关,人们不识水墨久矣。
相反,我们应该从水墨的脉系及其精神维度上挖掘其内在的生命力。如果水墨还留有生命之气,全在于这种满含精神内蕴的东西的存在,如果失去了水墨的精神内蕴,任是什么虚晃一枪的招数都无效。水墨绘画的外延及转换为其他媒介形式,是另外的艺术,不是水墨;水墨以假象的外表借用今天的一些艺术招数,也仅仅增加了一些异化感,也并非真实的水墨的内蕴。具有内蕴的水墨就如同功夫一样,具有个体的生命体验在里面,是潜心修为的结果,它是非机械的、非器具的,而是心手合一的迹化。
水墨有品格,但识之者不多。多少流行的水墨格调不高、境界低劣,俗气俗眼的东西泛滥。今天的水墨病态不亚于上文那些前贤批判的东西,所以我们提出让水墨回到水墨,就是要让真实的人回来,让真实的心性回来,让非水墨的身份论消失。前贤批判的是水墨的语言问题,上世纪80年代李小山批判的是水墨的庸俗社会学问题,那么今天要警惕和扬弃的是水墨的自狂和偏见。今天,远离社会偏见,才有真实的水墨存在;远离社会权力网络,才可能存在真实的水墨。看不懂人性,实际上就看不到真实的水墨。所谓“墨点无多泪点多”,早已超越了水墨本身。
水墨在今天,只有回到躬身自省,才是水墨的可行之道。真的中国水墨艺术,将是在回溯来由脉系的路上获得新生。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水墨何尝不是。
2017年12月29日于央美灯下
注释:
[1] 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作于1917年,原刊于中州书画社出版的《康有为墨迹选》(二),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1、24、25页。
[2] 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原刊于1918年1月的《新青年》6卷一号,见《二十世纪中国画讨论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3]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原刊于1919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月刊》及《绘学杂志》,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4]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原刊于《绘学杂志》1920年第一期,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5] 高奇峰,《画学不是一件死物》,本文原载于《高奇峰先生荣哀录》(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20世纪20年代中),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6] 黄宾虹,《谈因与创》, 1929年,本文原载于《艺观》1929年第3期,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