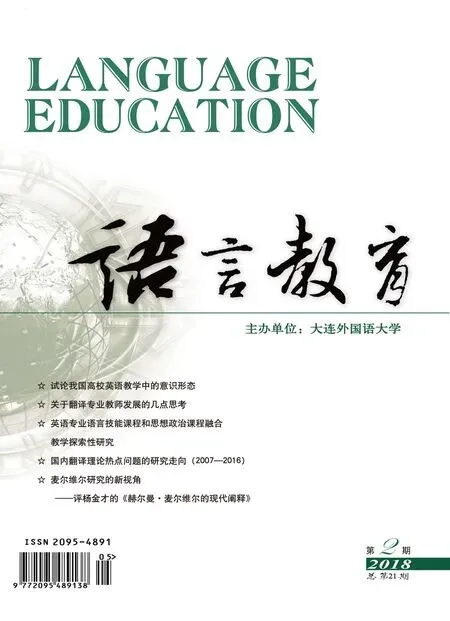论汉语的“事件句”
2018-11-28袁庆德
袁庆德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事件句是汉语陈述句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的完整形式是“时间词语-处所词语-不及物动词+了-名词语”,语法结构是“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谓语—主语”,这种句式专门用来陈述某时某地所发生的事件,所以我们称之为“事件句”。以往汉语语法学界对事件句的认识有所不足,在汉语语法专著和汉语教材的句式系统中甚至还没有“事件句”这一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汉语事件句的教学效率。
1. 以往学术界的观点
由于事件句所陈述的大都是人或事物出现或消失的事件,因此以往学术界把它称为“隐现句”,或者把它与存在句统称为“存现句”,因而以往学术界对事件句的看法,实际就是对隐现句或存现句的看法。
1.1 关于事件句的结构
关于事件句的结构,以往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1.1.1 “主—动—宾”结构
这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汉语“主—动—宾”(SVO)的一般语序确定主语和宾语,存现句属于“主—动—宾”结构的句子。如丁声树等在《语法讲话》(《中国语文》1952年7月至1953年11月连载)中指出:“表示事物存在、出现、消失的句子常常拿地位词做主语”,主张把存现句中谓语动词前的处所词语看作主语,把谓语动词后的名词性词语看作宾语。在之后发生的关于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中,邢公碗(1955)、洪心衡(1956)、徐仲华(1956)等都赞同这种观点。如邢公婉(1955)认为,在“村子里死了人”这个句子中,“村子里”是主语,“死了”是动谓词,“人”是宾语。那些把存现句看成“主—动—宾”结构的学者被称为“形式派”。
1.1.2 “附-述(谓)-主”结构
这种观点认为,存现句句首的时间词语或处所词语属于述语(或谓语)的附加语(也就是状语),而谓语中心采取的是主语与述语(或谓语)倒置语序,整个句子的结构是“附-述(谓)-主”。早期的汉语语法学家大都持这种观点,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 50-51)、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 40)等。在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汉语主语宾语问题大讨论中,王力(1956认为在“台上坐着主席团”、“隔壁店里走了一帮客”这样的句子中,“主席团”、“一帮客”是句子的主语,并且明确地指出:“必须否定‘台上’和‘店里’的主语资格,因为‘坐’和‘走’的行为并不是属于‘台上’和‘店里’的……‘主席团’和‘一帮客’在这里是主语,因为‘坐’和‘走’的行为是属于它们的。”曹伯韩(1956)认为存现句的结构是“附—谓—主”,他指出:“只管结构不管意义是不行的,因为一切语法形式的作用就在于表达意义……‘台上坐着主席团’这样的句子,‘主席团’是‘存现主语’,因为存在或出现的主体正是‘主席团’。”祝孔嘉(1955)也明确地指出:“表示出现、存在和消失的句子,主语往往在谓语的后面,这类句子是:某时(或某处)出现了(或存在着、消失了)什么。这类句子也叫它‘主语后出现’。”那些把存现句看成主谓倒置结构的学者被称为“意义派”。
在那场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中,“形式派”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几乎成为定论,之后只有少数学者还坚持“意义派”的观点,如廖雅章(2001)认为,以往学术界把“村子里死了一个人”、“丛林里跳出了一只老虎”等存现句分析成“SVO”结构的句子,这是“非科学”的,因为“‘死了一个人’有主谓关系,由‘静态(动)’赋予‘一个人’抽象主格。倒装是存现句的句型(固定的),也是汉语的特征之一。理由是‘村子里’为已知信息,‘死了一个人’为未知信息,因此发生倒装。”并且其明确地指出:按照汉语抽象格赋予者规则,上述两个句子中的“一个人”和“一只老虎”是句子的主语。
1.1.3 无主句
这种观点认为,存现句是“根本上没有或不需要主语的”句子。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1986)中以“客厅里来了一个生人”为例,说:“‘客厅’并不是‘来’的主语,只是在客厅这个地方来了一个生人罢了。这个句子也并不是‘一个人到客厅里来了’的倒装句,因为这两个句子的意义并不相同。”孙毓平(1958)也认为这种句子是无主句。
1.2 关于事件句的句式意义
目前学术界在对事件句的句式意义的认识上,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1.2.1 “存现”或“隐现”说
这种观点认为事件句的句式意义是人或事物的出现或消失。这是自20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学界的主流学说,常见的汉语语法专著和语法教材都持这种观点。
1.2.2 “发生”说
这是一种新观点,认为隐现句的句式意义是“发生”。李杰(2009)说:“前人对于隐现句的句式意义的概括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有些具体的隐现句可以表示‘出现或消失’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表示‘消失’的句子是非常少的,大约只占隐现句的5%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句子所表示的意义很难用‘隐现’来概括……据我们考察,当发话人使用诸如‘地上碎了一个碗’、‘路边翻了一辆车’这类句子时,上下文语境表明他的表达意图不是要表示某处出现或消失了某人或某物,而是表示某处发生了某事。”李杰(2009)认为隐现句的句式意义是“某处发生了某事”,这是本文所赞同的,但李杰过于注重句式间的共同性,强调句式的“连续统”,把传统所说的隐现句与“领主属宾句”看成了相同的句式,并把它们的句式意义笼统地概括为“发生”。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领主属宾句”与隐现句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并不相同。隐现句表示某时、某处发生了某事,所陈述的是一个事件,如“村里死了一个人”,表示“村里发生了一个人死了的事件”,而“领主属宾句”并不是用来陈述事件的,而是用来表示人或事物发生了某种变化,它是通过隶属者的变化来表示领有者的变化,如“王冕死了父亲”,表示由于父亲去世,王冕成了失去父亲的人(孤儿);“王冕瘸了腿”,表示由于腿瘸了,王冕成了残疾人;“王冕红了脸”,用脸色变红来表示王冕的心理变化(害羞/愤怒)。可见,隐现句属于事件句,而“领主属宾句”属于“变化句”,二者并不属于同一种句式(关于“变化句”,笔者将通过专文来讨论)。
1.2.3 “变化”说
周燕(2011)在李杰(2009)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隐现句的句式义是“变化”。她说:“我们把隐现句式的句式义概括为‘变化’……隐现句式本身表达的是一个变化事件……出现、消失类动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变化动词,由它们所代表的事件均同变化有关。”同李杰一样,周燕也意识到了隐现句是用来陈述事件的,却根据隐现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特征,把它的句式意义概括为“变化”,这同样是不准确的。
在上述关于事件句(隐现句)的句式意义的三种观点中,本文的观点与李杰(2009)的观点有相同之处,认为事件句的句式意义是“某时某处发生了某个事件”(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1.3 事件句的生成方式
由于事件句看起来像是“主-动-宾”结构的陈述句,但从句法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上看,却是“状-动-主 ”结构的陈述句,显然它不是一种原生的汉语句式,而是由其他句式转换而成的。关于事件句由何种句式转换而来以及具体的转换方式,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3.1 主语中心后移
沈阳(1996)认为,隐现句是通过“主语中心后移”的方式生成的。如“仓库里烂了不少苹果”,它的深层结构是“仓库里(的)不少苹果烂了”,是通过将作主语的定中短语的中心语“不少苹果”向后移位转换成的。但事实上,汉语定中短语的中心语本来就在定语的后面,如果要发生移位现象,也只是将中心语移到定语前。例如:
(1)自1988年建校以来已办班227期,培训学员3万余名。(《人民日报》,2003年)
这里“办班227期”是由定中短语“办227期班”转换成的,“培训学员3万余名”是由定中短语“培训3万余名学员”转换成的,都是将定中短语的中心语移到定语前。同样,如果将“仓库里的不少苹果烂了”的主语中心“不少苹果”移位的话,也只能前移,结果就是:“不少苹果,仓库里的,烂了。”由此可见,事件句不是通过主语中心后移的方式生成的。
1.3.2 谓语动词前移与“轻动词”合并
朱行帆(2005)、李杰(2009)等认为事件句的底层结构(深层结构)是“主语(时间、处所)—主语(人或事物)—不及物动词”,主语(时间、处所)的后面隐含着一个轻动词“OCCUR(发生)”,不及物动词前移,与轻动词“OCCUR(发生)”合并,便生成了“主语—不及物动词—宾语”这种“表层结构”。下面是朱行帆(2005)所举的例子:
(2) a. 工厂OCCUR一堵墙倒了。——工厂倒了一堵墙。
b. 昨天OCCUR一堵墙倒了。——昨天倒了一堵墙。
这种“轻动词”假说很难能成立,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工厂OCCUR(发生)一堵墙倒了”之类的“深层结构”,所以“工厂倒了一堵墙”之类的事件句也不可能是由“工厂OCCUR(发生)一堵墙倒了”之类的说法转化成的。
1.3.3 主语与述语(谓语)倒置
综上所述,早期的几位汉语语法学家认为存现句的谓语中心采取的是主语与述语(谓语)倒置的语序,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存现句是通过将句子的主语与述语(谓语)倒置而成的。关于这一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 50-51)说得最明确。黎锦熙把存现句句首的时间词语或处所词语称为“不用介词的副位名词”,认为它是“副夺主位”,指出:“这种在句首的副位,尤其是表地位的,在汉语的习惯上往往要变更主语的位置,让它倒装于述语之后。”其认为“茶棚里坐着许多的工人”是由“许多的工人在茶棚里坐着”转换成的,“前面来了一个和尚”是由“一个和尚到前面来了”转换成的。
2. 事件句的语法结构
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主语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中,“意义派”根据句法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关系认为存现句的结构是“附—述(谓)—主”,而“形式派”则认为存现句的结构是“主—动—宾”。“形式派”的观点后来之所以能占上风,主要是因为“意义派”在根据施受关系分析存在句的主语和宾语时,得出了矛盾性的结论,如把“台上坐着主席团”中的“主席团”分析为主语,却把“墙上挂着一幅画儿”中的“一幅画儿”分析为宾语,而这两个句子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人的语感上都完全相同,于是“形式派”认为,既然“一幅画”是宾语,那么“主席团”也可以看成宾语,这样分析可以避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又符合汉语句子的“主—动—宾”的常规语序。但实际上,当时的学者们在分析“墙上挂着一幅画儿”这种谓语动词为及物动词的存在句时,对及物动词意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其实,存在句中的及物性的谓语动词并不能表示对存在主体进行处置的动作行为,而是在持续体助词“着”的配合下,表示存在主体的存在状态,“墙上挂着一幅画儿”中的“挂着”表示的就是“一幅画儿”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被挂着的状态,而不是表示有人正在挂一幅画儿,所以“挂着”和“一幅画儿”之间并非是动宾关系,而是主谓关系。可见,当初的“意义派”根据句法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确定存在句的主语和宾语,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至于隐现句,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借用英文字母把它表示为“TLVi了N”,其中T代表时间词语(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和能够表示时间的短语等),L代表处所词语(包括处所名词、方位名词和能够表示处所方位的短语等),Vi代表不及物动词,N代表名词性词语。隐现句的谓语动词Vi 都是不及物动词,而不及物动词本来就是不带宾语的,所以它与后面的N也不可能是动宾关系,同时它表示的是N的出现、消失或变化,而不是T和L的出现、消失或变化,所以它与N能构成主谓关系,与T和L不能构成主谓关系。而且实际上,T和L并不总是名词性词语,有时T是时间副词,有时是介词短语,而L有时也是介词短语,而这些都不能作主语,显然T和L只是用来表示后面的部分(Vi了N)所陈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处所的,属于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这样,一个完整的事件句的语法结构就是:“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谓语—主语”。例如:
(3)那一年(T)我的屋前(L)死(Vi)了一棵丁香树(N)。(《作家文摘》,1993年)
(4)这时(T),迎面(L)来(Vi)了一个人(N)。(温瑞安《惊艳一枪》)
(5)当晚8点20分左右(T),在首都德黑兰(L)又发生(Vi)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N)。(《文汇报》,2005.6.14)
由于表达的需要,事件句的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有时前后易位,而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或处所在上文中已经说明,或者是不言而喻的,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经常省略,形成“TVi了N”、“LVi了N”、“Vi了N”的形式。例如:
(6) 正在这时候(T)来(Vi)了一个人(N),他双手把我的腰抱住!(《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这里省略了处所状语“后面”。
(7) 突然,对面(L)来(Vi)了一辆两人骑乘的脚踏车(N)。(木原浩胜、中山市朗《怪谈新耳袋》)
这里省略了时间状语“这时”(“突然”本是“来”的状语,为了强调它,把它提到了句首,占据了时间状语的位置)。
(8) 十九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Vi)了许多人(N),毁(Vi)了许多家(N)。(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这里省略了时间状语“在这十九年里”和处所状语“我的故居”(这里“毁”是“被毁坏”的意思,表示的是状态的变化)。
3. 事件句的语法意义
以往学术界把事件句看成表示人或事物出现或消失的句子,实际上就是认为它的句式意义是人或事物的出现或消失。实际上,如果仅仅要表示人或事物出现或消失的意义,是不需要采取主谓倒置语序的,如“许多人死了,许多家毁了”,就足以表示许多人和许多家都已经消失的意义,而巴金《爱尔克的灯光》一文说“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例8),显然是为了说明在过去的十九年里故居所发生的变故,是把许多人死去和许多家庭毁坏当作故居所发生的事件来陈述的。事件句是专门用来表示由人或事物的出现、消失、变化所构成的事件。从多个语料库中我们搜索到了许多在前后语篇中带有“事件标记”的事件句,充分证明了事件句的句式意义是“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个事件”。例如:
(9)村里死了一个人,这应该说是大事了。(李佩甫《羊的门》)
(10) 偶尔看了一部电视小品:《局长的小鸡死了》。说的是某局长家死了一只小鸡,本来区区小事不值一提,然而一些献媚讨好者却群起而围之,演出了这样的一幕:上门慰问的、电话“告急的”、送鸡赠物的,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人民日报》,1996年4月份)
(11) 此外,施工期间死了三名员工,造成巨额的赔偿,这些意外事件,导致公司业绩下降,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走上破产之途!(《哈佛管理培训系列全集·第13单元 哈佛经理弊病诊治》)
(12) 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欧阳山《苦斗》)
(13) 说到停止娱乐,不由得联想起丧事来。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国死了人,一国哭。(俞平伯《国难与娱乐》)
(14)“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工人问。“没事!碎了几个瓶子……”(乔雪竹《城与夜》)
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6例中的“村里死了一个人”、“某局长家死了一只小鸡”、“施工期间死了三名员工”、“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一家死了人”、“一国死了人”、“碎了几个瓶子”等句子所陈述的都是事件。
通过事件句与普通陈述句在表意上的分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件句的句式意义是“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个事件”。例如:
(15) a.记得吗?那一年我的屋前死了一棵丁香树……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死了丁香这件事,只记得姥姥那阵子常偷偷磕头祷告,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文摘》,1993)
b. 胜利油田机关报上曾有人写了一篇《树祭》为其作传,第一句话是:孤岛一棵树死了。(《人民日报》,1994年第3季度)
例(15)a中是把“那一年我的屋前死了一棵丁香”当作一件事来陈述的,所以采取了主谓倒置语序,而例(15)b中《树祭》的作者是为了“祭祀”孤岛上一棵死去的树,而不是要叙述孤岛上一棵树死去的事件,所以开头便说“孤岛一棵树死了”,而没有使用主谓倒置的事件句,说成“孤岛死了一棵树”。
通过实际用例和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件句是一种专门用来陈述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句子,它的句式意义是“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个事件”,而隐现句的名称并不能表明这种句式的实质。
4. 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总的说来,事件句的语用功能就是陈述事件。事件句实际上有两种,格式都是“TLVi了N”,但其中有一种事件句的谓语动词是典型的事件动词“发生”(有时是“爆发”等),后置主语N又是名词“事件”、“事变”、“运动”等“事件标记”,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它的格式就是“TL发生了……事件 / 事变 / 运动”。例如:
(16)今年5月2日,位于深圳市深南东路的三九太空月光城发生了一起歹徒持枪伤人事件。(《人民日报》,2002)
(17)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作家文摘》,1997A)
(18)1891年初,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宋氏家族全传》)
“TL发生了……事件 / 事变 / 运动”式事件句是一种显性事件句,而普通“TLVi 了N”式事件句是一种隐性事件句。这两种事件句的语用功能是有差异的。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两种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4.1 隐性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隐性事件句主要用来陈述由人或事物的出现、消失和变化等构成的瞬时发生并结束的简单事件。由于隐性事件句的谓语动词都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可以采取主谓倒置语序,从而与普通陈述句相区别,非常适合用来陈述简单事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能够使听者或读者充分注意事件的整体。为了能够充分实现陈述事件的功能,隐性事件句采取了主谓倒置语序,使事件的参与者位于句末,这样可以避免用事件的参与者作话题,因为如果用事件的参与者作话题,听者或读者注意的是参与者的出现、消失、变化等,而采取主谓倒置语序,听者或读者先听到或看到的是一元事件动词(不及物动词),继而在悬念的作用下,再去注意听或看这个一元事件动词的唯一必要论元,也就是事件的参与者,这样就充分注意到了事件的整体。例如:
(19)我们满洲里线的这边昨天发生意外死了一个人,听说漠河线的那边翻了一台车。(微博
这里说“死了一个人”、“翻了一台车”,而不说“一个人死了”、“一台车翻了”,是因为“一个人死了”、“一台车翻了”表示的是“一个人”和“一台车”所发生的变化,而用“死了一个人”、“翻了一台车”这种事件动词在前、参与者在后的主谓倒置结构来表示所发生的“意外”(意外事件)、所“听说”的事件,就能使听者或读者注意到事件整体。再如:
(20)a.1992年阴历十一月,河底镇失踪了一个年轻人。(杨平、胡晓光《铁血刑警张晓峰》
这里用主谓倒置的事件句来陈述“一个年轻人失踪了”的事件,而不说“一个年轻人失踪了”,显然是为了避免人们把句子的意思理解为“一个年轻人”所发生的变化(失踪)。试比较:
b. 本月中旬发生了大陆劳务合作工人失踪死亡事件。(《人民日报》,1994年第3季度)
这里谓语动词是典型的事件动词“发生”,听者或读者自然知道后面将要陈述一个事件,所以后面的事件内容“大陆劳务合作工人失踪死亡”用正常的主谓语序来陈述,而无需像20a那样采取主谓倒置语序,但后面需要加上事件的标志“事件”,共同构成体词性成分,以便与事件动词的“发生”相照应。
c.下午发生了第二件事:一个挑夫失踪了。(凡尔纳《巴尔萨克考察队的惊险遭遇》)
这里前一句是一个显性事件句,但没有说出事件的内容,只是表明后一句要陈述一个事件,而有了这个事件标记,后一句也只需采取普通主谓句的形式,无需采取主谓倒置语序,同样可以使读者知道这个句子陈述的是一个挑夫失踪了的事件,而不是在强调一个挑夫的变化(失踪)。
第二,符合汉语已知信息在前、未知信息在后的语序原则。事件句所陈述事件的参与者对听者或读者来说,通常是未知的,属于未知信息,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汉语在语序的安排上,有一种让已知信息在前、未知信息在后的强烈倾向,而事件句采用主谓倒置语序,让事件的参与者位于句末,正符合这种要求。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36)举了一个典型例子:
(21)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都已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丁声树等说:“‘大黑、三个民兵’是上文已经提过的,是确定的,所以说‘大黑、三个民兵都已回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是上文没有提过的,是不确定的,所以说‘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
不过,尽管未知信息在后的原则对汉语事件句的语序有影响,但决定汉语事件句采取主谓倒置语序的主要因素还是陈述事件的需要,因此,有时为了让听者或读者关注所要陈述的事件整体,即使参与者是已知信息,说话人或作者也会采取主谓倒置语序,让参与者位于句末。例如:
(22)这时来了《美文》杂志的编辑穆涛,往衣盆里看了,问:“主编给哪个婆娘洗裤衩?”(《作家文摘》,1994B)
(23)当客轮停靠在目的地马赛港以后,在全部的乘客中,惟独失踪了一个叫雅克·萨非的前S市法租界警官。(蔡骏《猫眼》)
以上二例中的“穆涛”和“雅克·萨非”对读者来说虽然是未知信息,但作者用“《美文》杂志的编辑”、“前S市法租界警官”表明了“穆涛”和“雅克·萨非”的身份,使“穆涛”和“雅克·萨非”临时成了读者的已知信息,本来可以用“《美文》杂志的编辑穆涛”和“一个叫雅克·萨非的前S市法租界警官”作主语,但作者为了增强语言的故事性,仍然采取了主谓倒置语序。
第三,可以更流畅地陈述事件。隐性事件句的谓语中心采取主谓倒置语序,让事件的参与者位于句末,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后续篇章进一步描写或说明的对象,后续篇章可以自然地省略主语,这既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又使语篇连贯,在小说等记叙性文体中经常使用。例如:
(24) 刘乾站立檐前,只见南门那边来了一个人,腰束皮挺带,身穿布衫,行走如飞。(《封神演义》第16回)
(25)洞门外来了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许大粗的铁棒,要他师父哩!(《西游记》第二十回)
(26)后边又新从景州来了一个尼姑,姓郭,年纪三十多岁,白白胖胖,齐齐整整的一个婆娘。(《醒世姻缘传》第八回)
以上3例中的后置主语“一个人”、“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一个尼姑”可以自然地作后续篇章的逻辑主语,而无需另用代词代替,行文简洁流畅。
第四,有利于对话语的顺利理解和记忆。有时事件的参与者较多,并且需要通过并列短语的形式分别加以说明,这样的主语就显得比较复杂,而隐性事件句的谓语中心采取主谓倒置语序,就可以使复杂的主语处在句末焦点的位置上,能够使听者或读者集中精力听或看构成主语的各个参与者,这符合简单成分优先、复杂成分靠后的语序安排原则,有利于理解和记忆。例如:
(27)这成都是四川省会之地……来了十二名皂隶,四个书办,四个门子,八名轿夫,一副执事,一顶明轿,齐齐的接到江边。(《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一回)
这一例陈述的是有多个参与者的事件,如果不采取主谓倒置语序,事件的多个参与者罗列完之后才说出事件动词,那么排在前边的事件参与者与事件动词相隔较远,影响对话语的顺利理解,也降低了对事件的多个参与者记忆的容易程度。
4.2 “显性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我们知道,“隐性事件句”通常用来陈述由人或事物的出现、消失、变化等所构成的瞬间发生并结束的简单事件,它的句式意义相当于“某时某地发生了……事件”,但陈述瞬时发生并结束的简单事件时通常不采取“某时某地发生了……事件”这种“显性事件句”的格式,因为对于陈述这种简单事件来说,这种格式不够简洁。“显性事件句”通常用来陈述由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等构成的具有一个持续过程的较复杂的事件,如打人伤人事件、劫机事件、劫持人质事件、暴动事件、骚乱事件、爆炸事件、自杀式袭击事件、枪击事件、谋杀事件、自杀事件、家庭暴力事件、考试舞弊事件、泄密事件、中毒事件、溺水事件、上访事件,以及被称为“事变”的重大的政治性、军事性事件,还有各种被称为“运动”的群众性事件等。“显性事件句”具有浓厚的书面语色彩,大都在新闻报道中使用,通常是用来概括地说明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由后续篇章对该事件的过程进行具体的陈述。例如:
(28)黎巴嫩首都贝鲁特3日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袭击俄驻黎大使馆的事件。(《人民日报》,2000年)
(29)新华社北京电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发生了一起罕见的球形闪电穿过客运飞机的事件。(《福建日报》,1984.1.19)
(30) 2003年6月在成都青白江区发生了一件因警察渎职导致3岁小女孩被活活饿死的事件。(《文汇报》,2005.7.4)
(31)1931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人民日报》,1996年10月)
(32)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7年,发生了“五四运动”。(《人民日报》,2000年)
(33)正当微电子产业蓬勃兴起之时,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95年1月)
有些“显性事件句”所陈述事件的参与者往往由施事和受事双方构成,这种事件只能用“主语—动—宾”格式来陈述,而不能用主谓倒置的“隐性事件句”格式来陈述,否则会造成施受关系混乱,如例(29)的“球形闪电穿过客运飞机”就不能说成“*穿过客运飞机球形闪电”,但是“主—动—宾”格式本来是用来陈述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的,如果用它来陈述事件,同时没有事件标记,人们注意的是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而不是事件整体,于是人们就在“主—动—宾”格式的后面加上事件标记“事件”,表示所要陈述的是由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所构成的事件,然后再用“发生+了”来表示该事件已经发生,不过这时仍需采取主谓倒置语序,表示把该事件的发生当作一个事件来陈述,而不是单纯强调该事件已经发生,如“发生了教师体罚学生事件”、“发生了恶狗咬死人事件”等。如果单纯强调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不需要采取主谓倒置语序,如:“就这样,一场逼婚抢亲的事件发生了。”(《福建日报》,1980.11.19)。
5. 事件句的生成方式
如前所述,事件句采取的是主谓倒置语序,那么它的生成方式并不复杂,就是将一个主谓句的谓语提到主语前,无论是“隐性事件句”还是“显性事件句”都是这样生成的。一个完整的事件句的原型是“TL NVi了”,将主语N与谓语“Vi了”倒置,就形成了“TL Vi了N”式的事件句,如将例(15)b的“孤岛一棵树死了”的主谓倒置,就可以形成“孤岛死了一棵树”这样的事件句。当然,并不是每个事件句都经过了这样的转换过程,事件句的格式一经形成,人们便可以直接按照这种格式类推造句,而无需临时转换。也正因为如此,不是每个事件句(主要是隐性事件句)都可以意义“无损”地转换为非事件句,如将例(11)的“施工期间死了三名员工”转换为“施工期间三名员工死了”,意义会发生轻微变化,因为汉语句子的主语通常是有定的,如果这样毫无添加地转换,人们可能会把“三名员工”理解为特定的三名员工,而且是全部的施工人员。
6.结语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汉语事件句的结构、语法意义、语用功能和生成方式等问题,希望能够对重新认识汉语的隐现句和全面认识汉语的句式系统有所帮助,以便提高汉语事件句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