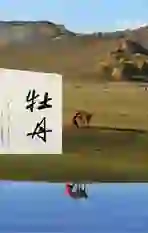浅析阿赫玛托娃诗歌中的“对话性”
2018-11-22张会燕
张会燕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在其哀婉、苍凉、悲怆的诗意符号之间回荡着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她的声音被称为自己时代、全俄罗斯人民、真理和信仰的声音。本文结合巴赫金“对话”理论从时代背景、抒情场景、诗歌意象等方面浅析阿诗的“对话性”。
阿赫玛托娃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是继勃洛克以后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其诗歌不仅哀婉、凄美、悲怆,还充满了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和强烈的情节性,“隐蔽心理学”的运用使其诗歌具备小说的张力和感染力。
巴赫金在《话语体裁问题》中指出:“言说充满着对话性的陪音,不考虑它便不能彻底理解言说的风格。”巴赫金将此机制称为言语的“对话性的陪音”或“内在的对话性”。日常生活会话总是指向特定的接受者,诱发和期待对方的回答和反响(赞成、同情、反驳等)。文学创作亦遵循这样的规律。人们如果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文本作为整个俄罗斯民族话语的一部分,那么按照巴赫金的观点,阿诗同样具备“内在的对话性”。此外,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提出了复调小说“对话”理论。本文试结合以上理论,从时代背景、抒情场景、诗歌意象等方面来分析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对话性”。
一、对话“动荡时代”
阿赫玛托娃作为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女诗人,从1912年发表第一本诗集《黄昏》至生命最后几年的诗作《夜半诗抄》(1963),其创作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见证并亲历了俄罗斯的风云变幻与动荡时代。她作为俄罗斯的“良心”,始终保持着与时代的对话,发出属于人民与真理的声音。
20世纪前20年是诗人创作的早期,适逢俄罗斯诗歌“白银时代”,诗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如果人们将不同的流派主张看作复调小说中的不同话语,那么同时代的不同话语所反映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本身就构成对话关系。象征派偏爱对“彼岸”精神世界的描写,诗风朦胧、神秘。未来派在诗歌体裁上标新立异,用语大胆、出奇,“阶梯式”诗行泛滥。阿赫玛托娃在诗歌中大量运用民俗体裁,这不仅代表诗人本人,也代表阿克梅派发声,与当时百家争鸣的诗坛同行进行交流对话,同时也期待回应和评价。她也的确得到了回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与歌谣的曲调相结合”是阿赫玛托娃诗学的独到特征。阿赫玛托娃在诗歌体裁上没有如某些流派一般全然舍弃传统,而是将民俗体裁完美地融入自己的创作。
巴赫金指出:“我们的言语、言说是处在社会的、历史的言语文脉当中的。不管我们的一段言说看起来多么具有独白性,实际上都是对别人言说的不同程度上的反应。”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正是对俄罗斯民歌传统的反应,她经常使用民俗体裁,如歌谣、哭诉、祈祷、送别曲等。在阿诗丰富绚烂的韵律调色板上,一种特殊的三音步诗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中1915年的《祈祷》和1941年的《哀歌》都属此类体裁。俄罗斯灾难深重的悲剧命运诱发诗人向圣母祈祷、向上帝哀求,试图与他们展开对话,以期达到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慰藉。
革命后的时代在诗人看来是充满破坏和失落的悲剧时代,然而她并没有背弃祖国。在1917年秋创作的诗歌《我听到一个声音》中,她写道:“可是我淡然地冷漠地/用双手把耳朵堵住/免得那卑劣的谗言/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诗人用诗歌回应了蛊惑的声音,她选择留在俄罗斯,接受并分担祖国的命运。留在国内的阿赫玛托娃没有向“铁的时代”低头,向道义上的压迫妥协。20世纪20年代,诗人发出这样的呼声:“我,是你们的声音,是你们呼出的气息/我,是你们镜中的面容/是无用的翅膀、无用的扑打——/然而我同你们总会相伴到最终。”面对时代的考验和生活的折磨,她成为自己时代的声音,为人民、真理和信仰发声。20世纪30年代和卫国战争时期是诗人创作的中期,充满爱国主义的诗歌将诗人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结合在一起,代表作有《誓言》《勇敢》《胜利》等。在创作晚期的《安魂曲》中,诗人将个人事件(儿子被捕)与全民族的悲剧结合在一起,在自我命运的悲剧中反映出整个俄罗斯的悲剧。
阿赫玛托娃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回响着俄罗斯传统的诗歌体裁,她不断与诗坛、与动荡的时代对话,代表人民和真理发声,构成白银时代诗歌、甚至是整个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多声部与复调性。
二、对话“黄金时代”
巴赫金认为:“每个言说都同先前于它的其他言说处在程度不同的对话关系之中,是先前的言说的继续、反响。”同理,阿赫玛托娃诗对19世纪诗歌抒情场景、诗歌意象的挪用等都可看作是与先贤的对话,是对“黄金时代”的继续和反响。
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你仿佛用麦秆吸着我的灵魂/我知道,那滋味让人痛苦,让人沉醉”,源于丘特切夫的诗句“他没有像毒蛇噬咬心脏/却像蜜蜂吸它的血”。诗人通过“吸”的动作将男性抒情诗歌的场景转用到女性诗歌之中,有挪用也有发展。试比较,蜜蜂吸血带来轻微的、肉体的疼痛,是可恢复的创伤。而“麦秆”口径更大,造成的疼痛也愈烈,何况它“吸”的是不可再生的“灵魂”,失去灵魂的躯体即使再光鲜亮丽也只是徒有其表,与行尸走肉无异。阿赫玛托娃在自己的诗歌中既回应了丘特切夫原有的抒情场景,又进一步深化了抒情主人公的内在感受,将痛苦的源头从肉体上升到灵魂。
诗人在《短歌》中写道:“我看到有个女孩打着赤脚/靠在篱笆上哭个不停。/尖细的哭声/听得我胆战心惊。”“哭个不停”的赤脚女孩形象让人不由联想到涅克拉索夫诗作中农家赤脚女孩的哭诉,两个同样对生命痛苦之声心怀怜悯的作家在这里融合在一起。诗节最后写道:“我将落个恶狠狠的奖赏/不是粮食却是石头/我头顶只有一片蓝天/伴着我却有你的声音。”“石头代替粮食”让人直接联想到莱蒙托夫《乞丐》里的诗句:“他只不过祈求一块面包/却露出无比痛苦的眼神/但有人拿起一块石头/放在他那伸出的手心。”两首诗中都有“石头(камень)”和“糧食(хлеб)”的意象。读者如果了解莱蒙托夫与初恋Е·А·苏什科娃的爱情悲剧,就能联想到“石头”所含的悲剧感。同样,阿诗中的“石头”和“粮食”兼具物质和精神含义。“石头”是阿赫玛托娃传递忧伤情绪的一个常见意象(石穴、心上的石头、沮丧的漂石、圣经中要“扔掉”又要“收起”的石头等)。因此,这里的“石头”不仅回应莱诗中冰冷坚硬的石块,也包含失去精神食粮的慰藉之后内心的凄凉与哀伤。
阿赫玛托娃和普希金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学关系”,普希金的创作如同对话双方中交谈的发起者,其诗作中的“皇村、大海、彼得堡、南方”等主题以及“世界性的关切”,诱发了阿赫玛托娃的附和与补充,从而令两位诗人跨越世纪的长河在诗歌中完成精神与心灵的对话。
三、结语
本文基于巴赫金言语“内在对话性”、复调小说“对话”理论等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进行了粗浅分析,发现其诗歌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发出了带有强烈女性意识与时代特征的声音,在诗人深刻的个人体验中包含着俄罗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从而在诗歌文本内外形成了一种广义的对话,即与时代、与先贤、与祖国、与人民的对话。
(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