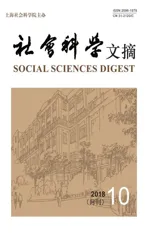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8-11-20
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
学界围绕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展开的论辩,与1939年暹罗更改国名引起国人的西南边疆危机感直接相关。暹罗本为君主专制国家,然而在1932年6月4日,国内军官发动政变,暹罗过渡到立宪君主政体,英暹关系从此衰落,日暹关系则迅速升温。
在日本的怂恿下,暹罗投入日本法西斯的怀抱,开始以激进的“爱国主义”宣传来塑造暹罗。1938年,少壮派军官批汶颂堪自兼国务总理,对外奉行反华、亲日、疏英法的外交策略。与此同时,文人阿谀附和军人政府,高唱“大泰族主义”,其中历史学者威集是策动改国名的幕后主使人。1938年,他发表公开演讲,斥责华侨不利于暹罗,尤甚于犹太人不利于德国,并称泰族在中国西南等地人口是暹罗全国人口2倍多,这些人“但闻暹罗有泰人则喜”,其目的在于宣传暹罗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同根同源,呼吁全泰族人团结合作携手进入“繁荣之域”。相比威集的演讲,批汶颂堪在向国民征求更改国名意见时,言辞更加直接,他认为在中国居留的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且部分泰族人不受任何中国政治势力的统治。
国人对于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和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仍心有余悸,此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教中心虽已移至西南,然而,即便苟安边隅,也未能避免日本支持暹罗分裂中国西南的阴谋。
事实上,早在暹罗正式改国号之前,傅斯年便对暹罗政治宣传的用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1939年2月1日,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道出了他的担忧:暹罗宣传中国滇桂是其故居,妄图收复失地的言论,将会酿成西南边疆的危机。他认为抗战后的西南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来到西南研究民族的学者,突出云南各民族的特征,可能为日本分化中国西南所利用。
顾颉刚此时正在昆明主编《边疆周刊》,定期登载分析西南各族的文章。傅斯年写信责备顾颉刚登载研究民族的文章,足启分裂国家之祸。为了避免学界的研究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他提醒顾颉刚谨慎使用“民族”一词,建议废止“边疆”一词,改用“云南”或“西南”。
事态的发展,应验了傅氏的担忧。1939年6月4日,暹罗正式宣布改国号为“泰”。同一日,陶云逵著文驳斥暹罗更改国名的依据,指出暹罗改国名的背后是日本暗中“施其播弄之术”,暹罗借“民族一体”思想高呼之际,向滇、桂、越、缅伸手。陈序经等人也认为暹罗的大肆宣传必将影响到西南边疆的稳定。
顾颉刚两次撰文阐述暹罗改国号对中国时局产生的不利影响。1939年9月,他在香港刊文指出暹罗改号是其狭隘的“泰族至高”思想的表现。同年11月,他再次发文重申暹罗改号会直接扰乱中国抗战建国的西南根据地,动摇后方民族的抗战意志,使日本坐收渔人之利,最终实现其独霸东亚的野心。
暹罗对“大泰族主义”的宣传,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及西南边省官员的密切关注。1940年4月,国民政府饬令云南省政府要“加切注意”,而暹罗宣传的“大泰族主义”,虽然尚未发生实际破坏作用,但足以让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不能不承认隐忧重重”。
毋庸置疑,由暹罗改国号给西南边疆带来的危机,引起了政学两界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后果是让傅斯年和顾颉刚开始认识到审慎处理西南民族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在西南边疆危机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避免以后出的观念来倒述此次论辩,才能更加接近于历史的本真。
人情世故与学术歧见
顾颉刚表示,傅斯年的责备是他写作《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直接原因。他在该文中指出:中国对内没有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今后应谨慎使用“民族”二字。文章发表后,引起费孝通的质疑。费氏指出,国家和民族不能等同,国家内部发生民族间的分裂,根本原因在于各民族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谋政治统一,根本在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对于顾颉刚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以防止敌人分化的认识,费氏认为国家的安全和强盛,需要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紧密合作,绝非取消几个名词可以达成,“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
顾、费持论孰更高明,不应简单肯定或否定一方。1940年,冯友兰著文批评顾颉刚早年为倡导“古史辨运动”,竭力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证明中国民族出于多元,抗战后意识到日本人利用中国民族多元,企图分裂中国,遂又主张中国民族多元之说应该废止。显然,冯氏对于顾颉刚观点的“前后反复”不以为然,进而指出:民族出于一元或多元的讨论,实质是“传统”与“历史”之争。一个民族与一个人同样既有其物质上的联续,亦有其精神上的联续。民族精神上的联续,要有历史与传统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冯氏强调:“说中国民族是多元底,是依照历史。说中国民族是一元底,是依照传统。”此传统虽与历史不合,但可各行其是,并行不悖。冯氏之意,在于批评这场争论割裂了历史与传统之间和谐的内在联系。
既然“中华民族是一个”论题是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危机感而引起,所以应联想到,对于西南民族研究最有成绩、影响最大的杨成志及其同仁的态度,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对于进一步认识这场争辩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28年,傅斯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促成了杨成志、史禄国等人,参加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计划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开创了“中国学术界上作西南民族之集团研究”的先河。与此同时,顾颉刚为了提倡西南地区的民族研究,在学界第一次喊出“西南民族研究”这个新名词,并鼓励包括杨成志在内的研究同仁拓展西南民族研究。杨氏也在晚年回忆到,在他进入中山大学工作之后,就在傅斯年、顾颉刚的领导下从事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也正是在傅、顾二人的积极引导下,杨成志立下“终身贡献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宏愿。
傅斯年和顾颉刚敬告在滇学者慎用西南民族的称谓,学界一般认为这些“敬告”针对的是吴文藻。理由是傅斯年认为吴文藻参与组织成立的云南民族学会提倡西南民族研究,“绝富于危险性”。事实上,云南民族学会只能算是中国民族学会在战时的特别组织。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会员星散,会务停顿,后因昆明人才集中,于1938年11月成立云南民族研究会,傅斯年老友兼同事李济任会长,师友蔡元培、顾颉刚、陶云逵等人均为会员。
解放前杨成志和吴文藻齐名,人类学界有“南杨北吴”之说。杨成志既是中国民族学会重要成员,也是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的实际负责人。傅斯年、顾颉刚所反对的对苗、瑶、罗罗、摆夷等民族的研究,都不是吴文藻的主要学术研究对象。而杨成志及其同事所从事的西南民族研究的事业,正与当年顾、傅二人的积极提倡有关,且在国内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傅斯年不遗余力攻击吴文藻,而却绝口不提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中山大学,尤其是杨成志及其弟子江应樑等人,内中的人事因素尤为明显。
“国族”构建与“民族”研究
南方学者最早著文回应“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是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胡体乾。1939年6月,胡氏发表《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认为“民族”一词原是中国用以指称欧美各族,在此之后推及国内各族,其中并无恶意。即使中国学界不用“民族”一词,也不一定就能达到感情融洽、裂痕消除、意志统一的局面。但是,他同时又认为民族政策的达成,有必要辅以适当口号的宣传,即在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有利于加强各族同化的信念。
1939年8月,杨成志发表《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该文不仅指出了顾、费论辩的核心问题所在,还提出了在国族构建中,“中华民族”意识与民族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杨氏针对学界对于“民族”认识的混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广义的“民族”是指人们认同的传统、宗教、文化、语言、惯俗、意识等,以及对某一群体、集团的归属感,这一概念相当于“国族”(Nation)、“民族”(Nationality)的意思;狭义的“民族”一词,与“人种”(Race)相同,指一种自然集团,以探讨民族集团(Ethnic Group),与广义上的国族或民族所含有的政治意义不同,故研究民族的专门学问不称为Nationalogy(国族学),而称为Ethnology(民族学)。
在杨成志看来,顾、费二人的文章,其内容几乎充满关于“民族”一词之讨论,二人因立场不同,见解自异,各有所偏,但总体来说颇能代表彼时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见解的纷殊。作为两人的共同朋友,杨成志指出他们关于“民族”一词观点不同之处在于:费孝通所言民族似近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而顾颉刚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
后来,杨成志在《民族学与民族主义》中又进一步阐述: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探讨的自然民族(Ethnic);民族主义所注重的是“国族”需要的政治民族(Nation)。国族(Nation)与民族(Ethnic)之真正含义,可分而又可合,前者属于政治支配之权力结合体,而后者则为自然或生物之血统集团。以政治力量使各族团结于主权国家之内,这是20世纪任何国家所取之一般自然趋势,中国自不能例外。其所不同之处在于,欧美列强采用科学的“民族”研究成绩,以实施其政治“国家”的政策。
杨成志针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问题的讨论,与顾颉刚和费孝通不同之处在于,在坚持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态度的同时,并非停留在抽象名词的讨论上,而是把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与客观现实联系起来,不仅指出了顾颉刚与费孝通在此次论辩中主要分歧在于对“民族”概念理解的不同,而且颇具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作为政治权力之下的“国族”构建,与作为学术层面的“民族”研究,不仅可以并存,而且还能有机结合。
1937年,杨成志的研究生江应樑阐述他对研究西南民族一贯见解:以汉族代表中华民族是绝大的错误,把中华民族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更是绝大的荒唐。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民族,西南民族则为整体民族中的一个大支派;西南民族是中华民族整体之一部分,应包括苗、罗罗、僰夷、溪蛮、黎、瑶等族。又在《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指出将数千万的西南民族摒弃在“五族共和”之外是错误的。民族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若西南民族不加入,则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团结。
江应樑在承认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统一”的前提之下,又承认多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多年的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经验,使江应樑深刻认识到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是开化西南边民的有益参考。显然,江应樑与其老师杨成志都是从民族学是一门实用性科学的立足点出发,来讨论学术研究对于政府民族政策制定的现实意义。
学术与事功的分合
徐益棠在回顾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十年的边疆民族研究时,认为“中华民族主义之鼓吹”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中国已放弃“尊汉卑夷”等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要团结边民,“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宣传甚属必要,惟理论宣传的基础,须特别慎重,至少不相矛盾。彼时学界常以学术研究与政治措施分为两途,“在学术上可以分割,在政治上必须合一”之立论,似乎并不适当。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联系密切,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所以从学理言之,应改为“在学术上可以合一,‘行政’上必须分割”。
徐益棠曾与杨成志同时在巴黎追随法国人类学之父莫斯学习人类学、民族学,他们与同期在欧洲学习人类学的陶云逵、杨堃、刘咸、吴定良一起,号称人类学“六君子”。回国之后,徐益棠、杨成志、吴文藻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后来成立的云南民族学会,则受到傅斯年的猛烈攻击,如“昙花一现,遽而夭折”。徐益棠的言论,实际是质疑傅斯年、顾颉刚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认为该主张罔顾事实,取消“民族”研究,以政治需要凌驾于学术之上,不符合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中国最早的西南民族研究,源于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在1920年代末的大力倡导,“西南民族”的概念也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才广为学界所知。然而十余年过去了,为何当时的倡导者竟然改变初衷?
1920年代,顾氏在学界竭力倡导研究学问的人只该“求真”,完全不用考虑应用问题。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顾氏的观点发生变化。他认为在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因采取“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坚持真理,不问功用。然当国势凌夷之际,所学必求致用。1944年,顾氏谈及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因时,其中谈到政治与纯学术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学术工作要同中求异;政治工作要异中求同。抗战时期国人“实在不应当横梗族类的成见,贻国家以不利”。
彼时傅、顾已成为国内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言论足以影响到整个学界乃至社会的舆论风向,或许他们本身也有不得已之处,但是与政治的靠近也非常明显。朱维铮认为,傅斯年、顾颉刚通过讲“中华民族是一个”,为蒋介石的政治服务,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直接痛斥在滇避难的学者,在报纸上借民族研究,大肆宣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人“最可恨”,学问也“无聊”,看似为学问而学问,实际是“不管政治”,贻害国家,建议教育部门取缔“民族学”。
然而,持论双方无论对错,历史已然做出了选择。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正好与国民政府倡导的民族政策相契。1942年,蒋介石开始起草《中国之命运》书稿,其中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绝口不提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只认可“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以“宗族”替代“民族”,把中国境内各族群比喻成“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完全否认多民族的存在。既然来自政府层面的政治宣传不提“民族”,此后但凡牵涉到“民族”问题,都用“边政”问题来替代。许文珊指出,傅斯年、顾颉刚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至蒋介石撰著《中国之命运》,用“宗族”二字称谓国内各民族,随后即被普遍使用,此举不仅“影响历史学术,也影响了民族心理,关系非常之大”。
在政治压力下,杨成志和吴文藻开始重新考虑在保证民族学学科存在的前提下,不提及“民族”概念,以适应国家政治需求的问题。1941年,杨成志发表《边政研究导论》,成为国内构建“边政学”研究的第一人。在其对中国“边政学”的构建中,自始至终坚持由多学科参与,但民族学任“主角”的主张。1942年,吴文藻又发表《边政学发凡》,提出从“理论”和“实用”两方面出发,政治学和人类学“同时着眼”,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文化的“中心科学”。杨、吴二人先后阐述“边政学”的理论,成为民国学界构筑“边政学”的源流,并非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