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借书沽酒外,无事扰公卿
2018-11-18陈远
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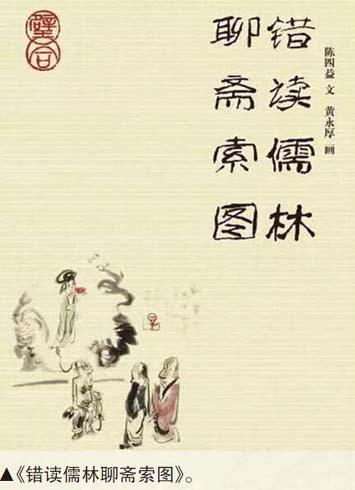


2018年8月7日,畫家黄永厚去世,享年91岁。这位“文真、字古、画奇”的艺术大家,大半生命途坎坷,其创作的中国画被称作“文人画”,兄长黄永玉对此评价道:“他的画风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陆游的读者,永厚的观众,对二者的理解多深,得到的痛苦也有多深,排解不了,抚慰不了。”
所谓“幽姿不入少年场”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慕为人了解。黄永厚为人仁厚、行事独立、不从俗流,身为艺术家的他有着对社会深厚的关怀,他的作品常常针砭时弊,只因他不愿做一个旁观者。
画画的也是读书人
“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这是一位大画家哥哥给同样是大画家的弟弟在一幅画上的题跋。
哥哥是黄永玉,弟弟是黄永厚。这个题跋,除了说这位黄家老二的风骨之外,还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喜欢书。
在圈内,比他晚的晚辈都管这个可爱的黄家老二直呼“黄老头”,同样,黄老头喜欢书在圈内也是人所共知。在他的住宅里,和卧室有一墙之隔的就是他的书房,连着书房的,则是他的画室。
1985年,57岁的黄永厚来到了北京,当时没有条件,在朋友家串来串去。中间住了很多地方,也有过自己的房子,一居室。
“当时书房起居室都在一起,画画也是,那就让我感到很美妙了。
后来条件好一些之后,黄永厚在通州潞河医院附近买了自己的房子,85平米,起居室、客厅、书房终于分了家。在那里住了五六年,才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
“我其实没有多少书,线装书更是没有。我在《瞭望》上画聊斋的时候,陈四益的一个老师问我,画聊斋用的什么本子?哎呀,这让我惭愧的不得了,我说,什么本子?不加注不断句的版本我都不会看。后来陈四益的老师送了我一套线装书,他说是最好的《聊斋》版本。
“我读书不是读给别人看的,我是给自己读的。”这个老头的叙述其实充满了陷阱,他自己说书少,读书也少。但是看看他的书架,虽然没有珍本奇本,但是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乃至当今文化领域内每一本受到关注的书,都在其中。
随手抽出一本,从头到尾,朱笔勾勾划划,写满蝇头小字,都是老爷子的读书心得。当今号称读书人的人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是为稻粮谋,“给自己读的”,可谓少之又少。单凭这份洒脱,就难得。
老头是画画的,他读的这些书,让他的画与当今画坛的画风有了迥然不同的风格,他的画,字比画上的笔墨还多,密密麻麻,每一幅画都传达一个思想,每一个思想都与当下的问题息息相关。
“我的画人家挑剔笔墨我都不在乎,但是我为我能在画中表达清楚意思这一点很得意。”当年老爷子在上海虹桥公园办画展,一个苏州花鸟画家走过去问:‘在画上写这么多字也叫中国画吗?这事正好被写意大师朱屺瞻碰上了,他回答说:“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了,要读很多书……”
大丈夫不从俗流
“我第一次买书是小时候当兵的时候,是一本王云五的字典。当时花了很大的工夫去背字典。结果工夫都白花了,因为中国的汉字要成句才好记。后来部队到了广州,我买了大量的书,见到书就买。当时已经是解放军的天下了,我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我几乎能背下来。
1954年,黄永厚到了中央工艺美院读书,那个时期黄永厚买的书也打上了当时时代的烙印。
“一到北京,我就买了一本余秋雨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还买了别林斯基选集,看了这些书,知道苏联有几个斯基都了不起。那时候我基本上就不买美术方面的书。这些书我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果成了我的罪状。”
黄永厚的罪状之一是说“洛蒙罗索夫是伟大的诗人。”黄永厚为此一头雾水:“洛蒙罗索夫是谁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一问才知道,洛蒙罗索夫是俄国的大化学家,批判黄永厚的那些人把洛蒙罗索夫和莱蒙托夫给弄混了。
1956年,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黄永厚到了广州。在那里,“我买了一套中学文学课文。从初中到高中,一直从诗经讲到鲁迅。”
“跟那套书配套的还有教师辅导材料,我同时看了下来,我的一点基础就从那套书来的。后来到了‘文革,流行的是北大五五级编的文学史。我认认真真地读了。我的文学观点,基本都是从那里来的。后来我又买到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我画《宋玉对楚襄王问》时用的典故,就是从这里面来的。
“别人都以为我写画跋不用思考,随手拈来,我说可没那本事,我都是现买现卖,读了之后有点感触,马上画出来。我不像别人,家学渊源、书香门第。但是我能活学活用,读了这个,能想到那个。我也不像别人一样,有个很大的文库,有需要,我就去买,我的书,都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我读书也跟风。钱钟书的《管锥编》,一出版我就买了,还画了很多画。王小波的书,也是一出来我就买了,买了很多套,送人。买王小波的书是因为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书的介绍,我马上就去买了,没多久,王小波去世了,我大哭了一场,虽然我不认识他。
“还有些好玩儿的。我说给你听听。‘文革后期,图书馆都关了。但是《论语》我就是那个时候读的。本来当时《论语》是属于封资修,不许读的。但是这是《〈论语〉批注》,可以放心大胆地读,观点我不去管它,只看内容,哈哈。要问我画的是哪个版本的《论语》,就是这个。
“还有这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我从图书馆里偷出来的,哪个图书馆我不告诉你,人家会找我算账的。”
老头儿说到这里又笑了,其实“文革”中的陈年旧事,谁也不会找他算账了。
按说一个画家的书房,摆满的应该是艺术绘画类的书籍,但是环目望去,黄永厚的书房里这一类的书甚至不够书架的一个格子,都是他的画家朋友送的,稀稀疏疏地摆在那里。
“那一类的书,不要看。现在的画家们作画、论评家评画,一讲我的老师是谁谁谁,这一笔像谁谁谁。艺术是创作嘛,你看看李可染什么时候说过他的作品像谁?我最近看书看到天津的大冯给一个大画家提意见:你的画风总是那样。那个大画家说:我变了,人家就不认识我了。我敢说,你要是总是按照一个套路写东西你肯定会难过,但是画家不难过。
那一类的书,我看它做什么?我画画也绝对不去借鉴他们,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就处在这样一个传统当中,一天到晚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跟书架的那些书相比,黄永厚的书房跟别人的不同之处是挂满了名人字画,刘海粟、范曾、黄永玉、黄苗子等等。这样的书房,有点像样儿,也有点不像样儿,这种风格,正像刘海粟给黄永厚的一幅字上写的:大丈夫不从俗流。
这个不从俗流的老头儿,把书房装在了他的脑子里,画入了他的画中。
■书情
《消失的动物》
作者:(英)埃罗尔·富勒
译者:何兵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在每個人都是拍摄者的时代,留给一张模糊、斑驳的照片的命运,只有删除键。但如果它拍摄自一百年前,并且被镜头捕捉到的对象是我们再无可能在地球上见到的生物,那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变得弥足珍贵,动人心魄。《消失的动物》收录了1870年到2004年间拍摄的大量难得一见的照片,它们的主角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是的,对于物种的加速灭绝,我们都从文字中读到过相关的报道,但照片记录下的真实,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
作者:(阿根廷)皮耶尔保罗·巴维里
译者:刘波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
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1933-1945)在“二战”期间一度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但最终昙花一现的帝国。历史的这一面已为世人所熟知。而实际上,纳粹德国还进行了一种纳粹治理经济的扩张,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下控制西班牙等国外市场并从中获益。《希特勒的影子帝国》再现了亚尔马·沙赫特如何设计出经济民族主义体系及其命运:从使纳粹德国成功干预西班牙,到在政治派系和扩张战略斗争中衰落。书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政权的史论读来也可谓惊心动魄。
《人类的明天》
作者:(法)席里尔·迪翁
译者:蒋枋栖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故事书”。因为里面的故事不是常见的虚构故事,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切身相关的故事。在讲述这些故事之前,席里尔·迪翁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面对交通拥堵和雾霾等生活危机,我们如此不快乐,但为什么没有行动起来?他带领团队遍访全球各行各业的意见领袖和普通人,以寻求应对人类困境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将这些人和他们扣人心弦的故事汇聚到一起,以此告诉我们,我们也能去创造类似的故事。
《优雅的离别》
作者:(美)艾拉·比奥格
译者:晏萍?魏宁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如今,死亡教育正走出禁忌地带,成为公共话语空间讨论的一部分。
与其他生死教育的心理类书籍相比,《优雅的离别》将很大的篇幅与重心放在了倾听上。作者毕奥格是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领域内的领军人物,本书选取了临床上真实的案例,细致入微地讲述了十余个真实的临终故事。在这些讲述中,我们看到了死亡临近的阴影,但透过临终者和陪伴者的互相支持和安慰,我们也看到了勇气、力量与深沉的爱。这事关死亡,更事关生命。
《新学记:
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作者:傅国涌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8年8月
近年来,关于民国教育,时不时会掀起一阵热议。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现代学堂取代旧时私塾,现代教材取代四书五经,“新学”与新的政治体制一样,走过了从被误解质疑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西学东渐”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历史学者傅国涌对近代教育的研究持续多年,这本新著是在其八次演讲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旨在追本溯源,还原中国现代教育从传统教育中脱胎换骨并逐渐占据主流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