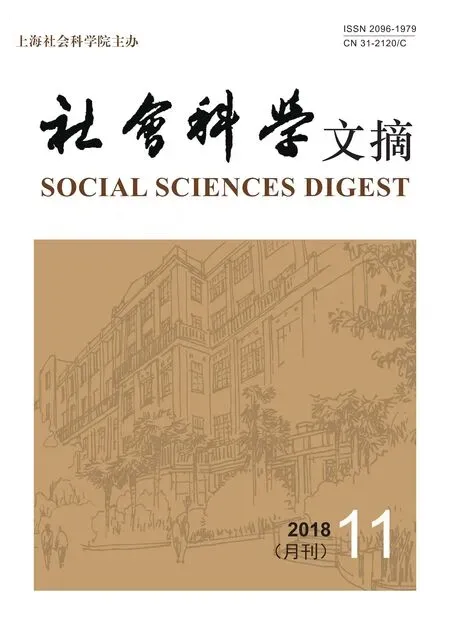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11-17
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既是对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的深化及再开拓,也是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及范式加以利用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对中国边疆现实情势的因应。
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历程
20世纪90年代以降,出于推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强烈愿望,“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被提出。从中国社科院中国疆研究所30余年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演进的轨迹来看,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199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十年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一个出发点”,即是“为下个世纪完成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总目标努力”。2013年,中国边疆研究所提出了“123战略”。“1”即以构建“中国边疆学”为中心,进一步夯实构筑“中国边疆学”之基础。
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进入厚积薄发的阶段,日渐成为显学,国内数所大学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一些期刊杂志以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为使命,开设“中国边疆学”学术专栏;“边疆智库”建设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此间,一些边疆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术优长,分别创出了“边防学”“边疆政治学”“边疆安全学”等不同学术概念,并希冀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
对于一门从无到有的新兴学科而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之路仍然“道阻且长”:(1)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目前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2)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的范式,包括学科的代表人物、经典性著作、普遍性理念等,以此标准来审视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研究领域,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目标任重而道远;(3)对照相关成熟学科的发展历程可知,一门学科的形成,从来都不是建立在本研究领域学者自说自话的基础之上,基于此种认知,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者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交流,获得他者的认同,同时还应积极面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边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边疆理论研究的初步开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疆域、边疆、边界与民族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可视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鉴于此诸文献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一些研究者毅然投入其中,做了一些筚路蓝缕的工作。吕一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于逢春等编《马恩列斯论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可视为代表性成果。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边疆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研究:(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法、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纳入边疆研究视野,打造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平台,构筑一个具有开放性、多学科视野的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2)基于中国自身的经验与探索,厘清中国边疆学学科边界,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界的国际话语权;(3)破解“中原中心主义”“西方殖民主义”史观提倡的“中国乃汉族国家”“长城以北非中国”等错误思潮,梳理自古至今中国边疆形态与疆域范围,充分展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4)在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边疆与周边态势的基础上,构筑新时期中国边疆战略框架;(5)探索历代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经验与局限性,希冀服务于政府当前各种边疆政策与作为的进一步完善;(6)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正确认识、理解边疆与中国乃至世界的联系。
“从边疆观中国”的兴起及检讨
最近10余年间,陆续有研究者提出,应逐步冲破传统“中原中心”史观和西方“殖民”史观的束缚,从边疆观中国,以边疆为本位(中心)来考察中国边疆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发展。“从边疆观中国”的研究范式,旨在构建中国边疆本位,阐释边疆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学理上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多样性。然亦须提防另一种风险,即过于强调边疆的历史主体地位,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来,已有研究者针对“边疆属性被置于一种无上的高度,以至于取消了传统中原社会的重要性”的研究趋向,表达了疑虑。有论者明确提出,片面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边疆属性”,其初衷即在于“解构”“中国中心论”或质疑“中国同一性”。
显然,为阐释边疆的“本位性”,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应当是“从边疆观中国”,但作为重要补充,必要时亦可循“从中心看边疆”的理路,围绕“边缘—中心”、“民族—国家”两个宏大视角构筑研究框架。边疆社会、边疆民族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对边疆历史的研究,需置于国家宏大历史叙事的背景下,考察边疆地方对国家的认同,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边疆地方民族精英等关键性媒介,在“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变化的。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与知识话语
梳理学术界就中国历史疆域范围问题展开讨论的学术思想史,我们大概可知,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几代学者习惯以“历史上的中国”来称呼讨论的主题。那么,何为“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谁可代表“中国”?这涉及到确定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这正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存在学术分歧的症结所在。经过多年的探索与讨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关于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确定原则,至少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避免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二是要摆脱传统的王朝史观。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同样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问题,研究者们或引入政治学的“国家学说”,或运用历史学的“长时段”理论,提出了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认识。关于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与模式问题,有研究者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创出并论证了“五大文明板块”理论,希冀“发掘中国统一多民族历史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力与机制”。
总体来看,40年来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的讨论,一方面继承了此前的传统,着重探讨历史上“以谁代表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确定原则等理论性问题;另一方面则逐渐摆脱“如何看待”一类理论、思想性的纠缠,开始更具体地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及其形成规律之类的问题的探索与讨论。
在我们看来,造成认知“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认知困境的根源在于,当前一些国内外学者习惯于在西方所拥有的思想资源与历史传统的语境中探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及其范围,亦即以“民族国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疆域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疆域发展的一般进程。然而,民族国家体系、殖民主义理论并不具有一种先验性的普遍意义,而是在特定环境、经验条件下催生的规范性体系。我们承认这些理论对于塑造欧美国家历史疆域和当代世界国家边界的维系作用,但亦应观察到,其理论并不具有历史应然的超越性,对于中国而言,王朝国家“大一统”的疆域观维系中国历史疆域形态的解释尊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无疑更具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土的历史资源与当下的政治实践,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理论。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朝贡制度研究
几十年前,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考察古代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时候,指出,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一种“世界体系”,并曾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认同,影响迄于近代。“朝贡制度”这一学术概念被提出之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相对于国外研究者从对外关系的角度阐释朝贡制度,中国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有自身的问题意识。
研究者对朝贡制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从实证性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二是基于疆域理论研究的维度,考察朝贡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研究的指导性意义;三是从古今衔接的视角,探讨朝贡制度的近现代命运。
最近10年间,朝贡制度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前沿学术问题。探讨其内在缘由:一是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一直将朝贡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疆域理论予以对待,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二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平崛起,作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因应,研究者开始重视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构建的“中华世界秩序”。然亦应指出,对朝贡制度的认知,亟应注意这一名词产生的时间和空间,如果不加区别地加以使用,则可能陷入“误用”、“滥用”的境地。显然,无论是作为“中华的世界秩序”,抑或是作为“东亚的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所承担的亚洲的历史模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在当前的东亚地区回光返照。
结语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构建中国边疆学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要细致梳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从历史当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还要从动态的视角认知新时期乃至未来边疆省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着重展望中国边疆学研究如何回应“变化中的边疆”,深入阐释重塑边疆的重要变量,回答“变化中的边疆”所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