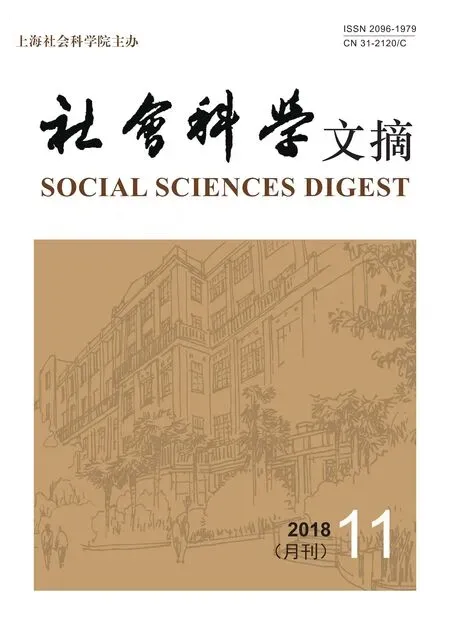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2018-11-17
本文就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脉络、重要议题、成就与不足,作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经历10年。
(一)酝酿: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1976年10月—1986年9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模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史“骨架”,需要补充生活的“血肉”。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以补充由于既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而缺乏的历史内容。冯尔康率先发表《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强调“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为“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接着王玉波发表《为社会史正名》,区别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乔志强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框架倡导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一文中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文化史的兴起也为社会史开辟了道路,而区域史为社会史扩展了地理空间。
(二)发轫: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1986年10月—1996年)。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标志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当时学者们强调研究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冯尔康提交会议的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提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三)成长: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997年—2006年)。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史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学界在界定社会史上存在分歧,经过讨论逐渐缩小,趋于消解。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社会史与人类学结合,历史人类学成为最活跃的学术领域。由于重视地域社会史,地理学也深刻影响历史学。新的社会史理论探讨,也带来对社会史史料的新认识。冯尔康出版了《中国社会史概论》,提出了社会史史料学的概念。郑振满则倡导民间历史文献,强调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是新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四)壮大: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2007年—2017年)。该时期由社会经济史研究发展演变出来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发生了向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在新历史认识论影响下民间文献更加受到重视。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交融,促进了社会史学科建设。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自2006年以来推出,并出版《清水江文书》3辑。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论坛,并出版“民间历史文献论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005年起出版《徽州文书》5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生活探索》6辑,出版有关社会文化的访谈录、论丛等系列出版物。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田野·社会丛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推出《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出版资料丛刊多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这里侧重于社会史理论体系问题,分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一)社会史的概念之争。从1986年中国社会史正式兴起后,对于什么是社会史存在三大分歧,即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对此进行学术梳理,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建议借鉴费孝通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定位,走综合的路线,一是研究全盘社会结构,二是从具体研究对象上求综合,从而把握当代社会史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三大研究特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进一步将社会史表述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并分别从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作为整体的社会史、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三方面论述什么是社会史,使得这一讨论更加明晰。
(二)整体性、碎片化、政治史与区域社会史。社会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学术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之别,具体理解上会见仁见智。新时期的社会史脱胎于宏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应在区域史中把握社会史的整体性,微观史学的个案研究可以有效地探讨事物整体。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出现零碎、细小的弊病,强调通过整体性来纠正。杨念群提倡“中层理论”以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改变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新社会史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2012年《近代史研究》(第4、5期)组织“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涉及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中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在了解国外已经讨论过“碎片化”问题后而发的“经验之谈”尤其值得关注。
(三)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社会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风格值得关注,此类研究也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显现的。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中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其学术追求,或许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所要表达的: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强调说,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区域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单位,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区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四)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我国较早的社会文化史,比较强调揭示社会精神面貌。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从研究文化生活、文化成就向社会生活转移的过程。李长莉《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30年——热点与走向》指出,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内容为风俗习尚、社会群体生活、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消费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生活史综合研究等,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生活变化之互动,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关系。不过,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缺陷在于理论分析与理论创新不足。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常生活史转变。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指出,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该书涵盖5个主要问题领域: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空间及其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取得大量学术成果。如有一批通论、断代、区域性的社会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士大夫、商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丰富多彩,城市、乡村的研究别开生面,民间信仰的研究精彩纷呈。至于关乎学科建设和研究途径的方向性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一)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20世纪90年代,海外学者讨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影响到国内学术界,先是政治学后是历史学。这一影响表现在近代史、明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表述为“社会与国家”,体现出自下而上从社会看国家的研究立场。明清史领域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成果较多,代表性的成果有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
值得注意,社会学学者李友梅《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活实践始终存在无法摆脱的张力,主张尝试构建“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以“自主性”为观察对象,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这一社会变迁过程。
(二)结构与生活的社会史。新时期社会史强调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重视从群体关系的结构探讨社会。有别于以往比较单纯重视生产关系,而兼顾法权关系的探讨,从阶级关系向等级身份的研究转变,或者说将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着眼于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吴琦《明清社会群体研究》等。
新时期社会史的重要特征是强调全方位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社会史除了重视社会结构,同时重视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史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研究比较平面化、泛化、重视事项而忽略人的作用。尝试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著作也有问世,如黄正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近年来出现了日常生活史的法学研究。如郭东旭等《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徐忠明编《〈老乞大〉与〈朴通事〉: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等。
(三)生命、生计、生态的“三生”结合。社会史的跨学科属性日益突出,在生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医疗社会史表现得比较明显,生命、生计、生态是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三者密切关联。
新时期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研究较早开展。李文海等人1985年以来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灾荒研究,关注灾荒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灾害与社会也受到关注,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郝平《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以及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都是这方面的著作。瘟疫随灾而起,讨论瘟疫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与《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是这方面的著作。与此相关,公共卫生的研究也得到展开,如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等。医疗社会史关注的是疾病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命与常态的谋生问题即生计与生态密切关联。
疾病、瘟疫以及灾害与生态环境也关系密切,同时是环境与人的活动关联。研究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的新方向。古代社会早期的环境史研究代表性论著如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明清以来的研究最为丰富,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均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王建革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著有《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等。水利与社会关系也为成热点。研究南北方水利社会史的专著都有,讨论浙江的有两部: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论述山陕地区水利的也有两部专著: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中,涉及人的生计与生态的问题,如王建革、张建民的著作即是。但生态环境史的著作往往见物不见人,而传统的生计问题研究也往往脱离生态环境,比较缺乏从生命角度认识问题。
生计是为了生存的谋生活动,不仅表现在士农工商的主要职业上,也体现在各行各业上,涉及生计的研究很多,专门研究则缺乏。对于生计的认识,也反映在衣食住行物质的获取与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渐多,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赵兰香与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何辉《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多涉及这些问题。
一般来说,生命与生态既是人地关系,更是天人关系,体现在生存之道上,以往的生计研究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生计也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的探讨,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下,生计的探讨还应当与生命、生态结合。生命、生计与生态的有机结合,是探讨历史变迁的重要途径。
纵观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焦点还是如何把握什么是“社会”。从社会史研究复兴伊始,在何谓“社会史”上就存在争议,大致有广义、狭义的不同认识,好在社会史研究同行并不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搁置争议,抓住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与学术前沿力行实践,从研究中体验、升华对于社会史的认识,从而使得学术共同体成长壮大。面向未来,社会空间的扩展,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跨学科的视野,或许是近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