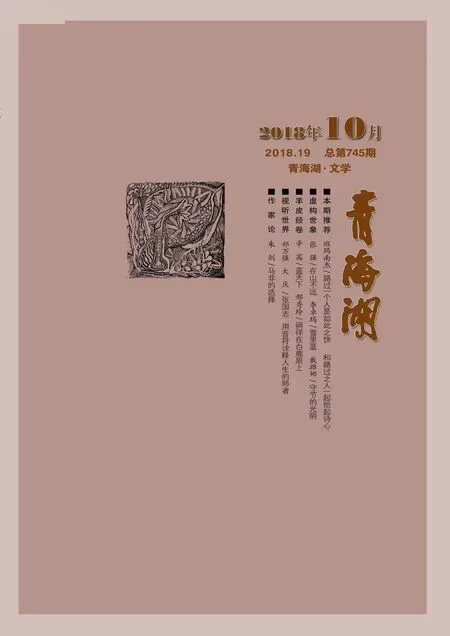马非的选择
2018-11-15朱剑
■朱剑
马非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诗歌界的酒王”,一个是“口语鹰派”。对于前者,据我了解,他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不置可否,至少本人没有亲口承认过,对于后者,他则是欣然接受,似乎在说:能不能喝不重要,写得好不好,关键是口语诗写得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符合马非的天性,他是有性情之人,我曾多次目睹他酒后高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拿手曲目,唱得很投入很抒情,有性情可他从来不耍性情,比如他没有传统文人的那种故作清高,也不像某些民间诗油子,一身江湖气,他不混官方,同样也不混民间。而且我清楚,他是很烦那种耍性情之人的,耍性情之诗,更是为他所看不上。马非的诗,整体上是冷静的、反传统抒情的,或者说他是在用智性、反讽、解构、自嘲等在进行反抒情,反抒情也是抒情,是口语诗人的抒情方式,是更高级的抒情,马非作为口语之鹰,自然深谙此道。
诗人伊沙曾对古典诗人、现代诗人和后现代诗人进行过描述,大意是古典时代的诗人充当的是国师这个角色,老有为君分忧的意识,现代诗人自觉扮演精英知识分子,为文明代言;后现代诗人呢,则更像是邻家大叔,和芸芸众生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很平民主义,对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日常,也不为谁代言,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仰视世界也不俯视世界,而是平视。马非是这样的诗人,我认识的不少诗人也都如此,他们中一些人在单位上着班,用笔名写诗,名满天下了,而单位同事毫不知晓他是一位诗人。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在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诗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和我过着一样日子的人,一个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人,怎么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于是便对这样的诗人进行嘲讽、攻击,更多是冷漠对待。曾有一段时间,我对此很不理解,现在却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没有跟上,他们还不是现代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心目中的诗人还是国师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得让他们仰视,他们才服气,所以他们认古典诗人,认现在有头衔、体面的官方诗人,如果官方诗人还能耍个性情,他们就更服气了,反过来,就对那些写出了他们生活中此时此刻的欢乐与悲伤的诗人漠然待之,对那些更生活更人性的诗歌嘲讽有加,认为不是诗。
看到了这一点,就会知晓一位口语诗人在当下的处境,说白了,就是谁也不认,官方不认,民间也不认。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对马非这样的“口语鹰派”更加充满敬意,他们本质上不是对抗者,只是在坚持个人的价值选择,并自然而然承担了新文明的建设与传播,没人承认也没关系。
马非的“鹰派”做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最明显的一点,他除了口语诗,什么其他类型的诗都不写;最极端的一点,是他评价一个诗人,先要看你写的是不是口语诗,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档次就会在他心里自降一档,哪怕你写得再好,也在他这里得不到满分。当然他有他的理由:你写的都不是口语诗,能好到哪儿去呢!
这样的话,当然会让很多人不愉快,甚至愤怒,这样的话,懂者自懂,不懂的人,和他说破了天也没用。单就马非自己的创作而言,真正做到了言行合一,他选择写口语诗,更确切地说,是选择写后口语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旦开始,就一条道走到黑。
2017年7月,长安诗歌节到宝鸡千阳县办活动,去的途中,我和伊沙盘点中国后口语诗的历史,发现马非资历之老,是绝大多数比他年纪更大的诗人都比不上的。口说无凭,来看这些事实:中国后口语诗歌始于伊沙,1988年他就写出《车过黄河》这样标志性的作品,伊沙北师大毕业回到西安后,在他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受他影响的大学生诗人,这帮诗人中,有人写着写着不写了,也有人一直写到今天,他们便是马非和东岳。据马非自己讲,他见伊沙的时间是1991年,在此之前,他写的还是抒情诗习作,见了伊沙后,写作立马变了,彻彻底底变了。可以这么说,马非是最早的少数几名追随伊沙写作后口语诗的诗人之一,虽然在年龄上他是70后,但他在后现代语境中浸淫的时间足够早,也足够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资历的问题,更是创作的保证,举个例子,每遇社会重大公共事件,各色诗人几乎都会留下自己的诗作,口语诗人也不例外,往往这个时候,那些“道行”还不够深的口语诗人则会“露怯”,或陷入集体无意识,或滥抒情以图打动人,而这样的现象,你不会在马非诗里看到,他一定会有个人的视角,一定会用一种更智性的方式来处理。
当然啦,出道早,不能说明你就行,还得有实实在在站得住脚的作品。1995年,马非与严力、伊沙合出了一本诗集《一行乘三》,收录了他1992年至1995年的部分作品,在严力与伊沙的压力之下,马非还是扛住了,贡献了《九三年》《法国人加缪》《陈小娟事件》这样的佳作。虽然有人评论说马非作品有伊沙的影子,但有伊沙的影子又有什么错呢?!这点马非从不避讳,反而说:“我的传统就是伊沙。”在此,我还要反问那些批评者一句:在“麦地诗歌”横行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有多少人敢跟着伊沙朝“后现代”走呢?恐怕寥寥无几吧,马非跟起走了,就是意识到位了,就是当之无愧的先锋。顺便再说一句:当下流行的“截句”,在《一行乘三》这部诗集里早就有了,而且已经被三位诗人玩得精熟完美了。
同年,马非写出了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恶作剧似的改写》,在我看来,这首诗标志着马非创作的完全成熟,请看:
(原作)午夜她离去后两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我有东西丢在你那啦/我问是什么/她说——/心//(改写)/午夜她离去后两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我有东西丢在你那啦/我问是什么/她说——/乳罩
我要说的是,一个在1995年,就写出了如此后现代作品的诗人,怎么还会对那些传统抒情诗、学院派诗歌、泛口语诗歌等等高看一眼呢?不可能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马非的创作更加深入日常生活,技艺也更加成熟。这时,口语诗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写得过实的问题,比如手法单一的问题,很多诗人往往只是止于简单的解构了事,等等。客观来说,马非和我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当面或在电话中进行过多次交流和探讨,也互相有过非常尖锐的批评,但对于怎么变,我们却不甚明了。2008年,伊沙开始写作《无题》,率先做出了变化的实践,两年后,《无题》结集出版,这本杰出的诗集,标志着口语诗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为此,我写了《无题,为口语诗的未来命名》加以解读,马非也写了《无题——读伊沙超大型〈无题〉的一点认识》,重点谈了《无题》诗作中对意象以及其他修辞逻辑的借鉴和碰撞,这个在我看来有点固执的家伙,终于认为融入了“微意象元素”的口语诗是“有益且有效的尝试”,大概是受其启发,在实际创作中,他也写出了一部分精深微妙的作品,比如下面这首《一把铁锹》:
雪后中午/在麒麟湾公园/偏僻的一角/一小片树林之间/我看见一把铁锹/支在其中一棵树上/还有两行脚印/从我站立的小径/迤逦到那里//这时一束阳光/从树杈处倾泻而下/铁锹猛然一颤/仿佛活了/闪闪发光/逼人眯眼/白雪也顿失其白/惊起两只乌鸦/和一伙麻雀/扑棱棱四散开去
一个好诗人,一定是生命直觉好的诗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意识会越来越强烈,随着而来的就是其诗也跟着变化,有时候,就算你自己没刻意去求变化,生命与岁月也会替你做出完美的选择,到了这时候,很多诗就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来读读马非这首创作于2014年的诗作《秋天的蚂蚱》,这年他43岁:
有一晚散步回来/上台阶的时候/老婆想从一级台阶/蹦上更高一级台阶的愿望/未能得逞/过去能跳四级台阶/并且一口气蹦好几次的我/也只勉强跳了两级
从《恶作剧似的改写》到《秋天的蚂蚱》,可以看出马非的写作功力和境界确实提高了不少,口语诗的变化,亦可从中窥其一斑。
人的一生中,时时刻刻,总会面临着或大或小的选择,看起来每一次选择,都会有多种可能性,最终却发现,替我们做出决定的,还是自己的天性。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以及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方面,每一次,马非都做出了符合自己天性、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现在看来,他乐在其中,自然就是选对了,在我等旁观者眼中,他毫无疑问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很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需要的就努力去追求,不需要的则不搭理。世俗社会中,马非是有机会也有条件在诗歌圈换取一些实际利益的,但他并没有那么去做,和中国大多数口语诗人一样,他的诗作很少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他几乎没拿过官方的奖项,他真正谈得来的朋友也极少。关键在于他自己不感兴趣,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他珍惜自己的写作胜过这一切,他明白这个道理:不能搞投机,一次选错,满盘皆输。2013年,马非拿了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和新世纪诗典金诗奖,都是民间的奖,然后他就心满意足了,蛰伏在高原,自写自乐,甚至都很少外出参加诗歌活动,直到2017年拿了磨铁诗歌年度大奖,依旧是民间奖。这几个奖项,都给他带不来实际的世俗利益,但都是优秀诗人对他的承认,他要的是这个。
所以,他不是智者,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