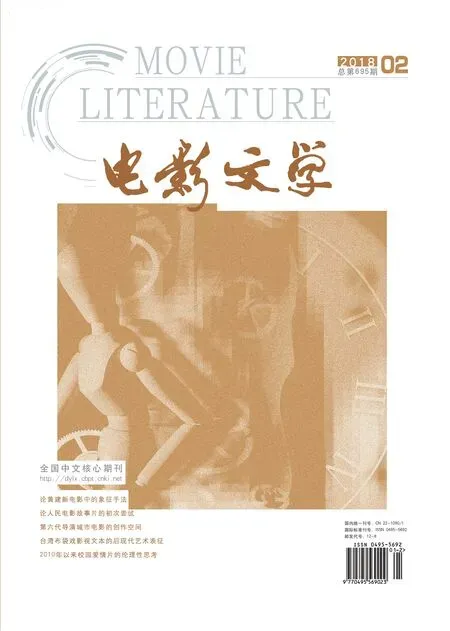从《明月几时有》看主旋律电影的新特质
2018-11-14张贞
张 贞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明月几时有》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香港沦陷以后,以传奇人物“方姑”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的抗日活动。在导演许鞍华一贯的日常生活散文化叙事节奏中,电影虽然被归属于“剧情/历史/战争”类型,却摒弃了同类型电影所惯用的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战争场面,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呈现出特殊历史时期普通人在平凡日常生活中的抗战故事。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抗日战争题材电影来说,《明月几时有》并不太符合观众现有的审美期待标准,所以票房和评价都不太理想。但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假如我们始终停留在已经形成并且固定的某个“总问题”视野内,就会忽略新出现的问题和对象,或者在它们面前沉默、失语,因此,“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论述的连续性。只有采用‘征候解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文字表述中辨别出沉默的表述……”这种“征候解读法”要求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文本的表层意义,而是要通过表层征候中的空白、沉默与缺失,去发掘文本潜在的问题式,对文本本身进行反思。《明月几时有》和原有同类型电影的脱节、在同题材叙事上的空缺与遗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备了呈现新问题、新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从《明月几时有》的文化征候入手,可以窥见主旋律电影的时代话语特征。
一、寻求“主体身份认同”的精神内核
《明月几时有》中有一个看似与剧情发展没有太大关联的细节——周迅饰演的方兰饱含深情地诵读茅盾先生《黄昏》中的片段:“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远处有悲壮的笛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来看这段话,“远处有悲壮的笛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但是当“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又重新回来时,是挟着雷声、打着鼓而来的,夕阳的宣言深入每一寸土地,成为斗志昂扬、激昂奋进的表征。方兰第一次诵读这段话是在茅盾先生寄居香港的房间里,彼时的她还未成为从事抗日活动的地下游击队员,只是下意识地喜欢这些文字构建出的美好意境。但是按照拉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主体是通过语言系统来建构自身的,方兰对这段话的选择,恰好折射出她无意识中对战斗、奋进和光明的向往。在随后的很多个日夜里,这种意境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在不停召唤她,使她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角色意识,最终在象征界完成了自我主体的构建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同样,叶德娴饰演的方母也经历了类似的“主体身份认同”的过程。方母刚出场时,有着非常明显的市井烟火气息:在自认为要去和租她房子的茅盾夫妇进行重要谈判时,先精心打理了一下妆容,拿出珍藏的糕点,谈判失败后又气呼呼地拿走了糕点。茅盾夫妇不告而别之后,方母不停地抱怨他们没打招呼就走了,为这些琐碎的礼节耿耿于怀,但是当女儿提醒她茅盾夫妇付了一个月的房钱却只住了五天时,方母立马喜上眉梢,开心起来。对于方兰加入东江支队、成为地下工作者这件事,方母最初的反应是女儿太瘦弱,不像是能参与革命斗争的英雄好汉……正是这些举动,让有的观众认为她之后的革命行为转折太大,缺乏合理性。但如果我们深入方母的生活中去,会发现她在逐渐接受并熟悉方兰的这种生活和工作模式之后,已经在无意识中慢慢调整自己的主体认知,等到她说出那句经典台词“死不重要,但不能连累队友啊”,实际上已经标志着她对自我“平凡英雄”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完成。随后,她主动帮女儿送情报、被捕后坚决不承认认识阿四,乃至最后英勇就义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这种自我认知顺其自然的表现。
这种对“主体身份认同”的追求,成为抗日战争年代平凡英雄共同的精神成长路径。所谓“身份认同”,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角色定位、自我认同和他人的承认。拉康说:“主体的历史是发展在一系列或多或少典型的理想认同之中的。”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一定的历史性现实行为,主体无法凭借单纯的想象来认同自我。电影中刘黑仔曾经对方兰说,没想到她那么瘦小却能做出如此勇敢的举动,方兰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香港沦陷,方兰可能就是一个对小动物充满爱心、沉浸在恋爱中、憧憬婚姻生活的少女,方母也会一直寻找琐碎生活中的点滴乐趣。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年代,每个主体自我的建构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和感召,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认同,并在主体和他者认同的交互关系中得以确立。所以,方兰因为茅盾先生的缘故结识了刘黑仔、接触到革命组织,她关于革命、理想、奋战的追求被不断强化,最终建构起“平凡英雄”的主体身份。方母接受方兰主体身份的过程,也是她调整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的过程。而当方兰在雨夜的小山村里,搂着童年的彬仔再次诵读茅盾先生的那段话时,这种意境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又一次通过语言浸入一个孩子的心中,引导他在那个年代成为抗战小英雄,又在和平年代的香港成为一个自食其力、努力拼生活的计程车司机。当已经垂垂老矣的彬仔跟众人讲述过去和历史,并内敛而深情地说出那句“我很想念方老师”时,电影不仅在视觉景象上把半个多世纪前的港岛深山与今天高楼林立的维多利亚港联结起来,更是用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把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对“美好生活、拼搏进取、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追求,在战争年代引导着一大批普通人完成了“平凡英雄”的自我主体建构,又在和平年代同样鼓舞着众多普通人毫不倦怠地进行着个人生活和城市、国家的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月几时有》显示了主旋律电影在时代表述上的一个新尝试:在日常生活中讲述“英雄”的主体自我建构过程,并赋予其跨时代语境的可接受性和可延续性。在文艺界,“主旋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吁求下对文艺创作提出的时代要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旋律电影主要通过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来感召大众、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如《大决战》系列、《开国大典》《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消费文化的逐渐盛行,主旋律电影又以更宽容、更灵活的姿态充分吸纳时代元素,通过大场面的视觉冲击、明星的吸引力等来满足观众的观看预期。近年来涌现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电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续了主旋律电影的时代生命力。同时,主旋律电影的时代发展还有另外一条途径——从革命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大众文化和民间话语的挖掘,《南京!南京!》《东京审判》等电影均是将抗日战争题材的讲述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身上,通过个体的遭遇和命运来唤起观众对历史事件、时代抉择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的共鸣。
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侧重视觉消费文化还是倾向于个体命运感知,都需要尊重观众的现实生活体验和日常生活认知。在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中,那种“几十年不变的僵硬模式和狭窄的题材、刻板的面孔”,“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影响力和感染力”,“它的存在事实上仅仅成了一种具有姿态性的表意符号,既不符合市场条件下的文化生产规律,也失去了对主流文化宣传的功能”。因此,如何寻找时代语境中大众能够接受的新的情感模式,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明月几时有》的价值意义,恰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绕开了主旋律电影原有的叙事策略和情感模式,细致地刻画了以方兰、方母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如何在时代语境中进行自我主体建构,并通过主体间性相互影响,从而催生了一大批可歌可泣又可信可爱的“平凡英雄”。这些平凡英雄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言行举止和性格表征,但他们的成长历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看似“反英雄”的叙事策略恰恰在无意识的文化征候上预示了当前社会语境中讲述“英雄”故事的一种新的可能。
二、碎片化散文叙事的审美追求
《明月几时有》另外一个招致争议的文化征候,就是主题不明确、线索繁杂不清晰。一般来说,主旋律电影往往围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一个英雄人物进行叙事。《明月几时有》却有三条叙事线索:一是以方兰、方母和刘黑仔为主的东江游击队队员,他们在电影中主要承担起营救各界知名人士、传递情报等任务;二是以李锦荣、张咏贤为代表的潜伏在日军司令部中的地下党员,他们主要负责搜集、探取情报;三是后来成为计程车司机的少年游击队员彬仔,他的讲述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三条线索的铺设,以分散的人物群像的方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碎片化的散文叙事,从而消解了高潮迭起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日常生活合理性的描写。
导演许鞍华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她和编剧曾经看过200多个关于东江游击队的故事,其中很多都可以拍成大片,比如刘黑仔率队搭救一个美国伞兵中尉并护送其安全离开香港的故事,足以拍成一个生死救援的跨国大片。但她舍弃了传统的大片风格,选择了这种最能体现日常生活细微处的艺术形式。所以本可以惊心动魄的“知名人士大营救”被一场短兵相接的对抗取代;方兰的地下工作更多地呈现出琐碎和劳累;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在整个游击队生涯中肯定历经了各种惊险,电影却只展示了他几次有惊无险的机智行为;方母的英勇就义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重笔渲染的场面,电影却把重点放在她如何在码头上化险为夷又不幸被捕的环节……这种取舍很清晰地凸显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 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和每一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与体现出来”,而主体的自我建构和身份认同,也只能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
同时,电影在展示平凡英雄们的日常生活时,特别注重对日常生活真实性、复杂性的挖掘: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陷入热恋的李锦荣刚向方兰求完婚,后一秒钟就说自己要走了,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言行,恰好显示出人们无所依存、慌乱不安的真实心理。方兰在送情报的过程中还要顺道去参加表姐的婚礼,她最危险的一次地下工作就是在码头上被检查行李,行李中放满了抗日活动宣传单,被检查出来后,对方却因为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担心方兰有埋伏在周围的同伙,惊慌失措地放走了她。方母送情报时先是有惊无险,以自己不识字的理由躲过对方的盘问,但就在观众期待她能幸运地凭借这种民间智慧安全过关时,方母却因为带的钱不够多被搜身,最终被捕。李锦荣成功潜入日军司令部,看起来似乎还和大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电影也非常真实地告诉大家,喜怒无常的大佐可以一言不合就拿刀威胁李锦荣的生命,等到李锦荣的身份暴露,大佐更不会因为私人情谊放过他……这些反戏剧化、反模式化的细节处理,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年代人们的经历和遭遇,而不是讲述被类型化叙事培养起固定期待视野之后的观众想象中的游击队员们的故事。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说过,很多被思想、政治、经济等日常生活行为所掩盖的本质区别,只能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来展现:“我们当然可以到菲尔内去拜访伏尔泰,同他长谈,而且对他的谈吐不会感到惊奇——做一次想象的旅行不会付出任何代价。18世纪的人在观念方面同我们当代人不相上下;他们的思想和爱好同我们十分接近,因而我们不会感到身处异地。但是,只要菲尔内的主人留我们在他家待上几天,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甚至他的养生之道,都会使我们大为吃惊。他和我们之间将会出现可怕的距离:照明、取暖、交通、食物、疾病、医药等等。”因此,“我们发掘琐闻逸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明月几时有》对琐碎、冗长、复杂日常生活细节不遗余力地渲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主旋律电影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审美价值:从短时段的宏观战争回到长时段的生活细节,不是用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镜头语言去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是带领观众去走近平凡英雄们碎片化、断面化的日常生活,感受他们的烟火气及其坚韧和勇气。
此外,这种碎片化的散文叙事结构在电影的情绪节奏把控上也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苏联早期心理学家、艺术理论家维果茨基曾经提出:“要在一切艺术作品中区分开由材料引起的情绪和由形式引起的情绪”,因为“这两种情绪处于经常的对抗之中,它们指向相反的方向”,而艺术作品“应包含着向两个方向发展的激情,这种激情消失在一个终点上,好像消失在‘短路’中一样”。从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明月几时有》的题材是沉重的家仇国恨、生死离别,其艺术表现形式却是零碎、诗意的,再加上久石让轻松而节奏明快的配乐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和题材产生了对抗的艺术张力。当观众带着对抗日战争题材的审美期待进入影片时,首先会因为题材本身产生深厚的历史感和家国情怀,但在观影过程中又会被艺术表现形式的诗意所感染,去体会细琐场景中平淡而悠长的爱情与亲情、事业与信仰、希望与失望、烦恼与牵挂、相聚与离别……而这些日常的情绪和情感,是存在于每一个时代中并被观众所熟悉的。当题材的沉重和形式的诗意融合在一起,产生出的艺术效果就超越了某种单一的审美体验,使观众在内心深处接受了平凡英雄们存在的合理性,并扩大了对那个特殊年代中抗日战争活动的认知范围。
三、视觉化的日常表述
为了更好地展示日常生活中“平凡英雄”们的主体身份建构过程,《明月几时有》在影像风格上采取了“视觉化的日常表述”这一新的尝试。
从视觉化表达来说,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和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大跨步的现代化转型,人们的生活被五彩争胜、流漫陆离的社会景观所充斥,各种奇观景象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人们已无暇慢慢欣赏“静默”的艺术形式,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震惊”中体验“审美浪潮”的冲击与离去。在这一时代语境中,电影也开始从“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转变。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在电影世界中,“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到波澜壮阔的自然美景,从对身体的展示到隐秘心理的探寻,甚至是虚拟出来的科幻空间,电影的视觉画面在带给人们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观看癖(窥淫癖)和自恋心理。近年来,随着视觉消费时代的到来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注重各种奇特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动作场面的奇观电影逐渐成为中国影坛的主流,甚至成为各大导演的自觉追求。
具体到主旋律电影,视觉化主要体现在战争场面的渲染、英雄人物的特写等方面。《明月几时有》也有类似的场景选择,但在表达方式上却有所不同。比如电影中有一场刘黑仔和方兰躲避追捕的战争戏,导演没有着重表现双方的正面激战,而是用子弹快速穿梭产生的流光溢彩来营造诗意的画面,使之在另外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层面满足观众对视觉冲击的审美期待。与之相似,电影在人物形象的视觉表达上也有独特的处理。近年来,借助明星的号召力和粉丝效应来提升观影率,逐渐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时代选择之一,《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南京!南京!》等影片在这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明星们的视觉吸引力不容小觑。但《明月几时有》中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剥离了明星容颜的视觉审美效果,转而寻求其内在的日常化表达。饰演方兰的周迅,在电影上映后引起了众多粉丝和观众的感慨:毕竟也是40多岁的人了!而就在2014年的电视剧《红高粱》中,饰演女主角九儿的周迅还被众口称赞为“不老的少女”。据《红高粱》的摄影灯光负责人说,周迅的脸比同龄人年轻10岁,剧组再用化妆、灯光等技术手段给她减下来10岁,最后就显得很年轻了。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明月几时有》也可以让周迅在大银幕上展示出少女般的精灵。许鞍华却舍弃了这一选择,让镜头下的周迅呈现出法令纹和萎缩的苹果肌,让一众粉丝直呼心碎。但从视觉效果来看,这样的周迅才能如实地表现出人物的家常甚至是疲倦。也就是说,《明月几时有》不是靠视觉的精美去让观众获得震惊感,而是采取了“陌生化”的视觉化表达,让观众在瞬间即逝的视听轰炸中停留下来,去反复品味和思考导演的用意,从而从习以为常的视觉刺激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新奇的感受和审美体验。
桑塔格在分析摄影时曾经说过:“观看意味着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事物中发现美的颖悟力。摄影家们被认为应不止于仅仅看到世界的本来面貌,包括已经被公认为奇观的东西,他们要通过新的视觉决心创造兴趣。”在奇观电影刚流行时,精美的妆容、奇特的场景、大场面的视觉轰炸确实可以让观众感到震撼。可是一旦观众对类似的视觉画面产生审美习惯和依赖性,它们也就失去了自己原初的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拍摄、剪辑和后期制作技术的提升,必须要依靠内在审美理念的不断更新,才能产生新的艺术效果。李安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之所以采用120帧、4K、3D技术,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更逼真的战争场面和让观众获得更真实的身临其境感,而是因为这种新技术更有利于展示人物的面部表情,从而更清晰、更完整、更真实地把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反映在脸部的每一个细节中。同样,许鞍华对演员容貌的如实再现,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其内心活动的变化和真实,所以我们在方兰最终决定放弃救母的那场戏中,清晰地看到了周迅的情绪转折和变化,那个越走越矮的瘦小身影,才能深深地打动观众。
当然,由碎片化的散文化叙事决定,《明月几时有》在展示平凡英雄的人物群像时,并不能详细地讲述每一个人物的主体建构过程,以至于有些人物的视觉化表现有类型化之嫌。比如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在电影中十分跳脱,大多数出场时刻都会自带喜剧效果。但是从他杀死敌人之后常说的那句“不久就会见面了”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地感知他是抱着有去无回、舍生取义的信念参加革命的,在这一内心写照的衬托下,他的游戏人生姿态更显示出一种侠义和洒脱。再比如霍建华饰演的李锦荣,进入宪兵队之后,因为要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所以初看起来的轻佻和暧昧,也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复杂而真实的体现。只是因为电影的叙事风格所限,导演并未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演绎。而这种艺术上的留白,也恰好给视觉化的日常表述提供了一定的艺术空间,给观众留下更多的审美余地。 德国社会学家克鲁格把电影比喻为一种类似于“巴别塔”的“建筑工地”,认为它“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成为彻底开放和民主的公共空间中的一种运作范型。由于这种空间需要想象的介入和争辩,它成为基础广大的、志愿结合的会集地。这种人际关系便是通向启蒙的最佳途径”。《明月几时有》在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碎片化散文叙事的审美追求和视觉化的日常表述等方面的探索,也是在观众的积极参与和审美想象的配合下,成为当下主旋律电影寻求时代突破的一个文化征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更好地尊重观众的时代审美心理,探知真正的“受众意识”并与之融合,是主旋律电影不断延续时代生命力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