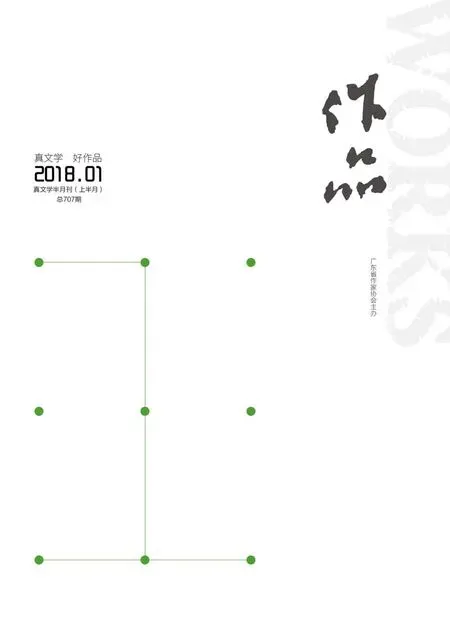事情在它发生以前
2018-11-14文/宋玥
文/宋 玥
“事情在它发生以前,其实早已呈现出它该有的样子,好比胎儿在母腹中便已生得有鼻有眼一般,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目光如B超,一眼便可见事情的真面目,当我们为之赞叹时,殊不知那人在此之前早是双目一黑,不再用眼看人看事,看自己。”
——摘自老鼠日记
一、念 城
我的名字叫二鼠——准确来说,我是一只老鼠,人们总爱给事物加个量词以形容其存在姿态,于是老鼠和猫是只,狗和鱼是条,而人和灵魂,则是个。
阿舍丽是这座城中最美丽的姑娘,据说她长发如瀑,面若满月,纤腰似柳,可这一切仅限于据说——念城中无人用眼看人看事看自己,日子久了,面中双目也自觉无趣,便日渐退化,终成一缝。某年某月某日,具体来说,应该是某个秋染麦田黄,云卷西风凉的傍晚,阿舍丽自远方来到念城,念城人为争睹她的美貌,便强睁双眼。奈何退化已成定局,阿舍丽是看不成了,念城人却养成了个习惯——从缝中窥人、窥事、窥自己,于是便有了夹缝生存一说。
念城生于山,育于河,经千年风露养,历万世人情炼,某年某月某日,具体来说,应该是某个春抚柳梢绿,雨浸夜梦长的夜里,念城生得一缕魂,自此城中树能言,草能语,花会笑,就连墙根底下的坏花狗也生得一张巧嘴,见人则好言好语讨吃喝,见鼠则鸡飞狗跳满城撵——在念城,狗拿耗子的情况并不罕见,可它们一次也没得逞过。城墙上,鸳鸯眼儿白猫最爱看这样的热闹,他曾高度总结道: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彼时彼刻,那白猫于我眼中俨然一智者。
二、阿舍丽
我曾经问过阿舍丽她自哪来,要到哪去——阿舍丽说她自远方来,要到远方去,我问她远方是什么,阿舍丽指了指我的胸口,说:“心里。”
念城中无人有幸一睹阿舍丽之美貌,而我则常伴她的桌前灯下——阿舍丽从不驱赶我,相反,她总会给我留半拉白面馒头,这点馒头已足够让我高兴上好半天了。阿舍丽说我是个好人,我纠正她的说法:我是老鼠,不是人。
那日雨来,我实在无法在城中觅食,便想起往阿舍丽家瞧瞧,于是以荷叶为舟,麦秆为篙,划船顺水而下。途中偶遇绿皮野蛙踞石台而鸣,青鳞鲤鱼结队而行。水路蜿蜒,一盏茶时间,阿舍丽家便已可见。
阿舍丽家门前围了好些人,很是热闹——在念城,但凡是过节都会很热闹,除欢度佳节的过节外,还有就是不欢而散的过节,反正于我而言,都是一场热闹。
我打开窗缝溜进屋里,阿舍丽朝我招手笑,我问她人们又过节了吗?阿舍丽笑笑,她们是在给我过节呢。
“幺鸡儿他媳妇儿说那天幺鸡儿在水边瞅了阿舍丽一眼后,回家就丢了魂。”——按城墙头白猫所言,那日过节的起因大致如此,我问白猫幺鸡儿那媳妇开眼了吗?她怎么看见幺鸡儿瞅阿舍丽的?白猫将短手往胸下揣了揣,一双鸳鸯眼在大太阳底下成了一条线,“按你说的,那幺鸡儿的媳妇儿就开眼了?”——听罢白猫语,我恍然:都是有眼无珠的!
三、邮 差
长街的名字就叫长街,好比我叫二鼠,他叫谢辽沙——谢辽沙是长街上的邮差,他说他曾在长街上看见过一个丑姑娘,她在与一只灰老鼠谈着什么。
谢辽沙和念城中的所有人不一样,他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双眼皮大眼睛。那日风起,谢辽沙头上的邮差帽被风拨弄到了地上,那一瞬间,我发现谢辽沙没有耳朵……
垂柳让长街很好地隐匿于念城深处,它仿佛是念城的一个秘密。长街和世间的所有秘密一样,终日顶着不可知的面具招摇于市,人们既想将之揭开,却又不想揭开。
谢辽沙的邮差包便是念城的另外一个秘密——那是一个泥土色的旧挎包,上头还打着几块补丁。每天凌晨,乌鸦会将整座城中的信件送到邮局,清晨六点,谢辽沙睡眼惺忪地将属于自己负责的街区的信件从分件员(狐狸)手里接过来,装包,出门,开始一天的工作。
那日我从阿舍丽家出来后,雨势见长,阿舍丽将自己的手绢撕成条,给我将白面馒头裹成个包裹,让我背在背后,好腾出双手来撑船。无奈河水湍急,我被冲到了长街的河道里。好容易翻身上岸,才发觉背上的白面馒头没了,凑水边看看,一尾青鳞鲤鱼正一脸得意地嚼着什么。细细看去,大嘴边上还留了点馒头渣子——城墙头上那白猫从不吃鱼,我问他别的猫都吃鱼,你怎么不吃?白猫回答:因为它们脸皮儿厚,吃起来费劲。
我穿过垂柳林,越过野红花,路边上打着伞的老鼹鼠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想起阿舍丽的话,便回答:远方。
谢辽沙的挎包此时已逐渐空瘪下来——我瞅准他弯腰系鞋带的时机,带着一身水,窜进了包内,随后稳当且无声地落入了几个瓶子中间。
念城中人写信不用纸笔,光凭一张嘴便能说破大天,于是机智的狐狸以青鳞鲤鱼的脸皮做成了装信用的瓶子,结果无人再能说破,狐狸每日捕鱼无数,勤奋制瓶,他说狐生艰辛,双爪要勤,幸得有人常向他买瓶,钱得赚,得赚。
我在谢辽沙的挎包里住了好几天,谢辽沙没有发现我,可我却发现了他没有耳朵……
四、家
我一直觉得谢辽沙面熟——过去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
阿舍丽说念城中千人一面,一面千人,见过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我说他没有耳朵,很新奇。阿舍丽笑笑,念城人普遍有眼无珠,缺耳短嘴的,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也对,这里是念城——正如阿舍丽所言,一切都那样稀奇,却又显得无比理直气壮。
谢辽沙家有个乌木神龛。
那神龛高大而壮实,经年不语。那日我打神龛底下过,忽而听到有东西在叫我,以为显神了,便回头看看——城墙头上的白猫说:念城中人信神信灵信妖信怪,唯不信人;邮局那黄眼狐狸则说念城中人多类精怪,所以它们对自己深信不疑——从某个程度上来说,狐狸较白猫更像个智者,他自诩这叫狐生阅历。
神龛脚下垫了个王八——准确来说那是一个王八壳,发声叫我的正是它。我问那王八壳:你怎么被踩脚下了?王八壳说你一鼠辈懂个啥!我说你怎么就剩壳了?王八壳怒了:无知鼠辈,满嘴胡言!
雨止于后半夜,河里水满致漫。
清晨时分,那青鳞鲤鱼被卷上了河岸,谢辽沙将之捡回家并掷于水缸中养起。神龛脚下那王八壳一眼便认出了青鳞鲤鱼,它朝鲤鱼吆喝:厚脸皮的,你还没死啊——鲤鱼打水里探出头来四处张望,好容易发现了王八壳的存在,俩人立刻热情攀谈起来。
青鳞鲤鱼说王八壳还是王八那会儿就说自己是河神的儿子,我问它后来呢?青鳞鲤鱼努努嘴:喏,就剩壳了。
念城人信神信鬼信精怪,王八说自己是河神的儿子,自会有人信,于是某个有眼无珠的念城人便把它供到了神龛里,终日受香火缭绕,好生仙气。奈何那王八自己不争气,受不住香火,磨蹭了十天半月,终滚落神台。可没走几步,便被人擒住了。
青鳞鲤鱼笃信,以王八壳的法力指定能让它重回河里——理由是王八壳说自己是河神的儿子,尽管王八一回神通也没显过,但也不妨碍鲤鱼对其信服不已。
谢辽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恐怕没人知道——他将油灯拧亮了半挡并挪了挪位置,于是身处黑暗角落中的我瞬间如遇佛光普照般亮了起来。谢辽沙定睛看看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吃饭了吗?
在念城中生活久了就会发现人们关心别人是否吃了饭其实是在关心它们自己的饭是否被吃了,更有甚者则在关心怎样连别人的那份口粮也吃了——尽管它们不饿,甚至已经在打饱嗝。
谢辽沙将半拉白面馒头推给我——这让我想起了阿舍丽,我想对他说点什么,可想起他没有耳朵,也就罢了。
那天夜里,我听到王八壳和青鳞鲤鱼在嘀咕什么,谢辽沙告诉我它们在想办法把你淹水缸里去——我问谢辽沙,原来你能听得见?谢辽沙笑笑,我能听见你们的声音。
五、智 者
城墙上那白猫仿佛是打水泥砖缝里生出来的一般,终年立于墙头,岿然不动,风雨不挪,倒三角脸上白毛密布,蓝黄双色鸳鸯眼中写满智慧。
我对阿舍丽说那白猫定是念城中的智者,毛长见识不短,一眼能辨人鼠狗,真厉害。
每回我打城墙根底下过,那秃尾花狗必会朝我嚷嚷。那狗生得獠牙长舌,却也关不住一嘴哈喇子,稍一张嘴准能洒我一头一脸。白猫见状便哧哧笑道:饱食终日就为蓄一腔唾沫,一无是处只懂四处喷鼠。
邮局里的黄眼狐狸说我鼠目寸光,他说城墙头那白猫撑死就一痔者,你问他你是不是智者,狐狸黄眼如炬,笑笑:鼠目寸光。
连日暴雨。
那白猫的盛粪之盆被风雨拐下了城墙头,啪一声,扣花狗头上了。那狗一通扑腾,盆没掉,反扣得更严实了,远近一看,俨然狗头军师般,不丑!确不丑!
雨毕,天晴。
猫寻盆不得,低头瞧瞧,见花狗一副趾高气扬样于在城根下游荡,头顶粪盆,形状威武,白猫将狗指给我看:如此智者,念城之首!
六、不见了
谢辽沙家位于念城东南面,依水而筑,青砖绿瓦竹栅栏。清晨时布谷鸟的叫声自林中来,将梦唤醒,我和往常一样,准备钻进邮差包中随谢辽沙开工去。此时谢辽沙一脸诧异地盯着我看,末了他伸手往我脑顶上捞了一把,我生怕他碰到我的耳朵,便赶紧弯腰躲闪,谢辽沙告诉我:你的耳朵不见了……
我在谢辽沙家住了三天,神龛下的王八壳和水缸里的青鳞鲤鱼无时无刻不在谈论怎样才能把我淹死在水缸里,偶尔听腻了,我便会对鲤鱼说你要小心点,听谢辽沙说今晚要把你杀了炖肉吃,你的厚脸皮则会被卖给邮局的狐狸,做成装信用的瓶子。
那天谢辽沙告诉我我的耳朵不见了——我发现念城较往日改变了许多:王八壳像故去了一样安息在神龛脚下;青鳞鲤鱼在水中游动,偶尔发出吸嗦吐泡声;城墙头的白猫朝我挥手,嘴里发出喵喵声;墙根下,秃尾花狗依旧是嘴里吐不出象牙,大嘴中却汪汪叫个没完——我问谢辽沙:念城是疯了吗?谢辽沙说是你失去了耳朵罢了,我问他要去哪里才能找回我的耳朵,谢辽沙朝西北面指了指道:翻过思山,淌过念水,便能到达城西北,那里有座磨坊,兴许你的耳朵也去了那里。
七、磨 坊
念城西北面,无山无水无人无烟,只有无边齐腰荒草以及无尽蓝天,无、无、无、无,“无是无,有也是无。”——磨坊主老驴望天吐了口烟圈,如是说。
按照谢辽沙所言,三天后,我真的在荒草丛中找到了磨坊——那日磨坊门虚掩,月光无法深入其中,在光影交界的最黑处坐了头驴子。驴子黄牙长脸,胸前吊个荷包,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我想要回我的耳朵。
驴子摆摆手,将我放进了磨坊,并让我称呼他老驴。
老驴的磨坊庞大无比,数不清的巨型石磨有序运转着,每架石磨都由四个两腿直立动物在拉动。我问老驴:这里都是人在拉磨吗?老驴笑笑,你怎么知道它们是人?——“念城中树能言,草能语,老鼠能打工,猫能守城头,皮相,早已不能说明问题了。”老驴用指缝间的烟斗朝其中一个拉磨的两腿直立动物指了指。
老驴让我睡在干草垛上,并嘱咐我入夜后千万不要乱跑。
是夜,我从干草垛上翻身下地——城墙头上那白猫曾多次告诉我,好奇会害死猫,我想我是老鼠,应该不怕——我想去磨坊中转转,顺便找回我的耳朵。
此刻磨坊中灯火通明,巨型石磨依旧在转动,拉磨的两腿动物沉默不语。我在石磨群中穿梭,偶尔抬头,发觉拉磨的两腿动物果然如老驴所言,都不是人——它们披着人皮,却没有人的面孔。此刻,一个头顶皇冠的白须长者笑着朝我走来——它在笑,它居然在笑!那拉磨动物的笑,着实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鼠辈,起来了!”一股浓重的烟味儿顺着鼻孔直冲脑门,“噗嗤”,我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老驴的长脸因此挂上了两行清鼻涕。我问老驴:那拉磨的呢?老驴用前蹄抹了把脸,反问:昨晚没睡好吧?
昼夜交替,明灭相生,日光终如擦窗布般将黑夜抹去,大把大把的阳光不知从何处洒进磨坊——窗前灰尘大方起舞,地上跳蚤浑身温热。草垛上,老鼠被赏赐了个影子,它向影子挥手问好,影子亦礼貌回应。石磨前,散落的纸片如被抽去了魂儿般瘫在地上,其中一张纸片,老鼠一眼便认出了是昨夜里的白顺老者,此刻它依旧面带微笑,头上皇冠铮亮——老鼠回头对老驴说:就是它,它昨晚在这儿拉磨来着!老驴深吸了一口那裹着暖阳、尘埃的空气,旋即咳声惊天动地。咳毕,看了一眼老鼠所说的白顺老者,道:有眼,无珠,盗听,图说,如今做了那拉磨扑克,也倒是消停了。
白日天光,所有拉磨的扑克变成了纸片,随意且随性地撒了一地,酣然睡去,只是石磨依旧有序转动,呼呼风声灌满整座磨坊——老驴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那不是风声,是现世安稳的锣鼓声。
我问老驴:那扑克王是怎么回事?老驴笑笑:不愿安生做人呗——人之所以生为人,恐怕便是人不愿安生做人的最大原因。老鼠安生为鼠,所以打洞,驴子安生为驴,所以拉磨,可人生来便无法安生,故一眼一言皆风浪,遂家家安神龛,户户供神明,求天告地,也只为求一“家宅平安”罢了。
月起夜临,磨坊中的扑克恢复了生机——两腿直立,四个一组,石磨有序转动。
磨坊外,荒草经秋风的抚弄,黄了头,经北风的打压,弯了腰。磨坊内,扑克昼伏夜出,驴子、老鼠日出作,日落息,一日一世,一世一日。
按照老驴的说法,磨坊中为他打工的扑克都是心甘情愿的——而在扑克成为扑克之前,它们也曾是人,一个有鼻有眼,口耳齐全的人。我问老驴后来呢?老驴将烟斗在自己的蹄下磕了磕,道:听了不该听的,腻了,看了不该看的,烦了,说了不该说的,糟了,于是就把眼耳口鼻送到了磨坊来,自己便成了扑克,从此不看不听不说了。我问老驴那我的耳朵呢?老驴笑笑,该在哪的就在哪,我赶紧摸了摸头顶——我的耳朵回来了!接着我又问:那谢辽沙的耳朵呢?老驴听罢这个问题,笑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该在哪的就在哪。
八、信瓶子
“山川河流,草木花石,禽鸟鱼虫,皆与人同魂,这个道理打我出生前便已晓得——是的,你没有看错,我能记得出生前的事情。在出生前,我便有个心愿,那就是找到你,自此不再走散。”——给谢辽沙的信。
念城依山而起,临水而生,那山是思山,那水是念水——山有魂,故草木花石能言,水有灵,则禽鸟鱼虫能语,某日魂、灵碰撞,念城自此生生不息。
谢辽沙是怎么来到念城的,他自己也记不得了——蠢,是他的一大缺点,也可以说是一大优点。某日在长街上,那个丑姑娘和一只灰老鼠在交谈,眼下情景让他感觉自己确已蠢出了新高度——一人一鼠,能谈什么,怎么谈,他在街对面看了好半天,末了他只能断定自己已疯——他居然开始关心起那场谈话的结果了。
就在那天,不祥之事接二连三——邮局的信库被凿了个洞,有人从这个洞钻了进去,并将架子上整齐码放的信瓶子给逐一打开了。这个人似乎在找什么。事后,邮局里的黄眼狐狸仔细检查了信库门上的洞,他认为能打出这样的洞的,只有老鼠,也只有老鼠,才能从那一掌见宽的小洞溜进信库——而那只老鼠要找什么,则不得而知。
很不巧,谢辽沙那天头一遭到邮局上班,当他走近信库等候取信瓶子时,铺天盖地的人声从信库门后冲向他:抱怨、哭诉、谩骂、调情等天地间该有的、不该有的一切话语,瞬间将他淹没。当黄眼狐狸赶到现场时,谢辽沙已昏厥过去,与此同时,他脑袋两旁的耳朵亦不翼而飞了……
九、卦
许多年以后,阿舍丽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海滩边上的长脸驴子——那驴子自诩擅长龟卜,于是他给阿舍丽算了一卦。当那彰显着命运魔力的银币从乌龟壳里掉落的瞬间,阿舍丽的心亦随之沉了一下:长途跋涉,翻山过水,却总不得零星消息,人心如斗兽场,终日上演着失望与希望的角色好戏,此刻也只好暂将希望寄于那乌龟壳了。
银币无声跌入沙滩,一枚底朝上,另一枚却竖了起来,驴子俯身凑近银币,细细看了好一阵子,半天才抬起头来问:姑娘,你要算点啥?——阿舍丽不禁失笑,反问他:你那乌龟壳果真灵验?驴子摆出一脸的高深莫测:我信我的王八壳,因为它是河神的儿子。
河神的儿子?阿舍丽笑笑,我几时生儿育女了,我自己居然不知道。
待阿舍丽走远后,驴子将银币收起,口中自语:只要你没忘记,他就一直在。
许多年以后,驴子对一只灰老鼠说:也不知那丑姑娘听没听到那一卦,老鼠问驴子后来呢?驴子笑笑:后来我把那王八壳送给了念城中最蠢的家伙,于是换来了这座磨坊。
那日老驴将我送出磨坊,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遍地的扑克,便随口问:你这磨坊叫什么名字?老驴再次摆出一脸的高深莫测,回答:人世。我想了想:人是?保不齐还有人非?又问:你的石磨叫什么?老驴吐了口烟,回答:命运。
临走前,我请老驴给谢辽沙算一卦。老驴笑笑:王八壳都归他了,还怎么算?
“人蠢至极其实也是一种聪明,这样的聪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大智——那个蠢人说家里的神龛瘸了腿,想找个有灵性的物件将之垫起,遂以磨坊与我换走了那河神的儿子——王八壳,从此供起了他心里的神明——而事实证明,这个蠢人果真大智,他将世间最烦人的物件甩给了我。至于那一卦,其实早已算过:只要你相信,她就一直在。”老驴面朝荒草地自语道。此刻星斗漫天,夜深沉,荒草地已开始抽新芽了。
十、来
那年暴风袭城,致海水倒灌,随波逐流,于是我来到了念城。
沙滩边上的那头驴子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只要我相信,那人就一直在。驴子以为我没听见,可实际上,我听见了,一字不漏,这一卦让希望在斗兽场中暂时占据了上风。
很庆幸,念城中人有眼无珠,因此我的容貌也不至于惊吓到谁——那坏驴子定是在背后说我是丑姑娘,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女人的第六感有时比神明更灵光。
我希望他就在念城,也许正如驴子所言,他一直在。
闲来无事,我也学着念城人的样子,开始邮信——邮局里的狐狸成天在河边捉青鳞鲤鱼,他说鲤鱼脸皮厚实,做成装信的瓶子,谁也说不破。于是我向他买下了大量的信瓶子,我想邮信,希望他能收到。
“山川河流,草木花石,禽鸟鱼虫,皆与人同魂,这个道理打我出生前便已晓得——是的,你没有看错,我能记得出生前的事情。在出生前,我便有个心愿,那就是找到你,自此不再走散。”那日我在书桌前念信,安东尼又来找我了——安东尼是个好人,可不知为什么,他总认为自己是只老鼠。
安东尼问我回信收到了吗?我摇头说没有,安东尼说他替我去找回信,我问他要上哪里去找?安东尼回答:邮局,信库。
许多天以后,安东尼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告诉我,我要找到的人,兴许他已经找到了,我问他:他现在还好吗?安东尼说他很好,只是没有了耳朵。
念城西北,磨坊里,那海滩边上的长脸驴子已不知何时染上了抽烟的习惯,我告诉他抽烟不好,驴子笑笑,你是神明,还有什么是不好的?我直接对驴子说把他的耳朵还给他,驴子说可以,那就以你的嘴巴来交换——人生命运,万物平等,神明亦然。安东尼提醒我,没有了嘴巴就不能再给他念信了,我没有回答,只是投眼望向那有序转动的石磨……
十一、回
布谷鸟的叫声如期而至,又是一个工作日。
谢辽沙从床上爬起来,此时他感觉耳旁分外清静——王八壳和青鳞鲤鱼不再讨论坏计划,它俩安分得像死了一样。在途经穿衣镜时,谢辽沙停下了脚步,他感觉自己和平日有些不一样,认真端详,他才发觉自己的耳朵已不知何时回到了脑袋两侧……
安东尼伸手折了一片竹叶,那叶上盛了几点晨露——也许是那日天光晦涩,林等风,山候雨,谢辽沙感觉安东尼的一头黑发竟有些发灰,那灰似曾相识,好生面熟。
磨坊。
老驴接过安东尼交给他的王八壳,笑笑:尘归尘土归土,上了神台,扛过神龛又如何,生来便是一俗物,还是老实回来好。
谢辽沙对老驴道了声辛苦,便将磨坊钥匙揣进了包里——土色补丁邮差包。
临别前,谢辽沙对我说:念城万物,皮相应运应心而走,如你心中常自愧如鼠,则果真是鼠了,懂吗?
十二、不 知
念城依思山起,环念水存,山水风物养心养道养人,如神明。
水绕山行,却不知山,水养孤鹤,却不知水——此时彼刻,灰鼠打你心间一跃而过,你可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