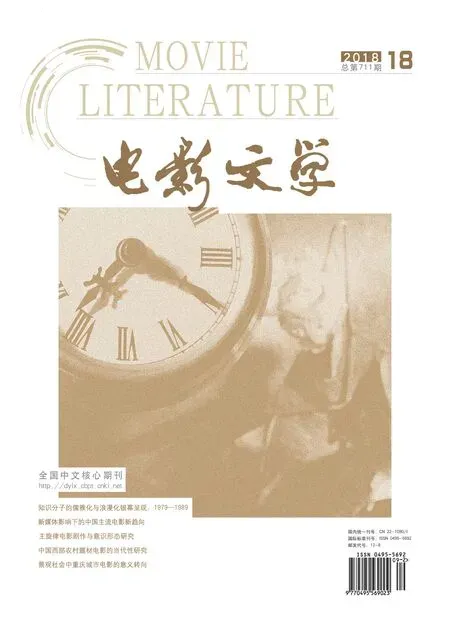纪录片《二十二》中的零度写作
2018-11-14王健
王 健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罗兰·巴特在其著作《文字的零度》中借助了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范式,提倡将语言从思想、内涵的附属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使意义和情感直接由语言结构生成,而不是由作家的主观感情倾向所支配。在写作中,作者要采用中性的辞藻、回避式的情感色彩、不夹杂任何态度的文字表达方式,使得结构形式焕发自身的力量,从而引发读者理性、冷静的思考。他认为,这一种完全的“不在”,“是一种毫不动心的纯洁的写作”,以消除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给写作带来向度。在纪录片《二十二》中,导演并没有将22位老人作为宣扬国族历史复仇的政治工具,而是运用“零度写作”去避免人为的介入,在镜头语言、影像风格上尽量保持冷静和沉稳,无论是固定的景物空镜头还是无配乐所烘托出的沉静、寂寥的气氛,都使得导演的主观感情降至冰点,语言所承载的零度“无意义”也正是影片意义的所在:国族身份认同下的民族主义立场、先入为主的“复仇”意义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历史、女性记忆的重新审视。
一、零度“乌托邦”:影像的客观性
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主张在创作中回避感情、抛离主观意图来进行白描式的创作,这是一种将主体性隐藏起来的,超然于个人的艺术观点,在这个乌托邦式的文本世界里,写作的痕迹被泯灭,文本涵义的呈现也是透明、多义的。《二十二》作为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不同于之前同题材的影片,它将官方口径的意识形态意味降至了最低点,无论是对日常生活影像的捕捉、选取还是对提问的着意控制,都使得影片保持了一种客观和中立,导演选取了大量看似和主题无关的镜头素材,包括老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以及片尾有些冗长的葬礼,用未经修饰的素材传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思考,这也正是零度写作所构筑的乌托邦式的影像世界——它不带任何民族立场,不是任何饱含政治意味的意识形态传声筒。
“零度写作”本身所传递出的客观、中立的理念成为影片重要的风格化呈现特征,它试图建构出一个避免人为介入的影像世界,在这里,摄影机的“特权”被限制,转而变成一名“静观者”,自然与质朴、真实与客观被放置在了第一位。在影像处理上,导演采用了极简的纪实手法,这主要体现在影片的镜头语言和声画处理方面。首先,贯穿于全片的长镜头不仅创造了影片的整体风格,还体现出了一种寓情于景的美学特征。长镜头确保了时空完整性的同时也展现了生活的原貌,作为具有时空绵延指征的摄影手法,它赋予了影像一种感觉上的真实。例如,对于老人生活境遇的呈现,导演没有使用旁白,而是只使用了简练的长镜头来贯彻“零度”的理念,真正实现了一种“不置一词”的客观呈现。片中毛银梅的养女在讲述老人冬天的生活状态时,一个固定长镜头将她们两个人分别置于画框的前景和后景,这种镜头下真实的话语与行动就远比通过主观性旁白来介绍老人的生活状态要更具情感表现力。导演刻意将镜头语言所带去的激进的意识形态锋芒隐藏,用“静观”的长镜头最大限度地去捕捉主体最真实的反应。除此之外,在表现老人生活细节上,导演尽可能使用中景或全景镜头来保持摄影机与老人的距离,这种距离感产生的“陌生化”效果使得观众始终游离于事件之外,从而不断产生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在声音的处理方面,影片用人声(老人的口述)、自然声取代了具有情感化和戏剧化的旁白和背景音乐,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影像的视听呈现更加真实自然,避免了旁白和音乐对影像意义的直接干预,使之更接近于“零度”的表达。
综上,通过对影像的“纪实性”的处理,导演构建了一个日常化的视听情境,从而使观众“捕捉到那种被记载而不加一语解释的重大事件所引发的效应与效果”。
二、零度叙事:对叙事性的消解
在纪录片创作中一些导演会借鉴叙事电影的手法,通过人为地铺排情节、设计冲突来达成某种预设的“虚构真实”,这种“虚构真实”是“非零度”的、强制性的。而零度写作则不像叙事电影一样对现实世界进行人为的干涉,而是使观众亲自去探索影像世界中的不确定联系,叙事层面的因果关系也是松散的。
《二十二》中导演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影片没有一条完整的主线,而是在零散、琐碎的伤痕记忆中进行克制的陈述,使“日常化”取代了“戏剧化”所带来的“拉仇恨”功能。亦如在范俭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导演没有刻意去放大余秀华与丈夫的离婚事件,而是使得冲突“日常化”,在朴实、沉稳的运镜中显现出生活的平凡,余秀华和丈夫都是普通人,他们也都会向生活妥协。《二十二》的重点不是叙事,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有着时间进程的叙事序列,它的行动指向是处于一种无目的的状态,它并不是想通过几位老人对过往回忆的陈述去制造矛盾冲突,以民间的力量使得日本政府道歉。要求“道歉”不是目的,也不是预设的结果,只是在碎片化、零散的访谈中,将老人们所处的环境、氛围展现出来,从而引发我们身边人的关注,因为比无能为力更可怕的是无人问津,被边缘,被隐形,被消音。
在零度叙事中“感知—运动”模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时间—影像”模式。即在自然的时间中生成表述,感受时间的绵延,将环境、氛围、情绪代替行动、运动。影片选取了老人最日常化的生活素材,用“情感影像”替代了“行动影像”,使得观众融入老人的生命体验中。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本体论中提出,世界的本质在于以生命冲动为基础的绵延。在他的观点里,我们可以从时间里感受到生命绵延,时间被分割成影像,达成一种情绪的感染力,这便是零度写作,将行动的影像转化为使得观众去感受的情绪影像。例如影片开头的追悼会,观众原本会认为,“追悼会”这一沉重的话题出现在开篇,会是一个酝酿矛盾冲突的集结点,但是,影片并没有如观众所想会将类似声讨日本政府、民间请愿的影像表现其中,从而去强化意识形态煽动性或者从艺术形式层面,使得影片跌宕起伏,增加观赏性,导演只是一笔带过,使得原本会继续展开的冲突戛然而止,“追悼会”只是作为一个“抢救式纪录”的引子,旨在强调一种老人会相继离世,纪录迫在眉睫,而不是承载“声讨”“谴责”的功能。直到在影片的结尾,首尾呼应,以“追悼会”开始,最后以“葬礼”收场,配合清冷、疏离的中立镜头,将零度叙事真正极简主义化,使复杂的外在行动的叙事性吸引力内化为单纯的个体内心的生命体验,大大强化了影片的文化反思力度。
三、身份书写:从民族主体到女性个体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在于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使其臣服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把个体改造成主体的这一功能,“询唤”作为一个动词,它的功能便是将意识形态作用于个体使之成为主体,而“民族主体性”便是民族主义和国族身份下的意识形态的“询唤”,它将民族个体改造成民族主体,将民族认同、国家意识渗透进去。《二十二》区别于具有政治“询唤”功能的主旋律电影,它更多的是将重心放在对女性个体的书写上,“零度写作”的手法将题材中原本的民族主义立场搁置,以客观的叙述来引导观众去关注老人的个体经验。
“慰安妇”这一特殊的群体,她们遭受着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他们不仅在殖民主义下面临着民族身份的缺失,同时,在父权社会下的女性话语权也被剥夺。在战后,对于她们来说本来应该是解放,是重生,但是面对的可能是群体的忽视或者是偏见,即使得到了重视,那也被物化成为父权社会下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斗争的工具,她们的女性话语是不在场的,是被男性话语占领的,男性是处于拯救女性的地位,在许多反映慰安妇的纪录片中,政府、社会团体的男性角色常常是强硬的、正义的化身,他们积极为妇女请愿,与日本政府进行博弈。弗洛伊德认为,一旦男性意识到了自我的生命力,就立刻进入了创作作品、拯救女性的崇高幻想之中。女性被看成了男性的崇拜者,父权和夫权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二十二》中男性角色几乎是不在场的,他们只是一个起引导作用的视点,例如,片中采访韦绍兰的儿子罗善学,作为“日本人”的身份,他的失语的状态与受害女性是处于同等的地位,男性权威是被“阉割”的。
但是在现实中她们是被男性或者是男性意识歪曲和误解的,韦绍兰在被日军掳走三个月后逃回家,丈夫只是说了句,你还晓得回来啊,女性的尊严不仅被殖民者践踏,而且被身边的男权意识践踏。《二十二》不是男权政治下的民族神话,它无意采用任何艺术形式将观众“询唤”为灌输意识形态的主体。在具有政治导向、意图指向的电影中,导演会精心策划影像,例如使用蒙太奇制造的“冲突”和“碰撞”,但是《二十二》里零配乐、朴实的镜头语言不具备任何煽动性,它让观众将注意力关注到女性个体上。而对于这个群体,她们之所以被曲解的深层原因,是她们的性别所承载的功能,即男权语境下生育、照顾后代的任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人是具有双重性别的,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则是建构出来的。女性的性别功能是被男权社会语境下的文化阐释出来的,但是在殖民的压迫下,女性的这一功能被剥夺,受害女性这一被“阉割”了的群体,在男权社会往往会被男性歧视和不认同。
零度书写消解了国家记忆下所燃起的复仇火花,将宏大叙事下的国家话语置换成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这一特殊群体不再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不再是爱国主义的“代理”,而是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主体,她们的首要的身份就是普通妇女。林爱兰老人会自豪地拿出自己的抗日勋章,毛银梅老人会唱起朝鲜民歌《阿里郎》,李爱连老人会给野猫喂食……她们的身份不是“慰安妇”,是抗日英雄,是背井离乡的朝鲜妇女,是“猫奴”。
与其说像《战狼》《红海行动》之类的主旋律电影是书写男性神话的爱国主义强心剂,是对英雄的崇拜,那么《二十二》中的女性同样也是英雄,因为她们承受着普通人承受不了的苦难,更是弥足伟大的。
四、结 语
在影片里导演即便是运用再克制的手法,观众依然可以在冷静的镜头语言中感受到历史的阵痛,因为镜头慢下来给观众带来的思考,不可避免地会融入民族情绪。片中老人对伤痕记忆避而不谈,但是生活的细节已经“出卖”了她们,就像毛银梅老人口中会不断说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的日语,在镜头中的呈现甚至有些滑稽的感觉。但是细思极恐,老人在过去说这段日语的时候,她正经历着多大的磨难。克制不代表抑制,冷静不代表冷漠,在自由的镜头语言下,导演选取的素材仍然是加工过的,是活生生的有感情色彩的一组组镜头。零度不是虚无,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仍然要将之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下,因为历史是由个体的书写组成,个人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影片虽然呼唤对个体的关注,但是它的历史意义绝不是空白的,历史的思辨性仍然是存在的。“零度写作”背后所传达的价值意义正是在于通过对22位幸存老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来反思战争、反思历史,从而启示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生活,同时也启示我们在这个和平安定的时代,依然要关注边缘人群,对生命要时常保持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