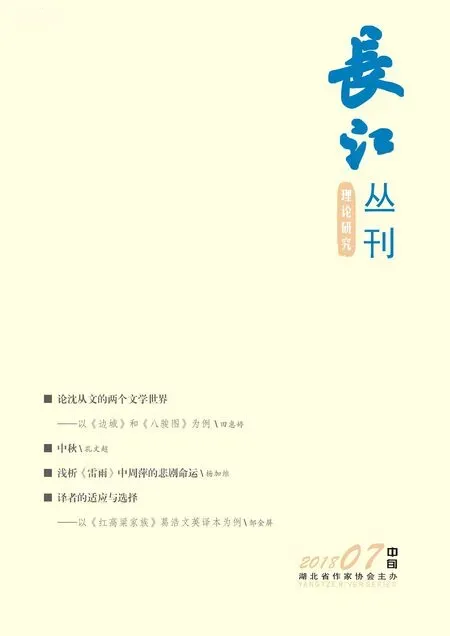乡野的呼喊
——剑男诗歌浅议
2018-11-14■/
■ /
湖北大学文学院
自《诗经》以来我国悠久的诗歌传统中,专注于描写人在大自然中的日常生活,如田园里的劳动场面,恋爱及求爱,亦或是宴会场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和煦的氛围。基于悠久的农业文明,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亲密和谐。崇尚自然,向往自然之美,表现田园情趣成为诗人的艺术追求。
这一文学传统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之时断裂。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强烈震撼,迫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开始全面审视和反省自己的现实处境。“苦难是中国诗歌革命的真正出发点” ,与此同时,诗歌也走出了文人吟弄风月的范畴,走向如何接近并改变现实的、底层的、个人之外的苦难社会的思考。
历经百年中国终于摆脱了积弱和贫穷之后,人们猛然发现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是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牺牲、文化的失落为代价的,人与自然的对峙更是导致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千疮百孔。二十世纪末,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日益深化的语境中,掀起了一股生态写作的浪潮。诗人纷纷思索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以己之笔写下对生态破坏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憧憬。
湖北诗人剑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以家乡幕阜山为文学地域,对自然的书写贯穿其创作始终。面对生态恶化的现实背景及工业文明对乡土世界的冲击,他的诗歌有着从乡土诗向生态诗转向的轨迹。
自然的还魅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世界屡屡遭受着工业文明的入侵,城市凭借其强势姿态完成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谋杀及丰富感知能力的挤压消解。现代文明造成了人类感知能力的破坏和精神生活的无处安顿。诗人剑男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将写作视点转向人类的“内宇宙”,从感知生态的角度完成对乡野的复魅。
“感觉生态文学”流派,是现代美国环境主义思潮中异常活跃的一个领域,这一西方话语目前在国内较少被提及。1987年,桑德斯曾在其随笔《为自然说一句话》中指出“感觉生态”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在我们生活中大多数时候,自然像被镶上了窗框,就像录像的屏幕、照片的白边一样是以镶着边框的状态显现的。另一方面,自然的有机的网眼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内部,而我们却几乎感觉不到”。可以说,“感觉生态文学”是对当代文学生态写作中轻视乃至忽视人类与自然之间感觉体验的倾向的扭转,它关注各种生命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有着体验性和情绪性的意味。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有机的网眼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内部”,唤醒人类的感知体验,是感觉生态写作的意义所在。
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人剑男,其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成长轨迹以及流转于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身份,使他可以敏锐地感受到乡野对人的感觉体验的唤醒和都市对人类感知能力的破坏。这一鲜明的反差体验成为他感知自然魅力的契机。
在其生命出生之地——幕阜山中,诗人的感知力被原初的自然所唤醒。他在《疼》一诗中写道,“很多个春天过去了/但一到春天我的胸口就生疼/我希望我是喜欢春天的/像一粒种子迎接秘密的雨水/但我一见到风就想起凋零的花瓣/一忆起往事就想到到处沾惹的柳絮”。作者笔下,花开花谢调动着人类的情绪,人会因为凋落的花瓣而产生疼痛的感觉。大自然唤醒了人类身体的敏锐感知,在乡野之中,人类会本能地将自我与动植物的生长、气候的改变、季节的变迁联系起来,并以它们为参照,关照自我的生命状况。乡野中和谐美好的生态世界及大自然的原始自由野性,是涵养人类审美感知体验的沃土。
乡野唤醒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是剑男诗歌的重要特征。《远行或者从头开始》中呈现了母亲和孩子劳动的场面,“到了秋天/收获从内心的欢愉开始/母亲在风中挥起了镰刀/田埂上奔跑着挟着破旧识字课本的孩子/从一种远行到另一种远行/艰辛的劳动和盲目的奔跑要采撷生活中的甜蜜”;《春天的蜜蜂》里则刻画了蜜蜂采花的画面,“可能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硕大的花朵/它们嗡嗡地叫/像找到心中隐秘的欢乐”。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命,劳动是生命体与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方式,其间获取的是最直接的体验和最本质的快乐。生命体通过劳动享受土地的赠与,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是与自然血脉相连的感情体验。
而在城市,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体验在现代化技术的入侵下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收割机、刈草机等现代机械代替“镰刀”,将人类从土地驱逐;游戏等各类间接性体验的娱乐以及电视等置换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凌驾于真实的自然之上,切断了人和自然的血脉相连。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其昼夜被电灯操纵、温度被空调调控,以致人对自然的直接体验被人为的虚假及舒适破坏。在城市中,人们的感觉被统一化、整齐化,来自自然和土地的真实感受被扼杀。现代意义的都市是一个特意制造非自然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场所,科技和理性切断了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和体验,完成了对大自然的彻底祛魅。
技术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城市的高楼大厦更是进一步将人和自然完全隔绝。“慵懒的城市里/人们开始丧失很多概念/森林、河流、大山/他反复诘问/什么是青砖绿瓦/什么是翱翔和嚎嗥……博物馆太大/或者是太狭小/他在玻璃切割的阳光中反复踱步/消失得太快/这曾经是什么地方/他想/这可能是一座池塘/或者一片草地”(《在博物馆》)。建筑的作用是隔离性的,人类的建筑,哪怕仅从一堵墙开始,就拉开了人与生态脱离的历程,而城市规划中形成的单调统一的建筑风格更是日益窒息着人类对自然丰富的感知体验。
在城市,把空地铺设成公路,森林改建成公园,河流围上栅栏,这就意味着人类没有机会接触到原初的自然。不接触造成了感知体验的缺乏,接触性和体验性感觉的丧失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自然的多样性从人类的视野中慢慢消失,始终处在单一性的景观中,人就会陷入经验灭绝之危险境遇。自然和人类的联系不再密切,自然的变化于人类而言也不再重要。人对自然“集团性的无知就变成集团性的不关心” ,冷漠、自私、封闭、虚无等人性精神异化问题随之而来。人的感受萎缩、雷同,生命感窄化,敏锐的情感体验不复存在,城市变成人类失去人性和感知体验、价值判断的荒野。正如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言,“未来的史学家会发现,20世纪的一个奇特之处是人类知识广博而价值判断却很狭隘,人类对于世界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知道得这么多而又评价得这么少,无怪乎我们会面临一场生态危机” 。
人对自然的敏锐感知是形成深刻审美体验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这种感知能力,才能从停留在表面的对自然景观的观赏进入到从内在精神的层面与自然进行深度交融渗透的境界。剑男从感知体验的角度对自然复魅,力图挣脱以自然是否能为我所用、其形式是否愉悦了人类身心为标准来判断自然价值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将关注点放在自然的本身存在及人与自然的深层交互,达成一种“自然全美”的生态感知体验,这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特殊生命的治愈体验
剑男非常关注某些特殊群体在乡野中获得的生命体验,其诗歌中常常出现盲人、肢体残缺者、正在经历身体疼痛乃至承受精神痛楚的人物形象。当此类“有缺陷”的生命体放置于自然之中时,其身上存在的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在乡野的接纳和包容中得到缓解。
《两只鞋子》中写道,“几只鹭鸶练习单立/一个人正在湖中挖藕/鹭鸶的腿直而修长/挖藕的人双腿埋在淤泥中/当他在浅浅的湖水中移动/我看见他用手从藕筐旁边/摸出一只拐,像一个/熟练的水手驾驶一艘快要/搁浅的木船,轻轻一点/就把自己缓缓的送到前面的淤泥中”。通过单腿鹭鸶和缺了一条腿的挖藕男子两个画面的交替呈现、切换,在自然对人的无限包容中表现出残缺之体在大自然中获得的和谐感。
这种和谐感在《一把镰刀》中体现为万物对人的顺应及人与物情感的渗透,“仍然被挂在墙上/仍然倾向一边/仍然保留一个左撇子的手势/从老屋向外望,是它曾经收割过的/如今长满荒草的田野和河滩……一把镰刀一定不会只是工具/一把镰刀也会日久生情/你看它的主人,挂在墙的对面/他们的眼神似乎从没有离开过彼此”。在作者笔下,一把镰刀仿佛被赋予了生命,顺应着人类的生活习性,并在长久的相处中两者达成生命的交融。
剑男诗歌中不乏有感官缺陷的生命对自然之美的憧憬。“春天的下午这般迷人/一个忧郁的少女/在干涸的眼睑盛下了清纯的泪水/但一只夜莺与她不同/它胸中埋着激情/它从一个枝桠到一片草地/它的跳跃暴露了少女的言辞/它运送时光到春天/一个充溢着血液的下午/风铃和琴音处处的盲人学校/他们不看/但听见”,亦或是“哑巴爱人世爱得多么苦……那么多叽叽喳喳的鸟儿/却没有一只喜鹊替他喊出心中的欢喜”。与感官缺陷相补偿,这部分人的感知体验极为敏锐,这恰好为其内在生命与自然的接通打开了通道。他们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看自然,而是灵与肉都深深地参与并嵌入到自然之中,与自然发生真实的生命交融。他们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的生命,在其他的生命中感悟自己的生命,在与自然万物深层的交互中满怀对自然美的触动、渴望。
自然具有一种无疆的美感,即便生命体看不见、道不出也不能阻止这种美感的传达。残缺的感官不仅无碍生命对美感的接收,反而更增添了其对自然之美向往的热情。也只有寄身于大自然之中,才能使有缺陷的身体获得和谐感。
相比身体的残缺,更加困扰现代人的是灵魂的无处安放。精神苦难在剑男的诗歌中突出表现为“孤独”,这是典型的现代都市病,也是其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无论是不悔之年“一个人的灵魂在风中疾驰”,而立之时独自“乘明月醉卧他乡”,还是在不惑的年纪里“敲遍一条长街,问张怀民的下落”。纵使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甚相同的内涵,但孤独的情绪是剑男诗歌中不曾改变的主题。
“一个独身女子穿过寂寞的街道,在一座/石雕旁吐出了隔夜的思想、食物和胃”,城市的孤独者散发着消沉、腐朽和死亡气息,给人一种无可救赎的窒息感。
将处所置换到乡野,剑男在《夜宿大别山》中写道,“一些事物在黑暗中沉睡过去/一些事物像我一样在夜半醒着/人生所寄又能怎样/千里大别山也不过有着人世一样的孤独”。自然使人豁达、通透,能让人拥抱赤子之心、接触到生命本质。在乡野中人能与自然交融,更能在与自然的交融中明白孤独是世间万物的普遍属性和本质特征,从而不再局限于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孤独。“生命不过是寄居,秋色寄居枝头/鸟雀寄居于浮云,人寄居于大地/万物寄居于彼此/如风吹过风”,只有在与自然的对话中,人才能变得清醒而自知。这个时候,身体和精神的每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会打开,去敏锐地感知世界、体悟生命,与自然产生一种内在精神的契合。对于无处安放灵魂的生命主体,乡野带来的新鲜经验,可以实现精神生活的短暂栖息和回归,在人与土地内在生命的契合中完成对精神苦难的疗救。
自然意象感知盛宴
剑男诗歌中的意象纷繁丰富,注重从视觉上建构美感,用大笔墨铺陈的绘画手法将众多意象一一呈现,使之具有直觉感和可见性。例如,《共和国的菜园》中,“省略掉对泥土的吮吸和对阳光的抢夺/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没有/约束,也不需要节制和道德感/就像丝瓜藤昨夜还在和空心菜纠缠/早上又爬到墙头和一群蜜蜂打情骂俏/藿香放肆地喷洒香水,番茄偷偷/在叶簇下珠胎暗结,我喜欢它们的/散漫、自由、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每一株都能活出自己的样子”。剑男从日常生活中采撷意象,刻画出一幅幅生态意象图。加上一系列动词的修饰,赋予意象以角色感和生命力,从而将单纯的视觉感官引申到多感官的交融互通,形成立体的美感效果。
剑男对自然之真充满执着,他谛听自然的声音,紧贴自然的生命节律,原汁原味地呈现自然的本真状态,诗歌创作常常摈弃自然物被赋予的文化含义。例如《昙花的方式》一诗,“这生命中的练习曲/昙花要开放在时间的峰尖上/一现就暗合了一生的宿命/它缓慢的恢复是那样的漫长/不能遏止/不能在春天中看到一人最后的歌唱/仅仅是一种方式/毁灭了自身的礼仪/死亡成就了一生不能宽恕的完美”。
由昙花开合到人的一生,剑男力图通过对意象的去象征化来建构人与自然物的联想关系,赋予意象以鲜活感。昙花是沉默着的生命体,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都是沉默无声的,因此长久以来它们都被形形色色的语言和各种符号涂抹覆盖,承受着文化对鲜活生命的视而不见。“人类走向文明的过程,就是自然逐渐丧失话语权利的过程”,而在这里,诗人洗涤去了历史和文化长久以来赋予给“昙花”这一物象的种种象征旨意,拨开人类主观意志对其作为鲜活生命体的遮蔽覆盖,让昙花回归到生命本身,作为生命体为自己的命运发声、诉说,从而实现生命的自我指认,重新绽放生命的质感和光泽。对生命祛蔽显真,让自然中的鲜活生命突破层层遮盖,最终回到其生存现场和生命本身之后,形而下的实体自然物象才能因自身的生命律动与人类的心灵实现共通,未经干扰和践踏的乡野为实现这种异质同构的生命契合提供了可能。
将去象征的意象重新变为隐喻,是剑男给予自然物生命的又一种方式。蜜蜂与“单身汉”,丹顶鹤与“少女、缪斯”,乡亲们、溜冰的女孩和“一列列蚂蚁”,“一朵跳动的火焰或一只蝴蝶”……动植物自然意象的拟人化和人的拟物化使剑男诗歌中的乡野世界极富感知力和生命力。尤其是将植物意象形容词化,如用“山茶的娇羞”形容邻村的少女,“杨花的轻佻和孟浪”形容妖娆的女郎,更是让其笔下的意象具有了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
句式的选择使剑男对自然意象的书写带有鲜明的主观化、情绪化特征。诗中频频发出“我藐视集体出现的东西/包括暴雨前归巢的鸟/不夹带一丝杂色的紫云英/成片的二月兰,十里飘香的桃林/我藐视把春天集中在一处/把兰草从山中挖出来/把映山红移到路人可见的山坡”、“没有必要动土……没有必要焚烧荒草/没有必要剪枝/没有必要移栽幼苗”这样的呐喊。可以看出,剑男将乡野中的自然万物视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意象和鲜活的生命体,对它们的情感显现出惺惺相惜的呵护和尊重。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自然本来的样子已不能再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审美消费主义下,自然是“等待被考察的面孔,而不是栖居的家园”。形式主义审美观念的诱导下,人类忽视了自然拥有按照自身生态规律生存的权利,不顾自然的原始生命存在、不再认为自己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平等的生命体,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价值需求随意修剪和改造自然,使其服膺于人类的视觉暴政。剑男对此持坚定的拒绝和批判,他对原生态自然美和自然本真天性发出热情的呼唤。大串排比句的使用将诗人内心的情绪烘托得淋漓尽致,让其诗歌书写言简意赅、表义明确、表情用力。
诗人笔下的乡野不再是现代化和工业文明冲击下真实存在的乡村,而是类似于古代山水田园诗派笔下的传统意义上的、延续着和大地血脉之源的淳厚而质朴的乡土世界。他对未经人为干涉的荒野之地、对乡野中的自为生命体及原生态的自在生活姿态、甚至对乡村封闭、贫穷却又无拘的生活方式充满了眷恋,带着审美回望和推崇满怀渴望地加以美化,使之成为被距离化、审美化、理想化的显现出超越姿态和浪漫气质的灵性世界。可以看出,诗人是把乡野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来建构的,旨在借助对乡土世界的美化来表现对残酷现实的精神逃亡、对可栖居的理想家园的追寻、对传统文明价值回归的怀想。这是他在传统与现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冲突中做的价值选择,更是诗人为在乡村和城市的夹缝间生存的一代人寻求的精神出路。
剑男挖掘出自然对人类内心世界建构的积极意义,这也让我们看到文学指导内心建设的可能性。封孝伦曾阐释过自然美的力量,“如果说,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扭结,在社会的网络上被撕碎的话,那么在自然中他又重新被缝合了;如果说,人在社会阶层的挤压中被削平了的话,那么在自然中,他复又膨胀为一个四维立体的生命存在”。在与自然的拥抱中,人能收获感官上的审美体验,更能在对自然的沉思中回归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及和谐状态。与自然的对话能促进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人摆脱心灵溃败、生命感萎缩的生存现状,感受到个体人格的独立完整及个体生命的鲜活存在。剑男的生态诗歌证实了,越深入自然便越能看到大自然对于人类身心的建构和充盈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乡野蕴藏了提供再教育的可能性,能够唤醒人的感知力,将人与自然间被切断的联系再度衔接,从而提高人类与其生活处所之间的和谐感,激发人的生态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