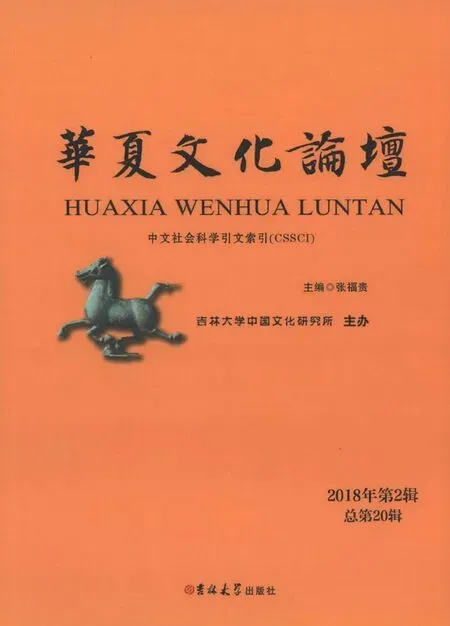写作和阅读是一种相伴终生的素质
2018-11-13陈晓明谭宇婷
陈晓明 谭宇婷
陈晓明:
我们的学制是两年,现在应该招生三年了。我们一年招四十个,其中一部分是中文系保研。学硕招收很少,大概六十个,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类的。创意写作四十个,合起来一百个左右。相当一部分是中文系的保研,大概二十几个。一部分是直博,直博加保研才三十几个。其他的是考研的。一部分同学想读研究生或愿意读创意写作,就到创意写作这边来了。创意写作中,中文系保研的有十到十五个,二十五个外面考的。每年报名的有三百个的样子,这要比学硕录取率高得多。学硕呢,有的专业三十比一,有的专业五十比一。像古代文学,报名的差不多一百个,录取两个,就是五十比一了。同学们看起来对这个专业蛮有信心的。创意写作会开一些写作课,因为很多同学读中文系还是有写作的梦想,创意写作正好满足了同学们对自己原来的理想的追求。创意写作就业率很高,就业情况很好,基本上百分百地就业,有些还考博,就业工资、薪酬待遇都不错。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摸索经验,但还是在良性地发展。你们想了解一些什么情况?
谭宇婷:
老师,很多人经常会问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写作是不是可教的?陈晓明:
写作当然不一定是可以教的。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写作可以说可以教的,也可以说不可教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兴趣和天分。你对没有兴趣和天分的人再怎么教也是没有用的。对有兴趣和天分的人来说,他通过训练肯定能提高写作能力和创作热情。就像刘震云说的,作家不一定要上中文系,有没有上过北大中文系决定这个作家能够走多远。他是在给自己找个说法。但也就是说,读过中文系的作家能够成长得比较顺利,同时他的创作道路会走得更宽更长,这点是无异议的。对于创意写作,两年的时间,学生更多接受文学的课程,能阅读很多作品,可以练笔,可以写作。那么,美国创意写作课程是很普遍的。著名作家卡佛就教过写作课,美国波士顿大学有个很有名的中国作家哈金,他就教创意写作教了十几、二十年了。他们毕业了很多学生,有的成为专业作家,有的成为报纸的专门作家。在美国,还有一些人想拥有写作的经历,他就自己努力写作。这也是挺好的一个经验。
谭宇婷:
老师,国外的创意写作开设的比较好,国内很多高校借鉴了国外的做法,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陈晓明:
我们当年做这个专硕是拿学硕的名额去换,所以各个专业的研究生就被砍下去了。砍下去后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老师就不能带博士。副教授的导师,他就需要带硕士。而学术硕士就减少了。所以我们学硕就让硕士生自主选导师——全校的导师名单打给他,让他自己去选。同时规定一个老师带的创意写作的硕士不能超过三个。所以四十个学生,会集中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文艺理论或者比较文学这些方向的老师。选古典文学的老师的学生也有。选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老师的学生就少一点。那边老师确实带的硕士名额会减少。我们这么做也是要尊重学生的兴趣,因为创意写作也有一个写作的问题,有的老师能指导学生,有的老师不太愿意指导,对这个方面不太有经验。上课的话呢,主要是金永兵老师去管,他是做文艺理论的。再就是,中文系的课,学生都可以选。中文系规定学分,满多少学分你就可以毕业。有必修课,有新媒体的课,有写作课,有外面请来的作家的讲座。我也计划以后有机会给创意写作的学生讲一门课《当代外国优秀长篇小说细读》,选十五部当代外国长篇小说,跟学生一起读,一起探讨。我想,这个对学生的写作也好,对他的文学的能力也好,都会有一定的提高。我们做的话,一方面是基于中文系目前的情况和条件,我们从学硕转型过来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努力把它跟今天的关于写作的理解结合起来。因为今天的写作变得更加多元,并不仅仅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有一些网络小说、新媒体的文本、游戏文本、电影和电视剧本等,所以它教的课相对面广一点。但是研究生阶段,说实话,最重要的是自学,同时同学们交流。有这样一个平台,几十个同学在一起,他们通过阅读,互相交流,寻找自己的兴趣。
谭宇婷:
老师,您平常上课是带着学生做文本分析吗?陈晓明:
对。阅读,细读这种。几门课都是跟作品有关,《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研究》《当代小说文本分析》《当代外国优秀短篇小说细读》,还有一个《当代外国长篇小说细读》,所以你看我这四门课起码跟作品有关,直接读作品。我现在讲课都是当代方面的。像《白鹿原》《尘埃落定》《受活》《长恨歌》《独药师》……外国的《太阳来的十秒钟》《水泥花园》《人性的污秽》《金阁寺》《我的名字叫红》《耻》等。每一门课都选十五部作品。谭宇婷:
老师,请问你们会开设一些偏重写作技巧的课吗?陈晓明:
具体的我不太了解,具体的金永兵管。有些课请了一些作家和编剧,以一个讲座的方式,而不是以一门课的方式去讲。按一门课去讲,倒不一定那么有效果。因为我想这类的书挺多的,但是创作必须是按作家的切身体会来谈创作方法,所以这些主要是请一些作家、编剧通过讲座来谈。创意写作这方面的有些课程还是根据同学们的兴趣,有一部分课程跟写作有关,有一部分确实无关。无关的,像一些古典文学课等,但古典文学修养对写作是有帮助的。现当代方面,对现当代文学有更深的了解,了解哪些作家,了解哪些作品,起码给同学们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方向。再像有些课程,语言啊,现在有些年轻作家写作语句不通,语法老出语病,适当学一下确实有好处。谭宇婷:
老师,请问您觉得创意写作应该怎样融进大学中文系教育教学体制中?陈晓明:
它不但要融入,而且同学们选课也是自主的。同学们可以选古典文学,也可以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选满学分就可以了,他们甚至可以选外系的课,像艺术、传播、外语等学院的课,都可以选。选修的角度都很开放。必修课有几门,把学分选上就可以了。谭宇婷:
现在我们文学教育可能更加注重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对文学创作就没有那么偏重。陈晓明:
对,文学创作,实际上,对学生来说,也是文学素养的一种体现。知识基础,对他创作有用。你不能说一些作家没有文化能写出好作品。固然中国过去有特殊的情况,“文革”那一辈人,他们有些人没有上过大学,比如莫言、余华、铁凝、王安忆等,贾平凹在“文革”后期上过大学。但他们都非常认真努力地读书,他们读书都非常下功夫。包括严歌苓,虽然没上过大学,她在美国读过创意写作研究生,严歌苓就是这个写作班出来的,所以你看严歌苓就不一样了,她的作品本身跟她的天分有关系,当然也跟她出国受过专业训练有关系。谭宇婷:
老师,请问您觉得严歌苓写出来的东西跟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陈晓明:
这个很难说,这究竟是跟她上过哪个班有关系还是跟其他因素有关。她原来的小说技巧就用得非常好,所以严歌苓是一个天才型作家,天分很高。她没上过大学,她十四岁就去当兵,在部队里当舞蹈演员。她自己写作,写得就非常好,她去美国读创意写作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然后去美国读书。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觉得作家的天分、经验更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更重要?陈晓明:
这很难说,我们很难做一个数字的划分,你说天分重要,还是经验重要,还是训练重要,可能各自都有吧。如果我们说的好听一点,那就三三开,天分,经验和生活。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接触的作家,他们对作家接受训练有什么看法?陈晓明:
作家,我跟他们没怎么聊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作家,他们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天才。他觉得写作就是自己的天才,作家甚至说他书都不看。像王朔,他说自己不太读书,没读过几本书,那你知道他读没读。但我知道很多作家是读书的,像莫言啊、贾平凹啊、阎连科啊、余华啊、阿来啊、苏童啊、格非啊、李洱啊、毕飞宇啊,都读书的,读很多书,而且很下工夫地读书。所以你说作家能不能训练,那肯定能,自我训练。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但是确实,作家有天然形成的,他是对写作怀有很大的热爱。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对现在中文系教育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呢?陈晓明:
中文系教育确实面临转折。过去我们老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过去我们急需教育人才,急需专业人才,过去对作家的需求没那么大,而且作家也是自然养成的。过去中文系毕业生马上就要去高校或者中学教书了,或者到研究机构去,或者直接走上别的工作岗位。像过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到八十年代早期,北京大学或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就可以到大学去教书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可以到延边大学,或者吉林师范学院或者长春师范学院这些地方去教书,没问题的。“文革”后那个时候是大学一毕业就可以到高校教书,现在不是了。现在你必须有硕士博士学位,硕士毕业了你都不能教,博士毕业了还有博士后,博士后历练之后你才能走上大学的讲堂,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没有必要本科专业化就搞得那么强,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做通识教育,这是对的。现在大学本科没有必要弄得那么专,学生今后不一定会用到,而且有些学生没有兴趣。过去不管你有兴趣没兴趣都得学,因为你能进大学的门就不错了。像我们能进学校的门,真的是非常珍惜了。现在的人读书很大程度上都是兴趣,有的热爱文学,有的喜欢语言,有的热爱文献,总体上热爱文学的偏多。你们现在大学二年级,可能对语言、对文献的课不一定那么有兴趣,会吗?谭宇婷:
我们觉得挺好玩的。陈晓明:
挺好玩,那就还行。有些同学就不一定有兴趣了。大部分同学还是愿意学文学的,他理解中文系就是文学,因为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中学语文的影响,中文语文讲的都是著名作家的小说啊、诗歌啊、散文啊,这是一个情况。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觉得创意写作教育对大学中文系改革有什么启发吗?陈晓明:
也没有什么启发,因为改革是很困难的。所有创新改革都要在传统前提的条件下。中文系长期就是这种建制,有这么多学科,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上也有这么多学科和专业。我们也不可能说学生想学文学想学写作,就让他学这个,还是得让他有这个专业教育。理解中文专业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知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专业训练。这才是你不同于物理、不同于化学的地方。否则你说起文学,好像都懂。我出去开会、评奖,跟那些物理啊化学啊理工科的老师在一起,一提到文学他们都能说话,说得比我还内涵,这个诗歌那个小说,他也读过,如何如何,说到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啊,他们说都懂。但是一说到物理化学,他们说我们就不懂了,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实际上呢,中文专业属于一个整体的训练,谁都不可以说我自学就成才了,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还是不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专业能够面对文学、语言、文献;教学、科研或者工作,需要有专业基础。所以这种专业分工是需要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满足学生学习的愿望,特别是对文学的愿望。所以这方面课程有必要加强。这一方面,大学里也有很多讲座,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讲座,很丰富,同学们可以有多种选择。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平常也会写一些文学作品吗?陈晓明:
写不了,虽然说自己老是想写,几十年,但是没时间。因为你做了学术研究,你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学术上了,时间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只能做一件事情。你不能说你学术做得好,创作又做得好,肯定会分心的。再一个,长期使用理论思维,再去面对创作,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练习的。我们在做学术,写学术的书是很苦的,得怀着很大的毅力和精力去写。你看我头发都白了,写了几本书头发就全写白了,它确实需要你要吃苦,要精力,靠熬夜,靠熬出来的,靠坚持。学术是长跑,是很累的。不像创作,创作还是更持有一点潇洒,一张纸一把笔,写。但学术你要阅读很多书,甚至要翻很多书,有时候一个上午就是为了找一本书,累得满头大汗。就是我的书架上,一本书,经常,要用的时候它找不着,不用的时候它都在那里。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沮丧,费很长时间。所以写小说,我至今还没写过。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写过一些诗,但都丢掉了,没保存下来。
谭宇婷:
老师,请问您觉得做学者的理论思维和创作的思维有很大的区别吗?陈晓明:
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你可以说阅读没问题,说哪个作品好哪个不好,你可以谈得甚至比作家还在理。你可以概括,面比较广。但是你要去写作,还是另外一种思维。但是还是有啦,有很多学者兼作家这样的,像曹文轩老师,格非啊,但他们的课也都偏向于创作。曹文轩老师有一门课《小说的艺术》应该是面向全校的,创意写作有不少学生去选。像徐则臣,他也读很多书啊,他是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的,所以我想读研究生对他写作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不是读创意写作的,他属于当代文学专业的,属于研究型的。谭宇婷:
老师,请问您对我们的写作有什么建议吗?陈晓明:
写作就是这样,要体验生活,要多阅读,多写,这个没有别的。就是生活、阅读和写作,多练习。当然阅读一方面凭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应该读一些经典作品,经典作品的水准是我们文学艺术历史传承下来的。再一个,写作的知识面要广。谭宇婷:
请问老师,您觉得创意写作这么发展下去,会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吗?陈晓明:
我相信是的,因为现在整个文化产业越来越壮大,对人才的需求增大。你看出版也好媒体也好,主要是文学性人才。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过一句话,他觉得现在的青年人,特别是到他们文化单位用的,主要看两个素质,一个他能写一手好文章,第二个他能判断好作品,能判断一个作品是好是差。但是现在大学中文系教育恰恰缺这两点,就是说一个学生毕业出来,一篇文章是好是坏分不清楚,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第二点他写文章,写小说诗歌散文都不擅长。所以他觉得大学的中文教育是有问题的。当然按他的这个观点看,我们大学课程结构要做很大的改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语言文献没被使用,就会慢慢忘记。写作是一种素质训练,阅读是一种素质训练,这是不太一样的。语言和文献也是素质,但它主要是一种知识训练,知识是会遗忘的,但写作和阅读还是一种终身相伴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