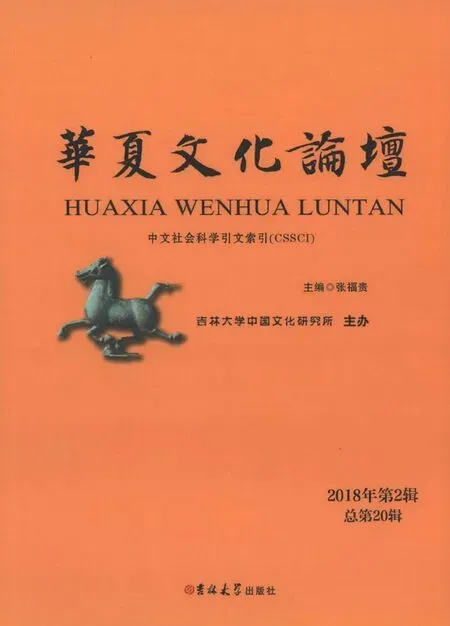文学教育
——在尴尬中的选择
2018-11-13谭宇婷
孙 郁 谭宇婷
谭宇婷:
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的作家驻校制度吗?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较好的作家任教的传统。我们的前身延安鲁艺就集结了许多知名作家,丁玲、艾青、孙犁、何其芳等人给文学教育带来了许多有趣的经验。进入新世界以来,文学院多名老师有文学创作背景,像王家新、王以培都有不错的实绩。2009年后随着阎连科、刘震云、张悦然、梁鸿等人的到来,人民大学重新恢复了过去的传统。建立作家驻校制度,其实是为了丰富学校的文学教育,给日趋单一化的教学体系带来一种鲜活的气息。我们选择的标准是国内一流的、有影响的作家加盟。这样可以带动学术研究与创作的对话,使淡出人们视野的写作成为新的可能。由于驻校作家的影响力,许多作家也被吸引来学校交流。比如诺贝尔奖获奖者略萨和索因卡,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忠实、贾平凹、格非等,他们的到来给文艺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新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作家还有一种是阶段性的。比如驻校诗人多多、蓝蓝、陈黎(台湾)等。他们都短时间在学校参加各类活动。举行诗歌朗诵和诗歌研究等活动。这给驻校作家体制带来了灵活性和便捷性。
谭宇婷:
引进作家进院校是出于学科建设的考虑的需要么?还是有别的目的?孙 郁:
引进作家进校院不是我们的首创,国内曾有过几所大学都有作家进校园的尝试。我们当时的设想很简单,主要是想改变文学院的学科生态。大学的文学院教学已经形成了模式,只注重文学史知识的学习,以及文学阅读与文学批评的训练,但几乎没有文学写作的培养和训练。建国以来,很多大学的中文系都强调“不培养作家”,中文系毕业生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寥寥无几。这对爱好文学的学生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而以传授知识的单一性写作模式,实际上在弱化学生对母语的把握能力,文学院没有文学,成为一种尴尬的现象。引进一些作家进校,设立创造性写作教研室,是为了改变这一尴尬局面。
谭宇婷:
在工作上,你们对驻校作家有什么要求吗?孙 郁:
我们学院的作家一部分不上课,一部分和普通老师一样参加各类考评。这两种方式给作家提供了不同的工作空间,使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在此愉快地工作。我们对于阎连科、刘震云没有规定动作,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主要是因他们的存在而使学生感受到创造性写作的价值。他们偶尔有一点讲座,和学生有一些互动。近来他们招收了创造性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像阎连科老师等还兼一点课程。他们还带领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比如到国外名校访学,和域外翻译家、作家对话等。前不久还与台湾作家群进行了有趣的对话活动。外国的创造性写作的老师要上许多课,课程有自己的规则。我们这里课程设计不同,分两个部分,一是请专业作家授课,集中讨论一些写作的问题。另一部分是讲授文史哲课程,带有学术的因素。这些课程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扩大视野,使学生在多维空间里建立理解世界的理念。
谭宇婷:
您觉得建立作家驻校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孙 郁:
文学院的作家的存在,使学科的结构出现变化。许多学生有机会亲近国内外一流的作家。文学院后来引进的作家张悦然、梁鸿等很有人气,她们的课很受欢迎,许多学生因之而喜欢上了写作。现在创造性写作的课程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如何培养写作习惯的养成和提升诗意的表达,还有许多探索的空间。另外,大学的评价体系不利于创造性写作课的发展,作家的成果不被教育部的考核所承认。做好这项工作非有超功利的意识不可。所以,这项工作看似没有实际价值,但却有根本的意义。缺乏感性体验和诗心的中文专业学生,是不合格的学生。同样,大学里缺乏有写作实践经验的老师,那样的教学生态是不完整的。
谭宇婷:
从现有学科分布看,创造性写作专业如何融入到大学教育教学体制内?孙 郁:
我们知道,写作分为学术性、实用性和文学性等不同类型,而目前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范畴内的培养和训练普遍集中于学术性写作这一单一形式。应该说,文学性写作是文学的根本。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批评,其围绕的对象都是文学的文本。文学创作的文本既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提供文学审美经验的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创造性写作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文学文本的生成,换一个角度——即在创作者而非接受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领会文学的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可以得到语言和思维方面的锤炼,同时还有可能在思想内容及主题等方面去进行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创造性写作不仅能够培养文学性写作者——作家或诗人,同时也能够为文学阅读者和批评者提供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这是穿越旧的知识结构的调整,使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更贴近文学的本质。谭宇婷:
听说你们把这种写作列入自设的二级学科,这有理论依据么?孙 郁:
在我们制定的方案里,对这个新设立的二级学科进行了理论描述:创造性写作吸纳并综合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同时,创造性写作还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写作的理论核心在于“创造”。与其它类型的写作相比,创造性写作更直接来源于写作者自身的主观意图,是写作者自身的想象、情绪、经验和体验的文学性表达。但与此同时,创造性写作又必须考虑接受者的一方,尤其在当今文化生产的特殊机制当中,需要同时对文学的接受、阅读、传播、影响、批评等诸多环节进行研究和考量,并将考量结果纳入到写作的过程之中。这种写作的培养,旨在唤起对形象表达的敏感度,从既成的思维模式里走出,以一种原生态的感受力,进入事物的本质。
创造性写作不是一般的文体的训练,而是借助形象,以陌生化的笔法,呈现生活的本质和精神的内涵。文学研究是对知识的渴求,追求的是规定性的、确切性的存在。创造性写作不属于规定性的实体,它是一种不断陌生化的不定形体。写作不是将自己变为一种形体的奴隶,而是注意在无法之中的“法”,学会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捕捉存在的意象。或者说,它绕过了科学与实证的领域,进入混沌与无意识之所,以形象的方式表达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真相。它是对认知极限超越的训练,是在对智性与趣味的诗意的表达的训练。这个过程乃反程式化、反教条的一种精神的放逐。它是去匠气的过程,是神灵飞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人的品性、操守、信念都得以从世俗的层面超脱出来。
因此,如何进行个性化的文学写作、如何在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中保持个性化创造的同时符合文化生产的规律,这都是创造性写作自身的使命。当实用、功利成为写作的动力的时候,思想是不能产生的。而创造性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提升精神价值的动力之一。
谭宇婷:
创造性写作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如何?孙 郁:
与创造性写作相近的二级学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我们的方案这样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侧重通过文学历史中的文学文本的产生、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现象的分析,以及流派群体的集合等等方面的研究,来考察文学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和审美判断。“文艺学”则侧重研究中西方文论、阐发文艺思想,在理论的层面对艺术的规律进行探讨。这些均是一种理性的沉思,是对文本的细读后的一种精神的归纳。可以说是文本的文本。
而创造性写作则是文本的培育,乃文学的母体之打造。但这种打造是经过了理论暗示的打造。创造性写作结合两者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原则,并吸纳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作为写作实践的一种参考,以一种文学史的发展的眼光和理论的高度指导写作,力图创作出更加符合时代、现实、思想和艺术需求的作品来。
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就与研究对象有了共振的关系。它们不再是分裂的状态,而变为一个较为系统化的整体。这对丰富学科,培养学生的母语表达能力,是一种促进。
谭宇婷:
您对目前的文学教育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孙 郁:
目前文学教育的问题之一是,传统的文章学理念消失了。自从桐城派的文章被逐出文坛,文学教学与语文课堂,都不太讲文章学,许多大学的文学史课偶有涉猎,亦言之不多。民国初年,说桐城派坏话的人,都有些底气,多能写一手好的文章。那是受到西学影响之故,但内在的功底亦含有古文的妙意,他们未必意识到此点。而后来白话文学的八股调渐多,连方苞、姚鼐那样的文字也没有了。这对文章学的发展,是一个不幸。白话文学的经验与古文的经验,其实形殊而理一,中国的文章气脉,割断起来去讲,总还是有些问题。谭宇婷:
如何理解文章学的理念?孙 郁:
现代文章学理念的变迁,与西学的渐进有关,文章观与先前大异起来。梁启超开风气于前,章太炎扭转态势于后,彼此价值态度迥异,而对词采的突围的渴望是相近的。后来的学人与其相互呼应,对新文化的推进都有不浅的功劳。旧时文人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不正经的文章,一类是正经文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就喜欢写雅正的作品,思想要合乎孔学之路,才情不逾孟子之矩。他们推崇孔孟,而荀子、韩非子、李斯的文章,因为偏离雅乐而被排斥。谭嗣同就批评过荀子的思想,章太炎则挺而为荀子辩护,其思想的呼应外,主要是在文章学的层面。荀子的文章,不像孟子那么单一,处处有复杂之气,内中有一种变化,层次多样。他看到人性的恶的意味,又能以非道德化的眼光看人看事,文章则有超逻辑的意韵,拷问与诘问都有。他从庄子那里看到其悖谬的地方,又能补孔子思想之不足。这在章太炎看来是不小的价值。太炎还推崇魏晋之文,对其弟子颇有影响。钱玄同对明清以来的文章的不满,也可以从太炎那里找到依据。鲁迅对阮籍与嵇康的喜爱,大约都与老师的理念有关,那是被其逆于流俗的风骨所打动的缘故。谭宇婷:
我们的文学史家对此是否有所研究,文学史家如果注重文章学,也许会对文学教育更有帮助。孙 郁:
此类观点在阿英、唐弢的那里都有,他们内心的文学史,总是与学院思维有些差异。唐弢主编《现代文学史》时,受极左思潮干预,不能使自己的“论从史出”的观点一以贯之,便写了《书话》,聊补那本文学史之不足。这《书话》呈现出另类的文学史的思路,有文章学的理路。但那时候的研究者,一时还没有顾及它内在的价值。我觉得唐弢先生其实是在周氏兄弟的思想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他的读书趣味、藏书趣味,很多地方和周作人四大弟子是接近的。他们彼此文思是有相通的地方。但他又警惕这些人的文章,怕滑到士大夫的路上。这原因是他来自底层,有过苦难的经验。加之思想近于左倾,便又有与周作人冲突的地方。他认为鲁迅是好的,鲁迅思想里的一些元素比周作人要高,那是脱离士大夫痕迹的缘故。但是周作人散淡、迟暮之感对他亦有引力。其间的快慰与自得其乐之情与其思想相吻。这是士大夫的遗存,那种书斋气,衔接了中国古风里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也未尝不好,至少在文章学层面,亦有价值。
谭宇婷:
您所说的文章学理念,好像是更宽泛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作家的文本,似乎还有学者的文本。孙 郁:
研究新文学的人,不太注意学者文体的艺术问题。学者文体也含有美文的因素。比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的文体。他们的诗很有感染力,散文也自成一家。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贡献表现在一种述学的文体上。王国维的词写得好,词话亦佳,但述学的文章从容不迫、博雅阔大,透明的思想与科学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不已。《观堂集林》写西北文物与考据,短小精悍,毫无废话,陈述间冷峻深切,有奇思涌动,读者望洋兴叹者再。陈寅恪写隋唐研究的文章,是文言里的轻歌,好似带着旋律。义理、词章、考据均在,且态度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一种,比晚清文人的关于儒家典籍的文章,更有魅力。至于钱钟书,则有鬼才之喻,那文章起伏之间的机智与才学,亦可谓前无古人。钱钟书在白话文进入衰败期时,拒绝以流行色为文,写古往今来之事,多六朝语境,间杂英文词语,东海西海一体,南学北学同道,文章乃碎珠贯串,以小见大,遂有汪洋恣肆之态。《管锥编》是一部奇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章学的一种新式的尝试。周振甫在《历代文章学》一书里,多次提到钱钟书《管锥编》关于历代文人文章的看法,实乃同代知音。在白话文流行多年之后,能以从容老到的旧式辞章里唤出新意,乃一种绝唱。古文在这些智者的手下,有了新的气象。现代文章学理念的变迁,由两类人所推进。一是大学学者,一为社会边缘上的作家。于是便有了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的区别。这里的情况复杂,有的作家之文从学者之文里脱胎出来。有的学者之文受到了作家之文的暗示而渐生新意。学者中又有公学的与私学之分,文体的样式就各不相同了。
上面谈及的许多人的文章属于学者之文。但作家之文就复杂了。小资作家是一种样式,流浪作家是一种风格,还有市井作家,文字在雅俗之间,系另一种风格。比如徐志摩的文章,就甜得过分,浓得过分,可是真意在焉。萧红的文字是泥土里升腾的,乃另类的文本,有天籁般的纯粹。赵树理的文章系旧学与大众精神的结合,通俗而干练,开新文学另一种文风。后来的左翼作家竭力要写出巨作,但却没有多少新意,除了观念的问题外,文体缺乏生命的亮度也是一个原因,这里的深层因素,是大可以深究的。
谭宇婷:
文学教育如何贯彻文章之道,训练的办法是什么?孙 郁:
对此意识最为清楚的,大概是中学的老师和散文家。自叶圣陶、夏丏尊起,已有了理论的摸索,后来吕叔湘、张中行倡导文章的理路的训练,功莫大焉。这个传统,已经深入人心,而做好此事,却并不容易。前不久读到人大附中的学生的文章选,看到指导教师的训练理念和学生的实践,颇有感触,觉得是叶圣陶那代人精神的延续,对当代文章学理念的充实都有可借鉴之处。这一本学生的作文,有许多老师的心血,谋篇布局多有深思,练笔的方法含有巧意。古今的文脉,在此不是隔膜,而是连贯起来了。许多知识可以在课堂上传授,但作文却另有一路,有时显得无迹可求。古人的办法是多读、多思、多写,那确也是一种选择。桐城派对于义理、考据、词章的讲究,就有一点这样的意味。而白话文的写作,道理是一样的。附中老师是懂得其间妙意的人,选择了许多的办法催促学生,在文章的世界寻找自己。一是学会模仿,从课文里找到自己的行文逻辑。一是让学生逆向思维,任意谈论自己的观点,不刻意追求什么样式。还有的是通过讨论,形成自己的思路,达到各抒己见的目的。印象深的,是老师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引导,这是学生文章大有进步的原因之一。仔细想来,这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规律在。
谭宇婷:
指导学生写作,是否会因为目的性而形成套路?他们是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孙 郁:
我看这些学生的作文,最大特点是言之有物,思想的含量很高,没有被八股的东西所扰。老师的引领方式引起我的兴趣。有按部就班的仿照、延伸阅读,有打破常规的个性练笔。从经典的文本读后感写作的培养,再到回到己身的冥思,让学生不是匍匐在前人的思路里,而是学会怀疑,自己判断。哪怕观点错误,亦是自己的偶得,乃血管里流出的声音,不是套话里的罗列。比如讲授沈从文的《边城》的时候,便让学生看看汪曾祺的《受戒》,相近传统里不同意趣,则使人忽然悟出玄机,知道审美的万千变化与内在的脉息。这样的引导,是深通文学史的一种训练,老师就不仅仅是课文的分析者,也有了作家的文章学的思路,其思路与古人的妙悟暗合,离当代文章家的理路亦近,穿透力是强的。我很喜欢他们的讨论的方式。《雷雨》的教学,看出开放性的特点,学生对人物的不同理解,看出训练有素,与老师的思路多有差异。这个选题的价值在于没有定论,宿命的话题,是用逻辑无法解析的,但在不同思路里的撞击中,审美的神经经受了洗礼,诗意与哲思便在心底刻下痕迹,是可以形成认知世界的暗功夫的。对孔子的讨论更有意思,学生的观点多种多样,亦有会心之处。老师训练的路数里一直贯穿着五四那代人的思想,不是以奴性的眼光打量遗产,在理解与同情中,多了个人主义的视角,批评的话语也水到渠成地出现在文章里。
中学生写作,是走步的尝试,只要能让大家自由言志,有骨有肉即可。幼稚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心口一致或文言一致。不过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也在学生的作业里看到不同的理念,比如有位同学的《论世贸双塔的倒掉》,乃模仿鲁迅的文章,讽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者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来形容美国受到的攻击,不免国家主义的气量,乃当下思想环境的必然产物。可是我也在书中读到另位同学《关于日本地震》那篇非民族主义的文字,普世的意识就有生命的温度,考虑问题则非意识形态化的。这种不同的思路的文章,可以给读者一种思考。对比是重要的。附中的老师对各类文章的宽容,可见自由的思想已渗透骨髓,乃健全理念的闪烁。我们于此可得的,是独思的成果。教育的目的,乃让人独立思考,“始之于怀疑”是重要的,能否“终之于信仰”那是另一个问题。前者的重要性,我们的前人早就说过的。后者的可意,是要慢慢锻炼方可达到的。文章学不是凝固的形态,乃催促生命的内觉不断丰富的内力。胡适生前一直主张写实主义,不为套路所囿。在词章上,他自己写不出怪诞幽默的文字,但对那些有个性的文章是喜欢的。讲到新文化的几位文章家的时候,就看重那些不正襟危坐的文字。文章太正经,易成为假道学的遗存,不易产生审美的力量。胡适觉得新文学作家中,有些人是有逆忤精神的,词语与句式与常人不同,反逻辑的亦偶有出现,遂有了迷人的趣味。
我们多年的教学,让学生多去写空幻的话题,虚假与平和的东西太多。这原因大概是缺少思想的碰撞,思路在别人的身上,出格的精神甚少。附中的教学一直鼓励学生的思想性,就产生了诸多有个性的作文。有位同学解析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很有意思,文字间是自我的觉悟。“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还有位同学批评朱自清的文章“教给我许许多多描写的技法,却没有带来思考与启迪”。都是悟道之言。他们的文章好,与这种越界的思维不无关系。
谭宇婷:
在大学阶段,知识训练越来越多,感性的写作如何与科学理念结合起来,的确是一种挑战。孙 郁:
大学的写作训练,比中学更丰富了,自由度更大。但我们的老师的学术思维和文学创造性写作的思维不同,不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满足。作家进校园,可能会改变这一局面。学生的创作,最好是由作家来引导。沈从文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授课,就影响了汪曾祺先生。作家的引导示范,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一般的教授不同,可能更接近写作的本质。当然,写作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领悟出来和实践出来的。没有写作天赋的人领悟不了,但有天赋的人没有被激发出潜能来,也是教育的失误。汪曾祺回忆说,沈从文的课很单一,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但细心听下去还是很有意思的。他随意讲些创作经验一类的东西。这些非学院派的东西让他感到新奇,有些东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状态。一些谈天式的讲授还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不过沈从文日常的那些状态更让他着迷。因为在文坛很有名气,就和各种作家有交往,同学们也跟着沾着仙气。比如请一些作家来校讲课,推荐同学们的作品发表,对青年学生来说都是难得的记忆。这是一个纯情的人,没有教授腔与文艺腔的人,而且他的驳杂,多趣,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的情感方式,是打动了汪曾祺的。
谭宇婷:
但汪曾祺的出现,恐怕不只是沈从文的影响,创造性写作如果只在这个层面,是不是也缺少了些什么?孙 郁:
是的。小说写作、戏剧写作只是训练的一种。其实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文章学的理念,就是培养学生对书画、文物器皿的兴趣。启发大家有杂学的感觉。除了专门性的知识外,还要有对古文、戏剧、历史遗物的感受力。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常常参加拍曲的活动,这对他的审美训练很重要。他还喜欢绘画,这些士大夫的兴趣成就了他的小说的写作。五四之后,新文人吐故纳新,有诸多佳作问世,遂引领着社会风潮。但那些新锐作家,都有很好的国学基础。比如鲁迅、知堂、张爱玲,古文的基础都好。还有一类人的知识结构也很有意思,比如齐如山、张伯驹等人,文章也都好。他们对戏剧、民俗、文物的研究很深,文章有东方的气派。现在的文学教育不涉猎这类人物的经验,也是不行的。
前几日看一位朋友写的《张伯驹年谱》,觉得很受启发。像张伯驹这样的人物,主张文化里的静的一面。近代以来的革命,在动的一面甚多,忘记了文化的安静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气,在于超时空里的安静。古老的遗存定格在生命深处,外面的风雨如何变动,均不能撼摇其本性。于是在晦暗之地有奇光闪烁;于风雨之夜能有安定之所。张伯驹的文化理念,其实并非落伍者的选择,至今想来,那温润的词语与旷达的情怀,岂不正是今人所需要滋润者?旧的戏文与辞章,乃几代人精神的积淀,是粗糙生活的点缀,也系由无趣进入有趣的入口。张伯驹深味我们的时代缺少什么,于是苦苦寻梦,且与世风相左,那恰是他不凡的地方。
谭宇婷:
在教学中注重传授这样的文人的经验,的确有意思。这些都是在通识教育中完成的吧?孙 郁:
是的。是在通识教育里进行类似的训练。在本科培养的路线图中,进行这样一些训练是必要的。文学院毕业的学生,起码要会填词,写旧体诗。这是最基本的本领。而要有这样的本领,则非注意知识结构的丰富性不可。还以张伯驹为例,我注意到,他平生留下的文字不多,除《红毷纪梦诗注》外,还有《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叢碧词话》《叢碧词定稿》《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叢碧书画录》等。我于此看到其知识结构,觉得那一代人的杂学里,有文化中最美的元素,这些在如今的文学学科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被认为是一种小道。但其实我们细细查看,则有文史里贵重的存在。我们从中所得的,是在新文学里所无的东西。比如他的书画题跋,几乎篇篇都好。所谈的名画、名人笔记,鉴赏的深度外,还有知识的趣味。明清之后,士大夫喜欢写短的书话,从钱牧斋到纪晓岚,从知堂到黄裳,写过许多美文。张伯驹与他们不同,他写的文字,都与实物有关。从古人的遗迹里,摸索历史线索,又谈及思想与诗趣,就没有空泛的感觉。文明在他眼里,是形象可感的存在,触摸到的文与画,可激发我们对遗产的爱意。所藏的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复赞》卷,宋黄庭坚《草书》卷,均为国宝,都捐给了国家。言及这些作品时,鉴赏的眼光独特,有了诸多妙文。他在谈论书画的题跋里,常能道出原委,又点明真伪,于线条色彩与气势间,揣摩古人心境。他对民间流传的艺术品,多有警觉。知道什么是赝品,什么是杰作。现在从事文物鉴定的人,多不会写文章,有语言功底者不多。而他笔锋从容明快,如久历沧桑者的独语,文人雅事,悉入笔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对其遗文,只有佩服。谭宇婷:
您觉得在中学、大学的文学教育中,作家的示范、学者的示范的互动的确重要。可是大学真的能够培养出作家来么?孙 郁:
中学、大学的教育,除了知识接受训练外,重要是一种校园氛围。校园里要有现代的东西,也要有古老的遗存。重要的是要把智慧与趣味衔接起来,让学生对文字的表达有一种好奇心,一种渴念。而我们的表达,要在古老的文明里久久浸泡着,也要在现实生活里久久浸泡着。让青年人了解各式各样的表达里,都有乐趣。论文有论文的乐趣,小说有小说的乐趣,诗歌有诗歌的乐趣,书评有书评的乐趣。这些是要浑然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引进作家进校园不是指望培养出多少作家,而是改变文学教育的生态。让学者与作家互动起来,给学生更广阔的空间。福柯曾说,大学有点像一座监狱,意指知识传授的被动性和思想训练的机械性。如果文学院的各个学科长期只有一个模式的存在,那是可怕的。关键在于对学科生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多层次的。一是学科内部的调整,一是学科之间距离的调整。文学院的学生多听一点哲学院的课,也留意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知识,都会丰富自己的知识,懂得表达的多元性。在某种层面上讲,作家的思维,对青年学生来说是重要的。可以启示学生如何对认知极限的超越,如何面对传统,并在现实里跳出既定的语境,以智者的方式反观存在。存在其实就在语言之中。可是我们的语言已经被污染了。惟有那些天才的作家,以奇异的方式在召唤我们的灵智力和良知,召唤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力。一个青年要学会用我们时代的陌生的语言进行写作。鲁迅如此,汪曾祺如此,贾平凹也如此。这也是我们引进作家进校园的目的,至于它的效果如何,只能在实践中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