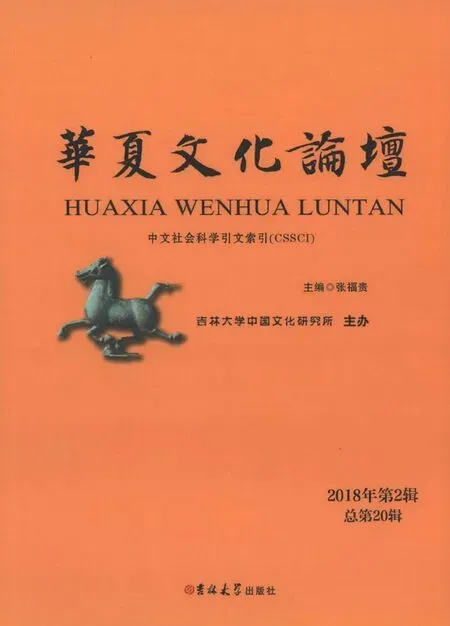关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教育
2018-11-13陈思和谭宇婷
陈思和 谭宇婷
谭宇婷:
老师,可以先介绍一下复旦大学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缘起吗?陈思和:
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原来在中国高校学科体制里是没有的,但在美国有创意写作的专业。在美国,艺术概念包含了文学的概念,所以在美国的教育体制里,创意写作属于艺术门类。像旅美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他们都是创意写作专业培养出来的。创意写作办得比较出色的是爱荷华。聂华苓先生的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在爱荷华创立了一个工作坊,然后把全世界的作家都请到爱荷华去听课、研讨,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培训班。但在中国高校里没有这样的专业,中国历来的传统观念里,大学学府是不培养作家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有一种理论认为,“作家不是靠大学培养的”,而是从生活实践当中培养出来的。首先要有生活,才能有写作。许多作家可以不经过大学培养,或者说,社会实践就是一座大学。原来的综合性大学里当然也有写作课,但这个写作课与文艺创作没有关系,多半是教你写一些公文啊,应用文啊,或者是对不同类型的文体做些技巧性的介绍,没有专门培养文学创作这一说。创意写作专业在中国是由复旦大学第一个办起来的。起因是2003年,王安忆加盟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王安忆到复旦来以前,也有作家到大学任职的,多半是驻校作家的性质,就是说作家去了只是做个讲座啊,与学生做个交流啊,等等,不是正式作为大学老师。王安忆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我们考虑给王安忆设立一个岗位。当时学校里定她的岗位是硕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导硕士生。问题是她在什么专业上去带学生?现代文学是接近写作的。当时我问过北大,北大很早就有写作硕士,但学生拿的是现当代文学学位。所以我们开始也是像北大一样,把王安忆的学科挂靠在现当代文学学科。后来学校里可以自设专业学科,系里就为她申报了一个新的专业,文学写作。但这个方向的学位是科学学位,学生毕业是要写论文的。这个论文可能与现当代文学有点关系,与创作也有点关系。王安忆在这个岗位上培养了几个很好的作家,有两个青年作家现在也小有名气,一个叫甫跃辉,一个叫张怡微。安忆教授还培养了好几位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但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为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我们请了严歌苓来复旦来上课,教文学写作。严歌苓是作家嘛,她说她自己不大会上课,就为我们邀请了她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老师。她的老师是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教创意写作的,是一对老夫妇,年纪很大了。美国人都有知识版权的。创意写作里有一块“如何教学生讲故事”的课程形式,是这对老人创造的,他们有知识版权的。这对老人就来了,上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王安忆就一直在边上听,非常认真。当时我们中文系的创意写作只有两个学生,于是就开设了公开的创意写作课,由学生自己报名选修,主要来的是外文系学生,那两个老人主要用英文讲课。他们上课也是很有意思。它就是教你如何编故事,比如他们给你一个字母C,让你想象C有什么字,然后再诱导你去编故事。很多时候是一对一的教学,比如一个小组有八个人,老师是与八个学生个别谈话,讨论他的作品。王安忆从头到尾听了一遍。那两个老师讲了一个学期以后就回国了。他们走的时候,我与他们交换意见,其实他们很想讲下去。他们说这个课有三个学期,现在他们讲了一个学期,还有两个学期。我就问他们,三个学期都是讲什么内容。他们就向我介绍了这门课程的情况,然后给我讲到美国MFA的学制,那个学制是作家的最高学位,专业硕士。如果毕业了,作家就完成了教育体系了。如果学生要留在大学里教书,那就要再读博士课程。
听了他们的介绍后,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我后来就请严歌苓把他们学校的课程拷贝过来,我看了之后就明白了。于是我与王安忆商量,她说她听了一学期的课以后,基本上就会上这样的课型了。这门课与我们平时讲文学史、文艺理论都不一样,它主要是从写作角度训练你怎么进入写作。王安忆说这个课她完全可以上。然后我们商量,向教育部去申报这个MFA。
MFA专业在国外是艺术范畴。我们这里碰到的问题是,我们教育部设立的学科门类是文学大于艺术,与美国的情况相反。我们这里是文学门类下面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艺术、新闻……这样分的。我们去申报设立MFA要通过艺术专业,艺术是一级学科,下面有七个二级学科,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广告、舞蹈等,MFA被建议在戏剧二级学科下设一个专业,戏剧与创意写作关系也比较具体。创意写作培养的写作人才,有些方向是产业性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编电视剧有一个写作工厂。当时我们就打算放在戏剧这一块了,当时艺术教指委还是不愿意,他们不愿意把我们文学写作揽进去。为什么呢?他们想把艺术一级学科从文学门类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个艺术的门类。所以他们急于要把艺术与文学撇清关系。这个事也纠缠了很久,我们去申报,通过教育部,教育部也支持我们。主要是王安忆起了作用,我们也是要为王安忆定身量衣。最后我们是成功了,复旦大学首先创办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点。后来艺术门类成功了,戏剧成为一级学科,创意写作自然而然成为二级学科。那时候已经到了2009年。我们是从2007年开始运作的,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谭宇婷:
请问,你们MFA学位是艺术方面的学位?陈思和:
对。2009年开始,教育部就给我们三年的时间做试点。三年以后就可以向全国开放这个学位点。导师就是王安忆啦,还有王宏图和龚静。王安忆和王宏图是做小说的,龚静做散文的,没有写诗歌的。于是就下设了两个方向:小说写作和散文写作。它属于专业硕士学位,不属于科学硕士学位。专业硕士人数多,王安忆过去一年只带一个,现在专业硕士一下子可以招收十几个。第一届专业硕士点招收了十三个,学校给我们二十个名额,但王安忆招生要求还是很严格,最后定下来是十三个吧,名额还多出来了。教育部那时开始规范专业硕士点,以前MFA里唱歌、跳舞啊,MFA内部里是可以都有的嘛,门槛很低。但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教育部就强调规范了,英语和政治考试是全国统考,各个学校不能放低门槛,然后还强调招收应届生。否则的话,MFA可能招收很多已经是作家、但没有学位的人。但现在它强调招收应届生,强调英语考试,把很多社会上的生源挡住了。我们招生完全是按教育部要求做的。2010年开始正式招收,到现在大概8届了。到后来名额非常紧张了,大多数生源都是来自985高校的,北大、武大、南大等的都有。这是一个过程。现在据我知道,其他大学中文系也在办创意写作专业,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教学情况。我从报上看到有个大学请了一个美国教师去上课,那个美国人说,他走进教室发现有一房间的人,几十上百人。那个美国人后来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到了这件事,他认为这么多学生是无法教好课的。所以他们是不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这样上课我不知道,但在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的人数是被严格控制的,创意写作的课程也是不对外开放,外人不能旁听的。
谭宇婷:
老师,目前国内创意写作存在一个很大的争议——作家能否被培养。这一方面,您的看法是什么?陈思和:
高校能不能培养作家的问题,也是现在经常在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在申报的时候也认真讨论过。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写作需要有天分。有些天分极高的人,比如高尔基,没有经过学校的系统教育,也能在社会实践中学习成长。这种我们就不讨论了。第二,如果不是天才,写作应该是有技巧的,有基本知识的,这个是可以通过大学教的。大学教了以后产生的效果,可能不是一流作家,一流要靠天才,但他至少不会是三四流,他可以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规范的写作水平上。你看美国文学就是这样,像福克纳、海明威那样特别优秀的作家比较少,但大致上作家水平是比较齐的。因为美国作家基本都是受过基本教育的,通过这种教学方式还是能焕发人的文学想象,教给他们基本写作技巧,这是有一个套路的。这个套路对于没有写作天分又愿意学习写作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培养。当然你真正成熟了,你也可能摆脱这些套路。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作家是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校开设专业教育、文学教育对未来作家的整体素质提高肯定是有好处的。复旦大学文学教育是有传统的,我进校之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复旦大学是有写作专业的。当时强调应用型,要实践嘛,所以“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在中文系学习,分成两个专业,一种是文学评论专业,一种是文学创作专业,就是来了你要么写评论,要么写创作。那时也强调培养作家的,比如,现在很有名的一位作家梁晓声,就是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的。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填写报考表格的时候,我记得还是设文学评论专业和文学创作专业,但我们进校以后就取消了,只有文学专业,然后老师们都说我们不培养作家的。这个话就口口相传了,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王安忆进复旦以后,有MFA以后,就把这个概念打破了。其实我们MFA出来的学生也没有真正成为作家的,至少现在没有,但是很多人到电视台工作啊,到杂志社工作啊,出来教书啊。王安忆有个说法,她说MFA培养出来的学生就算后来不从事写作也没关系,因为学校教给学生的是一种写作技能。这个技能是可以培养的,你学过跟没学过还是不一样。谭宇婷:
老师,现在大学里有些老师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您觉得作为学者的思维方式和作为作家的思维方式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陈思和:
关于写作思维问题,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是两回事,作为学者与作为作家的思维肯定不一样。创作是形象思维,如果是非常理性的作家当然也有,我们经常说教授作家,或者说学者作家,都属于这类型。但实际上,学者作家写的小说大多数是失败的,因为理性比较强,靠小说来讲道理,或者相对来说,学者的社会生活面总是比较欠缺,总是待在大学里面,他的生活比较狭隘,所以学者要成为作家,一般的写写是可以的,但是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国外的学者作家还是有的,比如美国的索尔·贝娄,他就是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老师,他的写作也非常好。但索尔·贝娄的创作与福克纳、海明威的创作还是有距离的。你看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萨特是个理论家、哲学家,但他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他的小说是在宣传他的存在主义理论,戏剧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他的作品并不好,至少是很难读的。但是有个别作家,在大学做老师,小说写得很好,但学术上没有什么杰出成果,你就不能用学术的标准去要求他的。很多作家的所谓的论文,就是一些读书笔记,与学术上的发现和理论归纳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谭宇婷:
但是老师,一个学者、教授平常也可以写一些散文之类的。陈思和:
散文,我认为啊,有两种所谓创作,其实不是创作,一种是写旧体诗,一种是写散文,那都是很自我的写作,是非虚构性的。像自传式的散文,写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写熟悉的人啊,这都没问题的。因为这是你私密的元素。我觉得这个写作并不妨碍理论思维。比较妨碍理性思维的是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虚构性思维。反过来也是。谭宇婷:
虚构的那一套,不也需要理论吗?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创意写作书系”中,有一本书就叫作《叙事与虚构》。陈思和:
那是关于虚构的理论,或者说,讨论形象思维的理论,并不是形象思维本身。国外创意写作很成熟了,这些都有传统的,所以编了很多教材。某种意义上说,教材也是属于理论性的东西。但这与我说的形象思维、虚构艺术的想象力,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说的理论也是一种思维的形态,逻辑的方式。这与创作所需要的思维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作家,现在的作家都喜欢谈理论,但他们谈的理论都是形象的。比如有个作家来做报告,他给你讲的都是村里有个老大爷啊,那里有个什么东西啊。哪怕是最好的作家来做讲座,他给你讲的都是故事,他不可能从理论层面上与你讨论问题。谭宇婷:
所以,文艺创作主要是依靠一种创造性思维的激发。陈思和:
对,创作是要靠创造性思维的,也可以说是形象思维。我的理解,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回事,不是说通过逻辑来推理出一个形象。好的作家通过形象的不断丰满、不断完善的过程,表达出越来越饱满、复杂的内涵。你看作家往往是这样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作品该怎么写,我就是抓住了一两个人的性格,写的时候我笔下的人物会带着我写下去……其实这就是形象思维,这个思维不是让作家在推理故事的前因后果,而是依靠一种形象,让你对这种形象的理解越来越生动。谭宇婷:
请问老师,从现有学科分布上看,创意写作该怎样融入大学教育教学体制里?陈思和:
艺术教育。艺术教育里有舞蹈、音乐、绘画之类的,都是既可以训练、但不培养天才的。创意写作就与戏剧一样,属于创造性的,这与学术性的训练不一样。再有就是,如果把创意写作放在现代文学学科专业里,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写论文。科学学位当然要写论文。它要用一部小说去取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MFA的艺术专业就可以不要,因为艺术专业,比如音乐学院,学生毕业除了通过写论文的方式,还可以做一个演唱会啊之类的。声乐系的要你唱歌演奏,美术系要你搞一个画展。它不是要你写论文。所以从这个角度,创意写作毕业生可以写出一部作品作为成绩。谭宇婷:
复旦大学的MFA可以拿一部小说毕业?陈思和:
好像是学生毕业主要靠创作,但也有一个论文形式的报告,但论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还有编辑出版专业,你也可以不写论文,可以完整地参与一本书的编辑,比如到出版社去实习,出版社就让学生完整地参与组稿到出书,这样也是可以毕业的。谭宇婷:
请问老师,科学学位这方面,就是培养偏学术型的学生?陈思和:
对。谭宇婷:
老师,可以讲讲您接受写作教育的经历吗?陈思和:
我没有接受写作教育,我在中文系就是好好读书读出来的。谭宇婷:
哈哈,那老师,请问您对我们现在学习写作有什么建议呢?陈思和:
你们现在都是中文专业的。MFA属于艺术专业,你们想进行文学写作,创作?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进了创意写作就能变成作家。但是创意写作将来慢慢发达了,高校都设立了这样一个专业,可能很多作家会觉得,有一个学位比没有学位要好,他可能就更在乎创意写作。谭宇婷:
之前我以为您会从人文精神、人文素质方面来谈建议,比如有人说创意写作不培养作家,但是可以培养你的人文素质之类的。陈思和:
你不读创意写作,也可以培养人文素质的。这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创意写作主要是培养你的写作技巧,激发你的形象思维。我觉得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是锻炼出来的。逻辑思维也是锻炼出来的,老师逼着你写论文,你这里写得不合格,那里写得不规范,不符合逻辑,也是训练你的思路嘛。形象性思维也是训练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