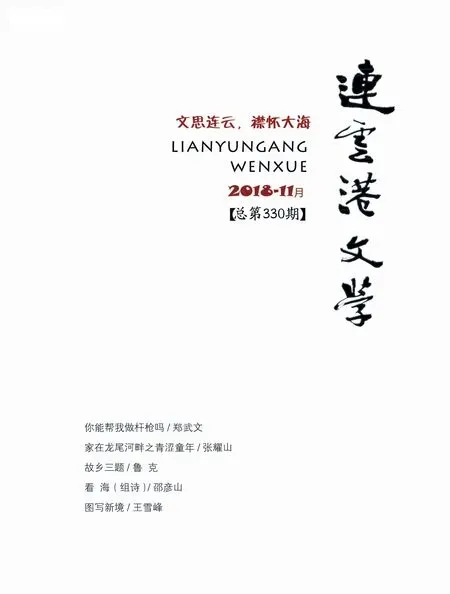故乡三题
2018-11-13鲁克
鲁克
遥远的西双湖
东海县城西边儿,两个湖,挨在一块儿,所以就叫西双湖,取这名字的先人有点懒,却也透着苏北人地瓜糊子一样的,特有的实在。
在我童年的感觉里,西双湖,简直就是大海。哇!真大呀!大得每次半夜噩梦里,都游不出来。恐惧大约来自不可预知和无法企及吧?西双湖,就横在我通往县城的路上,仿佛两张美丽又冰冷的脸,那是只有县城女人才有的气质,就像我那在县委当官的姑姥娘,连微笑着抚摸我额头的手,都有着不易察觉的距离和生分。
7岁那年夏天,肝大,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医院查血。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路过西双湖。
父亲一路都用他的的确良白衬衫罩着我的头,我坐在后座上,也不敢抱他的腰,只是两只手轻轻又紧紧地捏着他裤腚上端的布条。父亲太严厉了,从小,我和哥哥都怕他:只要不笑,父亲的样子就已足够吓人,是的,父亲的脸一年到头基本都是捋着的。那时候,父母亲正在闹离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书本里还没有“幸福”这个宝贵的生词。
父亲察觉出了我的胆怯,就鼓励我说:“抱着!抱我腰,甭(苏北方言读“掰”)掉下来……”
父亲的声音里是充满了爱怜的,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确信那一刻,他的脸上是有阳光的。
是的,那一刻,全世界都沐浴在盛夏的艳阳里。那时候,我的“全世界”其实比县还小,甚至比乡还小——我一个人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隔壁团林庄——还没敢进村,只是远远地站在村外,看上一会儿,就推着父亲单位上给他配的那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老式永久牌自行车,转身,把腿别在大梁下头,叮儿当啷地蹬回来……
感谢这场病,终于让我感觉到:父亲还是疼我的。
父亲的确是疼我的。父亲声音很大却依然不失温柔地唤了我三声小名。一声比一声高。直到快要接近平时调门的时候,我才赶紧答应一声:“哎!”
——我就是想让父亲多唤我两声,那样温柔的声音,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我做梦都迷恋着那样的声音。
“甭睡着啊!可甭掉下来!啊?!”
明明是训斥的语气,听来却那么暖心。那一刻,我居然大胆地搂紧了父亲的腰,甚至勇敢地把脸贴上了他的后背——父亲的脊背是瘦削而挺硬的,那件老旧的、都有了小窟窿眼儿的背心,都快被汗水湿透了。我把脸贴上去,偷偷地、贪婪地深吸了几口气——我爱那汗水混合着肥皂的味道,我爱那阳光伴随着暖风的味道——正是麦熟时节,我甚至闻到了麦子和家的味道……
没错,那是我幼小生命最初感受到的——父亲的味道。
“甭哈眼(闭眼的意思)嗷,得醒醒咯!你望望(方言读“汪”),都到西双湖咯!”
我从父亲的衬衫里钻出头来,第一次看到了我的“大海”。我没有激动,只有茫然:这么大的水面,我要是掉下去,一定会淹死的;这么大的水面,里边一定有大鱼吧?一定有比我还大的鱼,一张嘴不就把我给吃了?……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茫然就变成了恐惧。我把头躲到衬衫里,也把父亲搂得更紧了。
“马上过桥了!过了大桥,就近了!”
过那高高的拱桥,车子一点点慢下来。父亲弓起腰,使劲蹬,蹬一下,吆喝一声:“哎嗨!哎嗨……”我能感觉到车头在打摆子,父亲已经力不从心。
我掀开衬衫,我说俺大,我下来。
父亲跳下来,一手掌着车子,一手斜抱着我,想把我抱下来。我说,我自己能行!父亲微笑着,满头满脸都是汗,看着我自己爬下车,关切地问:“头晕不晕?”
其实我的头根本不晕,只是热,感觉阳光灼人。但我还是轻声应了句:晕。
父亲把车子扎好,疼爱地摸了摸我的额头:“哟,有热……”我怕父亲过于担心,又怕父亲过于不担心,就说,大,我渴。“走走走!过了桥有卖茶的!”
父亲推着车,一边往桥上走,一边回头问我:“腿麻不麻?来,扶着点!”我想说不麻,但没吱声,手却不由自主地抓住了车后座——不是扶,而是推。
父亲显然感觉到了我的好意,就转过脸,微笑着冲我说:“你甭使劲。”
过了桥,一下坡,我就看见大树底下有人卖冰棒和茶水。父亲问我:“吃冰棒吧?”我摇摇头。我想在父亲面前表现得懂事一些,不要那么馋。“不吃那故事(方言,意指东西)也好,茶才解渴哩!”
跟父亲一起坐在大树底下,望着宽阔的西双湖,我对县城一下子向往起来。就连那卖冰棒的小姐姐和卖茶的老奶奶,都有着说不出的神气。
我抬头看了看那些粗壮无比的开满绒花的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它们叫合欢,我在心底就管它们叫“绒花树”——碧绿的叶子细细密密,衬着满树盛开的花朵:那些花朵绒绒的、柔柔的,像一束束乍开的焰火,美得跟梦一样……
一转眼,4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病弱的小男孩早已长大,而宽阔无比的西双湖却在缩小。
“那些绒花树呢?”
“早伐了!都伐多少年了!”
西双湖东岸,当年广阔的荒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县政府也搬到了那里。哥嫂全家在湖畔小区买了楼房,早已定居县城了。初秋的傍晚,哥哥陪我去西双湖畔散步。爬上高高的大堤,西双湖尽收眼底:亭台楼阁,假山水榭,水鸟翩翩,画船悠悠;偌大的望湖公园里,市民们三三两两,或交谈,或自拍,笑逐颜开……
除了湖心岛上那片白发芦苇还有些眼熟,整个西双湖,哪还有一点旧时的影子呢?
“变化真大啊!”
“那是!亮化东海,光这个西双湖改造,就花了好几个亿呢!”听着哥哥自豪的话语,望着亮丽而陌生的西双湖,有涟漪漫过心海,我不知道那究竟是喜悦,还是伤悲?
40年前,卖我们茶喝的老奶奶如果还在,应该一百多岁了吧?
那些合欢树如果还在,应该两百多岁了吧?我实在想象不出:千百株两百多岁的合欢树一起开花,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父亲还在,已年近八十了。我跟父亲聊天,聊起过这段往事,父亲想了半天,笑笑说,真不记得了。
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来这世界走一遭,到最后,我们又能记住些什么呢?
美丽的西双湖,苍凉的西双湖,你是我儿时的一个梦啊,4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努力,却始终,不曾抵达……
捉蝈蝈
蝈蝈在我们老家叫“叫乖子”,顾名思义,是因为它们的叫声很乖。从仲夏一直到深秋,在大豆收割之前,豆田里总能听见它们吱吱啦啦的叫声。蝈蝈叫不是用嘴,而是靠背上两片透明的翅相互摩擦——那东西估计也不能称作翅了,反正它们也不会飞,只是弹跳力十分惊人。
盛夏晌午,太阳最毒,蝈蝈们也叫得最欢,这是捉蝈蝈的最佳时间。捉来的蝈蝈必须立即放到笼子里,不然它们一蹬腿,就不定蹿哪去了。所以,捉蝈蝈之前,须砍下一棵高粱——没有高粱就砍棵棒芦子(玉米)也成——用它们杆上的外皮做蔑,编八角笼。
如果说捉蝈蝈是技术活儿,那编八角笼更是。捉须心灵,编要手巧。
首先是剖杆。选最长、最壮实的一节,两端沿节头内侧截断,然后竖起来,用小刀依十字形剖开,刮去内瓤只留强韧的外皮。刮好后再一一劈开成条,就可以编了。先以井字状起头,两两相对,相互穿插,编织成蔑网。篾片之间空隙要适当,且最后要在四周留出余地。
这样正方形的蔑网需要编两片,大小也一样,然后相对着合掌而放——最光洁的一面都冲外——像十指紧扣那样穿插着,慢慢拢圆,这样自然就会生出八个角来,然后一一用麻线扎紧,圆溜溜的八角笼就做好了。
八角笼的大小是由选杆的长度决定的。一般来说,选高粱秆做蔑编出的八角笼要更大些。
一个八角笼只能放一只蝈蝈,放两只它们会打架,必定一死一伤。所以,想要多捉几只蝈蝈,就必须多编几个八角笼。
在大堰上的树荫里,一边编八角笼一边听豆地里的蝈蝈叫,那是我童年乡村记忆里最美妙的部分。
腰间挂着好几个八角笼,蹑手蹑脚下到豆田里,捉蝈蝈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日头越毒,蝈蝈们叫得越欢。毒太阳晒在脸上,你甚至能听见额头上痱子啪啪炸的声音。但你不能戴草帽——草帽阴影大,很容易惊着蝈蝈的。
大豆正在长荚,豆棵子浓密茂盛,不把脚拔起来,你是很难在豆地里行走的。而这一落,一拔,要多加小心;必须轻些,再轻些,且要努力保持上身稳定,摇来晃去是万万要不得的——蝈蝈眼尖,警惕得很呢。
向着蝈蝈的叫声你慢慢走,那叫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嘹亮了,你感觉自己的心怦怦直跳。最让你心跳的还不是越来越近的蝈蝈的叫声,而是无处不在的豆丹。
豆丹就是豆虫,它们的身体随着豆叶由青转黄,深秋时节黄中透红,因此得名豆丹。长大的豆丹个头很大,趴在豆叶上,边吃边慢慢蠕动,样子很瘆人,却是一道乡间美味。
说实话,我怕豆丹,仅次于怕蛇。别的孩子都敢拿在手里玩,而我一看见那东西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我却十分喜欢捉蝈蝈,因此每次下田捉蝈蝈,对我来说都是既兴奋又恐慌。
没错,下到豆田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躲着那些豆丹。要命的是,那东西你越想躲,却越是躲不开;有时候,它就趴在蝈蝈旁边,蝈蝈在那叫,它就在那爬,那情景才真的叫“触目惊心”。
一点点接近,接近,凭着叫声,你知道蝈蝈离你只有三五米了,你忍不住屏住呼吸;等它不叫的时候,说明它看见你了,这时候你们之间的距离往往不足两米。尽管近在咫尺,但想发现它却没那么容易。这时候你要站定,耐着性子,在骄阳下纹丝不动,直到它渐渐放松警惕,再次吱吱啦啦叫起来。但无论你怎样小心,离它一米远的时候,它总会息了声,如临大敌。
绿中带黄的豆叶上趴着一只翠绿翠绿的蝈蝈,还有什么样的美比这更迷人,更令人屏息?你看它的肚子一鼓一鼓,触须直竖一动不动,大眼睛瞪视着你,粗壮的大腿紧蹬着豆叶或豆梗,随时准备跳而逃之。
你把两只手伸出来,做包围状,徐徐向蝈蝈逼近。蝈蝈眼睁睁看见了危险逼近,它一动,再动,那动作极其细微,却充满力度。
这时候你下手要快,要臂实掌虚、既稳又准——成功和失败都在一瞬间,机会只有一次。
合掌一瞬间,你不要以为一切就都结束了;是的,还没有。
有时你感觉手心里有东西在动,你以为那就是蝈蝈了,可慢慢摊开手掌,你会发现刚才动的其实是一把豆叶,而蝈蝈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有时你以为没捉住,因为感觉手心里空空的;可就在你迟疑着将两手打开一条缝的时候,蝈蝈蹭地蹦出来,瞬间消失在大田里。
聪明的做法是左右掌配合着,一点点向内收拢,同时右掌指头向左掌心轻轻抠刮。空间变小,蝈蝈知道装死已经没用,便拼命挣扎。它的腿特别有力,一蹬一蹬,腿上的刺扎得你生疼;这还不算,它锋利的牙齿捞着哪里就咬你哪里。你要是经不住它的蹬和咬,稍一松手,那它就乘机逃之夭夭了。
小心捏着它两肩,即便它回过头来,也恰好咬不到你的手指,这才是最佳的捉拿蝈蝈的方法。一手捉着,另一手取一八角笼,五指配合扒大一网眼,将蝈蝈塞进去,再将网眼复原,这才大功告成。
刚被囚禁笼里的蝈蝈上蹿下跳,不时用大牙狠咬那蔑子,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大眼珠子都快瞪掉了。但等你把它带回家,挂到树上或屋檐下,塞一小瓣丝瓜花给它,等它吃饱喝足,就又开始吱吱啦啦唱歌了。
或许,在豆田里那才叫唱歌吧?
而在笼子里,是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呢?
叶落如雨
那么美的秋天,很多年没有了——
太阳斜照着午后的故乡,我在这片洋槐树林里抬头,满眼都是金黄。
春天里的洋槐林,到处都是绿眼睛;到了五月,洋槐树开花,开雪白雪白的花,漫山遍野,我的故乡就被这馥郁的香雪一层层覆盖……
这样的美景也只存在于我的记忆和想象中了。一晃20年,我都没有赶在洋槐树开花的季节回过故乡,我为此深深遗憾。而此刻,太阳斜照着午后的故乡,我在这片洋槐树林里抬头,满眼都是金黄。
风从哪面吹来?我不知道。起初不大,就一点点,仿佛微风吹拂着金色的海面,我就在海底,感受着海水在微微荡漾;后来风突然大起来,我听见了林涛由远及近,瑟瑟喧响;那涛声近了,近了!转瞬之间,我感觉大海在倾覆,整个世界都要飞起来了——
叶落如雨,叶落如雨……
如雨的落叶铺天盖地向我倾泻,倾泻,仿佛粮站里大机器正在倾倒麦子,而我就在下面,转瞬间就要被粮食掩埋……
那如雨的落叶并没有掩埋我,它们只是吞没并迅速席卷我,像洪流冲过堤坝,卷起一个草垛或一个稻草人,然后迅疾地冲向下游,而且打了个巨大的漩涡……
那一瞬间,我闭上眼,我感觉自己轻得就像一片落叶,正随着更多的落叶,已经飞起来了;耳边是轰轰的涛声,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飞溅的落叶的潮水……
叶落如雨,叶落如雨……
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被这落叶的洪流卷走,我就像洪水中一块大石头,定定地立在那里;黄叶还在落——地上已是厚厚的一层——落到一半的黄叶,正徐徐地飘下来,飘下来;而树木摇动,由深入浅,仿佛有只巨兽刚刚来过,现在,已钻进了更深的树丛……
前后也就一二十秒钟吧?片刻之后,风平浪静,静得出奇,阳光依然暖暖地、懒懒的斜照下来,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我知道,刚才刮过的,是一阵旋风。这在老家苏北,也被乡亲们叫作“阴风”或“鬼风”。这风一年四季都有,夏秋尤其频繁,没有规律,突如其来,又瞬间遁去,像极了没头没脸又坏脾气的鬼。
要是小时候,遇见这样的风,我是会害怕的。大人们总是说,见着鬼风,就冲着它吐唾沫,吐两口,鬼就走了。我没有吐。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大爷和二大爷。
大爷是春天走的,二大爷是秋天走的。大爷走之前,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二大爷也只见过那一面——大爷出殡,二大爷远远地望着棺材,眼里没有悲伤,我只看见了麻木和苍凉。
半年之后,二大爷也走了,村上的长者私下里悄悄地说,大爷出殡的时候,二大爷不该看。所以,二大爷出殡的时候,长者特意嘱咐我父亲,不要上前去,最好不要出门。
父亲就弟兄仨,两个老哥哥,一年里全走了,现在,就撇父亲一个人了。父亲跟母亲离异多年,他的晚年何其孤独。那几天,父亲的眼角总是湿的,但我确定他没有哭——奶奶死后,我就再没见父亲哭过了。奶奶死那年,我五岁。
我在想,如果这阵风与大爷或二大爷有关,也没什么好怕的——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在世的时候,都疼过我;如果真是他们,我真是该满怀感恩:是他们,让我在阔别二十年后,在那一刻,看到了故乡、看到了人世最美的秋天——那铺天盖地的汹涌的大美,这一生,怕是也不多见。
只不过是一二十秒,却仿佛过了很久,很久。我的心出奇地安静,仿佛有着微微的喜悦,又有着浅浅的悲凉。
我低头,看见虎妞正跟我一样,傻傻地眯着眼睛。我拍拍她的头,她就用脑袋蹭蹭我的腿,使劲地冲我摇尾巴。她是爱我的,像我爱她一样。
虎妞是母亲家的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还是个小不点儿,嗓门却大得很,我一进门,就冲我汪汪汪地叫。混熟了,就很黏人,我走的时候,她就在车子后面跑啊跑,追啊追,总追得我泪流满面。
虎妞稍微长大一些,母亲和大叔就把她拴着养了。那个秋天,送完了二大爷,我并没有急着回京,而是在母亲家住了一个月,继续我的剧本《幸福的模样》的写作。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带虎妞出来玩儿,她总是开心得要命,常常跳起来,扑到我怀里,抱着我,舔我的下巴颏。如果她会说话,我知道她会对我说什么。
树林里没人,我转过脸,小便,虎妞坏坏地绕过来,摇着尾巴,笑眯眯地看。我系好裤子,嗔打一下她的头,虎妞不好意思地摇着尾巴,用大舌头卷了下嘴唇。
我说,虎妞,回家了!我走出很远,回头,才发现虎妞也在那儿撒尿。见我看过来,她别过头去,仿佛很害羞的样子……也就那一瞬间,灵感直冲我的脑门,我回到家,暂停剧本创作,立即开始了长篇小说《挣扎》的写作——有谁会知道,这部寄托了我深深爱恋的长篇小说,它的写作灵感和故事的梗,居然来自虎妞和她的一泡尿……
去年冬天,我从合肥回京,路过徐州,弟弟开车带我一起回了趟东海老家。一进门,没听见虎妞叫,我和弟弟都很诧异。弟弟问,狗呢?母亲支支吾吾,说,卖了。“留着好看门啊!你卖它干吗?!”“你大瘫了,老得住院,家里谁劳它?你不卖还不饿死?”“卖多少钱?”“170……”
站在走廊里,听着弟弟和母亲的对话,我呆呆地望着南墙根,虎妞的窝空着,那个平时喂食的旧铅盆,也空在那里。
母亲见我难过,自己先流下泪来:“俺也舍不得啊!贩子一塞铁笼里,我眼泪哗哗的,可你不卖怎着啊?……”
回到北京,我把虎妞的照片设成了桌面,那是那年春节全家一起回老家时,女儿给虎妞抓拍的:黄黄的、光亮的皮毛,水汪汪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善良;虎妞正摇着尾巴,大舌头伸出来,一卷,舔了一圈自己的嘴唇……
“虎妞!过来!”我又想起那年秋天,虎妞听我呼唤,不顾一切涉过冰冷的河水向我奔来的情景;
“虎妞!回家了!”我又想起那年秋天,在那片天底下最美的洋槐树林里,虎妞一边撒尿,一边害羞地别过脸去的情景……
——那么深的秋天,很多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