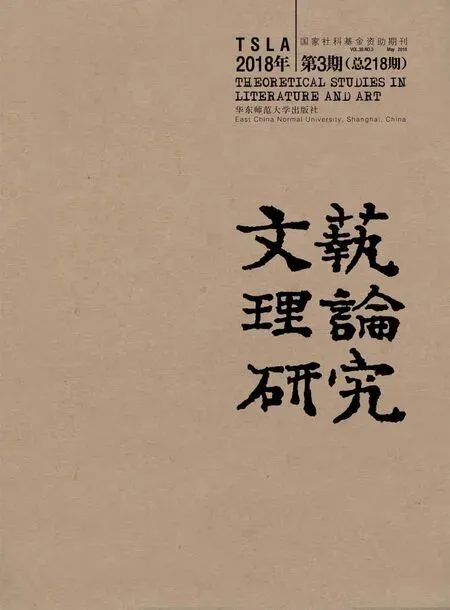论明代万历时期“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
2018-11-12李亦辉
李亦辉
“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传奇戏曲理论、批评及创作中风行一时、影响深远,于明清传奇曲辞审美理想的演进历程而言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但与学界对“雅”“俗”“当行”“本色”等曲辞审美观念的深入讨论不同,对“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尚无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万历曲坛的历史地位与明清传奇曲辞观的演进历程的深切体认。故此,本文拟将理论批评、创作实践与曲家交游三者相结合,对相关文献与文本作还原性解读,以期客观、深入地揭示“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来龙去脉、具体内涵、理论价值及其戏曲史意义。
一
在明清时期的诗文评中,“雅俗并陈”通常是指在某个作家的作品中雅与俗两种题材或风格因素同时并存的状态,如明代胡维霖《墨池浪语·明诗总论》谓袁宏道之诗“禘晚唐而祖眉山,雅俗并陈”(568),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诚斋集》提要谓杨万里之诗“是亦细大不捐,雅俗并陈之一证也”(纪昀等 2143)。而在戏曲理论批评中,“雅俗并陈”主要是指在一部戏曲作品中雅与俗两种风格的曲辞同时存在、各得其宜的曲辞审美观念。这一曲辞观之所以会产生并风行于明万历年间,与该时期曲家对明中期文词、本色二派的利弊得失的反思与扬弃紧密相关。
明代中期文人传奇兴起后,文人曲家不满旧南戏鄙俚无文的原生状态,绮丽藻缋、饾饤堆垛的时文风盛行一时,文词派成为剧坛的主流。鉴于此类作品过度雅化以至背离戏曲的舞台表演特性的弊端,李开先、何良俊、徐渭等曲家纷纷以元曲“本色”为号召,抨击文词派的不良作风。这些批评意见促使晚明曲家反思文词派的弊端,探寻与传奇文体相适应的曲辞风格,但因个体审美趣尚的差异,在创作及理论上逐渐呈现出二水分流的局面。一派是以沈璟、顾大典、许自昌等为代表的曲家,对文词派持否定的态度,遂以旧南戏为楷式,走上黜雅求俗、纯用本色的路子;一派是以王骥德、屠隆、梅鼎祚、汤显祖、吕天成等为代表的曲家,对文词派持扬弃的态度,主张并取文词、本色之长而去其短,遂转向雅俗相济一路。作为已然充分文人化的舞台表演艺术,雅俗相济的曲辞形态最符合传奇的文体特性。但对于雅与俗应该怎样“相济”的问题,不同曲家乃至同一曲家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语境下,所提出的具体解决方式并不相同。约而言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雅与俗在文本表层的“并陈”,一种是雅与俗的深层“融会”。“融会”型的曲辞观主要指向那种因雅俗适中而显得清丽流畅的曲辞风格,王骥德的“浅深、浓淡、雅俗之间”(332),吕天成的“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23)等,是其典型的话语表现方式。“并陈”型的曲辞观,主要见诸屠隆、王骥德、汪廷讷、梅鼎祚、臧懋循等曲家的曲论中,但研究者往往习焉不察地将其混淆于“融会”型的曲辞观,忽视了其独特的存在方式、理论价值与戏曲史意义。
在晚明时期的曲论中,明确使用“雅俗并陈”这一概念的地方并不多,就笔者所知,仅见于屠隆的《章台柳玉合记序》、汪廷讷的《刻陈大声全集自序》以及刘若愚的宫廷杂史《酌中志》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曲辞观声势微弱,因为还有一些相近的表述方式存在,且有多部践行这一曲辞观的名作。因此,“雅俗并陈”既是一个曲学概念,更是以这一概念为表征的一种曲辞观念与创作潮流。刘若愚《酌中志》所谓的“雅俗并陈”,是就明代宫廷戏曲“过锦戏”的内容与表演形式而言,虽包括曲辞但非单指曲辞,且《酌中志》成书于崇祯年间,出现的时间已相对较晚。汪廷讷《刻陈大声全集自序》作于“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系为《坐隐先生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所作的序,“坐隐先生”是汪廷讷的号,“大声”是明中期曲家陈铎的字,“乐府全集”乃其散曲、杂剧的合集,并附诗词;因此,该序所论之“曲”,虽为概括的曲学观,但毕竟以散曲、杂剧为主,出现的时间也不是最早的。屠隆《章台柳玉合记序》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为梅鼎祚《玉合记》传奇所作的序,既在时间上最早,又专为传奇而作,因而最具开创性与代表性。下面将结合相关曲家的交游情况,在考察该序的曲史观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具体内涵。
倡导或践行“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晚明曲家,如屠隆(1543年—1605年)、梅鼎祚(1549年—1615年)、汤显祖(1550年—1616年)、臧懋循(1550年—1620年)、王骥德(1542年?—1623年)、汪廷讷(1569年?—1628年)等,都主要活跃于万历朝(1573年—1620年),他们互有交往,互通声气,对彼此的戏曲创作与理论主张都十分熟悉;其中屠隆、梅鼎祚、汤显祖三人交往尤密,他们经历相近,志趣相投,除多次会面外,屡有书信、诗篇往答,相互之间影响颇深。梅鼎祚的《玉合记》完成于万历十四年(《徐朔方集》第四卷148),《章台柳玉合记序》是万历十五年十月梅鼎祚作诗招屠隆,屠隆为其《玉合记》所作的序(150)。全序除去结尾部分内容如下:
夫机有妙,物有宜,非妙非宜,工无当也。虽有艳婢,以充夫人则羞;虽有庄姬,以习冶态则丑。故里讴不入于郊庙,古乐不列于新声。
传奇者,古乐府之遗,唐以后有之,而独元人臻其妙者何?元中原豪杰,不乐仕元,而弢其雄心,洸洋自恣于草泽间,载酒征歌,弹弦度曲,以其雄俊鹘爽之气,发而为缠绵婉丽之音。故泛赏则尽境,描写则尽态,体物则尽形,发响则尽节,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故余断以为元人传奇,无论才致,即其语之当家,斯亦千秋之绝技乎!其后椎鄙小人,好作里音秽语,止以通俗取妍,闾巷悦之,雅士闻而欲呕。而后海内学士大夫则又剔取周秦、汉魏文赋中庄语,悉韵而为词,谱而为曲,谓之雅音。雅则雅矣,顾其语多痴笨,调非婉扬,靡中管弦,不谐宫羽,当筵发响,使人闷然索然,则安取雅?令丰硕颀长之媪施粉黛,被 裆,而扬蛾转喉,勉为妖丽;夷光在侧,能无咍乎!故曰:非妙非宜,工无当也。
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二百年来,此技盖吾得之宣城梅生云。梅生禹金,吾友沈典君总丱交,生平所为歌若诗,洋洋大雅,流播震旦,诗坛上将,繁弱先登矣。以其馀力为《章台柳》新声,其词丽而婉,其调响而俊,既不悖于雅音,复不离其本色。洄洑顿挫,凄沉淹抑,叩宫宫应,叩羽羽应,每至情语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绝,则至矣,无遗憾矣。故余谓传奇一小技,不足以盖才士,而非才士不辨,非通才不妙。梅生得之,故足赏也。(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589—90)
明中期的本色派曲家更多是着眼于一般戏曲文体的特殊性,来讨论传奇曲辞的应然形态;明后期主张雅俗相济的曲家则有了进一步的文体自觉,主要是立足于传奇自身的文体特性来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屠隆虽然与何良俊、徐渭一样以女性装扮为喻,说明传奇曲辞的应然形态,但旨趣却不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画太过,岂如靓妆素服,天然妙丽者之为胜耶”(《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466),徐渭《西厢序》谓“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498),皆旨在批驳绮丽藻缋的时文风,倡导自然本色的曲辞风格。屠隆的“艳婢”“庄姬”“丰硕颀长之媪”之喻,则旨在说明传奇文体的“宜”与“当”的问题,是对传奇文体特性的进一步深入辨析的结果。这一辨析建立于对元明戏曲的整体考察与逻辑推演的基础上,体现出学理性的特征。具体而言,他把其前的元明戏曲分成三个阶段,作为自己的曲辞观的历史前提。
第一阶段是元曲典范期。元曲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一个高峰,是明清曲家讨论戏曲问题的重要参照系。虽然明清曲家普遍尊崇元曲,但具体以哪种风格、哪些作品为范本却因人而异,一般而言,文词派曲家赞赏高华典雅之作,本色派曲家则赞赏质朴通俗之作。屠隆的看法与这二派不同,他认为元人之所以能尽戏曲之妙,是因为元代曲家“以其雄俊鹘爽之气,发而为缠绵婉丽之音”,因而具有“尽”,即穷形尽相、淋漓尽致的特征;“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即雅与俗均臻极致。因此,他特别推崇元曲的语言成就,认为无论在“才致”即文采方面,还是在“当家”即本色方面,都是“千秋之绝技”,言下之意,这两方面都是后人创作的理想范本。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就元曲全体而言,那么第二、三阶段则主要是就传奇的曲辞问题而言。第二阶段是明前期戏文的“谐俗”期,“椎鄙小人”即书会才人、下层文人,他们“好作里音秽语,止以通俗取妍”,结果是“闾巷悦之,雅士闻而欲呕”。虽然该时期南曲盛行,但因较少文人参与,所以曲辞多质朴鄙俚。第三阶段是明中期文词派的“向雅”期,创作主体已由“椎鄙小人”转换为“学士大夫”,他们“剔取周秦、汉魏文赋中庄语,悉韵而为词,谱而为曲,谓之雅音”。但因文词派曲家多非当行,故其曲辞虽雅却“语多痴笨,调非婉扬,靡中管弦,不谐宫羽”,背离了戏曲艺术适俗美听的舞台性特征。
可见在屠隆的曲史与曲辞观念中,元曲具有至高无上的典范地位,主要表现在雅与俗的谐和;明传奇的弊端,则主要在于仅取雅、俗中的一端,不能如元曲那样调和并用;文词派更在一味求雅的旧弊上,生出不协音律的新弊。基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理想的曲辞形态自然是向元曲回归,重返雅与俗、意与调的平衡状态——“雅俗并陈,意调双美”。关于曲辞的意与调,即曲意与曲律的关系问题,虽是曲论中的重要问题,但非本文的关注点所在;关于曲辞的雅、俗问题,特别是“雅俗并陈”的内涵,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先看“雅”“俗”二字的内涵。联系屠隆对元明戏曲的讨论,结合“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好作里音秽语,止以通俗取妍”,“剔取周秦、汉魏文赋中庄语”,“既不悖于雅音,复不离其本色”等语来看,“雅”主要是指绮丽典雅的曲辞风格,特点是多用辞藻、典故,具有深婉含蓄的美学效应;“俗”主要是质朴通俗的曲辞风格,特点是多用方言、俗语,具有酣畅显豁的艺术效果。这二字的内涵较为明确,在讨论曲辞问题时,多数曲家都持此义。
再看“并陈”一词的含义。从具体语境来看,这个词的内涵不十分明确,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雅与俗的表层并置,一种是雅与俗的深度融会。虽然从字面上我们比较容易认同第一种解释,因为“并陈”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并置、杂陈,但结合上下文,也有第二种含义的可能。那么屠隆的“雅俗并陈”究竟是指哪种含义呢?结合当时曲家的曲论与创作实践,笔者认为当是第一种。这与其《与友人论诗文》推崇杜甫诗“雅俗文质,无所不有”(蔡景康 259)的诗学思想是一致的,且可在他为自己的第一部传奇《昙花记》所作的“凡例”中得到印证。
屠隆的《昙花记》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昙花记凡例》第二条云:“虽尚大雅,并取通俗谐□,□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588)。从“雅”“俗”,特别是“并取”等字眼来看,可知在作《章台柳玉合记序》十一年后,他在雅、俗问题上仍持“并陈”的观念;由此反观其早年所谓的“雅俗并陈”,亦当是雅与俗的并置、杂陈之义。但恰如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艳品》所言,《昙花记》“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 548),未能臻于“雅俗并陈”的境界;两年后所作的《彩毫记》,更如徐麟《长生殿序》所言,“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洪昇 226)。由是观之,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尚不能完全一致。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创作上却未能尽善尽美,这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不能因而否定其理论的合理性。
二
任何有价值的文学理论都不是漂浮于文学实践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整体文学生态的土壤中,与作家的创作实践血脉相通、桴鼓相应。因此,戏曲理论研究也不应与当时的戏曲创作及批评相脱离。一些重要的曲学观念虽然主要呈现于理论著述中,但戏曲文本有时也会以感性的方式承载某些曲学观念,而相关的批评话语则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些观念的合理或偏颇之处。万历朝“雅俗并陈”的曲辞观与传奇创作实践之间,也具有这样一种共生性的内在关联。
屠隆之所以提出“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前述元曲的示范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更为切近的因素则是他对梅鼎祚《玉合记》本身的曲辞风格的体察。《玉合记》虽是文词派的扛鼎之作,徐复祚、沈德符等崇尚本色的曲家对其屡有非议,但其中也颇有一些本色通俗的曲辞,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言:“《玉合记》一向被看作是曲文典丽的案头剧的代表作”,“但也应该看到它也有如第三十七出《还玉》那样宜于舞台演出的一些片段,曲文明白如话,而又同剧情紧密配合”(《徐朔方集》第四卷 114)。换言之,该剧在整体上虽然尚非“雅俗并陈”的风格,但局部已粗具苗头。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艳品》评《玉合记》云:“骈骊之派,本于《玉玦》,而组织渐近自然,故香色出于俊逸”(《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 548)。主要是就此而言。屠隆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尚处于“青 之末”的迹象,并结合戏曲的历史与传奇的发展趋向,顺势提出了“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因此,这一提法既是对《玉合记》的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也是借评价《玉合记》提出自己的曲辞审美理想。这一理想在他自己的剧作中虽有一定的体现,但显然未能充分实践;充分践行这一理想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与其《昙花记》同年完成的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
屠隆与汤显祖订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徐朔方集》第三卷 339),二人同为梅鼎祚的挚友。早在屠隆作《章台柳玉合记序》的前一年,即万历十四年(1586年)八月,梅鼎祚到南京访汤显祖,乞序《玉合记》传奇,该剧系借鉴汤剧《紫萧记》而作(《徐朔方集》第四卷 112—14、148、286—87),汤显祖作《玉合记题词》,谓“予观其词,视予所为《霍小玉传》,并其沉丽之思,减其秾长之累”(《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605),可见其对己作“秾长之累”的反思。汤显祖的《紫钗记》约成书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前后,当在作《玉合记题词》之后,该剧虽“仍《紫箫》者不多”,但“犹带靡缛”(吕天成 220),基本还是文词风格的作品,尚未整体臻于“雅俗并陈”的境界。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屠隆于春、秋时节两次来访(龚重谟 188—90),汤显祖于“乙未上巳日”(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所作《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叙》云:
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观,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
这时汤显祖正在修订《紫钗记》,其间常取董解元《西厢记》相参,感佩之余遂加批订;正值雅好《西厢记》的屠隆来访,遂将自己的批订本拿出来向屠隆请教。正如王骥德所言,《董西厢》“多椎朴而寡雅驯”(《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444),“独以俚俗口语谱入弦索,是词家所谓‘本色’‘当行’之祖”(《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455—56),而此时尚为文词派曲家的汤显祖却对之情有独钟,从中我们不难觉察其创作思想的转变。实际上,如何“用俗济雅”是当时包括汤显祖在内的曲家们极力思考的问题,而从该序来看,汤显祖此时已然取《董西厢》之“俗”济己作之“雅”了,其后的《牡丹亭》更是多处融入《董西厢》的笔法(郑培凯 224—26)。
《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具体构思、创作时间当更早,或在遂昌任上,这一时期恰值“雅俗并陈”的曲辞观方兴未艾之时,该剧堪称是践行这一曲辞观的第一个成功范例。时人对该剧曲辞多有评骘,其中说得最贴切的莫过于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所谓的“古今雅俗,泚笔皆佳”(《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 49),而稍后李渔的抑雅扬俗之论亦不乏真知灼见。二人评价虽异,却都客观揭示出其“雅俗并陈”的整体曲辞风格。今人对该剧曲辞的评价,多强调、赞赏其绚丽典雅的一面,而对本色通俗的一面认识相对不足,这无疑会影响到我们对汤显祖的开创之功及该剧的戏曲史意义的准确把握。
对《牡丹亭》中那些绚丽典雅的曲辞,前贤时彦有很多精彩论述,尤其是《惊梦》《寻梦》等出,文采斐然,一片神行,深具精警蕴藉的文人意趣,最为后人激赏。王骥德谓汤剧“婉丽妖冶,语动刺骨”(332),吕天成谓汤剧“丽藻凭巧肠而浚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34),皆是着眼于剧中此类曲辞而言。虽然多数明清曲家都对《牡丹亭》中此类风格偏雅的曲辞交口称赞,李渔却不以为然,《闲情偶寄·贵浅显》谓《惊梦》出“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等语,“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语,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他所赞赏的是剧中那些虽浅近通俗却生动传神的曲辞,如《惊梦》中的“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寻梦》中的“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梦魂前”等语,“以其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也”(《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 248—49)。此类曲辞在《牡丹亭》中并不鲜见,如《忆女》《遇母》等出,曲辞浅近通俗,质朴无华,却情真意切,语力千钧,写出甄母孤苦无依的处境和对女儿深挚的思念。此外,在《劝农》《肃苑》《道觋》《冥判》《耽试》《围释》等出中,尚有大量以隐语、俗语、方言土语出之,今人看来略显庸俗、晦涩的曲辞。对这些曲辞我们不当简单以率意牵强或趣味低俗视之,实际上,此类曲辞是汤显祖在用俗济雅、雅俗并陈的曲学观念的引导下刻意为之的产物。
《牡丹亭》曲辞“雅俗并陈”的特征,还可以从晚明曲家对汤剧与元曲的渊源关系的评论中得到印证。当时的一些曲家特别指出汤显祖对元曲的学习、模仿,如王骥德《曲律·论引子》谓“近惟《还魂》、‘二梦’之引,时有最俏而最当行者,以从元人剧中打勘出来故也”(210);吕天成《曲品》卷上谓汤显祖“熟拈元剧,故琢调之妍俏赏心”(34);臧懋循《元曲选序》谓“汤义仍《紫钗》四记,中间北曲,骎骎乎涉其藩矣”(《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619);凌濛初《谭曲杂剳》谓汤显祖“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 189)。我们通常是从宗元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文献,却忽略了其特定语境下的文体风格的蕴含。北曲具有雄肆本色的风格,南曲具有柔婉华美的特征,这是明代曲家的基本共识。因此,这些曲家指出汤显祖对元曲的模仿、借鉴,实际是想说明汤剧中那些偏于本色的曲辞的渊源问题,这也间接表明他们都已认识到汤剧“用俗济雅”的倾向。这类曲辞的位置尤其值得注意,或是“引子”,或是“尾声”,特别是臧懋循所谓的“中间”,更是明确传达出汤剧曲辞中雅与俗相间、并陈的特征。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可见上述曲家的评论都不限于《牡丹亭》一剧,或包括“二梦”,或是就“四梦”而言。实际上在汤剧中,非但《牡丹亭》的曲辞具有“雅俗并陈”的特征,此后的《南柯》《邯郸》二记亦是“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王骥德 307),因此,汤显祖堪称是“雅俗并陈”的曲辞观最忠诚的信奉者与实践者。这既与汤显祖个人的趣尚、才情有关,也是当时曲坛的整体趋势使然。
三
理论既源于实践又可用来指导实践,实践则进而促成理论的升华,二者具有相互推进与转化的辩证关系。继屠隆率先提出“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汤显祖成功践行这一曲辞观之后,对其从理论上予以进一步探讨和总结的是王骥德,虽然在《曲律》中并无直接的“雅俗并陈”的提法。王骥德与越中曲家及沈璟等吴江派曲家交往密切,与屠隆、梅鼎祚、汤显祖等曲家交往不多,但身为戏曲理论批评家兼作家,他对三人的创作与主张都非常熟悉,推许梅、汤二人分别为“文辞一家”与“本色一家”的代表(332);对汤显祖尤为推崇,一些重要的曲学观念实源于对汤剧的揣摩与品鉴,“浅深、浓淡、雅俗之间”即是显例。因此,其“雅俗并陈”的曲辞观除源于对前代名家名剧的考较外,也和他对屠隆、梅鼎祚、汤显祖等当代曲家的剧作及主张的熟谙与总结有关。
王骥德的《曲律》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其后继续增订,直至辞世。他在该书中借《琵琶记》批评所提出的“正体”观,把“并陈”的曲辞观推到了几与“融会”的曲辞观同等重要的地位。《曲律·论家数》云:
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雕镂。《拜月》,质之尤者。《琵琶》兼而用之,如小曲语语本色;大曲,引子如“翠減祥鸾罗幌”、“梦绕亲闱”,过曲如“新篁池阁”、“长空万里”等调,未尝不绮绣满眼:故是正体。《玉玦》大曲非无佳处,至小曲亦复填垛学问,则第令听者愦愦矣!(154—55)
《琵琶记》的曲辞具有雅俗并存的特点,王骥德借以提出的“正体”观,正是其“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集中体现。比照明中期曲家的《琵琶记》批评,我们能更清楚地见出此点,因为明中期文词、本色二家对该剧虽然都有推崇之词,但观照方式却与王骥德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中期文词派的曲辞观主要体现于创作实践中,堪称其理论“代言人”的只有王世贞一人。王世贞反对何良俊置《拜月亭记》于《琵琶记》之上的说法,他在《艺苑卮言》中多方赞赏《琵琶记》的艺术成就,但肯定的重点主要还是在“作者之工”,有“词家大学问”,“琢句之工,使事之美”上(《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518、519)。与王世贞对《琵琶记》的盛赞相反,明中期的本色派曲家对该剧多有贬抑之词,只有徐渭持赞赏的态度,但着眼点却有所不同。《南词叙录》云:“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487)。“《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云云,显然是尚雅黜俗的文词派曲家的见解;徐渭则对《琵琶记》中雅、俗两种风格的曲辞都予以肯定,但有明显的高下之别。借用李贽的话,他目《庆寿》《成婚》等出的曲辞为“画工”,因其“犹有规模可寻”;目《食糠》《尝药》等出的曲辞为“化工”,因为这些曲辞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可见王、徐二人是各取《琵琶记》曲辞雅、俗之一端,虽然其间尚有畸轻畸重之别。
在王骥德的《曲律·论家数》中,对雅或俗的这种偏嗜倾向彻底改观。他在辨析本色、文词二派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以《拜月亭记》为“纯用本色”的代表,以《玉玦记》为“纯用文调”的代表,二者都不符合他的曲辞审美理想。《琵琶记》小曲“语语本色”,大曲中的部分引子、过曲则“绮绣满眼”,因其本色、文词“兼而用之”,所以是“正体”。“正体”无疑具有堂皇正大、堪为典范的意思。显然,这个“正体”既非“纯用本色”,亦非“纯用文调”,也不是“本色”与“文调”的深层“融会”,而是二者在文本表层的“并陈”。较之文词、本色二派各取雅、俗之一端的思路,王骥德对《琵琶记》的评价则是取其两端,皆予好评,前提当然是当雅则雅,当俗则俗,雅、俗各得其宜,所谓“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155),正是指此而言。
王骥德对《琵琶记》的评价有时显得自相矛盾。因为《西厢记》“极其致于浅深、浓淡之间”(《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444),是其雅俗相济的曲词审美理想的范本,所以他于元剧有独尊《西厢》的倾向。缘此,凡涉及到《西厢》《琵琶》二剧的比较时,他对《琵琶记》通常都有所贬抑(251、338、454),但在脱离与《西厢记》比较的语境时,又多有褒扬之语,乃至目为“正体”。可见他对《琵琶记》的实际评价还是很高的,只是较之《西厢记》略逊一筹而已;亦可见在“并陈”与“融会”这两种折中雅俗的策略中,“融会”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恐怕要高于“并陈”。尽管如此,“雅俗并陈”仍是他解决雅俗分裂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除《论家数》条外,《曲律》中尚有多处流露出此种倾向。如《论剧戏》谓“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207);《论过曲》谓“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212);《杂论下》谓汤显祖《南柯》《邯郸》二记“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307),皆是以并陈形态为主的雅俗相济观,虽然《论过曲》一则兼有融会型的特点。从中亦可见出,这种“并陈”不是随意地并置、杂陈,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因为有屠隆、王骥德等著名曲家的倡导,加之汤显祖《牡丹亭》等剧的示范效应,所以在其后的曲论中,“雅俗并陈”及相近的提法一再出现。如汪廷讷作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刻陈大声全集自序》云:“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所忌微独鄙俚而不驯,亦恐饶洽而太晦。即雅俗并陈矣,倘律韵少舛,其于合作无当也”(《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二集246)。首先批评曲辞创作中“鄙俚而不驯”与“饶洽而太晦”两种不良倾向,进而指出即使曲辞达到了“雅俗并陈”的境界,但如果音律不谐,也不符合曲作的要求。这里的“雅俗并陈”,显然是“并陈”意义上的曲辞观。再如臧懋循作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元曲选后集序》云:“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而要归于断章取义,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此则情辞稳称之难”(《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620)。明确提出“雅俗兼收,串合无痕”的曲辞观,较之“雅俗并陈”的提法,并置、杂陈的含义更为直截显豁。他以此为标准,批评汪道昆“纯作绮语,其失也靡”,徐渭“杂出乡语,其失也鄙”;其选编《元曲选》的目的,正是为了“尽元曲之妙,且使今之为南者知有所取则”(621)。他的这一曲辞观与屠隆一样,也是以元曲为范本,折中、调和文词派之“靡”与本色派之“鄙”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见万历年间的屠隆、王骥德、汪廷讷、臧懋循等主张文词、本色“兼而用之”的曲家,或以雅、俗“并陈”或“兼收”为基本策略,或以之为基本策略之一端。从时间上看,如果以万历三十八年王骥德《曲律》与吕天成《曲品》的成书为雅、俗“融会”型曲辞观成熟的标志的话,那么“并陈”型曲辞观的出现时间要略早于“融会”型,这当归功于其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而在“融会”型曲辞观成熟后,“并陈”型的曲辞观并未随之消亡,二者一度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一般而言,能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的观念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意义究竟何在呢?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
表面来看,“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似乎是从明中期的雅俗分裂到明后期的雅俗融合的过渡环节,是“雅俗相济”曲辞观的非成熟形态,价值和意义都不大;但通过对这一曲辞观的深入考察,可知此种看法实为皮相之见。只有从传奇戏曲自身的文体特性出发,将其置于明清曲辞观念演进的整体历程中,并与传奇创作实践,尤其是《牡丹亭》的示范效应联系起来作全面考察,我们才能深切体察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戏曲史意义。
“雅俗并陈”的曲辞观之所以为万历时期一些既认识到文词派的弊端又反对彻底求俗的曲家所认同、提倡和践行,主要是因为这一曲辞观与传奇文体特征的高度契合。一则作为已然充分文人化的舞台表演艺术,传奇的曲辞既要符合尚雅崇才的文人审美趣味,又要符合适俗美听的舞台性需求;二则作为反映社会生活面广阔的长篇戏曲,传奇中人物的身份、性格、声口各异,相应的曲辞自然当有雅、俗之别。传奇戏曲的这两个特征,就决定了其曲辞不当一味尚雅或求俗,而应具有雅俗相济的特色。正因如此,即使在片面强调文词或本色的明中期曲论中,已然可见“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端倪。如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谓“用本色者为词人之词,否则为文人之词矣”“若兼而有之,其元哉”,称赞袁崇冕《春游词》“语俊意长,俗雅俱备”(《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412),这显然是以元曲的雅俗兼有为范式,赞赏袁崇冕之曲的“俗雅俱备”。再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高则成才藻富丽,如《琵琶记》‘长空万里’,是一篇好赋,岂词曲能尽之!然既谓之曲,须要有蒜酪,而此曲全无,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所欠者,风味耳”(《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469—70),也并非完全否定《琵琶记》的“才藻富丽”,而是主张当用俗济雅,是一种“镶嵌型”或“点缀型”的雅俗观。凡此,既是万历朝“雅俗并陈”的曲辞观足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亦表明用俗济雅是文人传奇的大势所趋。屠隆等万历朝曲家的贡献,正是将这一已然存在但稍显隐晦的观念予以直截、明确的表述,使其成为引导当时传奇创作的一个重要曲学观念。万历以后的曲家对此有稍嫌片面但更为直观的体认,李渔《闲情偶寄·戒浮泛》云:“极粗极俗之语,未尝不入填词,但宜从脚色起见”,“以生、旦有生、旦之体,净、丑有净、丑之腔故也”(《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251—52)。徐大椿《乐府传声·元曲家门》云:“又必观其所演何事,如演朝廷文墨之辈,则词语仍不妨稍近藻绘,乃不失口气;若演街巷村野之事,则铺述竟作方言可也”(《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二集 57—58)。都是着眼于戏曲角色的类型差异,说明曲辞应当雅俗合宜的道理。诚如郭英德先生所言:“雅俗并陈的艺术修辞方式,指的是区别不同文体、不同语境或不同角色,当雅即雅,当俗则俗,恰到好处,适得其美”(153)。这虽是就具体的修辞方式而言,但其内在精神与万历朝“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是一致的。
万历时期“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是明清传奇曲辞审美理想的历史演进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环,为此前因依违于雅、俗之间而停滞不前的传奇创作找到了新的出口。从时间来看,“雅俗并陈”的曲辞观主要兴盛于明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曲辞观念由明中期的雅俗分裂到明末清初的雅俗融合的过渡期,亦是曲家们为进退两难的文人传奇寻找出路的时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应运而生,为徘徊不前的传奇创作指出了一条可行的出路。但如果光说不练,终究是假把式,无法验证理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自屠隆提出“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后,十余年间并无成功之作问世。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上,汤显祖的《牡丹亭》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文词派一统剧坛的沉寂局面,成为践行“雅俗并陈”的曲辞观的第一个成功范例。汤显祖之所以能认同并践行“雅俗并陈”的曲辞观,与其在后来的汤沈之争中所表现出的首重“曲意”的创作观念有关。他认为曲辞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充分传达“曲意”,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1735—36),“其中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答凌初成》)(1914)。因此,他对雅或俗并无偏嗜,惟取其合宜适用而已。加之他“才高博学”,于经、史、子、集各部均有涉猎,对前代各体文学用功颇深,这就使他在雅、俗两方面都能广泛吸收借鉴前代的文学遗产,在具体创作中左右逢源。其《玉茗堂批评〈红梅记〉》第十四出《抵扬》总评谓:“老、贴旦口中,虽不必文,亦不该太俗”(郑振铎 38),可见他对曲辞的雅俗问题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认为曲辞的雅俗当随人物的身份、教养等因素而定。反观《牡丹亭》的曲辞,绚丽典雅者有之,本色通俗者有之,当俗则俗,当雅则雅,全视具体人物、情境而定,随机变化,各得其宜,皆臻自然贴切、生动传神的化境,可谓“浓妆淡抹总相宜”;更有部分曲辞已超越了“并陈”的层次,臻于雅、俗深度融合的境界,对“融会”型曲辞形态的最终确立有导夫先路之功,如《惊梦》出【步步娇】【醉扶归】等曲,即有语不难解而含义幽深的特点。在英语文学界,莎士比亚以后的作家,都或多或少、或正或反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在明清曲坛,汤显祖的地位正与莎翁相仿,其后的很多重要曲家都深受汤显祖的影响,尤其是《牡丹亭》,始终是后人评论的焦点与学习的典范。
“雅俗并陈”的曲辞观虽有上述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的戏曲史意义,但无论多么有价值的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时限,而衡量其价值的大小则主要是看其出现的时机。这一曲辞观的进步与合理之处,是能够在时文风大行其道的时候,用以俗济雅的方式补偏救弊,承认本色通俗的曲辞风格在传奇创作中应有的地位,不失为调和雅俗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一旦脱离这一具体语境,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其不足,因其所主张的是雅与俗的并置、杂陈,而非盐溶于水、难分彼此的化合,所以在庸手的笔下,容易形成雅者过雅,俗者过俗,乃至雅、俗拼凑的局面,从而影响剧作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因此,只有将“并陈”型与“融会”型的曲辞观配合并用,才能完满地解决曲辞的雅、俗关系问题,这是“并陈”型曲辞观虽率先出现,但在“融会”型曲辞观成熟后却仍然存在的根本原因。
总括而言,明万历年间“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在戏曲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等方面均有体现,具有理论与实践递相推进、相得益彰的特征。理论方面,屠隆发其端,王骥德集其成,汪廷讷、臧懋循等殿其后;创作方面,梅鼎祚《玉合记》启其先,汤显祖《牡丹亭》肇其极,《南柯》《邯郸》二记承其波。从明清传奇整体演进历程观之,“雅俗并陈”的曲辞观及其践行者打破了当时停滞不前的曲坛僵局,开启了“雅俗相济”的曲辞审美理想,推进了传奇曲辞从雅俗分裂到雅俗融合的转化,为明末清初传奇的大繁荣推波助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转关性的戏曲史意义。
注释[Notes]
① “并陈”一词取自屠隆《章台柳玉合记序》,详见后文。
② “融会”一词取自吕天成《曲品》卷上《新传奇品》小序:“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一则工藻缋以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吕天成 22)。
③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云:“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不拘,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说笑话之类。”见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明人吕毖《明宫史》卷二、沈德符《顾曲杂言·禁中演戏》亦载此条,皆转录自《酌中志》。
④文中所列曲家的生卒年主要参考徐朔方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谱》(《徐朔方集》第二、三、四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程华平先生的《明清传奇编年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⑤徐渭《南词叙录》谓“国朝虽尚南,而学者方陋”,除《琵琶记》等数种稍有可观外,“其余皆俚俗语也”(《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486)。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亦谓“古曲”除《琵琶记》等数种外,多数皆“鄙俚浅近,若出一手”(王骥德 259)。皆是就这一阶段而言。
⑥ 徐渭《南词叙录》谓“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486)。王骥德《曲律·论家数》谓“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王骥德 154)。皆是就该阶段而言。
⑦屠隆《昙花记序》署“万历二十六年九月,一衲道人”(《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588),《昙花记》当完成于此年。
⑧ 徐复祚《三家村老曲谈·屠隆传奇》云:“《昙花》、《彩毫》,屠长卿隆先生笔,肥肠满脑,莽莽滔滔,有资深逢源之趣,无捉襟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浓盐、赤酱訾之,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二集262)。
⑨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署“万历戊戌秋,清远道人题”(《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 602),“万历戊戌”系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牡丹亭》当完成于此年。
⑩该序载《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关于该叙真伪问题,参见龚重谟《汤显祖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0—91页。
[11]屠隆《玉茗堂文集序》云:“义仍才高学博,气猛思沉。材无所不蒐,法无所不比。远播于寥廓,精入于毫芒。极才情之滔荡,而禀于鸿裁;收古今之精英,而镕以独至。其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恣(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汤显祖 3105)。冰丝馆《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凡例》云:“玉茗博极群言,微独经史子集,奥衍闳深。即至梵筴丹经,稗官小说,无不贯穿洞彻”(《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三集 31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景康:《明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Cai,Jingkang.The Selected Critical Texts in the Ming Dynasty.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3.]
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Cheng,Huaping.A History of Ming-Qing Chuanqi Plays.Ji’nan:Qilu Publishing House,2008.]
龚重谟:《汤显祖大传(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Gong,Chongmo.The Biography of Tang Xianzu.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5.]
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Guo,Yingde.A Study of the Style of Ming-Qing Chuanqi Plays.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04.]
洪昇:《长生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Hong,Sheng.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3.]
胡维霖:《胡维霖集》,《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6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Hu,Weilin.Hu Weilin Anthology.Books Listed as“To Be Banned or Destroyed”by the Editor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Miscellaneous Works.Vol.164.Beijing: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9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Ji, Yun, etal.. The Imperial Catalog of the Four Treasurie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吕天成:《曲品校注》,吴书荫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Lü,Tiancheng.Annotated Evaluation of Southern Drama.Ed.Wu Shuyi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Tang,Xianzu.The Collection of Tang Xianzu Anthology.Ed.Xu Shuofang.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5.]
王骥德:《曲律注释》,陈多、叶长海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Wang,Jide.Annotated Qu Prosody.Eds.Chen Duo and Ye C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屠隆年谱》,《徐朔方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Xu,Shuofang.The Chronology of the Drama Writers in Late Ming Dynasty: Tu Long. Collected Works of Xu Shuofang.Vol.3.Hangzhou: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3.]
——:《晚明曲家年谱·梅鼎祚年谱汤显祖年谱》,《徐朔方集》第四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The Chronology of the Drama Writ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Mei Dingzuo and Tang Xianzu.Collected Works of Xu Shuofang.Vol.4.Hangzhou: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3.]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Yu,Weimin,and Sun Rongrong.Compilation of Xiqu Criticism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the Ming Dynasty.Hefei: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2009.]
——:《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Compilation of Xiqu Criticism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the Qing Dynasty.Hefei: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2008.]
郑培凯:《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Zheng,Peikai.Tang Xianzu:A Life of Drama Dream and Cultural Search.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5.]
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
[Zheng,Zhenduo.The First Collection of Ancient Drama Serie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