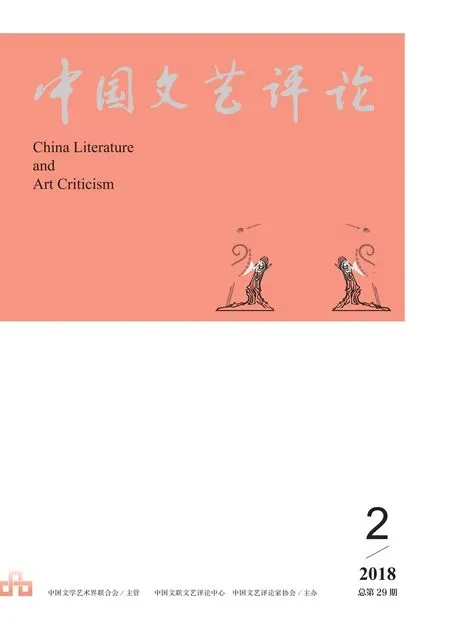诗学“三命题”刍议
——关于诗中“大我”“小我”的思考
2018-11-12罗辉
罗 辉
所谓诗学“三命题”,是指“诗言志”(《尚书·尧典》)、“诗缘情”(陆机《文赋》)与“诗缘政”(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这三个关乎传统诗学本原的问题。对于前两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对于后者,不知何故,却鲜为人知。当下,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统诗词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诗”与“志”两字的字源问题,闻一多先生研究过:“可以证明‘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当然,经过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后,“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体,从“志”的一个义项中分离出来。从字面上看,“言志”屡见先秦典籍,而“缘情”出自陆机,时间要晚得多,“缘政”则是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认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显然,认识诗与志、情、政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是需要认识诗与“志”的关系,这就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诗”与作者或读者之“心”永远相连。二是需要认识“志”与“情”的关系,这就是“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三是需要认识“人”与“政”的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的本质是“政治”,任何时代的诗人都不可能超然“政治”之外。所以,“在心为志”或“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并“发言为诗”,而作为“发言”的主体——作者、“接受”的主体——读者,又总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社会人”。千百年来的诗史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尽管诗坛对诗学“三命题”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却是客观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大我”“小我”与“诗言志”
诗中之“我”有“大我”与“小我”之分,是学界对自我与时代关系的形象表述。借着这个概念,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诗学“三命题”:一是从字义上看,“诗言志”之“言”,说的是诗“言”什么即写什么的问题;“诗缘情”或“诗缘政”之“缘”,说的是诗“缘”于什么即为什么写诗的问题。二是从诗体上看,文主发议论,诗主达性情,诗是用来彰显志向与抒发感情的。其中,“情”“志”两字,通常可用“情志”一词统称之。其中,“志”偏重“理性”,往往关乎“大我”;“情”偏重感性,往往关联“小我”。三是从诗材上看,有“大我”与“小我”题材之分,两者分别对应着“大我”之志与“小我”之情。四是从接受诗学的角度,将诗的“生产”与“消费”统一起来看,无论是写“大我”题材还是写“小我”题材,都与“小我”——作者或读者相关,同时又离不开“大我”。这是因为传统诗词是最富有个性、人性与时代性的文学体裁,一切作者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正如黑格尔所言:“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赖于特殊的历史的其他的观念和目的。”
显然,诗词创作需要诗人“自我”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只有进入无意识中,天才才成其为天才”(歌德语),也只有“本我”的存在,于“精神的无意识之中,隐藏着灵魂全部力量的根源”(伯格森语)。然而,正如相关学者所言,“自我”是在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凸显出来的,在语言中“我”作为主体的代名词,只有在与其他人称代词的关系网络中才能成立。脱离了这个关系网络,便无“我”可言。离开群体,所谓个体便无从谈起。这也充分说明,生活在“大我”中的诗人,其诗中的“自我感受”,自是脱离不了“外部经验”,必然会打下时代的烙印。从创作的角度看,诗的意象选取与意境营造,首先是诗人“小我”的切身体验,表现“大我”也是通过“小我”的感受去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在诗词创作中,是无法将“大我”与“小我”截然分开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大诗人”与“小诗人”,但这里所说的“大诗人”与“小诗人”,不是以诗作题材中的“大我”与“小我”来区分的,而是由每一位诗人的人品、诗品及其社会接受度等综合因素来决定的。对于不同时代的“大诗人”来说,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其人品与诗品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大我”。
众所周知,传统诗学理论是以“情志为本”的。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写“大我”题材时,诗作更体现为理性之“志”,而写“小我”题材时,诗作更体现为感性之“情”。《文心雕龙·附会》又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就是说,传统诗词讲究“情志”“事义”“辞采”与“宫商”四者的协调。孔子关于“《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至理名言,更是揭示了传统诗词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大我”或“小我”题材,诗所言之“情志”自当“无邪”,这也是“宜正体制”的应有之义。它与西方诗学所推崇的“诗不再承载着‘善’的使命,也不再以追求‘真’为目的,而一心一意地经营‘美’”的理念是不同的。
千百年来,无论是写“大我”题材的诗作,即言“大我”之“志”,还是写“小我”题材的诗作,即言“小我”之“情”,传统诗词的审美取向都必须用“礼”来规范。正如《荀子·礼论》所云:“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儒家经典中关于“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使人“和在心”,礼使人“敬在貎”等理念,论述了“诗、礼、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所蕴涵的内核,就是传统诗词意境所代表的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艺术追求。
这里,可用苏轼的两首《江城子》来作一说明。其一为《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二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显然,这两首相同词牌的词,其风格迥异。第一首词的题材关乎“大我”,是言“大我”之志,通过千骑出猎的描写,抒发了作者豪迈刚健的英雄气概,表达了作者为国效力、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而第二首词则是一首著名的悼亡词,其题材与“小我”关联,是地道的言“小我”之情,作者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梦遇亡妻的情形,表达了对亡妻深挚的思念之情。
二、“大我”题材与“诗缘政”
古今中外的诗学史表明,文化是诗歌的土壤,诗歌是文化的产儿,诗歌永远离不开它的时代,离不开它的民族文化。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那句名言“看来好像很奇怪,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就是对此最好的印证。对中华诗学而言,传统诗词的题材大多关乎“大我”,即诗所言之“志”,首先是“大我”之志,也就是与“政”密切相关的“志”。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是儒家思想,其核心可以说是“君子文化”。孔颖达围绕“诗缘政”,还明确提出了“非君子不能作诗”的概念。这就是《正义》疏所云:“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诗故也。”自古以来,《周易》中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始终是包括诗人在内的历代有识之士的座右铭。可以说,君子文化孕育了“诗缘政”,而“诗缘政”又让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成为以“大我”为题材的传统诗词一以贯之的审美标准。
例如,从屈原的“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到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鲍照的“捐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陈子龙的“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柳亚子的“飘零锦瑟无家别,慷慨欧刀有国殇”,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讴歌的捐躯报国精神,千百年来,一直强烈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志士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并始终鲜活地反映在历代诗人的诗作中。这也是“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陆机《文赋》),进而彰显诗教功能的真实写照。尽管各位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尽相同,但各自诗作的意境却彰显了相同的审美体验,这就是君子人格的诗意表达。
又如,从王昌龄诗《出塞》到祖咏诗《望蓟门》、王维诗《使至塞上》、李白诗《塞下曲》、高适诗《燕歌行》、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岑参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刘禹锡诗《西塞山怀古》、李贺诗《雁门太守行》、杜牧诗《河湟》、温庭筠诗《苏武庙》、李商隐诗《随师东》、范仲淹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诗《边户》、王安石词《桂枝香》(登临送目)、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岳飞词《满江红》(怒发冲冠)、陆游诗《书愤》、张孝祥词《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辛弃疾词《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与《永遇乐》(千古江山)、文天祥诗《正气歌》、元好问诗《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于谦诗《咏石灰》与《出塞》、戚继光诗《望阙台》、郑成功诗《复台》、丘逢甲诗《春愁》、孙中山诗《挽刘道一》、秋瑾诗《感愤》、鲁迅诗《自题小像》与《无题》、毛泽东诗《长征》……这些不朽的诗篇雄辩地表明,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那些耀眼夺目、奔腾不息的流韵,其题材无不涉及“大我”,所言之“志”无不彰显家国情怀。
古人张载的经典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早已融化于历代诗人的血液之中与灵魂深处。他们的许多佳作,也经常是“道己一人之心”,“言一国之事”,“总天下之心”。(《毛诗序》)即使诗人之诗意可能是萌发于一时一事、一草一木,但他们的诗心却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那些以“大我”为题材的历代诗词名作,字里行间所蕴涵的“大我”境界,植入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成为“诗言志”的永恒主题。“诗缘政”中的“政”,其首要之义是“政治”与“政事”;“诗缘政”中的“缘”,或解为“通”,即诗与“政”贯通;或解为“因”,即诗因“政”而作,因“政”而兴。
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其含义远比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要丰富得多。政治在古人眼里,不仅是指国家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的贯彻,社会安定状态的实现,而且它更富含道德评价意义。”这就是说,“缘政”之诗,其题材将更加宽泛。然而,对于与“政”相关的言“大我”之志,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国昌《回归审美: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与出路》就认为:“‘诗言志’的主张明确地指出了古典诗词的专注内心、感物兴怀、寄情山水的独特审美功能。面对当代中国文学媒介多样化的背景,在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报告文学等不同文类所承担的文学功能相对明确的前提下,过于放大旧体诗词功能发挥的文学功能,不但无助于旧体诗词创作水平的提高,反而有损于旧体诗词作品的自身完美。如果说当下的旧体诗词创作能够在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和反思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方面更展现其独特性的话,那么旧体诗词创作者就不应当过于注重对重大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问题的表现。”这里,郭氏关于“诗言志”有其独特的审美功能当然是对的,但“不应当过于注重对重大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问题的表现”的提法却值得商榷。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描写的就是重大社会事件,但其独特的艺术效果,却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可替代的。当代诗坛的问题不是“不应当过于注重对重大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问题的表现”,而是如何遵循“诗缘政”的理念,更好地用“诗家语”来表现“重大社会事件”与“新闻热点问题”。
自古诗魂壮国魂,当代诗人更应坚定文化自信,弘扬“诗缘政”的优良传统,坚守“诗无邪”的本质要求,发扬“主文谲谏”的文化传统,按照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要求,善于以“大我”为主题,选好“切入点”,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来。
三、“小我”题材与“诗缘情”
斐斐《诗缘情辩》认为:“大率而言,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并断言:“我国古代诗论的主流不是言志论,而是缘情论。”显然,该书作者的观点与传统诗学中的观点一样,是基于“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说的。但是,若是借助诗之“大我”与“小我”理念,又可将两者统一起来解读。
如前所述,对于以“小我”为题材的诗作,“诗缘情”即为刘勰所说的“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其感发动因就是个人的情感。正如孟庆雷《钟嵘〈诗品〉的概念内涵与文化底蕴》所说:“对于魏晋六朝诗学理论来说,诗歌与创作主体的个体性情之关系也随即成为理论关注的重心,‘诗缘情’即是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得以孕育、诞生。”中国历代许多论述“诗”与“情”的名言,亦是在论述同样的诗学观点。例如,“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诗本人情,情真则语真”(林弼《林弼诗话》)、“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徐祯卿《谈艺录》)、“词家先要辩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卷四)……这些名言中的“诗”与“情”成为“缘”的两端,一端是“因”,即诗人写诗是源于“小我”之情;一端是“果”,即诗人通过书面发“言”,写出了以“小我”为题材的“诗”。
孟庆雷还认为:“随着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理论的提出,即与此前一直盛行的‘诗言志’观念在理论上有着不同的旨趣,把诗歌由外在的事功价值转向内在的个体感受。”该书作者的系统研究表明,一是遵循传统的文化语境,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说明“诗由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的工具一跃成为展现个体精神风貌,体现自我风采的行为方式,甚至是个体本真生存的展示。”二是从字义解读出发,学界似未注意到“诗言志”中的“言”与“诗缘情”或“诗缘政”中的“缘”两者之间的区别。若是基于“文之理法通于诗,诗之情志通于文”(《游艺约言》)的理念,“通于文”的“诗之情志”,自然包括关乎“大我”与关联“小我”之“情志”,“诗言志”就是“诗言情志”。这样解读“诗言志”与“诗缘性”,一个说诗写什么,一个说为什么写诗,两者就可以不再对立了。
需要说明的是,以“小我”为题材的诗作,“发乎情”,但必须“止乎礼义”,即不能背离“大我”的主流价值观。清人叶燮《原诗》云:“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这就是说,“诗缘情”之“情”,其“源”表现为“诗之基”,其“流”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黄庭坚就说过:“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钱钟书也说过:“夫‘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者情感之天然发泄,而歌者情感之艺术表现也。‘发’而能‘止’,‘之’而能‘持’,一纵一敛,一送一控,相反而亦相成……”这就是说,诗人作为“诗缘情”的主体,尽管抒发的是“小我”之情,不涉及“大我”,但亦应懂得接受诗学的道理,重视诗作“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始终坚守社会责任,讲求社会效果,对自我情感进行必要的节制与调节,远离庸俗、低俗与媚俗。
实际上,传统诗词中的“喜怒哀乐”,自然会体现君子文化所推崇的艺术风格。无论是“喜而得之其辞丽”“怒而得之其辞愤”“哀而得之其辞伤”“乐而得之其辞逸”,还是“失之大喜其辞放”“失之大怒其辞躁”“失之大哀其辞丧”“失之大乐其辞荡”(《金针诗格》),传统诗词所“缘”之“情”都是源于“思无邪”而“止乎礼义”之“情”。从诗祖屈原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词宗苏轼,再到当代的许多著名诗人,他们的赤子之心与诗学文化心理,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诗人词家与广大诗词爱好者,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当然,“诗缘情”既要求“道”之“善”、“情”之真,同样要求“辞”之美。《礼记·乐记》云:“情欲信,辞欲巧”,就是主张情辞并重。辞中有情而巧,情中有辞而信。只有用“诗家语”来描述真情实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诗作。
余恕诚《诗家三李论集》认为:“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为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该书还说:“《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今天,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千百年来传统诗词中的诗情画意君子心,却是一以贯之地蕴涵在经典佳作中,并不断闪耀出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