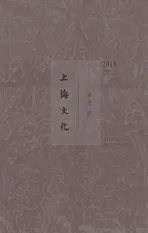谁是作家的敌人论阿乙
2018-11-12徐兆正
徐兆正
《作家的敌人》在阿乙的短篇小说谱系里多少有些特殊。首先,是故事的取材不再直接来源于一个实际发生的事件,而是某一抽象结论。小说正是围绕着这个结论展开的叙事。倘若我们熟稔作者历来对真理表露出的(或多或少)敌意,难免将诧异于此一小说悖离了从前的写作程式。换句话说,这一次决定写作的不再是一幅简略的场景、一件古旧的逸闻、一段崩坍的回忆、一场无休无止的对话,而是一个部分给定的清晰结论:作家的敌人……存在着。至于谁是作家的敌人,作者以叙事进行了一番追踪。
不过,更令我诧异的是小说并不止于呼应作者在随笔《写作的秘密》中的说法——从抽象理念出发的写作,其危险在于虚构的想象能力将让位于知性的论证,也就是说冲突的双方将被一个独一的、为作者僭越的真理主体所取代:文本中将不再有作者的分裂,也不再有两重自我之间的争执,而只剩下一个复活了的19世纪的道德上帝,它声明、审判并且宣告人间的法则真理。在此,真理的一元性仅仅暗示了服从或违逆将导致的拯救与毁灭——《作家的敌人》并没有陷入这个泥淖:当它看起来极不真实的时候,小说正是某一现实的缩影;而当作者有意表征这个缩影的真实性之际,故事又转而自证它是一个未经实现的乌托邦。这一点与小说在写法上的独特性不无关系。
在文学匮乏的现今,一个有天赋的人除了把自己——仅他一个人——变成文学,还能做什么呢
在文本中将注意力转向写作——此类元小说作者的确较少涉及,但是我们会看到阿乙如此为之,反倒是要抵消小说从理念写起可能发生的危险。简单地说,他制造了两个互相敌对的自我,不过是要取缔任何一种尝试着主宰文本的真理声音的合法性。除此以外,读者还要避免将这篇小说视为文坛秘辛之类的记录。因为这样无疑会抹煞作者谋篇上的苦心,也会悬置乃至舍弃作者对“作家的敌人……存在着”之后“谁是作家的敌人?”这个问题的追问;在我看来,它同时也是围绕着此一文本蕴藉的元小说与真理之间辩证关系的考察。但在此之前,我们必得先行廓清元小说的理论意涵及其他一些问题。
狭义上的元小说(概念)最早由威廉.H.加斯界定,他本人正是个中实践的一把好手;至于广义上的元小说——作为组构文本的自我指涉与囊括的元素——则并非迟于20世纪才出现。这一点是元小说与其他文学技巧的根本分际。自从塞万提斯抑或一个半世纪之后的斯特恩将它发明出来,自我指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技巧。我们看不出后世的元小说在本质上较之前辈有何逾越,反倒是在有意识的谋篇布局上,出于全文的自我指涉显露了停滞与返祖的迹象。究其根源,文学史缺乏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是其一,其二是元小说与小说在根底上有诸多契合之处,或者换个说法:元小说代表的是小说写作者对虚构本质的沉思。
在我看来,笛卡尔在《私人沉思》(1619)中写下的寥寥数语便是这一本质:“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世界这个剧场的一位观众,但现在,我准备登上舞台,并且戴着面具前行。”笛卡尔的这句话此后不断被人引用与改写;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也如是写道:“全部文学意味着‘Larvatus prodeo’,即‘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手指着自己的假面具’。”戴着面具,也就意味着作者在文本里部分地废除自我,他要另穿一件外套出场,换另一种身份行事,以另一种声音说话。尽管如此,这种废除也并不彻底(完全成为另一个独一的自我),也无法彻底(新的自我必得有赖旧的自我支配),它仅仅意味着写作者在分裂中为自我生殖了一个新的角色。文学的本质在于此一分裂生成的张力;任何时代的社会审查(斯宾诺莎)/心理审查(巴塔耶)因素一旦加剧,这种张力就会特别突出。
在20世纪下半叶,作者的彻底消隐表征的正是此一张力起伏的历史终局,而这一事实预先体现在佩索阿的断片写作中。如果说文学的本质处在写作者与其生产的另一重自我的张力之间,那么这个遁世者无疑是以他自身的消失为砝码,增加了另一重自我的重量。事实上,作者已然通过他所创造的大量异名人物及在其名下的那些作品,组成了他唯一一本——也就是说,佩索阿的确写成了一本在文本上支离破碎、有待读者自行编织的——“人格之书”。佩索阿因此称得上是极端怪异的普鲁斯特,但他馈赠给我们最富教益的一点却莫过于:由于佩索阿使用异名创作的缘故,我们引用他的任何一句话也都无法再归入作者名下,因为他并不以其初始的身份讲话,而是制作了无数张面具,藉此安排自己身上的众多生灵去完成各自的人格认同,诚如他在《论异名》一文所说:“在文学匮乏的现今,一个有天赋的人除了把自己——仅他一个人——变成文学,还能做什么呢?”
以上述角度观之,所谓元小说,便是两个或多个自我相遇的故事。如果时间最终证明后现代诸小说家将元小说搞砸了——这一点并非不可想象——那只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将自我指涉缩小为一项技术,而非反身的本真自觉。也就是说,作者创造出来的自我不再反对与质疑作者本人的真理,而作者也不再从形式层面对其所述之内容有所警觉和反思。元小说是作者分裂自我、打碎自身主体性的道路。把握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把握到《作家的敌人》的精髓:这篇小说是作者同时从两个人物(陈白驹,青年小说家)或者说同时从两个“危险的自我”的角度完成的自我指涉之作:他既将陈白驹看作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个危险自我,也将那个年轻写作者视为过去未曾发生的一个危险自我。因此,作者看似置身事外,叙事仿佛波宁水平,文本之下却隐藏了作者向前与向后观看到暗礁时的胆战心惊。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采用多角度刻画自身的其他几个文本,均不如这一篇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开篇即从爱伦·坡的《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里撷出了一句话(“靠已经获得的荣誉安度晚年”)作为小说题词,隐喻已然功成名就的陈白驹,正文部分则转而写起年轻小说家的情形:“年轻人就坐在那儿……”由此起始插叙了这位小说家为了创作所度过的不健康生活。在正常时态里,他被介绍到一个文学界的饭局中,此刻正等待着文坛中人的考核。对写作的种种障碍的描绘直到“在接到打印稿的同时,绑架就开始了”这一句起,陈白驹才再次出场,并且回忆了之前对这个年轻作者的印象:“两年前,或者三年前(时光真是快啊),如果没记错的话,陈白驹是见过这年轻人的。”这个插叙有如缓冲和延宕,意味着陈白驹对青年人的看法并无改观,也为下文的形势突变的火星积蓄了木柴。
陈白驹的回忆结束时,小说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萨特在《文字生涯》中做的居间题词:“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小说由此恢复插叙中断的讲述:“今天,情况有变。至少是陈白驹,像中弹一样,死在了对方的第一句话上。”但在陈白驹意识到这位年轻小说家的天才时,后者也随之死去,而陈白驹继续固守在自己的平庸中安度晚年。以上就是小说的大致结构。
这两个人的对跖者关系毋庸多言,我们已经看到作者是从两个互为敌对的角度予以展开和完成叙事的:一方是沉默、太沉默的青年小说家,更像是一片沉默的影子似的存在,一位缺席者,一个没有资格在文本的宴席中发表见解的下层人,但至后文则峰回路转,这种沉默倒更像是一种沉默的反讽:“那稳坐在一旁,几乎是揶揄地看着他们(是的,揶揄!)的人”;“即使是那偶尔出现的错别字,阅读者也害怕去修改,因为正等你提笔要斧正时,分明又看见作者那猎人般的耻笑”;一方是虽然在写作上已功成名就却不乏滑稽与嫉恨的中年小说家形象。但更需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作者是借用这两个人的视域来审视自我的诸种可能性。
那位引人注目的文学青年在不到两年(?)之内于写作上发生了巨大改观,然则作者却并未明确这一转变何以发生。同时,勾连起故事主体的也是这个文学青年有所改变前后的一首一尾:最初怎样,后来怎样,至于这之间的过程概付阙如,全赖读者想象。作为一个意外且重要的空白叙述,青年小说家代表了一种文本的可能性:《作家的敌人》由此被归类于那种中心缺席的元小说。与之相比,陈白驹的角度对于文本的意义就并不那么强烈,它更像是作者向自我提出的警告。置身陈白驹的视域,会看到一望无尽却毫无可能改变的日子的可能性:安于荣誉,代价就是无能于继续分裂自己,在杀死写作的荣誉或者说平庸的泡沫里,捱过时日;而将陈白驹与青年小说家的视域合而观之,尤其是后者那历经缺席的两年之后发生的转变,毋宁说是代表了作者之于新长篇写作的回顾、反思与期待。
至此,问题即演化为:什么样的荣誉?究竟是无限性的安慰,还是世俗构成价值的收受?真正困扰与刺激作者写下这则寓言的动力,也在于此
“名誉经常使一个作家变得十分虚荣,但是很少会使他变得骄傲。”
——W.H.奥登《论写作》
青年小说家日夜苦心孤诣于创作而葬送健康,陈白驹在当年同样经历了这样的险境,为此他有效地绕开了,以放弃独创性的写作为代价。两者勾画出了一条在生活与写作之间摇摇欲坠的道路,一面是生活对为想象的激情之火所环抱的写作抱有的敌意,一面是写作对生活的冷静自制所未曾中断的困惑。不过与其说它就此表明生活是写作之敌,不如说这一畏途复现了此在的有限性与写作的无限性之间的古老冲突,而它们的焦点正是荣誉问题——这也是阿乙在《作家的敌人》试图讨论的根本题旨。
至此,问题即演化为:什么样的荣誉?究竟是无限性的安慰,还是世俗构成价值的收受?真正困扰与刺激作者写下这则寓言的动力,也在于此。就后一种情况来说,它根据写作者的精神“独创性”(一部新的小说诞生就是为社会的精神贮藏添一笔新的财富)提供给对方在劳动分工的社会中畅通无阻的价值:但此一被予以认可的价值并非通过写作这一行为创造出来,而仅仅是写作最微不足道的效果:将作者还原为现行价值参照体系的有机个体。我们看不出陈白驹在小说中有何愧怍,即便是故事结尾时他像孩子一样笨拙地哭泣,也无非是为自己没能清清白白地参与到价值流通而内心不安(如果他能够创作出像这个年轻写作者一样的杰作,他会更有底气——举个例子——到徐萍家喝汤)。
这便是写作的停滞,写作的降格。当写作无能于创造和设定新的价值,就会如弃妇一般遥望社会并且期待它本着契约精神兑现曾经给出的承诺:“奴隶在主人的位置上幻想着自己凯旋的形象”。相形之下,无限性的安慰就更关乎人的概念,小说从居间题词之后即开始描述那样一种人们在阅读到杰作时产生的不可遏制的狂喜:“出于一种恐惧,就像行夜路的孩子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陈白驹合上文稿,以为凭此就可以躲开那种优秀对自己的折磨。然而徒劳。在合起来的纸张内,那些不同脾气的人物及它们之间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还在有条不紊地朝前运转着,就像装了什么神奇的小齿轮或有魔力的大转盘,就像是上帝已然撒手不管的漆黑宇宙,自有其永动的秩序与规律。”如果说作者能够体会这种创世的愉悦,读者同样能够体会:彻底的认识,彻底的创造,并不仅仅对应于一种荣誉,在无限性的安慰意义上,它更倾向于意味着人能够成其所是,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世间的荣誉观念始终都在寻求一份“确实如此”的证实,而真正的荣誉——无限性的安慰——乃是无从证实的,是“我愿如此”。
大半个晚上,他都捏着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他是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市作协、书协副主席,归有光文学院荣誉院长,师大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库》杂志联合主编,袁枚奖、归有光奖、AND诗歌奖终身评委),沉浸在一种想要去投缳自尽的沮丧情绪中。当他去卫生间尿尿时,发现小便淋漓不止,颇像狂风飘刮中的细雨。而镜中的自己,发根那里已白白一片。早上看还是黑的。
早上他意气风发。出门前鼓动两腮与唇部,用国外牌子的漱口水漱口,然后又在好一阵犹豫中拉开冰箱的门,伸出右手中指好好蘸了一块黄油。之所以用中指而非食指,是揩油的面积会大一些。“好吃极了。”每回陈白驹都这样,一边舔一边对着它忘情地赞叹。
小说里寻求荣誉之证实的例子很多,诚如上面这一段,它们落实在奖项、身份、资格与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哪里都有写作的影子,唯独写作之中没有。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性介入的困局,而写作真正能够带来的荣誉恰恰是社会性的暗夜。然而,陈白驹在锦衣玉食之中仍可感受到的那种无能的沮丧,也反过来说明他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实情。这是提问与回答结束的地方,是个人退隐至其自身时陈白驹向自己证实的又一件事:他与写作已没有关系。无从证实,还因为无限性的拯救并不处在理性的视域之内:“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从理智上进行理解;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还原为一个论断;也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语言中得到表达。”无限性的安慰同时也是一个非理性的断言,是写作者沉浸在写作的深海,而一群获奖者与一切可资证实的荣誉却无法令自身潜入其中,是故坐在海边望洋兴叹。
因此之故,我更愿意将奥登的话理解为写作者应当终生持有的一份警惕。尽管有两种荣誉——一种对应于创造性的敞开,一种对应于构成性的封闭,然而荣誉的实证主义倾向在更多的时候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否决掉前一种荣誉观念,拆毁那本来能够加以区分的可能,以及挫败作家本来可能养成的骄傲,朱迪斯·萨德本式的骄傲:为了写作,“如果我能够快乐那我就快乐,要是我必须受苦那么我也是能够受苦的”。
❶ 见第六则:“写作的耻辱在于,总有一个无形的长者,他是你的共谋,告诉你怎样才能骗到读者。演讲的耻辱也如此。效果的奴隶。”(《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第2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但这篇小说无疑要比“作家刻意讨好的邀赏本性”这个观点更为深入。
❷ 另一篇是收录于《灰故事》的《蝴蝶效应巨著》。
❸ 鉴于此,有必要在分析结构与题旨之前,就让那些习惯为小说寻找现实参照系的天真读者(一个来自于福克纳的笑话:在我们镇上,唯一的文学批评活动就是人们找出我在小说里又影射了哪一位太太或先生)获悉如下事实: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均来自作者的自我指涉:隐藏最深的不如说是小说结尾处陈白驹朗读的作品片段,是阿乙处女作《在流放地》(收于《灰故事》初版本,再版时被删去了)的开篇;青年写作者的形象—— “他姓甚名谁,陈白驹已忘了,只记得春卅说:‘他也是位写小说的。’此语一出,一团火便在年轻人的脸上腾腾地燃烧起来。不是不是,年轻人嗫嚅着,痛苦地摇晃脑袋。也因此,陈白驹当场就判断他一篇小说也没发表出来。”——则是阿乙早些年经常描述的一个场景。
❹ 现代作家的特质是设置谜题:有关镜子的隐喻不知解放了多少作者的想象力,但是除了象征,语言、形式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即它们必须转化为书写的一个契机,成为写作得以可能的奇迹。它们与文本的关系应当是有机的。
❺ 转引自巴塔耶《内心体验》第65页译注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尉光吉译,译文有所修改。
❻ 尼采在1886年读过司汤达的《拿破仑传》后做过一些摘抄,其中一则出自传记的前言部分:“我心中一种近乎本能般的信念是,人说话时必定会撒谎,而在他写作时更是如此。”尼采在这句话前加上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标题:关于面具问题。参看《1885-1887年遗稿》第206至207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孙周兴译。
❼ 《写作的零度》第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幼蒸译。
❽ 已有研究者开始根据散落的信息考证各个异名者的生平、特质进而制作这本“人格之书”的副本。这种传记实属罕见,但可能也仅止于趣味。不过不要忘了萨拉马戈据此写成的伟大小说:《里卡多·雷耶斯逝世那年》。
❾ 在这篇文章中佩索阿还写道:“我有人格解体和模仿的倾向,这个倾向持久且具有根本性,而我的异名的精神起源就在于此。有一点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很幸运,那就是这些现象会自行理智化,我的意思是,它们并不会出现在我的实际生活中,并不会出现在表面上,不会出现在我和其他人的交往中;它们只会在我内心中爆发,我与它们共存”(第18页);“对于这些书的作者在心中慢慢创造出来的每个人物,作者都会给予它们富于表现力的性情,并把人物看成是一本书或数本书的作者;在那些思想、情感和艺术之中,他,真正的作者(或是表面上的作者,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情是什么),从未发挥任何作用,而在写出他们的过程中,他只是他自己创造出的角色的媒介。……他写作时就好像有人把书中的内容口述给他一样,仿佛是一个朋友进行口述。”(第25页)《自决之书》,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年版,刘勇军译。
❿ 《李文俊译文自选集》第171页,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⓫ 日常生活可能富有欺骗性,却并非无关紧要或应视之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它是一切积极与消极可能的发源地。
⓬ 至于那位青年小说家,作者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可以料想到如果他渡过此劫,也会是下一个陈白驹。又,小说里陈白驹评价一批四处搜刮赞美的青年作家:“这些货自命为天潢贵胄,却管教不好他们的自卑,显得特别敏感和神经质,一批批的,遮蔽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堪比蝗害。”徐萍回应道:“你当初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可对观之。
⓭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1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周颖、刘玉宇译。
⓮ 参看福克纳《记舍伍德·安德森》,“仿佛他写作甚至都不是出于那种耗费精力、永不休止、难以餍足的对荣誉的渴望,而是为了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东西:甚至还不是为了不值一提的真理,而是为了完美,为了无与伦比的完美。”《福克纳随笔》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李文俊译。
⓯ 见艾德·米勒、容·延森 《万物的追问》第一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蓝江译。
⓰ “虚假的骄傲把它一时之间的不理解转化为轻蔑与残忍也因此把自己扭曲成愤激与刻毒,可是真正的骄傲却可以不贬损自己地自言自语我在爱,我可不愿接受任何代用品;在他和我父亲之间有点不大对劲儿;如果我父亲是对的,我就再也不见他,要是错了那他回来找我或是派人来把我接去的;如果我能够快乐那我就快乐,要是我必须受苦那么我也是能够受苦的。”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李文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