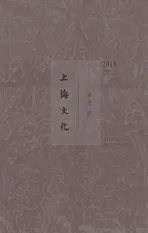宴无好宴读张怡微《细民盛宴》
2018-11-12王辉城
王辉城
一
在某个大雾弥漫的清晨,一阵哀悼的唢呐,穿透清冷的露水,钻进我的被窝。一位叔公,离开了。全村人很快就聚集在他家,分工处理后事。有人通知远处的亲朋,有人分烟倒茶,有人蒸饭做菜,有人点炮烧纸,有凄凄哭声……热闹是克制的、压抑的、肃穆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与葬礼。直到如今,当耳边响起唢呐声,我第一反应总是死亡与葬礼。
张怡微的长篇《细民盛宴》开头,便是令人不安的死亡。爷爷的“死亡”把袁家人聚在一起。父亲利用此机会,完成了难以启齿而又艰巨的任务:让女儿与再婚妻子相见。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系上了情感的线。
袁家的兄弟姐妹虽然不至于反目成仇,但也因现实利益分割,各自社会地位不同,各有生活,显得生分。爷爷的死讯,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大伯在家带孙子,二伯在北京顾狗,三伯躲债,小爷叔老婆在乡下顾成衣厂,他人在上海轧姘头,顺便挤出时间来祁连山路付过一两次水电费,就觉得自己对双亲已经仁义至尽”。只有爷爷袁焕荣面临死亡,分散各地的袁家人,才重新聚在大自鸣钟的老宅里。
在“没有死又马上死”的局促中,死亡成为一出喜剧,处处映照现实的荒诞。大伯家的五岁小天王,一句童言无忌——“太爷爷,你到底什么时候死啊?我要吃濑尿虾”——把荒诞推向最高点。
小天王这句触目惊心的话,无疑是文学对现实的冒犯。太爷爷的死亡,对于小天王来说,远不如一道濑尿虾重要。在小天王的心中,死亡是一个模糊的词汇,一个遥远的概念,他尚不能理解伴随死亡而来的悲伤与家族秩序的坍塌。
“我父亲所赋予我们的,还有类似于中国旧家族的伦理模式”,似乎逐渐被逼仄的现实所瓦解。作为大城市里的细民,没有宽裕的空间——一年辛苦工作,只能买个小厕所——去盛放大家族式的亲情。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一直强调血缘浓于水,个人附庸于家族。但父亲这一辈之间关系并非“血浓于水”,而充满着紧张、对立。张怡微塑造了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小叔骗光了奶奶的钱,最后逃离家族,成为大家口诛笔伐的对象——来完成对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消解。城市建设补偿的房屋拆迁款,更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家人对拆迁权的争夺让血缘亲情彻底变成虚与委蛇的物质关系。
小天王是“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直刺此次家族宴会的实质。袁焕荣虽未离世,但他已被家人当作“死者”或事件来对待。家族聚会彻底成为一场闹剧,死亡没有了庄重与悲伤,只有对“血缘家族”的消解与嘲讽。父子反目、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姐妹结仇……都是日常生活里反复上演的戏码。家族名存实亡,只能以“宴会”的名义,苦苦维系着。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Jean-Marc Albert)在《权力的餐桌》一书中,有句鞭辟入里的妙言:“餐桌艺术是一种统治艺术。餐桌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围绕着吃,可以产生决策,可以张扬势力,可以收纳,可以排斥,可以论资排辈,可以攀比高低,吃饭简直成了最细致而有效的政治工具。”当然,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宫廷餐桌艺术,其着眼点高屋建瓴,距离细民们的生活未免太过遥远,但也深刻地揭示了餐桌里人际关系的本质。
大到国家宴会,小到情侣约会,餐桌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权力的关系。不说国宴,就说生活中较为隆重的宴会,谁贵为上宾,谁位列末位,都昭示着客人与东道的关系几何。情侣约会的晚宴,或是两人关系的开端,或是出于纪念。所以,作为聚餐的仪式,作为权力场,宴会多多少少都带有表演的意味。
二
满月酒、毕业典礼、婚宴、生日宴会……人的一生,需要参加或经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宴会。与死亡相关的宴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满月酒意味着生命经过了最初的考验,想必古时候婴孩成活率低,便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各种大大小小的宴席,昭示着个人进入新的生命阶段,适应新的角色。新人举办婚宴了,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是儿子或女儿,而是丈夫与妻子。死亡意味着现实关系的终结,我们通过葬礼与死者建立起历史的联系。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每个人生活的基本,也是大多数人的焦虑所在。中午吃什么菜好,房价什么时候下跌,孩子的成绩怎么下降了?这些鸡毛蒜皮之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图景。重复与机械,乃是人生的常态。人生这部注定了结局的电视剧,大部分是无聊的。
为了对抗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无聊,宴会便显得无比重要。它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个逃离的机会。虽然这番逃离,仅仅只是短暂的三五天。经典电影《教父》里开场长达二十七分钟的婚礼,热闹非凡又暗藏玄机,江湖里的刀光剑影,都被歌声与舞蹈所掩盖。这种盛大的、隆重的喜悦,赋予了人们继续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细民,小老百姓、平民也。宴,仪式也,表演也;盛,盛大,多也。“细”与“盛”,形成了极端的对比,让人不禁想起绣像本《金瓶梅》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隆重与滑稽。小老百姓偏偏要郑重其事,偏偏要参与到大排场,难免会出现啼笑皆非的场景。一场力不逮心的表演,即将上演。正如刘姥姥再进大观园,参加了史太君筵席,装模作样,引得贾府众人的嬉笑。在大观园里的仪式中,刘姥姥用滑稽、出格的表演,让史太君们短暂地逃离了贾府的现实。
当然,袁佳乔并不是刘姥姥式的人物,她本身是家族里的一员。冷眼旁观,更觉察出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不堪与脆弱。宴会实际上成为一种低效的沟通,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在《细民盛宴》中,张怡微借袁佳乔之口,说出对宴会的不信任:“十七岁那年以后,除了婚丧嫁娶,我还分别随两方‘家人’吃了很多饭。或喜或悲。有些看似很有意义,有些仅仅是为了打发粘结。”“看似”、“打发”,已经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态度。宴会并不是日常生活逃离的窗口,而是无聊的组成部分。
宴会里的人情,是值得怀疑的。《细民盛宴》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宴会,熙熙攘攘,看似热闹,终究是无情。袁佳乔与小茂父母见面的宴会,充满了刺痛:“盛宴过半,小茂的父亲问了我家里的情况,语气特别和蔼”,在初次见面的隆重的宴会上,核实私密的家庭收入与健康概况,着实令人难堪。
大宴会不可信,与之相对的,家常饭则充满温情与暖意。“梅娘”(后妈)与“我”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处于紧张对峙之中,“已经差不多快要过完会有危险被可怕继母下手毒害的年纪”。后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向来是狠毒的角色。她是一个家庭的外来者,一个破坏者。在一个男人,一个“父亲”面前,她要跟他的“儿女”竞争,让这个男人属于她,成为实实在在的“丈夫”。
袁佳乔和“梅娘”之间的关系,在隆重的宴会上显得尴尬异常。但在小说结尾,却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梅娘’回家看见我时热烈地招呼了我,暖风扑面……她铺展开来的鱼香肉丝、素三丝、红烧豆腐、千层百叶……”不是宴会里的珍馐,家常菜却充满了温情。两人关系因而升华。
温暖的、令人怀念的人情,出现在非血缘关系里,是张怡微的野心与大胆。袁佳乔在与继父、“梅娘”逐渐升温的关系,让人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柔情。尤其是继父,一个沉默而温柔的上海男人,不似父亲那样口无遮拦,以“吹牛”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继父为袁佳乔的未来规划,担忧“我”的教育问题。
三
《饮食男女》的开头几分钟,我尤其喜欢,常常独自品咂。老朱忙碌着周日家宴,很是自得其乐。杀鸡、片鱼、烤鸭、蒸肉、熬汤……在李安精致的镜头之下,这些充斥着人间烟火的工序,君子所远离的庖厨,竟也美不胜收。
从饮食与宴会切入,以理解中国人家庭与人际的关系。李安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香港武侠电影,常有大侠与敌人,在方寸饭桌之间,你来我往、辗转腾挪,煞是好看;也有《舌尖上的中国》,搜罗各地美味,以食事来言人事,引无数观众津生两颊。至于从文学的角度,对饮食的关注与记录,更是源远流长。宋惠莲的一根柴火烧的猪头肉,马二先生游西湖逛了一路吃了一路。无怪乎,张爱玲在《谈吃》一文中直言:“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
这里的“吃”,准确地说,是饮食或食物。饮食习惯具有强烈地地域性,四川人嗜辣,广东人好鲜,上海人口味偏甜。一方水土一方人情,选择吃什么,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阿城在《思乡与蛋白酶》一文中,写到一个有趣的观点,直把饮食当乡愁:“所谓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这种乡愁的根源,是蛋白酶。这种解释,科学则科学矣,却稍让人觉得过于理性。饮食,便是一座城市、一个群体的蛋白酶,是实体的共同记忆。
所以,想要认识一座城市,应从饮食开始,食物里包含着地方的文化基因。多年之前,颜歌的小说《我们家》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想起,味蕾仿佛被打开,豆瓣酱的味道与人与事与家族与地方融盖一起。这是一本有味道的小说。
应是食物性格之故,相比于《我们家》,《细民盛宴》里的食物却寡淡得多。四喜烤麸、糟黄泥螺、水果色拉、盐焗鸽子蛋、上海熏鱼、盐卤拼盘、濑尿虾……这些上海人日常生活所依赖的饮食,每每出现,总是令人心安。
在《细民盛宴》中,我看到张怡微以文学构建上海细民日常生活图景的野心。所以,除了食物之外,张怡微就像是一名导游,克制地向读者普及着上海相关的知识
古典文学家们对生活充满热情,才会在饮食宴会倾注笔墨。因其世俗,所以迷人;因其平常,所以动人。这种用巨大的热忱与耐心观察日常生活的传统,经过革命与先锋的洗礼,日渐式微。在《细民盛宴》之中,我仿佛看到一股微暗之火,渐渐明亮。
然而,到底有所不一样了。我们所处的时代,食物丰盛程度远超身体所需。面包店、熟食店、零食店……线上线下的食品商铺,应接不暇,应有尽有。天南地北的美食,手机上下一个订单,即可获得。食物不再稀缺,神圣性便日渐稀薄。外卖APP的风行,终于让一日三餐成为流水线中的标准产品。
当饥饿成为遥远的记忆之时,“吃什么”的追问,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在琳琅满目的菜名之中,撷取日常生活中所需。无疑,《细民盛宴》里所提到的食物,便是张怡微所精心撷取。它们是上海人生活的日常,也是精准的上海饮食知识。
那么,唤起读者“看个吃”的欲望,会是张怡微小小的私心吗?想要得出答案,其实并不难。“看个吃”,其实是了解的初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张怡微对这座城市自然怀有特殊的深情。这种深情能称之为“故乡”吗?在我看来,所谓的“故乡”,是遥远的、是一个让人回望的存在。它存在于记忆中,是与现实遥遥相望的不安与惆怅。张怡微在《细民盛宴》里对上海的书写,难说是故乡情,而是更加复杂、更具使命感的深情。
在《细民盛宴》中,我看到张怡微以文学构建上海细民日常生活图景的野心。所以,除了食物之外,张怡微就像是一名导游,克制地向读者普及着上海相关的知识。“梅娘”是什么意思?哦,在上海话里原来是“后妈”之意;“大自鸣钟”、“祁连山路”,原来是上海的马路。这些语言、地理方面的知识,是张怡微眼里的上海世情。后人若是研究上海这座城市,可以精准地感知物和人,可以一窥上海细民们的日常生活。
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游客会喜欢这样的导游吗?尽管张怡微是克制的,但在某个时候,仍让人感到她的无奈与妥协。
四
“所谓物质生活,无非是人和物,物和人。研究物——包括食物、住房、衣服、奢侈品、工具、货币、城乡设施,总之,人使用的一切——并不是衡量人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方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这样定义“物质生活”。在他看来,物质只有为人所用,成为日常生活不可获取的元素,书写的价值才会最大化。他对一日三餐的关注、对生活用度的关注,重构15—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生活图景。
物质又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词汇。我们既然无法脱离它,那就时刻对它保持警惕。我们试图通过否定、冒犯物质,来保持灵魂的高傲、情感的纯洁。我们向往纯粹的、非功利的情感,却又无法摆脱用物质衡量情感价值几何的困境。我们生怕他人物化自己,然而却迫不及待地用经济数据去考量他人的情感。
张怡微的《“有情”与“无情”——与〈细民盛宴〉有关的亮点想法》,是我非常喜欢的文章。她敏锐地察觉到“有情”与“无情”的历史秘密:衡量“情”的轻重、有无,实际上是一个数学问题。“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布”、“丝”想必消除了女人的不安与疑虑,让她对婚后生活有了期待与信心。
数字化的情感,能被人更精准地感知;量化的伦理,能被人更有效地执行。某个时刻,《细民盛宴》里的日常生活,一度让我感到惊惶与恐惧。上海仿佛一个硕大的工厂,每一份人情、伦理都严格按照绩效考核表来执行。在袁佳乔与小茂的短暂、仓促的婚姻里,父亲一执意要“我”相信,没有给嫁妆并不是不爱女儿;袁佳乔与小茂父母初见的宴会上,小茂父母便直接、赤裸地评估“我”、家庭收入到底是否能承受得了双方的爱情。往后数次见面,小茂父亲贪婪无度地为儿子索求爱,“我们同意儿子找你不就是为了替他妈妈照顾他么?你怎能不去呢,我们对你那么宽容,你好意思吗?像你这样的女孩,嫁到我们家,应该感到珍惜”。袁佳乔仿佛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物件,时时刻刻得体现出实用价值。
另一方面,“梅娘”与父亲的感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牢固与熨帖。两人结合在一起,似乎是源于父亲口中大自鸣钟老房拆迁的愿景。大自鸣钟路的旧房子,等了二十多年的拆迁,让袁家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父亲索性将不吉利的房子卖掉,把钱给了我二姑,一来二往,反而倒欠了我二姑十来万钱”。
我们能去指责或批判这种计算吗?似乎也很难,毕竟生活在上海,面对着局促、逼仄的现实,我们只有在精确的数字背后获取一丝岌岌可危的安全感。
五
张怡微曾对“世情小说”,做出独到的阐释:“情的对峙在此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读者能够哀其不幸,又能感其炎凉。格调上显然不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情趣,相反充满了俗世男女日常生活的‘意见’。世情小说要表现的,正是这一类非客观理性的普通信念或流行见解。”
“普通信念”或“流行见解”,应是小老百姓所秉承的生活信念或道德理念。明朝士大夫们斤斤计较于妇女守贞,可在《金瓶梅》、“三言二拍”中,妇女改嫁却是寻常之事。知识分子的“意见”、政府的规训与百姓的生活呈割裂之状态。煌煌史书所忽略的,正是这群“沉默的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明末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继而催生了苏杭等城市,继而形成了市民阶层,继而出现了世情小说,继而“细民”成为书写的对象。“细民”一词,乃是张怡微对世情传统的回响。
然而,此“城市”早非彼“城市”,“细民”们也早就换了模样。通用的名词掩盖了太多的历史“褶皱”。明清时期的城市,按照格非的观点,其实相当于大市场,城市与农村并无明显的分野(《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第一辑)。即使是最繁华的城市,人口规模不过是百万。以今天的城市作为对标,大概相当于县级城市,传统的、乡土的价值观仍强劲地覆盖着日常生活。
张怡微所面对的城市,常住人口就高达两千四百万。两个时期的城市,在人口规模上就显现出质的区别。作为现代超级都市,上海就像是一辆庞大的、飞速运转的机器,每天数十万人上车下车。不同地区的人、不同地方的语言、不同时代的观念,在这机器里激烈地碰撞。也许,有人熟悉每一条马路,熟知街道的历史,洞察到城市过去与未来的秘密,可逼仄、局促的现实,让我们只能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一个基于个人心灵体验的城市,就此应运而生,“城市越是庞大,在我们心灵中呈现的印象却越是支离破碎”。
首次看到“家族实验”这个词汇,我心中是一阵愕然。 “实验”是有实证主义精神的词汇。张怡微仿佛冷酷的机械师,通过拆解家族、重组家庭,发表着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意见。在《细民盛宴》里,她把袁佳乔的人际关系,被她分解成“梅娘”、“继父”、“前夫”等几组,进行人情、道德的重构。袁佳乔与“梅娘”儿子瑄彦的关系,颇具代表性。父亲与“梅娘”结婚之后,一个尴尬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摆在袁佳乔与瑄彦的面前:如何定义两人的关系?兄妹吗,不尽然,两人早就到达可自主选择“人情”的年龄;朋友吗,也说不上,两人的生活、工作并无多大的交集。在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 中,张怡微对这种短暂的、悬挂的、暧昧的“伦理人情”有了更深的挖掘,如《蕉鹿记》、《过房》。
“实验”往往意味着风险,因家庭重组而产生的新的情感、伦理、道德模式,真的具备普遍意义吗?解答这个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式的追问,并非是小说家的工作。小说家的工作是提供一个可能性的窗口,以虚构之笔去叩问现实困境,以个人的思考去冒犯现实的秩序。
首次看到“家族实验”这个词汇,我心中是一阵愕然。 “实验”是有实证主义精神的词汇。张怡微仿佛冷酷的机械师,通过拆解家族、重组家庭,发表着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意见
❶ 细民,按照字面之意,可理解成与大人物相对的小老百姓。可这样的理解,我总怀疑过于简单。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小老百姓所指范畴非常广。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外卖小哥是小老百姓,公司白领是小老百姓;外地人、原住民,各有烦恼,显然是不可一概而论。按照张怡微“家族实验”系列作品所写,“细民”的范畴应是上海原住民与工人阶层。这一点可在《细民盛宴》的后记得到印证。我更喜欢把“细民”看作形容词,而非定义成一个群体。细民,乃是张怡微对生活于上海的老百姓心理、生存、日常生活的精准概括与描述。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却又坚韧地活着,袁佳乔一家不正是这样吗?
❷ 以胡金铨的《龙门客栈》为例,在龙门客栈里,曹少钦的手下皮绍棠、毛宗宪与萧少镃在饭桌前,有过一段暗藏机锋的对话,极其精彩;此后,徐克拍《新龙门客栈》,邱莫言、周淮安与金镶玉在饭桌前,也有一段令人拍案叫绝的打斗。李安在《卧虎藏龙》中也有类似的桥段,俞秀莲因怀疑玉娇龙盗取青冥宝剑,借着拜访名义前去查探。在桌前,她故意打翻水杯,玉娇龙自此露了功夫。饭桌上的打斗戏,是香港电影里的传统桥段。饭桌是日常,打斗是江湖。细细品之,颇有趣味。
❸ “褶皱”一词,似乎也是我从张怡微笔下发现的。在写作本文之前,我开始大量阅读相关的资料。在一篇后记,或一篇访谈之中,我突然读到“褶皱”一词,当时大脑瞬间被击中——与之关联的词,应是“伦理”——感觉实在是美妙。一种复杂的,如虎皮蛋糕一般的意象出现我眼前。
❹ 句子出自于《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一书导言。约翰·伦尼·肖特著,郑娟、梁捷译。我们越来越难以感知城市的整体,那是因为现代城市中,在庞大的建筑群面前,人会遭到严重的原子化危机。个人目光所及,皆是高楼大厦、皆是自身的孤独,故而所映照出来的城市,也就越发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