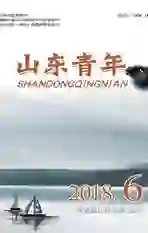“花呗套现案”评析
2018-11-06李昊成
李昊成
摘 要:
当前,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网贷行业,面临着“快”、“偏”、“乱”三大发展特点。花呗套现作为新兴事物,对其行为的定性尚存争议。本文拟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讨论,探索花呗套现类犯罪定性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以期对当下的司法审判困境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花呗;套现;诈骗;盗窃
一、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朱某向朋友李某请求借用支付宝账号以及密码用于购物,李某随即告诉朱某账户内现无余额,朱某告知李某会有朋友将钱打入其账户,朱某随后联系了支付宝上专门做套现的商户,约定其分红利率为3%至4%。朱某虚构了两笔交易,合计价值5000元,因为短信验证码发送至李某手机,故朱某向李某索要了两个手机验证码,付款提交后朱某申请退货退款,扣除手续费后,商家将剩余的4780元钱转至李某账户,到账后朱某又将钱从李某账户转至自己账户用于还贷。
二、 争议焦点
花呗套现和前些年的信用卡套现行为结构具有相似之处,均是通过虚构交易,现金退款的方式来套取资金,差别仅在于花呗套现通过支付宝蚂蚁花呗平台,而信用卡套现是通过实体信用卡。
(一)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陈某、叶某甲诈骗案 案号:(2016)闽0181刑初226号
在该案例中,2015年7月份,被告人陈某、叶某甲经策划,由被告人陈某在网络QQ群上发布套现“蚂蚁花呗”的信息,诱骗网民在网络上虚拟交易以套取现金,骗取网民钱款。具体操作手法为:陈某通过网络的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根据被害人的要求进行套现。而叶某甲负责寻找网络上专门提供套现服务的淘宝商家,并与商家约定了手续费以及相关的利息费用。随后,被告人叶某甲将商家发送的交易链接发送给被告人陈某,被告人陈某转发给被害人。被害人通过蚂蚁花呗购买价值与所期待套现金额相当的商品。在买家付款之后,由商家扣除手续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叶某甲指定的支付宝账户,后被告人分赃。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叶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数额较大,构成诈骗罪。笔者认为,陈某和叶某甲相互串通,告知被害人将为其提供花呗套现服务,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企图通过被告人陈某和叶某甲这个“中介”进行花呗套现,进而通过蚂蚁花呗支付被告人陈某和叶某甲提供的套现商家制作好的商品链接,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故意。
(二)争议焦点之辨析
通过上述案例可知,相似案情法院判决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蚂蚁花呗是否可以被纳入信用卡的范畴、信贷支付平台及机器能否被骗以及支付宝的账号有无实际价值。简言之,如果认为花呗可比照信用卡来处理的话,那么本案可认定为是信用卡诈骗罪。反之,则应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认为机器能够被骗,则冒用他人账户密码进行套现的行为属于诈骗类犯罪所规制的范畴。
三、 法理分析
(一) 花呗不能视为信用卡
信用卡又叫贷记卡,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的方式,是简单的信贷服务。而花呗是互联网金融领域创新的产物。二者都是先消费、后付款的信贷支付工具。
花呗有自己独特的评分系统,一般只要芝麻信用良好,额度都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蚂蚁花呗目前最高授信额度为5万元。相比之下,信用卡却有所不同,一般白金卡授信额度能达到30万左右,钻石卡则过百万,少数人手中持有的黑卡更是没有额度的限制,所以说,在购买大型耐用品时(比如奢侈品、汽车等),信用卡具有蚂蚁花呗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 纯粹的支付宝账号、淘宝账号没有刑法意義上的价值
虽然卡主李某的借用行为不属于处分行为,但由于朱某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实际管理控制经手该账户的地位,其利用便利在完全违反李某意志的情况下侵犯和破坏了李某对于账户内花呗额度的占有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紧接着,被告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商家恶意勾结,在创造虚拟的商品交易订单后,利用支付宝花呗信用付的功能进行付款,这一行为显然属于利用不为人知的方式采取不易被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其他人发现的方法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是为盗窃罪的实行行为。朱某之后联系商家退货退款的行为应视为是盗窃得手后取得财物的手段。
(三) 综合全案分析,朱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
1、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
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诈骗罪是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如果不存在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事实,则不构成诈骗罪。受骗者在处分财产时必须有处分意识,即意识到自己将某种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但不要求对财产的数量、价格等具有完全的认识。本案中,李某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关系将自己余额为零的支付宝账户和淘宝账户借给李某使用,其并没有将自己财产处分给朱某的意思表示。只要被害人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基于该错误认识对财物进行处分,或者虽然使被害人交出了财物但是实质上未处分该物,行为人是趁着被害人不备、秘密窃取财物。
2、 两罪的行为模式不尽相同
盗窃罪和诈骗罪虽然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占有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但所采取的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表现为秘密窃取,犯罪分子采取公私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未发觉的手段、方法,将财物据为己有,如顺手牵羊、深夜撬门扭锁、公共场所扒窃的手段等。而诈骗罪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常见的诈骗方法有编造谎言、假冒身份、伪造文书或者证件、涂改单据等,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后主动处分自己的财产。
3、 本案的最终受害人实际上是李某
刑法的作用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之所以要对违法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主要由于该行为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指向特定的人或社会关系,对相应的人或社会关系造成了损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害人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行为性质的界定以及罪名的确定。
4、即使两罪竞合,也可参照想象竞合处断原则择一重处罚
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本案中朱某的行为既符合盗窃罪的行为构造,又和诈骗罪的行为构造相一致,同一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与想象竞合的形态相类似,笔者认为至少应参照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择一重罪进行定罪处罚。对于诈骗罪和盗窃罪何者更重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既然盗窃罪是夺取型犯罪的兜底性犯罪,就可以认为盗窃罪相对于诈骗罪而言,属于基本类型,在同时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时,如盗卖他人财物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四、 结语
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互联网金融已是大势所趋,网络消费信贷属于新兴事物,我们理应满怀信心,悉心呵护其健康成长。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制度的设计总有疏漏之处。一些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互联网的漏洞,反其道行之。虽然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其不可不加区分地一概介入,对于花呗套现的行为如果已经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理应运用刑法这一工具加以调整与规范。
[参考文献]
[1]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
[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
[3]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版。
[4]张小虎:“拾得信用卡使用行为的犯罪问题”,载《犯罪研究》2008 年第 5 期。
[5]黎宏:“欺骗机器取财行为的定性分析”,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12期。
[6]陈兴良:“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10期。
[7]吴斌:“‘花呗‘白条套现违法吗?”,载《北京日报》2016 年11 月2 日第014版。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