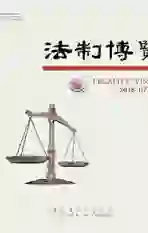夫妻忠诚协议的立法探究
2018-11-05张玮秦
摘 要: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辨析了法律意义上夫妻忠诚协议的概念范围,并对各种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夫妻忠诚协议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有效的问题,最后给出了对我国夫妻忠诚协议立法上的建议。
关键词:夫妻忠诚协议;立法探究;婚姻法
中图分类号:D9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8)20-0064-03
作者简介:张玮秦(1996-),女,汉族,浙江宁波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富足,人们的婚恋观逐渐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从好的一方面来说,离婚自由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离婚不再被视为个人的耻辱;而从不利的角度来说,这种追求浪漫自由的享乐主义风潮助长了婚外情的产生。据了解,目前离婚诉讼中,绝大多数原因就是婚外情,这大大破坏了婚姻的稳定性,增加了现代人对婚姻的不信任感。因此,夫妻忠诚协议应运而生,人们期待通过协议增强彼此对婚姻的信心,并防患于未然,使得自己即使在婚姻破裂后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然而,对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尴尬情况,立法的不明朗让夫妻忠诚协议在学界议论纷纷。
本文拟通过对学界对夫妻忠诚协议目前理论成果的归纳总结,从完善立法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夫妻忠诚协议的概念界定
通常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合法夫妻在结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内,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当一方出现协议规定的不忠诚行为,即将承担一定违约责任的协议。①目前,各种夫妻忠诚协议的版本层出不穷,其主要区别在于所约定的责任后果以及引发责任承担的先决条件不同。
(一)含人身性质违约责任的协议条款应被认定为无效
部分夫妻忠诚协议所约定的责任后果不仅包括了财产性的补偿,也包括了对违约方合法权益的限制乃至侵害即人身性的违约责任,如:对离婚权利的限制、离婚时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剥夺、离婚后对子女监护权和探视权的限制等,主要涉及公民的离婚自主权和抚养权的约定。
笔者认为,含人身性质违约责任的协议条款应被认定为无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侵权责任法》第2条也列举了包含婚姻自主权等人身权利。故公民的离婚自主权受法律保护,个人间协议不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否则认定为无效。而关于子女抚养权的条款,笔者认为抚养权本应由法院在夫妻双方离婚时根据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考虑经济等种种客观情况后进行最合理的划归,而夫妻个人间的约定将损害子女获得被适合一方抚养的权益,当双方约定不应损害他人利益,故该条款也应被视为无效。
含人身性质违约责任的协议条款显然无效不具有讨论的价值,故本文仅就具有财产性违约后果的夫妻忠诚协议条款进行讨论。
(二)财产性质违约责任的协议条款效力存有争议
对于触发财产性违约后果的不忠诚行为类型,学界将其划分为三个类别:离婚赔偿型、外遇赔偿型、空床费赔偿型。②其中,离婚赔偿型系以离婚作为责任承担的先决条件。夫妻双方都应努力维持婚姻稳定,若任意一方提出离婚,则该方需在离婚财产分割时承担一定经济上的利益。而空床费赔偿型、外遇赔偿型,则分别系以夫妻一方夜不归宿、发生婚外性行为作为引发财产性责任承担的事由。
此两种都系以法律未明文禁止的事项为约定内容,以违约方承担财产上的不利益为责任后果,以维护婚姻稳定为目的的协定。这是目前学界的讨论的焦点,其有效性广受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认定有效的法院一般认为协议符合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若认定其无效,理由则多为忠实义务系道德义务,不能以之为对价进行约定。③这正是本文所希望详加讨论,并予以立法规制的对象。
二、夫妻忠实义务的性质
夫妻忠诚协议基于夫妻忠实义务产生,只有先把握忠诚义务的内涵才能進行忠诚协议的性质及有效性的分析。我国《婚姻法》总则第4条指出:“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的义务所在,夫妻间应当互尊、互爱、互敬。”,然而正是这一规定的抽象性引发了在《婚姻法》第4条中夫妻忠实义务究竟是法律强制性义务还是法律倡导性义务的争论。④
笔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属于法律的倡导性义务,夫妻忠诚协议则是该项倡导性原则约定形式的具体化。首先并非所有的道德义务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当某一道德义务被赋予法律权利,以完整的逻辑结构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写入法律,那么该行为即受法律调整。夫妻忠实义务仅在《婚姻法》总则中有所规定,而其具体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却并没有在分则中加以说明,它缺少法律规范应有的逻辑结构。因此它并不是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强制性义务而是原则性、倡导性的法律义务。
三、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及有效性论定
学界主流有三种意见,一种将夫妻忠诚协议界定为“身份关系的协议”,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一种将其界定为财产性合同,主张其效力应依据《合同法》合同成立要件加以判定;另一种将其界定为民事法律行为,认为其效力应根据《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加以判定。具体分析如下:
主张“无效说”的学者意见认为,判定“身份关系的协议”的关键是订立主体的特殊性,订立主体一般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人或者意欲产生特定身份的人。⑤而夫妻忠诚协议的订立主体是夫妻双方,故应属于《合同法》的第2条第2款所规定的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应当由《合同法》调整。同时,婚姻属于非市场领域,而《合同法》调整的却是市场领域中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的理念和调整手段有很大不同。有学者认为,夫妻相互忠诚本身便应该是一项倡导性、原则性的道德义务,将这种协议市场化将导致整个家庭婚姻观念的异化。“这种协议具有非道德性,不仅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异化,也会形成对人身自由的约束,最终使婚姻自由名存实亡”,因此以《合同法》来调整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仅无效,而且会带来道德上的混乱。而法律领域对道德领域越俎代庖,公民自由权就产生被侵害的危险。而针对纠纷处理而言,只要不属于《合同法》调整范围,夫妻就无法根据协议主张权利。⑥
主张“财产性合同说”的学者意见认为,虽然《合同法》的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但夫妻忠诚协议并非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是对夫妻共同财产附条件的约定。身份关系的协议具有使得身份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律后果。而夫妻忠诚的协议却并没有涉及身份关系的变化,凡是有关人身性质违约责任的条款都系因违反法律强制规定而无效,故夫妻忠诚协议其本质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自由处分,仍应受《合同法》调整。⑦当夫妻忠诚协议的缔约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系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要求时,应被认定为是一份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⑧
而主张民事法律行为的意见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仍涉及身份关系,不应由《合同法》调整。⑨在《婚姻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在特殊法无法解决问题时,应适用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而根据《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夫妻忠诚协议中,夫妻双方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若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同时未违反公序良俗,那么其效力便应予以承认。
参考上述学界意见,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应被认定为财产性合同,其有效与否应依据《合同法》判定,这既符合学理上的逻辑,也顺应了实践的需求。具体分析如下:
(一)夫妻忠诚协议应受《合同法》规范
首先,将夫妻忠诚协议认定为有效乃是大势所趋。随着人们对婚姻不信任感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希望对婚内不道德的行为有所规制。在道德义务法律强制性规定不便介入的情况下,给予夫妻双方自由约定的权利,以财产性惩罚予以约束是最好选择。而现实中,夫妻忠诚协议在提升婚姻稳固程度、增加对失败婚姻中受害方的保护方面显现出独到的价值,在民间的广泛应用也从反映出它对人们这种需求的满足。若法律法规一味予以否认或无视,不仅将不利于发挥忠诚协议的良性价值,而且也是对社会正当需求的漠视。
其次,将夫妻忠诚协议认定为财产性合同并无法律障碍。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的本质仍是财产性约定。夫妻忠诚协议并不调整身份关系,它区别于结婚协议、离婚协议、收养协议、监护协议、遗赠扶养协议等涉及身份关系变动的协议,调整的仍然是财产关系,是在合法的夫妻关系背景下,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附条件的约定。因此仍应受《合同法》调整。
同时,夫妻忠诚协议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约定。对于“无效说”所质疑的侵害当事人自由权,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婚姻法将忠实义务确定为倡导性、原则性义务,意味着婚姻法承认夫妻双方将因婚姻的缔结而承担一定的忠贞义务,放弃一定的性自由。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互守忠贞义务是符合现代主流婚姻观念的。其次,夫妻忠诚协议并没有禁止当事人和他人恋爱、发生性行为。夫妻忠诚协议的规制对象是夫妻,若当事人觉得和现任感情确已破裂,那离婚便可,即可不受协议规制。
夫妻忠诚协议是将法律中未明确规定的道德义务以约定的形式具体化。这种转化在现实中已有先例,如小孩落水,父母向围观群众允诺救人者酬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而这种义务也可以通过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同样受法律保护。
最后,笔者认为将夫妻忠诚协议认定为有效并由《合同法》调整并不会异化人们的婚姻观念甚至带来道德难题。有效的夫妻忠诚协议应该是夫妻在平等自愿协商下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夫妻双方在婚姻期间履行对对方的忠实义务,维持婚姻的和谐,并给予无过错方受到伤害时的经济补偿。学者所担心的无非是金钱补偿会异化夫妻间的关系,使得夫妻间的情感扶持关系异化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从而败坏社会风气。但笔者认为,夫妻关系本身便已经属于公民自治的私权范围,法律所保证的是人们的婚姻自主,而并不是也并不能保证男女双方一定是因为情感原因而缔结、维系婚姻,法律无法阻碍夫妻关系的变质。相反,若因为害怕法律背负异化夫妻关系的骂名而不对夫妻忠诚协议加以规制,则将会放任乱象的发展,使得无过错方长久地处于缺乏保障的困境中。
因此,笔者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应在《合同法》现有的框架下增加具体内容予以规制。
四、夫妻忠诚协议立法的建议
结合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关立法。
(一)确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有效性
基于目前各地法院对于夫妻忠诚协议案件“同案不同判”的乱况,笔者认为,首先应以立法的形式确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有效性。夫妻忠诚协议作为夫妻双方平等自愿下订立的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附条件的处分约定,理应受到《合同法》保护。明确其有效性将有利于终结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情况,正视社会中对于借夫妻忠诚协议维稳婚姻的需求,促进婚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规范夫妻忠诚协议条款的内容
夫妻忠诚协议作为民事合同,订立双方对合同内容的设置应该享有很大限度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了不同夫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忠诚义务的理解,更有利于将法律倡导的道德义务具体化,便于双方执行。
但是法律应该明确的是,夫妻忠诚协议的条款包含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更不得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诸如,违约方禁止提出离婚诉讼,违约方将在众人面前跪下认错等。
(三)规范夫妻忠诚条款订立的程序
笔者认为,书面合同形式必不可少,甚至可参照遗嘱订立程序规范夫妻忠诚条款订立流程。很多夫妻在情浓时口头许下相互永不变心,一旦出轨就如何如何的约定,而当事人许下承诺时却并无愿受合同约束的意愿,一旦发生纠纷也难以证明合同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夫妻忠诚条款应以书面为宜,并可引入公证程序,增强协议的证明度。
(四)和离婚损害赔偿的同时适用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况,包括(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其中前两种情况明显违背了夫妻间的忠诚义务,和夫妻忠诚协议中的條款可能发生竞合的情况。此时,若允许守约方既依据法定又依据约定请求赔偿,违背了一事不二罚的规则,对违约方无疑也并不公平,因而应根据“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优先适用夫妻忠诚协议。至于其他两种情况,并不属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范畴,两者并行不悖,则可同时适用。
[ 注 释 ]
①陈其强.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J].商,2016(35):241.
②阳永恒.论夫妻忠诚协议[D].湖南大学,2009.
③王超.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D].南京大学,2016.
④王舒楠.夫妻忠诚协议效力问题的法律分析[D].贵州民族大学,2017.
⑤孙良国,赵梓晴.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09):270-273.
⑥同上.
⑦李晟.论夫妻忠诚协议[D].湘潭大学,2013.
⑧王文玉.论夫妻忠诚协议[D].北京化工大学,2011.
⑨王君.夫妻忠诚协议之有效性分析[J].法商论坛,2011(01).